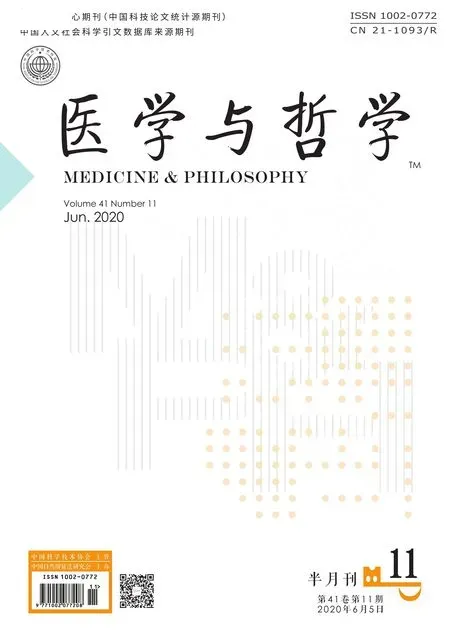西方經典瘟疫小說中的疾病隱喻與倫理抉擇——以《瘟疫年紀事》《鼠疫》《失明癥漫記》為解讀對象
安瑋娜
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認為,瘟疫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1]237。作為地球原住民的細菌或病毒,與人類社會發展相伴相生,它們引發大規模傳染,在制造混亂、留下創痛的同時,重塑著人類的生活方式、上層建筑與歷史命運。
瘟疫文學是疫病與人類文明相互作用的成果之一,清楚地再現了人類對瘟疫的恐慌、想象和理解,本文試從文學倫理學批評視角切入,通過《瘟疫年紀事》《鼠疫》《失明癥漫記》三部西方近現代經典瘟疫作品中的瘟疫敘事分析,探討有益于當代疫病倫理體系建構的啟示。
1 瘟疫的倫理歸因與隱喻構建
文學自產生之初就具備教誨功能、倫理性質,文學倫理學批評就是“從倫理的視角解釋文學中描寫的不同生活現象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并對其作出價值判斷”[2]。誠然,文學在描寫瘟疫時,首先呈現了各類病原在刺穿人類軀體時釀制的痛苦,筆觸所及包括鼠疫、霍亂、天花、麻風、流感、瘧疾、血吸蟲甚至艾滋病等種種烈性傳染病,也許這些描寫為生物學致病原理分析提供了某些細節依據,但文學作品所要關注的重點卻在于人類注入疫病的多種文化內涵。面對瘟疫的強致死性,恐慌的人們多用倫理歸因的方式探尋惡疾源頭,使得“瘟疫一詞,長期以來一直被隱喻地加以使用,用來指最嚴重的群體災難、邪惡和禍害”[3]139,瘟疫敘事中體現了人與社會和他人之間的倫理關系與道德秩序。
1.1 懲戒與報應
在人類早期社會,面對不可阻遏的瘟疫,先民往往依托想象把握未知,因此在古老的文學作品中,瘟疫首先被理解為神靈對個人罪責或集體過失的懲戒,如古希臘戲劇《俄狄浦斯王》中使整個忒拜城蒙受瘟疫、喪失繁衍能力的原因是俄狄浦斯王犯下了殺父娶母的罪行,而《伊利亞特》中使希臘聯軍遭受瘟疫籠罩的原因則是主帥阿伽門農搶走了祭司女兒而觸怒天神。在希伯來文明和基督教時代,瘟疫與贖罪形成了更緊密的聯系,《舊約》中摩西受耶和華指引帶領希伯來人離開埃及去往迦南地,因為他們不信神,在曠野上流浪了38年,憤怒的天神屢降瘟疫以懲戒不忠與叛離,人們在瘟疫中自省贖罪才能繼續前行,《新約》中也有耶穌引導民眾通過贖罪遠離災疫的故事。這些想象體現了先民對自然力量的恐懼,也推動了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盛行。
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創作的《瘟疫年紀事》以自然主義筆法再現了1665年倫敦瘟疫的全貌。整部作品通過生活在倫敦城的一個鞍具商H.F.之口進行講述,在他看來這場瘟疫就是上帝對倫敦施加的判罰,旨在引導倫敦民眾對自己的惡行進行懺悔,增強其對上帝的虔敬之心。H.F.代表了倫敦民眾的普遍觀點“上帝發怒的時辰,種種可怕的審判正在逼近”[4]65,而且在此之前上帝已經給了警告,連續幾個月天空中昏暗、渾濁、行進緩慢的彗星就預示了這場判罰的嚴重性。H.F.將上帝的旨意視為天意,服從上帝的引導留在了倫敦城,目睹瘟疫發生的全過程并最終保全了性命,整部作品就像一個虔誠的教徒在上帝指引下走出苦難,獲得肉體與靈魂升華的自傳。法國存在主義大師阿爾貝·加繆《鼠疫》展現了鼠疫肆虐下奧蘭小城的生活圖景,當人們突然面對鼠疫封城的消息時,恐慌混亂,帕納盧神甫在教堂布道,將矛頭直指人性之惡,告訴眾人鼠疫只是緣于天意的災難,這場災難具有懲罰性,懲罰大家平時所犯的罪過,幫助大家變惡為善“穿過死亡、焦慮、呼喊的通道……引向固有的寧靜和生命的本原”[5]73。前來參加布道的人把教堂圍得水泄不通,不少人從中獲取精神慰藉。將瘟疫視為懲戒與報應,都具有污名化的特征,其實除了艾滋病、梅毒等與性傳播有關的疾病可能與患病個人道德修養有關外,絕大多數瘟疫屬于病菌傳染以調節平衡的自然現象,污名化歸因往往會使感染者背上沉重的道德包袱。
1.2 絕望與疏離
瘟疫籠罩下的民眾往往處在無法把握生存環境和自身命運的絕望狀態中,社會恐慌不斷加劇,瘟疫不再僅僅指向疾病本身,也關涉社會心理與人際關系。丹麥宗教哲學心理學家基爾克郭爾在《恐懼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中指出“人是一種靈魂和肉體的結合,如果兩項沒有統一在一個第三項之中,那么,一種綜合就是無法想象的。這個第三項就是精神”[6],也就是說人的兩極如果不能和諧統一在崇高的精神之中,人就會處于分裂狀態,產生恐懼、絕望、疏離等心理癥狀。瘟疫暴發后,人們處于“無辜的恐懼”之中, 當恐懼不斷加深,人無法依靠自身去治愈,就會產生“絕望”,當絕望驅趕了希望,一些人認為瘟疫不僅致壞人于死地,也把同樣的懲罰施予好人,這就使得他們顛覆了曾有信仰,背棄了道義,在“社會求償”心理驅使下違逆上帝,嚴重的還會導致反社會行為的出現,恐懼和絕望成為“罪”產生的原動力。經典文學作品中展示了瘟疫肆虐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加繆《鼠疫》面對災難,有人及時行樂,揮霍無度;有人想方設法逃出奧蘭小城;也有人處心積慮發瘟疫財,販賣偽劣藥品從中牟利;而更多的人是聽天由命,在恐懼與憂慮中等待不可知的未來,世界變成了一派荒誕。葡萄牙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若澤·薩拉馬戈《失明癥漫記》以寓言的形式描繪了失明癥傳染蔓延導致的人性崩塌,被隔離在瘋人院的感染者們,由于處在無法復明的絕望之中,又缺乏他人眼睛的監督和評判,逐漸喪失了自我省察與約束能力,冷漠、卑鄙、邪惡隨之顯露,他們隨地大小便、互相為爭奪食物和情欲享樂自相殘殺,人類仿佛又回到了原始部落的時代。
當人背棄了上帝,社會信仰崩塌、倫常傾覆之際,個體人的精神覺醒,又無法依靠自身治愈絕望,從而產生懷疑一切的心理,社會成員之間形成不信任、疏離的關系。笛福《瘟疫年紀事》展現了瘟疫對政府權威和社會規則的顛覆,作品中出現了兩類話語,一類是倫敦政府正式發布的死亡統計表及防控法規措施,另一類是民間流傳的各種謠言,絕望中的民眾用想象和虛構填補闡釋官方數據,在社會普遍恐懼和信息真實度無從考證的可怕壓力下,虛構取代了真實,謠言具備了合理性,造成了更嚴重的恐懼與傷亡,一位可憐的良家婦女被路遇的醉漢碰觸,在聽說醉漢感染了瘟疫后,就因驚恐去世。加繆《鼠疫》展現了瘟疫對醫患關系的改變,作品中的里厄醫生原本深受市民愛戴,但因鼠疫與患者發生了沖突,里厄醫生每次出現在鼠疫患者面前都得帶上幾名士兵,用槍托敲門,在患者家屬極不情愿的情況下破門而入,很多家屬不相信醫生的治療,害怕被帶走的患者以后再難看見,于是甘冒被感染的風險也不愿跟親人隔離,對醫生出現了強烈的心理排斥和抗拒行為。當面對疾病的不可把握性,有限的人無能為力,深處絕望之中,為“罪”提供了內驅力,容易出現醫患之間“關懷-感恩”的關系斷裂,滋生恩將仇報的行為,瘟疫隱喻了絕望的社會心理和疏離的人際關系。
1.3 軍事戰爭或政治變革
身體有疾和社會、國家失序相似,因此文學作品常通過身體感染瘟疫來隱喻軍事戰爭或社會政治問題,瘟疫“成為對付國內外反對派、對手、異己分子或敵對力量的最順手的修辭學工具”。首先,隨著醫學診療技術和流行病學的發展,人們發現通商、傳教、戰爭等途徑使瘟疫跨國傳播,于是瘟疫成為潑向其他民族或國家身上的“臟水”,就如同蘇珊·桑塔格所講到的“梅毒,對英國人來說,是‘法國花柳病’,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對佛羅倫薩人來說,是‘支那病’”[3]142,瘟疫被賦予異邦邪惡的隱喻。笛福《瘟疫年紀事》中當倫敦城的最西頭出現了瘟疫,鄰里的言談透露出大家對瘟疫起源的猜測,有人認為來源于意大利,有人認為是土耳其艦隊帶著它侵入歐洲,還有認為來自于坎地亞腐爛的尸體,總之邪惡的瘟疫最終通過傳染駐足倫敦,并在這里猖獗肆虐,瘟疫是“他者”的入侵。隨著以西方為中心的沙文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更多的歐洲人認為“貧窮落后的亞洲、穆斯林地區、非洲是瘟疫滋生之處,是污染源”[7],這種瘟疫想象透露著文化優越論,具有典型的西方至上思想傾向。
人類面對瘟疫往往會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法保護自己,使防控瘟疫成為侵犯人權或損害他國自主權等政治迫害的幫兇。20世紀下半葉,隨著生物科學的飛速發展,細菌戰、生化武器的出現,使得病毒傳染走向政治暴力,人類的理性光芒在政治瘟疫中風雨飄搖。文學作品展現了瘟疫所帶來的政治暴力,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經典作品《霍亂時期的愛情》,將費爾明娜與兩個男人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情放置在19世紀歐洲霍亂肆虐的背景下,文章中瘟疫的隱喻意義是復雜的,既象征阿里薩對費爾明娜烈性、深刻的愛如霍亂一般摧毀理智,更時不時地暗示一些政客以霍亂為名發動戰爭、入侵他國,瘟疫與政治迫害密切關聯起來。加繆的《鼠疫》在解讀過程中,很多人更愿意從加繆寫作的真實背景深入剖析,當時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在法國南部的加繆無法與親人通信,從而陷入孤獨和對法西斯的憎恨中,于是,鼠疫重重包圍下的奧蘭小城,普遍被認為就是法西斯專治統治下的法國,里厄一行人與疾病的不懈斗爭,就是被囚禁的法國人與法西斯專政的持續反抗。
由此可見,文學作品記錄了人們對公共衛生事件的認識水平和審美想象。細菌與病毒釀制的瘟疫,本是生態環境自我平衡、不斷進化的自然規律,在人類社會中卻常被賦予特殊意義,作為神靈的責罰、社會心理與人際關系的絕望斷裂、軍事政治的迫害等狀態的表征,使瘟疫不僅限于疾病本身,而是上升為一種文化現象,與人類文明嬗變、政治法制形式、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連,具有極強隱喻色彩。
2 瘟疫敘事中的倫理選擇
人類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多,除了要賦予瘟疫等自然災害以意義,還要對其中的事物價值做出判斷和選擇。按照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理解,由于理性的成熟,人能在獸性因子和人性因子交織中做出合理的倫理選擇,人才真正脫離了低等生物界,成為倫理的存在[8]。伊甸園中,亞當和夏娃起初像野獸一樣生活,而當他們偷吃了智慧樹上的禁果,有了善惡之分,知道赤身裸體的羞恥,完成了倫理選擇,才從生物意義上的人變成了真正的人。瘟疫文學作品倫理表述的核心內容就是展現人類在重大災難面前理性意志與自由意志的沖突與選擇。
2.1 利他與利己
是維護他人和社群利益優先,還是謀取自己最大最終利益優先,一直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爭執不休的問題,形成了“社會整體論”與“社會原子論”兩大對立的價值系統,社群主義者認為個人利益的實現仰賴于社會整體正義的實現,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個人權利至高無上且優于公共利益[9]。在瘟疫事件所造成的突發性公共危機中,利他與利己之間的沖突愈發復雜,尤其是從事臨床、公共衛生、護理及相關科研的醫務工作者,他們始終面對著個人憂懼與承擔醫療救助社會責任之間的抉擇,瘟疫文學通過敘事探討了醫務群體應有的價值歸依。加繆《鼠疫》塑造了一個完美的醫生形象——里厄。平日里他總是不辭辛苦地跑遍城市的各個地方,一絲不茍地診治患者,無論有錢人還是窮人皆一視同仁;鼠疫降臨奧蘭初期,他無懼壓力,第一個向市政府抗議,要求重視老鼠大量死亡的現實,并采取積極行動抵抗瘟疫暴發;在瘟疫大肆橫行的時候,他堅決隔離鼠疫患者,號召人們不作無用的懺悔,而是用實際行動在病魔中突圍;他組建起志愿者衛生防疫組織,每日工作16個小時以上,努力研制抵抗疾病的血清,認真救護所有患者。他就像希臘神話中不斷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面對政府不支持、民眾不理解、惡疾不斷發展的重重阻力,始終勇敢堅持,與疾病進行殊死搏斗。作品還充分呈現了里厄利他行為帶來的號召性、調整性作用,一個名叫朗貝爾的記者,從外地來奧蘭小城做調研,不巧遇到鼠疫封城,起初千方百計采取卑劣手段企圖逃離奧蘭,最終卻因里厄等人不顧個人安危、全力救治患者的行為改變了初衷,留下來參與到共同抗擊鼠疫的隊伍中。作者充分肯定了朗貝爾在英雄與懦夫之間所做的自我選擇,也突顯了里厄先人后己、無私奉獻的利他主義在災難面前所起到的彌合作用,他凝聚起反抗命運的洪流。在這里,利他與利己的矛盾得到了和諧統一,治病救人是醫生職業的信條,濟世助人是里厄同行者的人道追求。面對烈性傳染病,他們堅定地與疾病斗爭,為公眾提供照護,體現了崇高使命和人道主義光輝,也完成了自身人格的升華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于他于己大有增益,證明了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個人幸福應服從社會責任的倫理原則。
當然,純粹不考慮個人的利他主義也是不現實的,在參與治療過程中,醫務人員的情緒面向是一個需要研究的焦點。面對生存條件惡劣、患者處境悲慘,而醫藥資源又十分短缺的狀況,醫療照護本身除強調醫道責任和弘揚利他精神外,如果沒有政策保障、物資補給、防疫戰線的形成,醫生群體孤掌難鳴,深陷情緒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必須仰仗政府的通盤協調和支援。
2.2 管制與自由
福柯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生命政治”的概念,聚焦政治治理與生命權利的關系,尤其是瘟疫暴發后國家權力積極干預個體的規訓方案,包括劃分人群、分配物資、進行組織監控、形成權力網絡等。瘟疫文學敘事也以此為重要主題,探討特殊時期國家公共管理措施的優劣。笛福《瘟疫年紀事》是18世紀瘟疫敘事的典范之作,再現了1665年倫敦當局在鼠疫侵襲時的政治干預與管理手段。通過每周公布《死亡統計表》,當局詳細統計各區因感染疫情而死亡的人數,以此動態掌握疫情發展變化形式。另外,當局出臺相應法規對人們的衣食住行進行嚴格管理,規定感染者的任何衣物用品都不可流通使用,任何變質、腐爛的食物都不得出售,禁止公共集會大吃大喝,限制密切接觸者的行動,規定垃圾清理與尸體掩埋的時間方式,禁止城里飼養貓狗豬等有可能攜帶病菌的動物等等。敘事人H.F.在作品中感嘆,即便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面包和煤炭這些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沒有太大變化,眾多死尸都被及時處理,不讓街道混亂。在這場災難性事件中,倫敦當局制定的公共管理策略重新塑造了社會生活方式,改變了危機狀態下的生存境況,并有效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但是H.F.對其中一項管制法規十分不滿,那就是當局實施的“封閉房屋政策”。倫敦行政長官下令將發現鼠疫感染者的家庭整個封閉,在屋門畫上紅十字,并指派專人日夜看守、警察嚴密監視。H.F.認為“因為有了被封閉起來的那些房屋,城里這個地方才恰恰有了這么多監獄”[4]102,這種把健康人和不健康人關在一起封閉房屋的舉措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很多被封閉起來的人沒有死于瘟疫,卻在孤獨凄慘中過世。而且封閉使屋里的人陷入絕境,不惜鋌而走險,欺騙、買通或殺死看守人,不顧一切從屋子里逃出去,后果更為嚴重。笛福借H.F.之口對瘟疫面前“管制”還是“自由”進行了充分探討,他認為從個別被封閉家庭中獲得公共利益是可恥的。這一觀點與笛福清教徒的信仰不無關系,歷史上的清教徒幾乎沒有政治權利,缺少服務公眾的機會和意識,多從個人角度看待問題。比如作品中H.F.曾被任命為教區檢查員,他竭力抗拒去檢查那些封閉的房屋,他更關心疫情下自己的個人健康和福祉,這些細節體現了作者身上存在的個體主義思想。其實,瘟疫暴發時,健康已不再是個體化事件,需要國家權力機構實施合理化干預手段,制定政策監控人口安全,才能帶領民眾走出瘟疫苦海。最終H.F.也承認將房屋封閉起來確實起到了一定效果,否則那些走上街頭的感染者會非常麻煩和危險。
當然,瘟疫面前利益的天平雖傾向于社會整體,但還應盡量防止群體性的過度防疫導致一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價值凌駕于他人之上,以保障社群公眾利益的名義,行極權暴力之實,從而造成規模性的歧視、排斥和侵害。文學作品中的具有爭議性的情節也啟示人們在保護集體利益的同時,還應盡力維護個人權利,避免集體濫用權力。
2.3 等級與平等
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等級制度逐漸形成,按某一標準將人群分為高下級別,享有不同的權利與資源,造成了劇烈的階級沖突。近代以來,平等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尤其是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通過,標志著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得到法律認可,已成為新的價值秩序和制度要求。在重大傳染病的應對中,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權及其他與之相關的經濟、社會、文化諸多權利,經典瘟疫文學也以此為話題探討了疾病面前等級與平等的問題。笛福《瘟疫年紀事》展現了瘟疫暴發后窮富不同等級的境遇,英國宮廷與權臣第一時間逃往外地,有錢人也紛紛出逃到鄉下避難,城里留下的家庭紛紛閉門鎖戶來抵抗瘟疫傳染,有的家庭直接將寄居在家內的窮苦工人驅逐出去,有的則在仆人穿街走巷買來生活必需品卻同時感染瘟疫后,將其拋棄,窮苦人不僅無法享有有限的醫療社會資源,且人格尊嚴受到極大的侵害。作品中一個重點情節講述了三位窮人因無處可居四處躲避瘟疫的故事,他們與路遇的其他窮人結成團體共同逃亡,不管來到哪個城市或村落,都受到攻擊與蔑視,只能在森林搭建暫時居住的茅屋,靠智慧與勇氣與臨近居民談判周旋,憑勤勞與品行最終被接納,從而保全了自己。但還有更多的窮人或走投無路、搶掠作惡,或四處逃竄、病死道旁,造成了更大規模的混亂與疫情的傳播。這些情節的對比不僅彰顯了仁愛、誠實等高尚品德在任何時候都不應缺席,同時也聚焦健康權平等問題,在瘟疫暴發的特殊情境中,不應僅依靠人性的同情與憐憫去救助貧病,而應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對感染者、攜帶者或疑似者給予及時救治,反對歧視與排斥,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保證和諧安寧。
薩拉馬戈《失明癥漫記》展示了另一個維度的等級與平等問題。作品中被隔離在瘋人院的失明感染者們處境艱難,人性之惡完全暴露,一個持槍的盲人組建團體強行霸占所有食物,并逼迫各宿舍輪流送女人來為他們服淫役,女性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肉體,一名失眠的女盲人在遭受凌辱后癱倒在地死去,“兩腿間血跡斑斑,肚子上青一塊紫一塊,可憐的乳房露在外面,一個肩膀上還有被瘋狂咬出的牙印”[10]。男性雖然感染瘟疫,但仍可以通過槍來擁有特權、通過強奸來展示他們的能力,對同樣處在可怕情境中的女性實施凌辱,這是女性弱勢地位的隱喻。等級與平等不僅存在于窮人與富人、特權階層與貧民階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也同時存在于兩性問題的討論之中。瘟疫本身可能會給女性帶來更多的傷害,在《瘟疫年紀事》中,笛福就以寫實的筆法寫到:“目前整個這場災難中,最可悲可嘆的一種情況,便是婦女生孩子,當她們到了自己那個可憐不幸的時刻,陣痛突如其來,這個時候她們什么幫助都得不到……數量極其非同尋常和難以置信的婦女陷于水深火熱之中。”[4]190-191文學作品中的情節展示了對災難面前弱勢群體的關注,如何更好地支持幫助弱勢群體,讓每個公民平等享有保持其生理機能和精神狀態健康的權利,應是所有國家和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2.4 全能救助與全民救助
按照公共衛生理論,瘟疫的預防和控制、公共健康的實現是一種群體性行為,不僅需要政府當局的全能調控干預,還需要依靠整個社會的力量進行全民救助。政府的缺位、社會過度市場化和趨利導向,都將極大地妨礙疫情防控工作。如前分析,瘟疫暴發、社會混亂,在個體弱小無奈、群體散落無力時大家會將生的希望寄托于全能救助的出現,或者是向無所不能的上帝祈禱,請求寬赦;或者是依靠政府機構制定合理的防控制度和高效公正的倫理守則來保障人類的完整、完善。薩拉馬戈《失明癥漫記》卻展示了重大災難面前全能救助的失靈,瘟疫暴發,教堂出現了奇怪的景象,所有的神像都用白布蒙上了雙眼,看不到人間苦楚;政府當局雖采取了將失明者及密切接觸者強制收容的措施,但對如何救治和管理患者根本不管不顧,使瘋人院成為人間地獄,最后整個城市全部受到瘟疫感染。在國家浩劫面前,“人類苦心營構起來的機制、形態、組織結構充其量只是一種把戲和玩耍之作”[11],作品展示了全能救助在一些問題上可能會出現的無力與無能,具有卓越的社會和現實批判性。
失明癥的暴發和蔓延警示人類,面對自身存在的“腫瘤”,需要大家通力合作,竭力尋找療救的藥方,在直面死亡的時候,也是全民進行道德選擇和理性重建的過程,作品中醫生的妻子和同一寢室的朋友們就經歷了自我靈魂的改造和救贖。醫生的妻子是理性和智慧的化身,為陪伴照顧丈夫假裝失明進入瘋人院,成為唯一可以看見的人,在洞察了種種人性缺陷和社會不公后,她引領和扶持著災難中的盲人艱難前行,保持著作為人應有的尊嚴,防止大家墮入獸類。醫生則是責任和理智的代表,自己感染失明后第一時間上報當局控制疫情發展,在瘋人院里時刻維護大家利益,妻子恐懼時及時給予安慰和支持,他雖深陷困境,但仍用良知和責任實施對自我和他人的救助。戴眼罩的老人是一個生活閱歷豐富的睿智者,他困居瘋人院,卻依靠收音機與外界相通,獲得精神指引去思考、去感知,在醫生妻子殺死持槍的盲人歹徒并遭到威脅后,他阻止了其他盲人要供出醫生妻子的自私想法,反復強調必須守護最后一點當之有愧的尊嚴,為自己作為人的權利而斗爭不止。戴墨鏡的姑娘是自我救贖的代表,盡管以前她是一個妓女,但在瘋人院中她努力保持自我尊嚴不受侵犯,全力照顧另一個與她毫無關系的斜眼男孩,無條件地支持和跟隨醫生的妻子,時刻想念自己的父母親人,災難使她身上的真摯情義灼灼閃光。作者薩拉馬戈用寓言的方式揭示出人類在面對災難時,仍要保有尊嚴與理智,不能僅依靠公權力,而要學會在自救過程中實現個人主體性價值,并與他者建立互助關系,共同維護社會秩序和共識,全民參與救助才讓人類保有恢復的希望與可能。
3 結語
“技術和知識,盡管深刻改變了人類的大部分疫病經歷,但就本質上看,仍然沒有也從來不會把人類從它自始至終所處的生態龕中解脫出來”[1]236。那些先于初民就已存在的瘟疫,將始終與人類同在。面對瘟疫隨時可能有的反撲,從文學功用性角度分析,瘟疫敘事至少可以有兩方面啟示:一方面,展示了歷史上瘟疫暴發時的社會生活狀況,揭示了人類面對瘟疫時的精神生活影像和倫理觀念,為人類反思疫情暴發和社會失序原因,建設更為合理的機制體制,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和精神交流提供了研讀范本;另一方面,呈現了瘟疫的復雜性、多樣性以及相應的文化意義,加深對歷史和自然的理解,警示人類從更為廣闊的層面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基礎上加以防控。
加繆《鼠疫》結尾部分,里厄在人們歡慶勝利時仍清醒地認識到:“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亡也不會消失……也許會有那么一天,為了給人類帶來災難并教訓人們,鼠疫會再次喚醒老鼠,并讓它們死于一座幸福的城市。”[5]233人與瘟疫的故事將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