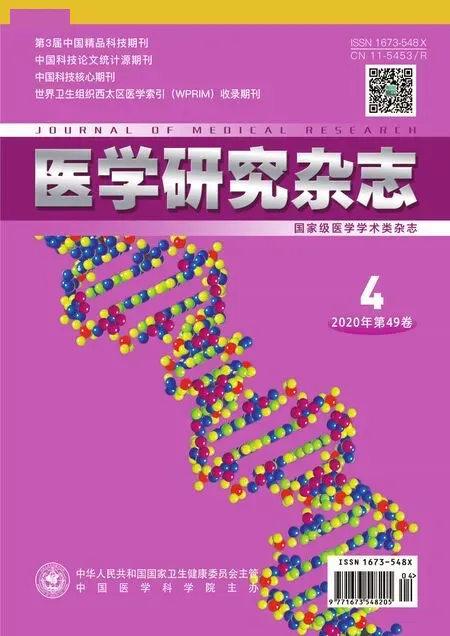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1在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及臨床應用
楊 依 趙 麗
神經退行性疾病是由神經元和(或)髓鞘的喪失所致,病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最終出現功能性障礙。常見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有:阿爾茲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等。目前這些疾病的發病機制尚不清楚,主要有興奮毒性學說、細胞凋亡學說、氧化應激學說等,這些學說均與泛素-蛋白酶體系統(ubiquitin proteasome system,UPS)密切相關。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1(ubiquitin carboxy-terminal hydrolase L1,UCH-L1)作為UPS中的重要組成蛋白,在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一、UCH-L1與UPS
UPS是真核細胞內蛋白降解的重要途徑,泛素(Ub)是UPS核心,是由76個氨基酸組成的高度保守的小分子蛋白。UPS有兩類重要的酶:泛素化酶和去泛素化酶(deubiquitinating enzymes,DUB),UCH是去泛素化酶中的一個重要家族。UCH有3種異構體:UCH-L1、UCH-L2、UCH-L3。UCH-L1主要分布在大腦神經元中,可以達到腦內總蛋白量的2%。用組織原位雜交的方法發現其多分布在黑質致密部,或者存在于周圍神經系統如三叉神經節等處。此外,UCH-L1也存在于卵母細胞及精母細胞。
UCH-L1主要有3種功能:①水解多聚泛素鏈,使泛素單體可以重復使用;②以二聚體形式作為一種不依賴ATP的泛素連接酶催化k-63形式泛素鏈的形成,從而競爭性抑制k-48形式泛素鏈與異常蛋白的結合,使異常蛋白不能被蛋白酶體識別、降解;③穩定泛素分子單體,并可以通過調節泛素單體水平起到對UPS的調控。
二、UCH-L1與阿爾茲海默病
阿爾茲海默病(AD)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變性病,為老年期癡呆最常見的一種類型,表現為進行性認知功能障礙和行為損害。臨床及組織病理學研究表明,AD主要有兩個病理特征:因病理性β淀粉樣蛋白(amyloid β,Aβ)沉積而生成的老年斑;因微管相關蛋白tau蛋白過度磷酸化而形成的神經原纖維纏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s)。UCH-L1已被證明在突觸可塑性、學習記憶的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與AD的發生密切相關[1]。
1.UCH-L1參與AD的可能發病機制:相關研究通過質譜分析的方法發現AD患者腦中可溶性UCH-L1與顆粒性UCH-L1的比例發生明顯改變[2]。可溶性UCH-L1是功能的主要執行者,它的改變可能參與AD發病。與野生型小鼠比較,作為AD模型的APP/PS1雙轉基因小鼠海馬區可溶性UCH-L1含量下降約30%,且海馬區長時程增強效應(long-term potentiation,LTP)受到抑制,出現認知障礙;而轉染UCH-L1后的小鼠能夠恢復UCH-L1活性且LTP恢復到正常水平[3]。
(1)UCH-L1與Aβ:UCH-L1可影響Aβ含量和神經元的活動。缺血性腦損傷處理后的小鼠腦中UCH-L1含量與活性均會降低,導致BACE1水平上調,BACE1作為β分泌酶可以促進APP向Aβ方向的分解,從而導致Aβ聚集。而小鼠經過注射外源UCH-L1蛋白后大腦中BACE1含量下降,神經元的存活率得到提高[4]。同時,小鼠原代神經元經此處理后由Aβ引起的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逆向運輸減少的現象得到明顯改善,使神經元的生存率和可塑性得到提高[5]。
(2)UCH-L1與NFTs:研究發現敲除UCH-L1基因的小鼠出現類似AD癥狀。該小鼠腦中可溶性UCH-L1含量下降,而腦神經元中神經元纖維纏結(NFTs)數量增多,提示UCH-L1可能參與神經原纖維纏結的形成[6]。具體體現為:一方面,UCH-L1的下調可促進tau蛋白高磷酸化而形成NFTs。LDN是UCH-L1抑制劑,經LDN處理后的小鼠N2a細胞中微管結合tau蛋白含量下降,說明UCH-L1影響tau蛋白的微管結合能力,而未與微管結合的tau蛋白容易聚集。利用高磷酸化tau(Ser202、Thr205)特異性抗體AT8進行免疫熒光與硫黃素染色發現tau蛋白高磷酸化并異常聚集,且都以LDN劑量依賴性增加[7]。另一方面,UCH-L1的下調還可減少異常聚集tau蛋白的降解。在tau相關神經系統疾病中,UPS由于超出其所能承受的負荷或功能受損而無法有效降解蛋白質。此時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6)可與泛素化蛋白形成復合物,運輸到微管組織中心形成聚集體,減小異常聚集蛋白對細胞產生毒性作用的范圍,并通過自噬-溶酶體途徑(autophagy-lysosome pathway,ALP)將其降解。轉染tau441后的HEK293細胞可過量表達tau蛋白,此后,與單獨應用蛋白酶體抑制劑MG132比較,同時應用MG132和LDN處理的細胞中HDAC6與tau蛋白的結合下降,不能形成標志性的核周球狀聚集體結構,而此時UCH-L1寡聚體水平顯著降低,k-63形式的泛素鏈水平降低。表明在tau蛋白過量表達、異常聚集的情況下,UCH-L1寡聚體的下調會減少k-63形式泛素鏈的產生,抑制HDAC6的激活,從而影響HDAC6與tau蛋白的結合,使得小分子泛素化的tau蛋白在細胞質中分散,影響聚集體的形成,阻止異常聚集的蛋白質經自噬-溶酶體途徑降解[8]。
2.UCH-L1多態性對AD的保護:UCH-L1多態性對AD的保護作用一直存在爭議。UCH-L1基因的3號外顯子上第54位胞嘧啶突變為腺嘌呤(C54A)可使得相應位點出現S18Y多態性。2006年,Xue等對中國漢族散發AD患者和健康人的基因分析結果表明A等位基因和AA基因型可能對女性散發AD有保護作用。然而,2010年Zetterberg等對瑞典AD患者和健康人群的調查統計則發現S18Y多態性未對AD產生保護機制。此外,有研究通過Meta分析發現,UCH-L1基因的5種常見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NPs),即rs11556271、rs3756002、rs3775256、rs4861387、rs28581187與日本AD患者發病無相關性,不能作為評估AD發病的風險因素[9]。
三、UCH-L1與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PD)是僅次于阿爾茲海默病的第2大神經退行性疾病,PD可分為家族性PD(FPD)和散發型PD(SPD)。中腦黑質多巴胺神經元的變性以及細胞蛋白內含物——路易小體的出現是帕金森癥的兩個病理學標志,α-突觸核蛋白是路易小體的重要組成成分。特異性敲除其多巴胺神經元UCH-L1基因后的黑腹果蠅出現神經退行性改變,導致其腦內多巴胺含量下降,從而出現運動功能障礙[10]。UCH-L1對PD的作用主要通過引發UPS異常而實現,而某些突變型UCH-L1的致病作用還與自噬-溶酶體途徑有關。
1.UCH-L1調節α-突觸核蛋白的細胞間傳遞:盡管諸如α-突觸核蛋白等蛋白質包涵體在細胞間傳遞的詳細機制尚未得到充分了解,但預計這種傳遞可以解釋許多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病機制[11]。近年來,脂筏(lipid raft)被認為可通過影響神經元中特異性細胞內含物的轉運、傳播從而與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研究發現,UCH-L1與脂筏功能密切相關:在UCH-L1含量下降的原代神經元中,脂筏依賴性內吞作用增強,內源性α-突觸核蛋白的含量沒有明顯變化但其在細胞間的傳遞顯著增加。考慮到UCH-L1的去泛素化作用及其與脂筏的聯系,UCH-L1可能是通過調節脂筏蛋白的泛素化和去泛素化狀態而調節脂筏依賴性的內吞作用[12]。
2.UCH-L1突變與PD
(1)UCH-L1I93M突變與PD:1998年Leroy等在德國一個PD家系中發現UCH-L1基因突變(C277G),這一突變導致UCH-L1編碼的第93位異亮氨酸(I)變為甲硫氨酸(M),水解酶活性降低約50%。2004年Ardley等研究發現,相比于對照組,轉染UCH-L1I93M突變質粒后的COS-7細胞中呈聚集狀態的內含物含量更高。UCH-L1I93M產生的毒性作用可能參與PD的發病。與野生型小鼠比較,轉染UCH-L1I93M基因的gad小鼠在行為學上表現出自發活動的減少,而在神經病理學改變上表現出黑質多巴胺神經元減少,一部分黑質神經元中出現致密核心小泡和嗜銀顆粒,這些表現都與PD癥狀極為相似。免疫印跡顯示中腦不溶性UCH-L1比率大大提高,提示I93M突變引發的毒性作用可能導致了多巴胺神經元的退行性改變,從而參與了PD的發病[13]。UCH-L1I93M活性的下降也是引發PD重要因素。DUB活性下降的UCH-L1I93M可通過影響自噬-溶酶體途徑而抑制α-突觸核蛋白的降解。用mRFP-GFP-LC3雙熒光自噬指示體系追蹤HeLa細胞系的LC3水平和自噬流發現UCH-L1I93M突變細胞中GFP/RFP比率沒有明顯改變,但LC3斑點輕微增加且細胞中p62含量明顯積累,表明自噬體和溶酶體的融合過程未受影響,但自噬體的形成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自噬功能出現嚴重障礙。此時,α-突觸核蛋白以及異常蛋白的清除必然受到影響,過多的有毒產物聚集形成路易小體,導致PD的發病[14]。
(2)UCH-L1S18Y多態性與PD:S18Y多態性被發現在PD中起到神經保護作用:UCH-L1S18Y基因所轉錄的UCH-L1蛋白二聚化趨勢降低,具有水解酶活性高而連接酶活性低的特點。此時底物α-突觸核蛋白更容易被蛋白酶體識別,經UPS降解而減少PD的發病[15]。S18Y多態性的保護作用在小鼠身上已經得到證明。經腺病毒轉染UCH-L1S18Y基因的小鼠可明顯減少因MPTP誘導引起的黑質神經元損失,同時紋狀體多巴胺含量的下降幅度也降低[16]。然而,S18Y多態性對于人類的保護作用卻一直受到質疑。Liu等[17]將22項遍及各大洲的研究進行Meta分析后發現,UCH-L1多態性與人群患PD風險中度相關;而對亞洲、歐洲和美國人群UCH-L1多態性進行的亞組分析未顯示任何與PD風險有關的種族依賴性;對年齡進行亞組分析時,仍未觀察到明顯關聯;但剔除其中3項低質量研究后的Meta分析顯示,UCH-L1等位基因A與PD風險顯著相關;同時,在隱性模型(CC vs CA+AA)中也顯示出S18Y多態性與PD風險密切相關[17]。
四、腦脊液UCH-L1水平對于神經退行性病變的診斷
近期的研究發現,腦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中UCH-L1水平對于PD、AD的診斷起重要作用。與正常人群比較,AD患者CSF中UCH-L1水平明顯升高。因此,CSF中UCH-L1可作為AD的診斷依據和分子標志物[18]。相反,與正常人群比較,PD患者CSF中UCH-L1含量明顯下降,也可用于PD的診斷。此外,研究發現PD患者CSF中UCH-L1濃度與發病年齡亦呈正相關,且用于突觸核蛋白病(包括PD和MSA)患者病情程度分級的Hoehn and Yahr(H&Y)量表得分與CSF中UCH-L1水平呈正相關,提示CSF中UCH-L1水平可能作為突觸核蛋白病的階段分層指標[19]。
五、展 望
近年來臨床研究發現,腦脊液中UCH-L1水平在AD、PD患者與健康人群中存在顯著差異,UCH-L1有望對臨床確診、疾病程度分級工作起到輔助診斷作用。然而盡管已有眾多研究探討了UCH-L1的結構和功能,發現UCH-L1對神經退行性疾病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UCH-L1在AD、PD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
UCH-L1對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的特殊內含物或標志物都有重要影響,其中可溶性UCH-L1的作用尤為重要。脂筏模型是近年來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的討論熱點,UCH-L1被發現可以通過脂筏蛋白調節α-突觸核蛋白的細胞間傳遞,且與目前一些已知蛋白對于脂筏的影響機制明顯不同,但這一具體作用機制還未被發現。關于UCH-L1S18Y多態性、UCH-L1I93M突變對神經退行性疾病的保護或促進作用仍然存在分歧,不同的研究調查顯示出不同的結果,因此還需要更多數據統計來源和人群分類方法以得出最終結論。
綜上所述,鑒于UCH-L1對于神經退行性疾病的重要影響,進一步深入研究UCH-L1在神經系統中的功能和作用底物對明確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病機制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同時也可為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早期預防、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以及新藥的開發提供新的思路和靶點。同時也應當認識到,不僅要探討UCH-L1的下游通路以發現其在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更要追根溯源,探索導致UCH-L1發生改變的原因,如導致UCH-L1不同形式之間轉換以及導致UCH-L1發生不同翻譯后修飾的影響因素,從根本上降低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