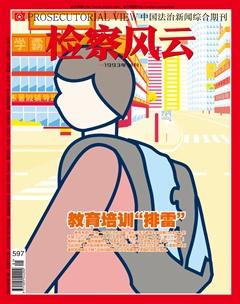飽受爭議的尋釁滋事罪
陳侃

(圖/網絡)
我國刑法第293條規定了四種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包括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然而,也正是這一罪名,在實踐中給辦案人員造成了一定的困擾,也在理論界成為飽受爭議的話題。
男子吃霸王餐獲刑
2018年12月,被告人陳某來到一家位于本市虹口區的餐館用餐。在用餐完畢之后,他直截了當地告訴老板自己沒有錢,他們有兩個選擇:要么讓他走,要么就報警。“陳某甚至還表示自己剛從牢里出來,這讓老板感到很害怕,只能容忍陳某吃了這頓霸王餐。”承辦此案的檢察官告訴記者,幾個月后,陳某再次來到該餐館,由于時間還早,老板娘告訴他暫時不能吃飯,沒想到這卻惹惱了陳某。“陳某不停地用言語威脅老板娘,甚至還動了手,忍無可忍的老板最終選擇了報警。”
其實,這已經不是陳某第一次吃霸王餐了。據了解,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間,他在4家店內有4次吃了飯但拒絕付錢。不僅如此,他還多次在網吧隨意拿取飲料、食物而不給錢,在服務員拒絕提供食品的情況下大鬧網吧,將電腦顯示器推倒,造成網吧財物損失。隨后的2019年5月至6月他又在3家餐館內吃了7次霸王餐,甚至有一次,喝完酒的陳某在路上隨意騷擾行人,在行人準備報警時,奪過手機將其摔壞。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檢察院受理本案后,認為應當以尋釁滋事罪追究陳某的刑事責任,并依法對其提起公訴。最終,去年11月15日,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依法判處被告人陳某有期徒刑7個月,同時追繳贓物折價款發還各被害人和被害單位。
同樣的,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檢察院也于前不久辦理了一起案件。“去年8月,犯罪嫌疑人彭某某與朋友前往一家位于本市金山區的餐館用餐,酒過三巡,當同行的朋友們陸續離開之后,彭某某來到收銀臺表示要結賬。”檢察官告訴記者,彭某某起初提出要把手機和鑰匙抵押在店里,等回去取錢后再來結賬,但是遭到了店家的拒絕。“隨后,彭某某還在店員面前倒起了苦水,表示自己賭博輸了很多錢,實在沒錢支付餐費。他還告訴對方店員自己身上沒錢,即便留在店里也沒用,可以先互加微信等他回去再想辦法。店員見其滿身酒氣,生怕繼續糾纏下去激怒彭某某,只得先答應了這一要求。”當晚,店員曾經在微信上多次催促彭某某付款,但都沒有得到回應,無奈之下只能選擇報警。經調查,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彭某某先后在金山區內的咖啡店、火鍋店、KTV等多家商鋪吃喝玩樂,并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消費金額共計四千余元。金山區檢察院受理本案后,以涉嫌尋釁滋事罪依法對其批準逮捕。
什么是尋釁滋事罪
說起尋釁滋事罪,就不得不提起另一個在我國刑法史上飽受爭議的罪名——流氓罪。我國1979年刑法第160條規定,聚眾斗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公共秩序,情節惡劣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這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流氓罪”。在制定1997年刑法時,立法者對流氓罪進行了分解,從而產生了尋釁滋事罪。
就現行刑法而言,尋釁滋事罪被歸類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結合這點也不難看出,刑法之所以要對尋釁滋事罪做出規定,其目的在于保護公共秩序或者社會秩序不受侵犯。然而問題在于,不論是公共秩序還是社會秩序,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恐怕很難有人能夠對兩者做出非常準確的界定。因而也有人擔心,刑法所保護法益的抽象化,必然導致對構成要件的解釋缺乏實質的限制,進而導致構成要件喪失應有的機能。比如,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羅翔就曾多次撰文呼吁廢除尋釁滋事罪。他認為,尋釁滋事罪是一個口袋罪,最大的特點是模糊,而模糊會導致法律適用的任性與隨意。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賦予了執法機關以絕對的權力去任意解釋何為尋釁滋事。
飽受爭議的“口袋罪”
關于尋釁滋事罪的爭議,首先集中于其作為一個兜底罪,抑或是口袋罪,是否會導致刑法規定的體系性失衡。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于,在毀壞財物類的犯罪中,如果行為人所故意損壞的財物價值不足5000元,那么是否可以對行為人適用尋釁滋事罪中“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的規定?根據司法解釋,造成公私財物損失5000元以上的,應當以故意毀壞財物罪立案追訴;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價值2000元以上的就可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罪。結合量刑來看,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就尋釁滋事罪而言,其基本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處罰金。如此看來,似乎確有體系性失衡之嫌。
然而,想要就這一問題做蓋棺定論似乎也有些草率。原因有三:其一,尋釁滋事罪所規定的罪狀有四條,每一條都有明確的司法解釋對此進行詳細的闡明,什么樣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什么樣的行為構成其他罪名都有明確規定,這些都需要司法辦案人員在司法實踐中根據不同案件的實際情況做出判斷。仍然以故意毀壞財物罪為參照。該罪所保護的法益是狹義的財物以及財產性利益,而尋釁滋事罪所保護的是公共秩序不受侵犯,而并非單純的財產,因此尋釁滋事行為所造成的結果也就不限于財產損失。試問,倘若行為人的任意損毀財物的行為導致他人被迫放棄在市場上的經營,或者難以保證正常的市場經營活動,依然以故意毀壞財物罪來評價,是否妥當?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實踐中,不能認為任意損毀公私財物就不成立故意毀壞財物罪,反之,也不能認為任意損毀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就不成立尋釁滋事罪。因此,對于辦案人員來說,當行為人的行為同時觸犯這兩種罪名時,其任務不應該是尋求兩者的區別,而是以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進行處罰。其二,對于尋釁滋事罪中所規定的情節嚴重、情節惡劣如何認定,司法解釋以及各地也同樣都有規定。至于司法解釋中的“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則更需要準確無誤的證據作為強有力的支撐。以前文所述彭某某一案為例,彭某某的行為已經不屬于一般民事消費合同關系了。檢察官告訴記者,一方面,他在多家店內消費拒不支付貨款,且部分店內消費款“拖欠”一年之久;另一方面,根據其與兩名店內工作人員的對話記錄及相關證人證言,足以證實彭某某不是拖欠不還錢,而是從一開始就沒有付款的意圖,直到最后甚至拒不接聽工作人員的電話。因此,應當認定彭某某的行為屬于尋釁滋事中的強拿硬要公私財物。其三,在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產生爭議的事件也時有發生,然而我們對此也應當謹慎區分,究竟是法律條款本身存在問題還是執法者自身適用存在問題,不應簡單的一概而論。
是否仍需繼續分解
其次,也有不少學者呼吁,可以考慮像分解流氓罪一般,對尋釁滋事罪繼續分解。我國刑法中規定了四種情形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而這四種情形又同時會與刑法中其他一些罪名“產生混淆”,成為困擾司法機關的一大難題。比如隨意毆打他人致人輕傷的行為既符合故意傷害罪的構成,也符合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強拿硬要數額較大的行為,既可能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也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等;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既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也可能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因此,呼吁繼續分解尋釁滋事罪的學者認為,尋釁滋事罪所規定的四種情形完全可以通過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以及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等進行打擊。
如果立法者認為在某些情形下,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尚不構成以上所列舉的故意傷害等罪名,也可以適當擴張這些具體罪名的犯罪圈,比如在故意傷害罪中增設輕微傷的情節。然而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導致刑法的擴大化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因為如果增設輕微傷的情節,那就意味著只要行為人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輕微傷就構成犯罪,勢必會導致大量原本根本不構成犯罪的行為需要以故意傷害罪來論處,明顯擴大了打擊的范圍。
故而本文認為,在現行罪名運行較為穩定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對尋釁滋事罪繼續予以分解,即便要繼續分解,也應當建立在充分考量和研究的基礎上。
結語
法律的普遍性本質決定了法律不能過于具體,法律所規定的內容,本質上既有相當的一般概括性,又不得不有相當的抽象性、相當的非具體性。正因如此,才需要對法律條文進行合理的解釋。筆者認為,不應該隨意的批判法律,更不應該隨意主張修改法律,而應當從更好的角度來解釋疑點。不論是對于司法工作者而言,還是法學家而言,將看上去并不理想的法律條文解釋為合理的法律規定或許才是信仰法律的體現。對于飽受爭議的尋釁滋事罪而言,相比于直接廢除,對其進行合理解釋或才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