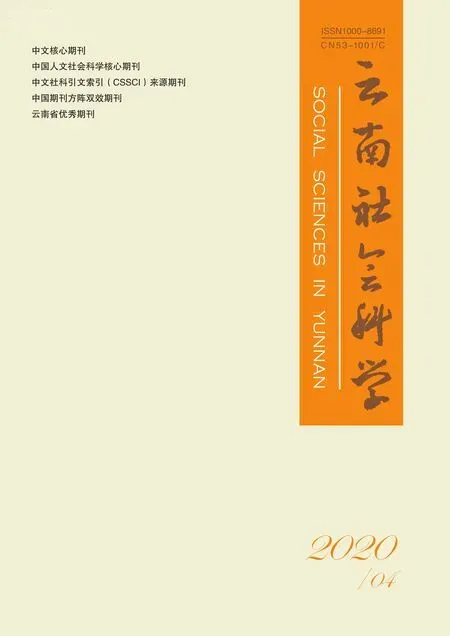變動與堅守:生計方式轉型與白族女性日常生活節奏的個案考察
蘇 醒
一、問題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的實踐活動背景下,諸如滯后、延遲、變換節奏等議題都出現在了社會性爭議的中心之中。其中關于日常生活節奏的相關考察較早就進入了哲學、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研究范疇。著名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將身體作為節奏分析理論的核心范疇,認為身體是進行節奏分析的重要工具和節奏分析的對象,并以此為突破口和重要工具分析了資本主義異化問題。他在晚年論述時間和空間的關系時將節奏第一次作為一個哲學問題進行了系統的闡述①參見關巍:《列斐伏爾節奏分析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大連理工大學,2017年,第18頁。,指出節奏是時間、空間和日常生活的統一體,各種異質性節奏在時空中不斷生成、交織、持存、消失,乃至再生成,如此循環往復,處于永恒的運動之中②吳寧:《列斐伏爾的節奏分析理論》,《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代表人物愛德華·湯普森(E.P.Thompson)剖析了早期工業化進程中工人的時間意向是如何被“重新部署”的,以此展示時間模式被高度內在化導致行為者的時間意向需要在長時間的并且是劇烈的變革過程中才可能適應新的結構性條件。③[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頁。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對卡比爾人時間觀的考察以及對身體慣習(Body Hexis)的討論反映出社會秩序、節奏與身體之間的關系,即社會秩序是通過一定方式調節活動的節奏,并將其深深烙印于身體之上。馬塞爾·莫斯(Marcle Maus)則對愛斯基摩社會在年度周期中的節奏變化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愛斯基摩人的社會生活在一個年度周期中會以冬夏兩季的規則二分節奏交替進行。①參見[法]馬塞爾·莫斯:《社會形態學:試論愛斯基摩社會的四季變化》,[法]馬塞爾·莫斯:《人類學與社會學五講》,林宗錦譯,梁永佳校,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5—192頁。在探討中國關于“時間”的民俗文化時,周星提出在單位時間內人們某些行為重復出現的頻次就可以視為其“生活節奏”。現代社會由于單位時間內人們所做的事情增加、生活節奏變快,于是容易感到疲乏,需要增加往返于“日常”和“非日常”之間的頻次來獲得休息和放松。并且中國人的生活節奏具有多樣性,比如東部沿海的居民對于日常生活的增快已經習以為常,而西部地區的居民卻還難以適應。②周星:《關于“時間”的民俗與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可以將日常生活節奏視作一面能透視文化和社會習俗的鏡子,通過它洞悉社區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特征③張雨男:《鄂倫春族日常生活節奏的變遷與適應》,《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近年來,以“日常生活節奏”作為切入點對特定社區的社會變遷問題所進行的研究也已逐漸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新視角。這一研究視角能夠較為集中、全面地反映社區居民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等。④肖紅新、王坤:《現代客家村落日常生活節奏的變遷》,《龍巖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總體上,學者們多嘗試從“現代性”的動態性和穩定性、內在的張力和發展趨勢中,將日常生活節奏同時作為一種結構復雜體和意義復雜體來發現其特性、邏輯和發展。尤其在少數民族社區傳統生計方式改變、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這更加成為了一種對社區適應問題的新興解釋框架,典型代表是張雨男從日常生活節奏角度對鄂倫春族社區的討論。他指出在應對禁獵和農耕的外來沖擊時,世代狩獵生活所形成的節奏難以適應農業生活所要求的節奏成為了禁獵轉產以來部分鄂倫春族群眾陷入生存困境的深層次原因。⑤張雨男:《鄂倫春族日常生活節奏的變遷與適應》。
如前所述,聚焦于社會結構、生計方式等因素的變化對日常生活節奏的影響并從整體性著眼來分析族群、社區對日常生活節奏變遷適應問題的研究為解釋社會文化變遷提供了視角和方向,但如果考慮到同一社區內部不同性別的成員在面對變遷時有可能在適應性上存在差異,那么對社區成員內部進行具有社會性別視角的微觀考察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已有研究進行補充和完善。有鑒于此,筆者對一個同樣正在應對傳統生計方式轉型的少數民族農村社區——云南大理白族村落N村進行了田野調查。調查發現,該社區在面對由生計方式轉變所帶來的日常生活節奏變遷時總體較為適應,并未發生因無法適應生計轉型而陷入生存困境的情況,但在適應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別,其中性別差異較為明顯。女性社區居民在面對日常生活節奏的變遷呈現出了較高的適應性與積極性——不僅順利地適應由鹽業生產到農耕生產之后生活節奏的改變,從事旅游經營后更是從被動參與轉為主動適應旅游業所需的日常生活節奏,進而還引領了當地的旅游業發展,在推動鄉村振興以及目的地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N村女性面對生計方式轉型、日常生活節奏變遷所表現出的高度適應性是如何產生的呢?基于這一疑問,本文首先勾勒出當地生計方式的轉型歷程;其次探討當地女性日常生活節奏是否隨之產生變動,如有變動,是本質上的顛覆還是策略性的調整?在此基礎上分析究竟是何種因素在主導著當地女性的日常生活節奏。
二、生計方式轉型中的女性日常生活節奏
(一)生計方式的兩次重要轉型
筆者的田野調查點——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龍縣N村其主要生計方式經歷了兩次重要的轉型,第一次是由鹽業生產轉為農耕勞作,第二次則由農耕勞作轉為旅游經營。N村所在地云龍是云南歷史上著名的產鹽區之一。唐代樊綽所著《蠻書》中就有“劍川有細諾鄧井”的記載。到明清時期,該村已有400多戶人家,并根據鹽業生產的分工將家戶分為灶戶、荒戶與商販三個類型。⑥灶戶是擁有鹵水份額、從事鹽業生產的家戶;荒戶為灶戶提供背柴、背水等服務工作;商販則負責將制作好的井鹽運輸到外地售賣。鹽礦的大力開發使其作為云龍產鹽區的重要集鎮經濟十分發達,作為五井鹽課提舉司治地,其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發展。但自清末開始,該社區的鹽業經濟開始衰落。后經歷了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間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1954年3月N村鹽井的全部產權收歸國有,結束了鹽井私有股份制。在此過程中,以鹽業生產為主要生計方式的“灶戶”和鹽商,以及原本砍賣山柴、為鹽業生產提供服務的“荒戶”也都轉為農業生產。期間雖然也存在縣辦鹽廠、生產隊隊辦鹽廠,但生產一直處于半停頓的狀態。至1995年,因林木過度砍伐、生態環境遭到破壞,N村鹽廠最終停產至今。此后大部分村民都轉向農業生產,主要種植玉米等農作物,人口也從明清時期的400多戶縮減至現今的200多戶。2003年N村被評為云南省歷史文化名村,社區居民的主要生計方式便開始從單一的農業種植轉為農業生產與旅游經營并存。2007年N村被命名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這時村中已有兩三家以旅游接待為副業的村民家庭。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N村村民抓住黨委政府實施旅游產業扶貧的大好機遇,依托厚重的歷史文化資源,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旅游業成為脫貧致富的主要產業。2019年,N村客棧已達近50家,其中幾戶村民還在原有客棧基礎上擴大經營,開設了咖啡吧、餐吧等。村中以旅游服務為主要生計方式的村民家庭已達到30余家。其余村民也都或多或少從事與旅游相關的產業,例如制作售賣火腿等土特產品、餐飲服務等。
(二)不同生計方式影響下的日常生活節奏
1.鹽業生產時期:旺平季制鹽、淡空季持家
以鹽業生產為主要生計方式的時期,N村女性日常生活節奏的快慢主要視井鹽生產的旺、淡而定。井鹽生產與雨量聯系密切,雨量少鹵水濃度高、井鹽產量就高,生產進入高峰期、平穩期;反之,雨量多則鹵水濃度低、井鹽產量亦隨之降低,生產即進入低迷、停滯期。當地傳統稱之為旺季、平季、淡季和空季。①每年11 月至次年4—5 月為旺季,這一時期雨水最少,鹵水濃度最高;9—10 月鹵水濃度次之,為平季;5—8 雨水較多、鹵水變淡,為淡季;其中6—7 月是一年當中雨水最多、鹵水最淡的季節,稱為空季。冬、春為旺季與平季,雨水少、鹵水濃度較高,是井鹽的主體生產期。鹵水被從鹽井下汲取②鹵水由“竜工”從鹽井數十米深處汲取。“竜工”由少數有專業技能的男性擔任,其余人等,尤其女性不得下井。后,送至輪值灶戶家中熬煮,直至干燥成鹽。據康熙《云龍州志》記載,熬煮鹽“用小灶一為圍,銅鍋四五口,晝夜煎熬”,期間須時刻注意火勢大小、水量多少等,不可離人,因此家中的婦女亦參與生產。由于該時期“晝夜熬煮”所耗甚多,灶戶家庭還相應實行一日三餐的餐制③中國自古便有以餐制計時的傳統,例如漢代人們就常用“朝食”“晝食”“晡食”“暮食”四次進餐來計時。——除早飯、晚飯外,額外加宵夜一餐以補充體力。熬煮后有散水、歸鍋、搜鹽、濾水、舂鹽、捏鹽、燒鹽等工序。《滇海虞衡記》有載:“白井鹽甚白,名人頭鹽,團鹽也。井女手始成”,即在熬煮過程中把鍋中結晶的鹽粒搜出,濾去汁水,由婦女用手捏成團,同時鏟出灶中的熱灰,鋪在地下,把團好的鹽放在灰上,使其滲濕而易燒干;最后用火烘烤,使其干燥堅固。④朱霞:《從(滇南鹽法)中看古代云南少數民族的鹽井生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4年第2期。由此可見,在旺、平二季,N村女性在整個井鹽制作的全過程中,除參與看顧灶火、熬煮鹵水、手捏團鹽等直接生產環節外,還要從事煮制夜宵、背賣柴薪等輔助性勞動,幾乎晝夜不休、異常緊湊。夏、秋兩季是井鹽生產的淡季與空季。“淡”指雨量大而致“鹵水淡”,“空”指鹵水過淡以致無法熬煮成鹽,為井鹽生產的低迷期與停滯期。此時,N村從事井鹽生產銷售的男性可稍事休息,而大部分女性則開始將生產重心從井鹽生產轉向糧食蔬菜種植、家禽家畜飼養、裁衣刺繡等與家庭責任相關的生產勞動并集中參加各類民間信仰活動,如農歷六月十三舉行的“龍王會”、農歷八月二十七舉行的“孔子會”等,統稱為“做會”。這些活動不僅形成獨特的地方生活周期,而且還反映出當地的自然地理和歷史文化風貌,例如專門祭祀鹵水龍王的“龍王會”就與當地以井鹽生產為主要生計方式有關。雖然這些活動的主導者為男性,但女性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參與力量——祭品、茶水等的準備、廚事等大量繁瑣勞動均由她們負責。
2.農業生產時期:農忙做活、農閑持家
在漫長的農業時代,民眾大多習慣于依靠太陽月亮的升落、星辰位置的變化或者雄雞鳴叫等自然現象來判斷時間,一面又根據日常生活的節奏、對時間進行粗略的把握。伴隨鹽業生產日漸衰落,N村也轉為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計方式,主要種植作物為玉米。因此,這一時期當地女性的日常生活節奏也轉向以農事節令為劃分標準并與農作物的生長周期同步——在當地體現為以農作物(玉米)生長為主軸,輔之以牲畜、家禽養殖以及農副產品的生產制作(野生菌采集、火腿制作)等。總體可以概括為“順時而作,農事為先”。首先,女性日常生活節奏反映出圍繞農業生產形成地方性知識和生態智慧,并與當地生態環境息息相關,與各種作物的生長周期同步,這也這構成了當地農時的基本框架。例如根據野生菌的生長特性,她們需要在夏季將起床時間提前至太陽升起之前以便上山采集;種、收玉米的季節則需從日出一直忙碌到日落等。其次,女性日常生活節奏還反映出對勞作時間的依從,即“農事為先”。餐制亦是農業勞作對生活節奏起決定性作用的典型反映:受勞作時間的限制和對農時的爭分奪秒,農業生產時期N村普遍實行兩餐制,早飯和晚飯。至于進餐的具體時間則視農時的忙閑而定:農閑時多在上午十點和晚上七點左右;農忙季節則可靈活變動。由女性將飯送到田間地頭亦是保證農忙期間田間勞作生產的重要措施,攜帶干糧至田頭的場景也很常見。總之,農業生產時期的女性勞作、生活大致上以農時為基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一年四季的基本狀態,晨出夕歸為其一日的基本節奏。這也體現出農家勞作生活規律性的一面,當然在這個常態下也可以進行一些個性化的靈活調整,構成了每個女性具體豐富的生產生活狀態。①參見鄧雅麗:《北宋北方地區的生產和生活節奏——以農時為線索》,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師范大學,2012年,第26頁。提姆·英格爾頓(Tim Ingold)認為,文化并不是建構的,而是在人們熟知世界的過程中所不斷認識得來的。②參見Tim Ingold,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Londres et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轉引自張雨男:《鄂倫春族日常生活節奏的變遷與適應》,《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通過棲居與生活實踐,人們逐漸形成了一套來源于整體性生活世界認知的行為方式。③張雨男:《鄂倫春族日常生活節奏的變遷與適應》。N村女性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勞動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符合當地自然發展規律和生態平衡規則的地方性知識不僅影響著她們日常生活節奏的規劃,而且使這種規律的日常生活節奏逐漸內化為一種無意識的“慣習”。
3.旅游經營時期:從“農事為先”到“游客第一”
自發展旅游扶貧產業以來,N村開始從單一的農業生產轉為農業生產與發展旅游并存,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從事旅游服務。旅游業的發展給當地婦女帶來了獲取利潤的巨大商機,原先的生產生活規律也逐漸轉向與旅游淡、旺季同步。旅游經營對時間分配的靈活性要求更多,同時需要對如何實現收益最大化加以認真考量。從事旅游經營后村民轉以“游客第一”為原則。當旅游旺季到來,從事旅游經營的女性大都全力投入旅游接待,這同時帶來了農事、家事、餐制以及節慶等方面的日常生活節奏的重大改變。
農事方面,旅游旺季與農忙季節如有沖突,那么應行之農事會被暫且擱置。受訪者L談到“原本應該是地里做活的,但算了一下,做了地里的活回來再給客人做飯來不及,而且家里沒個人守著,客人也不滿意,我想想就把地里活先放一放,要是過幾天客人還多,那我就請個人去幫我弄(地里活)。剛開始家里老人說我就是不想做活,后來發現給客人做飯掙的多太多,還喊我不要去地里了,有親戚來還夸我勤快會掙錢”(受訪者P,女,51歲,201808)。家事方面,傳統意義中婦女的“持家”行為也根據旅游經營之需求進行了相應改變。如制作火腿、炸制油雞樅等原屬婦女的家庭膳食制作,現已逐漸轉變為商業行為;又如N村經營民宿的年輕女性開始雇傭其他婦女為其看護嬰兒,以便自己能夠有更多時間接待游客,這在該村亦是從未有過的。她告訴筆者:“客人多,我太忙了,所以就雇兩個阿姨幫我看孩子。阿姨有錢掙很高興,把我的孩子當自己的孩子;我有錢掙也很高興,把客人當上帝;客人有好的服務也高興,這就是‘三贏’的事情”(受訪者L,女,30歲,201809)。餐制方面則由傳統的“兩餐制”轉變為現代城市社會普遍的“三餐制”,并盡可能地與客源地保持一致,一般在每日早八點、午十二點、晚七點固定提供餐食,部分經營咖啡吧的女性還需要在下午三點左右向客人提供下午茶,這無疑又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經營者的工作量,她們需要加快工作節奏以滿足游客需求。節慶方面,假日經濟驅動當地女性打破其節慶期間習以為常的輕松休閑的生活模式,生活節奏變得快速、緊湊、忙碌。在傳統社會,她們認為傳統節日的意義主要在于對傳統節俗的弘揚,同時也是對本民族文化的一種彰顯。但在參與旅游經營后,歲時節令更包含了“假日”的意義,能夠為旅游業提供更多文化內涵和發展動力。這種轉向自然也伴隨著日常生活節奏的變動與調適。以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春節為例,春節在當地被稱為“過正月”,即從農歷除夕至正月十五都要舉行各種慶祝和娛樂活動。除夕日全家吃年夜飯、“守歲”,晚間以紅封條“封門”,正月初一早上方揭開封條,以示辭舊迎新;農歷正月初四,婦女們忙碌完各種事務后要與家人一起“查運氣”①具有博彩性質的游戲在平時被視為賭博,女性參與此類游戲會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但春節期間參與這類游戲則被認為是“查運氣”,也就是在一年之初來試試自己的運氣,與品行無關,因此婦女們在春節期間也都會湊熱鬧參與此類游戲。正月初五后即止。;之后還有“接姑老太”等專門針對女性的娛樂活動。在從事旅游經營后,傳統的生活節奏被打破:受訪者L在村中經營一家民宿,她的微信朋友圈信息顯示:農歷臘月三十(除夕)接待游客14名,L一家人忙著給客人準備餐食,自家的年夜飯吃得簡單又匆忙,“封門”和“守歲”的傳統習俗也因客人在民宿內外出進玩鬧至凌晨而未能進行;農歷正月初四本是“查運氣”的娛樂時間,但因前來住宿游玩的客人多達12名,L一直忙碌到深夜而未能進行;“接姑老太”的活動由于前來住宿的客人已經預定到正月十六,只能取消。傳統意義上農歷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期間的“過年”逐漸被旅游參與后的村民們劃分為兩段:初一至初七強調其“長假”性質,初七之后方轉為其傳統節日性質,而這種差別被婦女們直觀地以“掙錢”和“不掙錢”加以區分。受訪者H談到:“以前不管男女過正月都是不掙錢的。不像現在,春節正是婦女忙著掙錢的時候。一年就靠這幾天呢,春節7天賺的比之前幾個月的都多。玩也不玩了,也不走親戚了。玩什么時候不能玩呢,輕重緩急誰會分不清。這幾年家家都想著趁春節這幾天能好好弄一下,多掙點錢,以后再玩、再休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改變的”(受訪者H,女,55歲,201806)。列斐伏爾在其早期日常生活批判概念中曾談到“日常生活一方面表現為節日與娛樂,另一方面則是非節日的與嚴肅的生活事務”。②劉懷玉:《論列斐沃爾對現代日常生活的瞬間想象與節奏分析》,《西南大學學校(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從N村的個案來看,從事旅游經營后節日與非節日、娛樂與嚴肅的生活事務逐漸地重疊、扭結在一起,節慶期間日常生活的節奏也從“緩慢休閑”轉為了“忙碌掙錢”。雖然許多傳統活動因此而被壓縮,甚至被擱置,但這均是源于從事旅游經營后“加速日常生活節奏,最大限度利用假日,以給家庭帶來盡可能多的經濟收益”這一核心理念。
三、變動與堅守:社會轉型背景下女性對日常生活節奏的調適
(一)表層變動:生計方式轉型中的日常生活節奏變遷
基于不同生計方式對行動者的要求各異,由此主導的日常生活節奏也在進行相應的改變與調適。鹽業生產時期,人們普遍遵循“觀雨而作”的原則。婦女在旺季與平季參與井鹽制作,淡季與空季則持家、做會,如此往復交替,形成了年度的“環狀”時間鏈。這與何翠萍在對景頗、載瓦人研究中所發現的“干季做人,雨季做活”③參見何翠萍:《生命、季節和不朽社會的建立:論景頗、載瓦時間的建構與價值》,載黃應貴:《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第158-159頁。的時間建構十分類似。盡管傳統觀念的偏見使得婦女緊湊的日常生活節奏難以在經濟價值上得到高度認可④男性辛勤的工作、緊湊的生活節奏以工資或價格形式加以估算,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其社會地位與尊嚴。,但是生產中婦女的各種直接勞動和輔助勞動實際上均在有效地保證井鹽獲得,她們主要以手工生產能力和家庭管理技能為家庭經濟做出大量基礎性貢獻。農業生產時期,女性的日常生活節奏則仿佛一個圍繞著四季自然節令與種植勞作周期而循環往復轉動的車輪。當地人認為,即使一年到頭辛勤的在田間地頭勞作所獲取的金錢比外出打工所獲的金錢要少,也應勤事生產,因為這是個體、尤其是女性良好德行的外在體現。有村民談到:“我們這里的女人覺得勤快才是本分,見不慣懶的。種地一年苦到頭,雖然掙不了幾個錢,但是心里踏實。住在上面那家的男人出去打工了,他家女人覺得反正她男的會掙錢回來,就很不做活,每天閑著,東逛西逛。其他的婦女都很見不慣。雖然她家經濟條件好,但是大家都不愛跟她來往”(受訪者W,女,50歲,201607)。從這段訪談可發現:當地傳統觀念認為男性緊湊的日常生活節奏主要意義在于“掙錢”,這是其主要的家庭責任;女性緊湊的日常生活節奏則主要起到維護家庭運轉良好的作用,即“持家”。雖然持家并不能帶來更多實際收益,女性工作的價值也常常因此以低于男性的形式被感知或者完全被忽略,但緊湊的日常節奏將會轉換為社會輿論對她們的正向評價與尊重,而這正是個體追求的榮譽。在由鹽業生產轉為農耕勞作的過程中,女性日常生活節奏的具體分配規則有所變動,但“守其業、勤勞作”一直是日常生活節奏分配的主導思想,是整個社會運行的基礎,也是衡量社會秩序穩定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鹽業生產與農業生產時期有片面強調勤于勞作的傾向,這一時期女性日常生活節奏的快慢與價值關聯度較低,主要是為實現家庭耕讀傳家、香火延續的傳統理想扮演好賢內助的角色,因而缺乏奮斗和進取的意識。
從事旅游經營后,N村女性的日常生活節奏表現出了一些與現代工業社會直指未來的線性時間觀相符的特質:由傳統“勞作—持家”的二分法轉為對時間的更有效利用,追求效率更加受到推崇。在生計方式轉型過程中,她們正在經歷著段義孚(Yi-Fu Tuan)所提出的那種由“非技術社會”到“技術社會”對其日常生活節奏的改變,不再以“非技術社會”中那種以鳥鳴春、以蟲鳴秋的方式來感知時間,技術社會將她們的時間精確地校準到了小時和分鐘。①[美]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王志標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04頁。相對于鹽業生產、農耕勞作時期,旅游經營時期最大的改變在于,測度時間的體驗使當地女性逐漸體會到日常生活節奏本身不僅蘊含著“時間資源”,更是一種“時間資本”。正如所羅門箴言所說的那樣:“勤勞的雙手是通往財富之門。”她們的勞動因為實現了經濟價值受到了尊重,而當其意識到旅游業的繁榮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力之后,更是希望通過勞動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和社會地位。個體通過日常生活節奏的調節可以獲得時間,對時間進行嚴格控制和積極規劃,從而進行更多具有價值的勞動。因此當地人認為,富于美德懿行的女性不僅勤于勞作,還應當懂得合理規劃時間、靈活調整節奏,以運用有限時間獲得最大的收益。尤其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民宿由女性負責,她們可以通過對日常生活節奏的調適將自身所蘊含的勞動力轉化成旅游經營場域中經濟貨幣、社會關系網絡等資本形式。因此當日常生活節奏松散緩慢、無事可做時便會產生時間被“浪費”的感受,目的意識也變會得空前的強烈,“奮斗”逐漸成為了這一時期當地女性追求榮譽的重要表現。這一點正如康德所言:“我們越忙碌,就越能體驗到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意義,也更能感知到生命的存在。在懶惰中我們卻只能眼看著生命分秒流逝、擦肩而過,讓日子過得死氣沉沉,毫無希望。”②張艷芳:《德意志民族市民階層的“勤勞美德”發展史研究》,《世界民族》2019年第4期。
從N村的田野調查發現,生計方式轉型引起了女性日常生活節奏的變動與相應的調適。這種調適通常以時間策略③關于時間策略,布迪厄曾進行了深入的論述(Bourdieu,1997年,第7頁)。的形式出現,呈現出暫時性、工具性和靈活性的特質。而事實上無論是從事鹽業生產、農業生產還是旅游經營,當地女性日常生活節奏中忙碌、緊湊的核心傾向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筆者認為,表層變動的背后存在著一種已被內化的性別觀念與道德取向在主導著當地女性的日常生活節奏并在社會轉型中被持續堅守。
(二)深層堅守:傳統女性文化中“勤”的道德取向
N村女性面對日常生活節奏變遷的高度適應性是具有其內生基礎的,即傳統性別觀念始終要求女性把勤勞作為自己生活的指向標。勤存在于人們內心世界的理性之聲對于自身的約束過程之中。在N村,“勤”這一道德指向往往通過性別勞動分工、道德教育和社會輿論的雙向強化等方式得以內化,從而持續、深層地產生影響。
1.性別勞動分工
N村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將男性規范到讀書、求取功名、延續家族的角色中,以實現耕讀傳家的社會理想;女性則被規范到持家相夫的角色中,以保障家庭運轉的秩序。日常生活節奏也基于性別角色的不同具有差異。個體從幼年時便開始學習與適應與性別角色相對應的日常生活節奏。當地諺語有云:“女兒像媽,苦不贏。”婦女主持家務,“女兒像媽”意喻著希望女兒像母親一樣勤事生產、操持家務。“苦”指“勞作”,“不贏”意為“沒有空閑”,“苦不贏”即深切反映出傳統性別角色構建與道德取向對女性的期望——勤勞不怠、片刻不歇的日常生活節奏。當地旅游業主要是為旅游者提供住宿、飲食等旅游服務的以農村家庭為單位的小型村寨民宿,受限于經營理念和資本、技術、人力等條件,通常只有餐飲接待、住宿服務和土特產制作售賣等為數不多的經營項目,而以上項目在N村的傳統分工中全部屬于女性“持家”的范圍,因此女性普遍成為主要從業者,男性則主要作為經營中較大問題的決策者,但較少從事具體勞動。一位男性受訪者表示:“現在搞旅游雖然是我拍板決定搞的,但主要還是你阿姨弄。女人家天生就是勤快,眼睛里有活,比如種著菜,就會想著摘個瓜回來。我也承認我們男的是要懶一點,但是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女的就不一樣了,女的要勤手快腳嘛”(受訪者C,男,52歲,201809)。既然當地人普遍認為旅游經營項目是傳統女性家庭勞動的延伸,那么女性的日常生活節奏就與旅游經營的經濟收益有著直接關聯,用她們自己的話說:“現在搞旅游,基本上還是以前家里那些活,客人要吃要喝要買特產,誰做?還不都是我們女人做。男人家懶,也不會整。女人家不勤快,(旅游)就搞不好。你懶得打理院子,客人看著不順眼就不來住;懶得種菜,成本就高了;懶得早起去山上采菌子,客人想買土特產你就沒得賣給他們的,還怎么掙錢?誰都不眼紅我掙錢,我一天從早到晚手腳不閑著”(受訪者W,女,51歲,201809)。由此可見,社會性別形塑著日常生活節奏,日常生活節奏也反之對社會性別進行劃分并與個體的活動、社會文化融為一體。①紀蘭慰:《論歲時節日民俗舞蹈的時空轉換特征》,《貴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9期。男女兩性在傳統社會文化的持續影響下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從事不同的社會勞動,也保持不同的日常生活節奏。從傳統社會“女兒像媽,苦不贏”的諺語,到現代旅游經營中“從早到晚手腳不閑著”的自我表述,N村女性的日常生活節奏始終被“勤”這一道德取向所主導。
2.道德教育
N村一直奉行“筆點文章先點德,斗量陰鷙后量才”的理念,從而將道德教育置于各類教育之首。在女性教育中,勤勉是德育的重要內容之一。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當地女性都有多種途徑學習勤勉的道德取向并據此安排日常生活節奏,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宣化等。家庭對女孩“勤勉”品質的教育培養貫穿其成長歷程的始終。幼年時,女孩在家長的要求下背誦 “勤則家起,懶則家傾”的家訓并從女性長輩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言傳身教的學習各種家務技能;出嫁前,長輩要叮囑訓導新娘在未來的婚姻生活中勤勉持家,以彰顯娘家的嚴格家教;婚禮次日清晨,婆家要求新婦早起打掃衛生,用嫁妝中的銅壺、茶盤、杯子給家人奉茶,然后下廚,以告誡新婦在未來生活中要勤勉持家。這些家教方式與傳統習俗至今在N村依然為村民所保留、延續。學校教育也是女孩內化“勤勉”品質的重要途徑,無論是N村清代、民國時期的教育,還是今天的小學義務教育中都有關于“勤”的教學內容。清光緒年間,N村辦有“內北鄉鄉立女子初級小學校”,校址在萬壽宮,經費由寺廟公款開支,教員由清末貢生一名、廩生一名以及師范生一名組成。除識字、識數等基本教學外,傳統道德教育更是首要教學目標。其中教員對女性勤勉品質的強調令村民記憶深刻:“我特別記得,母親說過,女子小學校里先生教識字的時候說‘婦女的婦字怎么寫,左邊是女子的女,右邊是掃帚的帚’,所以女子天生就是拿著掃帚掃地、做活的人,從此大家就學會要勤快”(受訪者G,男,81歲,201809)。時至今日,在2004年修訂的《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三字歌》中也有“個人事,應自理,家務活,要學習;好習慣,早養成,有教養,益終生”的內容。女孩們從小學教育就開始學習、踐行并內化著關于“勤”的道德取向。除學校外,社會宣化對女性“勤勉”品質的學習也具有重要影響。清代、民國時期村內設有“圣諭堂”,通過宣讀、講授的方法對民眾進行道德品行的宣化教育,稱之為“講圣諭”。所用教材稱為“善書”,通常源于儒家經典、佛教典籍、道教典籍、家法家訓等。針對女性群體“講圣諭”時“勤勉”往往是主要教學內容,如“白日種田園,夜晚搓索子,四時播百谷,春來撒秧子,夏天勤栽插,秋天獲谷子,金銀幾柜子”①來自于專門寫給婦女的“善書”——《閨閣錄》。當地村民楊榮槐家中存有手抄本一部,其余部分村民家中則存有油印版本和復印版本。或“五更雞唱,起著衣裳,盥洗已了,隨意梳妝,撿柴燒火,早下廚房,摩鍋洗碗,煮水煎湯”等。社會宣化能夠將原本離大眾較遠的高深的理論禮儀規范加以通俗化大眾化改寫,以簡單明了、朗朗上口的形式使當時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的女性群體詳熟易懂,為學習和踐行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鄉村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傳統道德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新時代鄉村道德也不再囿于傳統鄉村社會固有的道德規范,但其中勤勞、奮斗、敬業等道德理念始終作為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美德而得到傳承和發揚。
綜上可知,“勤”這一基本道德取向在N村的發展史中不但未被擯棄,而是隨著時代變遷在揚棄中被賦予了更豐富的經濟內涵和更深刻的社會意義。通過旅游參與的實踐,女性村民不但繼續將“勤”視為女性應當具備的美德懿行,還深刻意識到“勤”是以積極的方式改善生活條件、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手段,其體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與個人全面發展、家庭富裕和諧、社區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都息息相關。他們為了使自己的自我意識有一個載體,一方面通過把“勤”這一道德取向寫入女教典籍;另一方面,又通過宣化教育對社會的影響力來參與女性的生活,如對女性日常生活節奏的快慢進行監督等,這些由勤勉勞動衍生出來的生活方式,在提升了當地女性自我價值的同時,也使“勤”變成了該社區的一種公共道德。而一個事物一旦具有了價值和道德意義,也就具有了準宗教的性質,其約束力和推動力都會截然不同。②張艷芳:《德意志民族市民階層的“勤勞美德”發展史研究》,《世界民族》2019年第4期。
3.社會輿論的雙向強化
社會輿論的雙向強化指的是正強化與負強化的過程。正強化即通過嘉獎、贊許等方式鼓勵人們對某一行為持續保持并予以加強,這些行為多是社會和組織需要的行為。負強化則指預先告知人們某種不符合要求的行為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以使人們采取符合要求的行為或回避不符合要求的行為,從而避免或消除不良后果。通過這種強化方式能從反面促使人們重復符合要求的行為,達到與正強化同樣的目的。③邵建平、曹凌燕:《威脅激勵的理論與應用研究》,《管理現代化》2003年第3期。傳統上正強化方式有墓志、家訓、歷代《列女傳》等,內容主要是對符合主流價值標準的道德取向和具體行為進行記敘和傳頌。眾所周知,這些記敘傳頌的女性形象都是被高度概括了的、符號化的美德形象。N村《月翁老先生暨孺人徐太君墓志》中就述有“孺人徐氏,出自世族,秉德之厚,所稱幽嫻貞靜,柔惠且直也。年二十適公,優于內助,事闕翁姑,有先意承志之孝,嫻于持家,無倦勤詬誶之習。俾公益得以酣暢于學,不必屑屑于家計。及嗣君提名,孺人釋然于相夫鞠子,俱能有成,遂先辭世,享年七十一歲,與公伉儷偕老,顧子若孫,將怡然于九京爾”之內容,著重強調的是徐氏生前勤勉持家、使其丈夫得以安心科考的行為。考慮到當時的女教盛行的社會風氣以及N村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道德操守和道德理想,墓志上的頌詞便是社會輿論對女性“勤”這一道德取向進行正強化的典型。換句話說,為“勤”這一道德取向所主導的日常生活節奏是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要求,社會輿論也會相應對遵從該取向的女性加以肯定和褒獎,并據此對其他社會成員進行宣化教育,期望其他女性學習并踐行。值得注意的是,女子踐行“勤”的道德取向不僅為個人帶來社會輿論的肯定,更是其家庭甚至家族的榮譽,楊簡《紀先訓》有言:“女子事人能敬夫,能奉祀,事舅姑有道,則父母之榮。”④楊簡:《慈湖遺書》卷17《紀先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56 冊,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894頁。普通村民也有“培植一個有德氣的,父親母親、兄弟姊妹,一家子臉上都有光”一類的表述。
負強化能從反面促使人們重復符合要求的行為,達到與正強化同樣的目的。⑤邵建平、曹凌燕:《威脅激勵的理論與應用研究》,《管理現代化》2003年第3期。N 村諺語有言“一塊花帕四只角,花帕上面繡飛蛾。花帕爛了飛蛾在,不看人才看手腳”,這里的“手腳”指的就是姑娘的勤快與否。在當地傳統觀念中,女性的美好形象在現實生活中更多是勤勞與懶惰、能干與不能干、頂事還是不頂事的差別。她們把懶惰視為浪費時間,將勤勞視作人生的意義。在N 村,對女性的負強化普遍表現為輿論壓力,例如以議論、批評、指責等對個體施以壓力,使其產生羞愧、內疚、害怕等情緒或者以懲罰的方式,對個體的重大活動制造人為障礙,使其遭受挫折,產生沮喪、不安的內心感受,從而達到主動避免或更改不符合要求行為的目的。比較典型的就是婚姻締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負強化:擇偶過程中勤勉始終是考察女性的一項重要標準。時至今日,該標準依然適用且被看重。同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一樣,通過介紹人牽線搭橋仍是目前當地年輕人擇偶的重要途徑之一,在與介紹人溝通時“勤快”“能持家”往往是男方對未來配偶的基礎性要求。換句話說,年輕女性是否屬于優秀婚配對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她是否擁有勤勞的品德,而忙碌、緊湊的日常生活節奏又是其具體的表現。如此,婚姻排斥既是一種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也是一種通過社會輿論的負強化使女性內化“勤”這一道德取向的具體形式。
四、結論
既往研究顯示,日常生活節奏被打破有可能造成部分人群因難以適應新的生活節奏而陷入貧困。但在筆者的考察中,N 村女性在面對新興的生計方式和外來文化的沖擊時,非但沒有陷入這種困境,相反卻表現出高度的適應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主導當地婦女日常生活節奏的內生基礎的是傳統性別文化中“勤”這一積極的道德取向。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關于如何安排日常生活節奏的思考方式正是源于社會文化所賦予的道德觀念。正如巴特勒所說:“性別不應該被用作一個名詞,一個本質的存在,或者一個靜態的文化標簽,而應該被視為不斷重復的一種行為。”①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of Identity,2 th ediion,New York and London:R outledge,1999,p43.傳統社會中,女性“勤”的道德取向一直為儒家經典所贊頌,生產性的家庭最大程度上發揮了妻子工作的技能與積極性;現代社會中,這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同樣是女性在日常生活和職業生涯中獲得成功的重要保證。這一道德取向經由社會性別建構、女性教育以及社會輿論的雙向強化等方式而得以內化,并相應在外在行為上得以體現。通過女性的代際傳承、言傳身教,這一道德取向便會深深鐫刻進日常的觀念與思維里,久之,“社會的建構也被改造成了自然的存在”②魏開瓊:《社會性別的建構與形塑——對一個布朗村寨的田野觀察》,《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2期。。換句話說,基于“勤”這一道德取向而形成的日常生活節奏實際上已成為當地女性的“慣習”——它既是外在的客觀結構在個體身上的內化實踐,也是一種無意識的生活實踐,其產生及所引發的行動全部基于生活實踐,不假思索但符合規范。③張雨男:《鄂倫春族日常生活節奏的變遷與適應》。西方現代哲學認為,理性是工具性的支配意志,包括時間在內的一切事物都被合理化的工具性訴求所支配。④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5頁。無論是傳統社會中女性通過“勤”來獲取美德的贊許,還是現代社會中她們試圖通過“勤”來改善生活條件、提升生活品質、獲得社會尊重與自我實現,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合理化的工具性訴求。相應地,這些訴求的滿足都需要以日常生活節奏的加速為手段。如果我們形象地將生計方式轉型視作“萬變”,那么“萬變不離其宗”——傳統女性文化中的“勤”的道德取向正是其中的“宗”。
當社會政策在應對農村地區社會轉型問題時,既要正視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不同之處,也應將作為“慣習”的傳統性別文化、道德取向對當地人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的延續性影響納入考量。本文個案的分析探討能夠就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道德取向是否能夠在新時期的社會轉型中繼續并持久發揮積極影響、有助應對而成為了一個值得持續關注并深入研究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