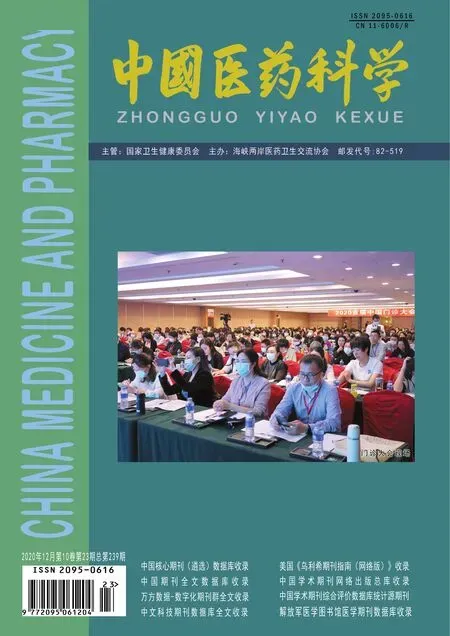賦能教育對男性抑郁癥患者用藥依從性及自我效能影響
林鵬瑛 黃麗英 王小菊
1.福建省寧德市康復醫院精神科,福建寧德 352100;2.福建省寧德市康復醫院護理部,福建寧德 352100;3.福建省寧德市康復醫院精神科男四科,福建寧德 352100
目前全球接近3.5億群體存在抑郁癥,我國抑郁癥患者也接近1億,抑郁癥已經成為了世界范圍內主要健康問題之一[1]。抑郁癥是抑郁障礙的一種典型情況,患者主要會出現興趣減退、情緒低落等癥狀,還有部分患者會出現幻覺、妄想,病情嚴重者可能會產生自殺傾向,會對其正常生活產生嚴重影響。現階段臨床治療抑郁癥以抗抑郁藥物為主,但部分患者藥物治療過程中醫囑依從性不理想,無法主動堅持服藥,容易出現病情復發的情況[2]。因此,在抑郁癥患者治療期間需要對其進行引導,做好相關護理工作,讓其能夠正視自身病情,主動配合治療,確保治療有效性。我院精神科男病區于2019年1月開始在對男性抑郁癥患者護理過程中應用了賦能教育,獲得了較好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標準:所選患者均符合ICD-10抑郁癥診斷標準[3];漢密爾頓焦慮量表評分(HAMA)≥14分;能夠正常溝通、交流。患者及其家屬對于本研究已經知情,且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存在嚴重認知障礙或精神病史者;存在語言障礙、智力障礙者;精神活性物質或非成癮物質所致抑郁者。
選取2019年1~6月(賦能教育實施后)我院精神科男病區收治的52例男性抑郁癥患者作為賦能組;另選取2018年7~12月(賦能教育實施前)收治的52例男性抑郁癥患者作為對照組。賦能組年齡22~65歲,平均(36.8±6.7)歲,病程1~5年,平均(3.21±1.26)年,文化程度包括高中及以下17例,大專及以上35例;對照組年齡21~68歲,平均(37.2±7.0)歲,病程1~6年,平均(3.32±1.34)年,文化程度包括高中及以下16例,大專及以上36例。兩組年齡、病程以及文化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獲得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抗抑郁藥物治療。對照組采取常規健康教育,由責任護士向患者闡述抑郁發病機制、危害性、治療方案、成功案例等,以PPT、短視頻、口頭宣教等方式進行講解,讓患者能夠了解自身病情。當患者出現疑問時,及時進行解答。同時對患者進行合理用藥指導、飲食指導、運動指導、日常生活指導以及心理疏導,讓患者能夠盡快克服病情影響,早日回歸社會。
賦能組在上述基礎上實施賦能教育。(1)明確問題。責任護士與患者進行細致交流,向其詳細闡述抑郁癥相關知識,包括發病原因、主要臨床表現、治療藥物等,強化患者對于自身疾病的認知。然后對患者提出開放式問題,如“您身體有哪些不舒服?”“您有什么問題需要協助?”“您對治療藥物是否了解?”等。結合患者回答,判斷患者對于自身病情了解程度以及態度,明確其需要解決的問題。(2)情感宣泄。責任護士給予患者鼓勵,讓患者對自身健康問題、病情以及心態表達真實感受。在這個過程中責任護士依然可采取開放式提問引導患者,如“是什么原因讓您出現抑郁癥狀?”“您在服藥過程中是否存在疑慮?”“最近心態上是否出現變化?”等。通過提出問題,讓患者適當宣泄負面情感,傾聽患者所提出的觀點,不予評判,給予患者情感支持,通過眼神、點頭等動作示意肯定患者。當患者情緒宣泄完成后,再引導患者認知自身問題,指導其加強自我管理。(3)目標設定。責任護士結合患者提出的問題,進一步引導,提出“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您覺得哪些地方需要做得更好?”,讓患者能夠根據自身情況設定局部短期目標以及長期目標,責任護士再結合其目標進行適當調整,以滿足患者實際需求。(4)計劃設置。當患者目標設置完成后,責任護士繼續通過開放式提問對其進行引導,如“為了達成目標,您認為應該如何做呢?”“您認為需要如何制定計劃?”等,再結合患者實際情況、病情以及需求等與其共同制訂目標,并讓患者做好記錄,督促其循序漸進達成目標。(5)效果評價。責任護士對患者提出問題,如“您的目標完成的如何?”“您對自身病情有新認識嗎?”等,引導患者對自身目標完成情況進行自我評價。對于患者已經取得的成果要給予肯定,讓其繼續保持。若患者出現未能達成的目標,護理人員協助患者找到原因以及問題,再通過開放式提問,如“您認為應該怎么改進?”“您覺得哪些方面可以做的更好?”等,讓患者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并設置后續目標,鼓勵其再接再厲。
1.3 觀察指標
干預后3個月,采取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對兩組患者抑郁癥狀作出評價,總分愈高表明患者抑郁癥狀愈嚴重[4]。采取用藥依從性問卷(MMAS-8)對患者進行評價,分數愈高表明患者用藥依從性愈好[5]。采取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對患者進行評價,分數愈高表明患者自我效能感愈優[6]。
1.4 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對本研究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HAMD評分比較
干預前,賦能組HAMD評分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604,P=0.547);干預后,兩組HAMD評分均低于干預前,且賦能組明顯低于對照組(t=2.386,P=0.019),見表1。
2.2 兩組患者MMAS-8評分比較
干預前,賦能組MMAS-8評分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533,P=0.128);干預后,兩組MMAS-8評分均高于干預前,且賦能組明顯高于對照組(t=2.778,P=0.007),見表2。
表1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HAMD評分比較(±s,分)

表1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HAMD評分比較(±s,分)
組別 干預前 干預后 t P賦能組(n=52) 25.75±4.56 16.15±2.78 12.962 <0.001對照組(n=52) 25.23±4.21 17.53±3.11 10.608 <0.001 t 0.604 2.386 P 0.547 0.019
表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MMAS-8評分比較(±s,分)

表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MMAS-8評分比較(±s,分)
組別 干預前 干預后 t P賦能組(n=52) 6.14±0.54 7.22±0.69 8.889 <0.001對照組(n=52) 6.31±0.59 6.86±0.63 4.595 <0.001 t 1.533 2.778 P 0.128 0.007
2.3 兩組患者GSES評分比較
干預前,賦能組GSES評分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743,P=0.459);干預后,兩組GSES評分均高于干預前,且賦能組明顯高于對照組(t=2.955,P=0.004),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GSES評分比較(±s,分)

表3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GSES評分比較(±s,分)
組別 干預前 干預后 t P賦能組(n=52) 12.44±2.22 22.54±2.69 20.882 <0.001對照組(n=52) 12.78±2.44 21.01±2.59 16.678 <0.001 t 0.743 2.955 P 0.459 0.004
3 討論
抑郁癥是精神科常見疾病,病程較長,容易復發,會給患者帶來持續性的痛苦及壓力,嚴重影響其正常生活[7]。臨床主要通過抗抑郁藥物治療抑郁癥,大多數患者通過合理服藥能夠有效控制病情發展及復發。當然,抑郁癥治療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部分患者無法按照醫囑堅持用藥,導致治療效果欠佳,容易出現病情反復的情況[8]。因此,在抑郁癥患者治療期間需要做好各項護理工作,特別要重視健康教育,讓患者能夠正視自身病情,主動配合治療,保證治療成效性[9]。
本研究中,賦能組采取了賦能教育,干預后賦能組MMAS-8評分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說明通過賦能教育能夠改善患者用藥依從性。賦能教育是一種新型教育模式,以賦能以及自我管理為中心,提倡通過激發學習者內源動力使其主動關注自我健康,以此來控制病情發展[10]。對于抑郁癥患者而言,在對其進行賦能教育過程中,通過開放式提問方式能夠讓患者充分意識到按醫囑堅持服藥的重要性以及隨意用藥的危害[11],讓患者自我表達服藥過程中存在的困難或問題,再對其進行引導,共同制訂改善目標以及計劃,讓其逐步達成目標,不斷提升用藥依從性。干預后,賦能組GSES評分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說明通過賦能教育能夠提升患者自我效能,與相關報道相似[12]。賦能教育實施過程中,責任護士與患者之間保持著一種平等合作的關系,這與常規教育模式大為不同[13]。如此一來,能夠將患者置于主導地位,責任護士主要對其進行引導,讓患者自己為自己賦能,引導患者思考,傾聽患者觀點,讓患者逐漸轉變錯誤認知,能夠認清自身問題并改進,增強其信心與主觀能動性[14]。干預后,賦能組HAMD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說明通過賦能教育能夠進一步改善患者抑郁癥狀,與相關報道相似[15]。經過一系列賦能教育后,能夠增強患者認知,使其正視自身病情,引導其通過自身努力解決問題。在責任護士協助下能夠讓患者收獲更多的成功體驗與信心,并給予其適當安慰、鼓勵、肯定,使其病情逐步改善,讓其能夠早日回歸社會[15]。
綜上所述,對男性抑郁癥患者采取賦能教育有利于緩解患者抑郁癥狀,改善其用藥依從性以及自我效能感,對于穩定患者病情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