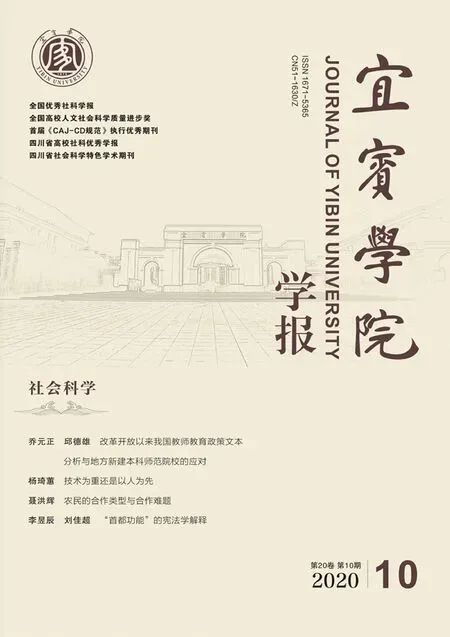論陶淵明《神釋》中的佛道思想
嚴予珩
(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 文學院,廣東 珠海 519087)
對于東晉詩人陶淵明的哲學傾向,古今學界一直有所爭議,有學者贊成陶淵明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同時也有觀點認為道、佛思想才是陶淵明生命哲學的主導。對于陶淵明的組詩《形影神》,清人馬墣曾評價說:“淵明一生之心寓于三詩之內,而迄莫有知之者,可嘆也!”[1]由此,《形影神》作為陶淵明“一生之心”的寄托,展示了詩人的創作思想與人生境界,同時也反映了其人生的矛盾。《神釋》作為該組詩中藝術性和思想性成就最高的一首,更是集中地體現了詩人的生命哲學——委運任化[2],而這樣的思想無疑在佛、道兩家思想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并且,無論是基于對詩人身處時代的社會狀況和主流思想的認知,還是出于對其自身經歷和作品風格的考察,佛、道思想對于陶淵明的人生和創作而言都是極為重要的。因此,筆者欲對《神釋》進行分析,以此探索其中對詩人產生深刻影響的佛、道思想。
在《形影神》中,“形”指生命肉體,詩人以其指代對長壽等肉體欲望的渴求。“影”則是比“形”高一級別的自我意識——與“形”是純粹追求物欲不同,“影”包含了對生命形態的思考,它認為肉體會消失,但行為造成的影響卻會永久留在世間[3],作者以此指代身后留名的愿望。而“神”否定了“影”對永恒名譽的追求,認為立善留名不過也是虛幻,因此它代表的是自我最高的理性,能消除一切悅生惡死,或憂生營生的觀念行為[4]。
該組詩共三首,其一名為《形贈影》,寫死亡難免,因而要及時行樂;其二曰《影答形》,寫既然今生有限,那便要立善留名于后人;而本文將要分析的乃是組詩的第三首,名為《神釋》,此詩旨在說明所謂的及時行樂和立善留名都不可取,相反,順隨自然、隨性隨遇方是人對生命真相有透徹領悟的體現。
一、 自然觀
魏晉是玄學盛行的時代,老莊思想及佛法成為士人們談論的話題,與此同時,魏晉的政治局面也日漸腐朽。身處如此環境的陶淵明在數次出仕入仕之后,其政治理想走向破滅,因而他最終選擇回歸自然和心靈,吸收道、佛思想,并逐漸建立起自己的自然觀。
(一)道生萬物
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
“三才”語出《周易·系辭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3]由此可知,“三才”便是指天、人、地。此處的“我”是神的自稱,且接下來的詩句皆是以神為第一人稱來進行敘述。該句在說,神認為因為有了自己的存在,人方能得以和天、地并稱。此處陶公借神之口,表明了自己對精神理性的看重。而詩人之所以賦予“神”如此高的地位,是因為神不同于形和影,它非名非利,亦沒有實體,但它所代表的理性世界和超越精神,即使在變幻不停的天地之間也不會消逝。因此,較之另外兩者而言,神更具真正意義上的超越意義和永恒性。
陶公之所以持有如此觀念,定然與受道家思想影響分不開。“道”乃是道家學說的核心與始源,它是一種自然規律,也是一種精神追求,它寓意著高尚的德性、人格的完滿以及靈魂的超越。從《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5]以及“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母”[5]中便可看出“道”的重要性乃至崇高性。詩中的“神”與此處的“道”大意是相同的,由此不難看出陶公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
(二)愛無偏私·等心眾生[6]
大鈞無私力。
“鈞”之本義是制作陶器所用的轉輪,此處的“大鈞”便借轉輪旋轉之意來指代運轉不停的天地自然。這一詞也曾出現在賈誼的《鵩鳥賦》和李白的《門有車馬客行》中,分別是“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和“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私”是個人的,“無私力”便是沒有個人的喜好意見。因此,上半句便是說天地自然對待萬物是沒有偏私的。從這般的平等大愛中,不難讀出道家的“愛無偏私”和佛家的“等心眾生”思想。
《道德經》第五章有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5]“芻狗”乃是古代祭祀時用草扎成的狗,這句話的意思是萬物在天地眼中沒有貴賤之分,天地也不會因為一己私欲和好惡而特別偏袒誰,對它們都是持一樣的態度。而在《維摩詰經》這樣一部以“度眾生”為重要法門的佛教經典中,亦有“等心眾生”的觀點,意在說明菩薩以平等之心對待眾生,不存在偏心偏私之說。
(三)自然無為
萬理自森著。
詩中的“萬理”便是萬事萬物,“自”是順其自然的意思,“森”乃繁盛之意,而“著”是謂立,這半句是在說任萬物因其自然、順勢而為,便能使其繁盛自立。此句的重點在于一個“自”字,“自”或許可以解釋為“自己”或“自由”,側重說明不受他者的干擾,亦不被外力所控制。但其實筆者以為,“自”最好的解釋是“自然”,此處的“自然”并非是通常生物意義上的自然,而是哲學語境中的自然,它指一種不施人力的、隨感所化的狀態。
道家思想以“道法自然”[5]著稱。《道德經》第二章有一言曰“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5]這便是說無需另施人為的力量,讓萬物自然地興起,若必須有所施行,也不要摻雜個人傾向。《莊子·養生主》亦有不少與詩句有相似含義的句段,“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6]。“緣”即是順著、沿著,它所表達的便是詩句中“自”的意思。而“督”指人的督脈經絡,是人生存之本,也就是說只要順應督脈經絡便能“森著”,即可以保身養生。
(四)萬物齊一·不二法門[6]
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
結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語。
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
第一句中的“君”是指形與影,第二句的“結托”意為交結依托,是共生共存的意思。通過以上二詞,再加上“相依附”一處,可以知道這兩句所表達的是神不以割裂的態度認識自己和形、影二者,認為它們之間是生來便相互依存、倚賴的關系。第三句中的“促齡”指壽命縮短,“具”在此處則是指酒。第四句中的“為汝譽”是稱贊你的意思。這兩句是神對形和影所說的話,它批判形影二者的主張和希冀是不切實際的。對于這兩句詩,筆者將從結構的層面去探討其中蘊含的道家思想。陶公意在批判,但他卻并未完全否定,反倒是先從正面去說形、影的主張具有合理性,承認它們的觀點也有可取之處的。繼而再將筆鋒一轉,從反面談其主張的不合理之處,從而在達到批判效果的同時,也展現自己的不對立的思想,即任何事情都有正反面兩面。陶公在此借神之語,闡發了取消差別、對立之心的思想,然而這一思想在道家和佛教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道家思想中,不對立、不區別通常被表述為“萬物齊一”[5],也就是萬物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看到“一”便會想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5],可知萬物皆始于“一”,因而縱使在形態等外表條件上有所差異,但其根本都是相通相同的。因此,就像神說的那樣,雖然自己和形、影是“異物”,但總歸都是生來便相互交結依附的。進一步說,神之所以能夠取消對立、區別之心,那是因為神做到了“無我”。在《莊子·養生主》中,南郭子綦便提出了“吾喪我”[7],“喪我”就是“無我”,指人沒有了成見、私欲和私利,因此便沒有了物我之別、是非之辯,實現了將萬物與自己等同的超越境界。
而在佛禪思想中,亦有“不二法門”[6]這一與詩句內涵相吻合的概念。“不二法門”是佛教用語,“法門”指途徑和方法,“二”意指一切差異和區別,因此“不二”便是無差別對立,即“空”。“不二法門”所象征的也是一種絕對平等,即不要在物我之間生起了差別之心,而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眾生。
二、 生命觀
在創作《形影神》之前,陶淵明就已經闡發過“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的想法,而《神釋》則是他關于生命觀進行哲學思考的成果[8]。在本詩中,他闡釋了對生命本體、榮譽名聲以及精神理性的看法,表達了任性自然的人生態度以及超然物外的生命觀念。
(一)死亡難免
三皇大圣人,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
“三皇”是指上古時期的三位帝王,分別是伏羲氏、神農氏和燧人氏。“彭祖”是古代傳說中的長壽者,據說他活了八百年之久,可仍嫌壽命不夠長,“愛永年”便是這個意思。“留”意為留在人世,指長生不死。而“復數”的意思則是再沒有別的命數了。這三句陶公是在敘述自己對死亡的認識,古代三皇如此賢能,但如今也不復存在,追求永年的彭祖最終也沒能如愿,可見人不論老少賢愚,皆有一死。
陶公對于死亡持自然順應的態度與道家思想不能分開。《道德經》第二十三章中有這樣一言,“飄風不終期,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5]《莊子·至樂》一篇中,莊子妻死,惠子問他為何要鼓盆而歌,莊子便說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7]。由此可見,陶公從中清晰地認識到有生就有死,生死都是自然的規律。從他的詩“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我們也能看出,他明白既然死亡必定是人的歸宿,那便將之視作一件平常的事情,從而也就能夠超然面對了。
(二)生死齊一·性無生死
甚念傷吾身,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委運”指將命運委托給自然,即順其自然的意思。“縱浪”意指自由自在,而“大化”指代宇宙天地。最后一句中的“無”通“毋”,意為不要。這是《神釋》一詩的最后三句,詩人表達了自己對生死問題的看破——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不論是思考及時行樂還是立善留名,最終都會因為多思而傷身,倒不如不再執著于此。正如詩人在《歸去來兮辭》中所寫的“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一般,順隨自然,以真正自由的態度地對待現世人生。此處是陶公對自己人生觀、生死觀的集中抒寫,是他寫作情緒的高潮,但也無疑是最能展現其內心寧靜平和之所在。
道家提倡“生死齊一”,莊子認為生死不過是“已化而生,又化而死”[7],實質上并無區別,同時他也提出了對“悅生惡死”的批判。而佛教禪宗則主張“性無生死”,“性”指佛心,也稱佛性或真如。當真如入定,便已然成佛,此時內心空靈明凈,如同一張白紙,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只余自身的完滿圓融,這便是“性無生死”。
“自然”是道家的“無”,是法家的“空”。陶公不再因生而喜、因死而懼,說明了他看破了生死問題,破除了自己對生死的所執與所迷。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中,將陶淵明對待生死的態度稱為“委運任化”[2],這可謂是“四字箴言”,將詩人思想中的“自然”體現得淋漓盡致。因為超脫了生死,詩人陶淵明實現了真正的自由,持心如一、平和寧靜。
(三)主神滅論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神滅論之爭是南北朝時期思想界的重要討論話題,屬于佛學范疇。主神滅論者認為人死后形神俱滅,而主神不滅者則主張人死后靈魂依然存在。
范縝是當時著名的主神滅論者,他曾說“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乎天理,各安其性”[9]。這與本詩中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旨趣頗為相近。且在最后一句中有“盡”一字,試問所“盡”者誰?神也。“盡”是完的意思,因而神盡即神滅。再者,陶公在《歸去來兮辭》中亦有“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出現一“盡”字,由此便不難看出陶淵明主神滅論的思想。
結語
陶淵明因其自身心性、經歷及所處時代的緣故,相較于儒家思想,他對道、佛思想的接受度顯然更高。這一點,在他的許多詩文中都有所體現,《神釋》只是其中的一首,因其中對道、佛思想的抒寫比較集中的緣故,故被筆者選作鑒賞的文本。
陶淵明選擇了內求,他通過佛、道思想回歸心靈,洞察了生命作為自然物的真相,那些在外部世界所受的挫折和困苦,此刻都在心中尋找到了安慰,他最終獲得了寧靜生命。但與此同時,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陶淵明不主名教僅限于不與政治勢力合作,卻不似阮籍之輩那般狂誕,他的自由與瀟灑更體現在他的平和心境中,一切都是自然而內斂的。
最后,筆者亦在思考:佛、道思想對于陶淵明而言是什么?“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說明佛、道思想正好符合他的本性,他們相遇和結合或許都屬于必然。此外,佛、道思想或許也意味著陶淵明的“不幸”——若官場得意、人生順遂,若不是在艱難的外部環境中步履蹣跚,恐陶公也難以選擇回歸心靈,選擇佛、道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歸依。不過,或許也是佛、道思想成就了陶淵明——若沒有內心的寧靜,何來“不愿為五斗米折腰”的錚錚傲骨,何來“自免去職”的勇毅果敢,何來“相見無雜言”的高雅志趣,又何來“心遠地自偏”的瀟灑超然?若沒有這些品質,便難以書寫那些傳世的優秀作品,難以創造出這一聞名古代文學史的隱士形象,也難以留給后代無數“不遇”“落魄”文人一個可以獲得安慰與寧靜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