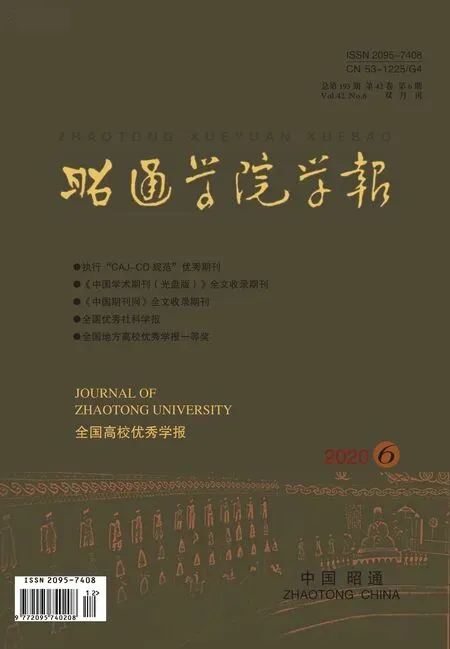抒情、唯美、現(xiàn)實及傳統(tǒng)
——對《數(shù)羊》的闡釋
朱 江
(鎮(zhèn)雄縣第一中學(xué),云南 鎮(zhèn)雄 657200)
《數(shù)羊》是尹馬最近出版的詩集,同時也是“東大陸青年詩叢”之一。尹馬是云南著名詩人之一,先后出版詩集有《尹馬詩選》《我的女媧》《群峰之上是夏天》(與人合著)等。本文以《數(shù)羊》起點,探討尹馬詩歌的某些特征。
抒情是尹馬詩歌文字呈現(xiàn)的一個核心,是其詩歌組織人、物及事的重要紐帶。以《大地》為例,“斧子追趕著森林,眾鳥放棄了人間/一根火柴喬裝打扮,碰了碰黑夜/村莊最干凈的部分哎喲一聲//我漆黑的內(nèi)心藏著一名刺客/想到花開兩朵,就想表一表生死/就把自己嚇了一跳”,詩歌開始寫“斧子”“眾鳥”“火柴”“村莊最干凈的部分”,短短三行詩,近乎宋詞意象的排列方式,將四個物象依次呈現(xiàn)。物象與物象的語義之間拉出距離,句子內(nèi)部語義相對獨立,相互依存,自身的詩意邏輯將物象整合成一個完整的畫面。而物象內(nèi)部,詩意又是密集的,“追趕著”“放棄”“喬裝打扮”及“哎喲一聲”使物象人格化,細(xì)節(jié),生動。尹馬像這樣的詩歌是很多的,如《大地真空曠》《關(guān)門》《天上謠》等,讀來句子內(nèi)部語義密集而詩歌整體節(jié)奏舒緩。
讀《大地》,還可以讀出淡淡的憂傷,斧子追趕森林,意味著砍伐,與森林一樣,這里都是泛指的,它們的方向指標(biāo)[1](波蘭羅曼·英加登的概念)是多元的。眾鳥放棄了人間,鳥為什么會放棄,結(jié)構(gòu)相似的第二種物象出現(xiàn),催化了詩歌的語義情緒,以此慣性一直往前走,等到詩歌結(jié)束,把自己嚇了一跳,作者最終要說出內(nèi)心隱含的憂傷。《天上,人間》這樣寫:“一直未離開過人間,我對冰冷的愛/司空見慣,如同點到田地里/那些擁抱著打盹的五谷/那些成群地搭乘雨水/吆喝著去秋天的云層;那些/死也不肯閉上嘴巴的,烏鴉”在三個“那些”的引領(lǐng)之下,物象纏綿。說其纏綿,是因為結(jié)構(gòu)類似的三個物象排比地陳列,這就相當(dāng)于語義不同的三個物象在一個旋律之下被反復(fù)吟唱。
《大雨》寫道:“一個人從鄉(xiāng)下趕回鄉(xiāng)下,找不到/一座破廟,想不起一扇虛掩的柴門/大雨傾盆,雨簾中有樹/他去雨中躲雨”,作者用了兩個否定句來描述鄉(xiāng)下,找不到一座破廟,想不起一扇虛掩的柴門,表面上是否定。事實上,這就是原初的鄉(xiāng)下,破廟及柴門是對鄉(xiāng)下的總結(jié)。而這種圖像與現(xiàn)實是有差異的,這個差異,本質(zhì)上講就是一種詩意。差異以物象的方式存在,我們隱約會感到一種文化向度,那就是中國古典文學(xué)。當(dāng)作者將諸如破廟、柴門之類的詞語融入一個近乎現(xiàn)代的現(xiàn)場,古典之美就重現(xiàn)光芒,詩歌圖景就變得十分唯美。敘事中動感的描寫,拯救了詩歌內(nèi)部節(jié)奏,敘事被切分開來,整個敘事階段性地變成各自的畫面及聲音,這樣的文字同樣是抒情的。
如果進(jìn)一步探討隱含在唯美物象背后的情感,可以用另一首詩來討論,《對面是彝良》第一節(jié)寫到“一朵云走得很急,打個呵欠/它就不見了;鋸樹的聲音很急/撒泡尿回來,就天不見了/不急的是一條小溪,它收留了/幾個恍惚的人,在溪邊洗臉、飲水說臟話”畫面是唯美的,是原生態(tài)的。人是自然的附屬物,人融入了自然。第三節(jié),詩歌回到有我狀態(tài),“我也想翻過這座山,到對面的彝良去/可以的話,帶幾節(jié)鮮筍,一壺泉聲/當(dāng)然,還有一支獵槍,一筒火藥/天黑之前,我要干掉那個偷食云朵的人”語言的局部,一壺泉聲,偷食云朵的人,這樣的句子極富表現(xiàn)力。幾節(jié)鮮筍,一壺泉聲,回歸自然情趣。再加上一只獵槍,一筒火藥,這種當(dāng)下生活格格不入的物象,與《大雨》中的“破廟”與“柴門”一樣,顯示了尹馬詩歌物象的懷舊情緒。為什么會懷舊?詩歌中,鋸樹的聲音很急,急什么,也許是偷盜者的急,也許是開發(fā)著的急,鋸或許是一種象征,它首先是一個物象,是一個過去時代和當(dāng)下都存在的物象,但是這里作為一個動詞,鋸演化成了一種暴力,是鋸樹,這就可以追究鋸樹背后的隱性因素,或者這就是鋸樹對整首詩的作用。樹的存在暗示的是一種原生態(tài)的東西,鋸樹意味著對原生態(tài)的一種肢解或破壞。
同樣,《屠魚記》中寫道:“買魚竿,魚鉤,買一頂斗笠/一件蓑衣”“在我之前,有人去集市上買了一筒火藥/一個膠桶,一把刀。在我之前/有人去山中鋸樹,拿走森林的墨跡/有人畫一所房子,在岸邊”“其實在我之前,有人在河上筑壩/放煙花,有人唱漁家傲/有人轉(zhuǎn)身拭淚,一條河早去了天上”文字寫到最后詩歌抵達(dá)高潮,一條河早去了天上,這里作者將語言做了陌生化處理,實際上說的是一條河流的消失,一條河流為什么會消失,因為有人在河上筑壩,這就是對現(xiàn)代文明的擔(dān)憂及反思。詩歌要寫的是屠魚記,實際上是以屠魚記為起點,最后抵達(dá)現(xiàn)代自然環(huán)境所遭遇的破壞。三節(jié)詩,三個畫面,構(gòu)成一幅壯麗的圖景,詩歌將生活中常見的諸如“魚竿”“魚鉤”“膠桶”“壩”之類的現(xiàn)實物象與“斗笠”“蓑衣”“筒”(這里的“筒”更多的左右了后面的詞語“火藥”)、“漁家傲”之類的“過去物象”精心組織成一幅唯美的畫面,以此來肢解其詩歌鋒芒畢露的一面,因為詩歌是用第一人稱寫出的,讀起來就像一個斗士戰(zhàn)斗結(jié)束之后的嗚咽,甚至更像一個人的囈語。
以此,也就不難理解像《運一堆石頭去鄉(xiāng)下》之類的詩歌,讀來觸目驚心,“從城里,運一堆石頭去鄉(xiāng)下/運一堆被切成塊面的石頭,倒影著云朵的/石頭,忘記了故鄉(xiāng)的石頭/去鄉(xiāng)下//從城里,把一堆石頭的骨灰/和它們穿錯的衣服,被刻畫成翡翠的/來世,運回鄉(xiāng)下/把一堆洗掉泥土的石頭/還給泥土;把一堆沒被燒制成水泥的/石頭,貼上水泥的標(biāo)號/縫補在另一堆石頭上”。在這些唯美的物象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些蘊含著“人”體性的物象,這些物象既不世俗,也不神圣。
明白了尹馬詩歌這些特征,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的很多詩歌,他的詩歌以一種唯美的方式來呈現(xiàn)這個世界。在《云南有牛羊,有花山》中他寫道“在花山,一只羊死去/另一只羊?qū)χ倚?空山就真的空了,白云/也真的遠(yuǎn)了。在塵土中斗地主的人/腰間掛著一個很重的相機/他們背不動浮云,和一捆柴”,如此大寫意的畫面,仿佛讀到唐詩。作者借助想象重造了一個現(xiàn)場。在尹馬的筆下,諸如《我們的牛羊》《春天里》《烏蒙》《走后河》《將進(jìn)酒》等,詩歌都通過唯美的畫面,寫出了詩人曾經(jīng)生活的大地,從某種程度上達(dá)成一種對過去時光的追憶。這些場景既是現(xiàn)實的,又是抽象的。
透過尹馬詩歌抒情唯美的表象,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現(xiàn)實生活的真相。《乙未詞》是一首很有現(xiàn)實感的詩歌,在密集的物象背后,詩歌史詩般地再現(xiàn)了鄉(xiāng)村的當(dāng)代存在,飽含著淡淡的憂傷。在尹馬看來,小路是“長滿荒草的”,這讓人想起“遠(yuǎn)芳侵古道”,這是道路在荒蕪,鄉(xiāng)村在衰敗的一種形象化的寫照,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到來,農(nóng)村人口的減少,鄉(xiāng)村發(fā)生了很多變化,土地“打烊”,環(huán)境遭遇了破壞,河流“蹲下身子”。隨著社會的進(jìn)化,交通在改變,馬匹“悄悄熄滅”,人際關(guān)系發(fā)生變化,妻子“躲著人群中”,訃告填滿了“土黃色的寫真紙”。讓人傷悲的是,母親“堆滿一生的疾病”,這還是我們生存的土地?作者用詩意的文字,直擊現(xiàn)實,語言靈動而有質(zhì)感。當(dāng)然,尹馬也有諸如《她撥弄著手機》《馬抖》《調(diào)音師》之類更是直接地關(guān)注現(xiàn)實的詩歌。
如尹馬在詩集的序言《自序:數(shù)羊我是認(rèn)真的》里所說:“很多時候,我總是慶幸自己生長于熱鬧的鄉(xiāng)下,在一個所謂文化沒有深淺、積淀沒有厚薄的地方,我看到的是使我無比沉迷的各式各樣的民俗禮節(jié)和能讓你笑出眼淚的一出出鬧劇,像‘過家家’一樣充滿泥土的味道,像‘?dāng)?shù)羊’一樣涂滿幻想色彩。……我曾有過這樣一個理想,就是站在這樣的一個戲臺上,面對那些我見過或沒見過的人,給他們講一些他們經(jīng)歷過且能聽懂的故事”[2]。詩人在這里所說的“講”的東西本身就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的,當(dāng)然,作為文學(xué),“講”也可以是虛化的。這就是文學(xué)的二維,文學(xué)是生活的,文學(xué)也是高于生活的。說文學(xué)是生活的,說的就是文學(xué)要關(guān)注現(xiàn)實;說文學(xué)是高于生活的,說的就是文學(xué)是對生活的再造。
尹馬的詩歌關(guān)注的所謂現(xiàn)實,就是關(guān)注他生活的這片土地,或者以此為契機,關(guān)注當(dāng)下社會。他的筆下,物象演化成了眾生百態(tài)或者當(dāng)代最為普遍的物、事,或許這是他寫作的方向或者思路。在《烏木鋪》中,他說“貴州的每一個村莊,都在暗示我/烏木鋪,奔跑著的樹不是樹,是風(fēng)/是留守孩子的患難同胞”。他的詩歌中同樣會將現(xiàn)代的物什融入到相應(yīng)的詩歌語境中。《飛翔》中,他寫道“往上是泥土,再往上,仍然是泥土/仿佛睡眠在生命空格鍵里的/泥土”“最終/帶著強大的動力,闖紅燈,緊急制動”,這里作者使用“空格鍵、闖紅燈”之類的現(xiàn)代生活中的物象,它意味著尹馬詩歌與當(dāng)代生活是協(xié)調(diào)的。又比如《鴿子花開》中有“開給一座森林的花,碰見鋼鐵,火/電商時代的利器;碰見一群/揮霍春天的人。那孤獨/堪比一座森林丟掉了自己的天空”,這里借助的是物,而不是人,但同樣是史詩般地記錄了當(dāng)代生活。
但是,這也意味著,我們要厘清詩歌現(xiàn)實的本質(zhì)。應(yīng)該說,詩歌的現(xiàn)實至少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真正”的現(xiàn)實,現(xiàn)實生活的現(xiàn)實,另一種是藝術(shù)的現(xiàn)實。許多人的詩歌是現(xiàn)實中的現(xiàn)實,是對生活的抄襲。而另一種現(xiàn)實,是對生活的歸納,是生活的本質(zhì)的再現(xiàn),是對生活的重造,它的現(xiàn)場是作者內(nèi)化之后的現(xiàn)場。很顯然,尹馬的詩歌屬于第二種。基于此,尹馬詩歌中除了《表妹》這樣的詩歌外,他更多的詩歌如《那些杉樹》《小憩》《她唱》及《苦難》等,現(xiàn)實生活經(jīng)過作者內(nèi)化,詩歌強調(diào)的不再是具體的物事,而是一些帶有普遍價值的東西。這與當(dāng)代的主旋律十分吻合,這也就不難看出,為什么我們在尹馬詩歌中讀到的很多東西都只是一種依附在美之上的淡淡的憂傷。
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理解像《烏蒙》這樣的詩歌,“蒼鷹隱在凡間,侍弄菊花,修破落的/莊園,在一面宣紙上嘲笑細(xì)碎的山河//當(dāng)然月亮,還從舊了的朝代過來/群山還在自己的腰間奔跑/當(dāng)然我貧窮的妹妹,還在月光下磨刀”,這里說的烏蒙只是詩人內(nèi)心的烏蒙,是一個想象中帶有時空的場景,正因為是大膽的想象,蒼鷹才會侍弄菊花,才會修補莊園,嘲笑山河,如此有氣勢,才會有破落的莊園,才會有細(xì)碎的山河,才會有貧窮的妹妹,這是詩歌借一種藝術(shù)的真實回到物象的本身,這些看似簡單的描寫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地域的精神,這或許就是尹馬唯美的場景背后所蘊含的凄美。
深究尹馬詩歌,不得不說到尹馬詩歌對傳統(tǒng)文化的挖掘,事實上,一個作者的根基總是建立在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之上,只不過有些是看得見的,被內(nèi)化了的,有些看不見的。這里從看得見的方面來說。
尹馬是一個很善于化用的詩人,《繞不開》中,詩人這么說,“但我始終繞不開/來自內(nèi)心的焦慮;繞不開/右眼皮的跳動,深夜趕回母親身邊”,這里寫到“右眼皮跳動”,諺語中有“左眼跳財,右眼跳巖”之說,說的就是一個人左眼跳要發(fā)財,右眼跳要折財。《山行》中,詩人寫道“走過一個馱馬的漢子/一個提鳥籠的窮人/一個賣春藥的光棍”其中“一個提鳥籠的窮人”就是化用諺語中的“叫花子玩鸚哥”,叫花子就是乞丐,鸚哥就是鸚鵡,是說有些人,沒有錢,不好好做事情,卻像公子哥兒一樣游玩戲耍。這些表面上很隨意的化用,實際上是對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挖掘運用。
另外,尹馬將民族意識融入自我的寫作經(jīng)驗。他有一首詩叫《散花令》,其中寫道“我手持冥紙散一曲/不說東長與西短,之說你愿意傻笑的那幾句/東躲西藏的河流,脫下單薄的外衣/想怎么干涸,由不得自己”。散花是祭儀中的一種禮俗,詩人在詩歌中,大膽的將這些帶有生活經(jīng)驗的東西寫入詩歌,舊瓶裝新酒,讓這些帶有民族意識的東西復(fù)活,詩歌借助這種形式,透露了一種憂患意識,讀來十分抒情。
居于此,當(dāng)我們讀到諸如《財門帖》之類的詩歌時,我們才會有所震撼。“主家財門四角方,沉香板子內(nèi)外裝”“一送當(dāng)年世歲好,二送鯉魚跳龍門”,讀者仿佛回到從前,作者借助生活經(jīng)驗及民族文化還原了某種生活場景,語言抒情,粗獷,原生態(tài)。《嫁女圖》,作者通過對嫁女中場面的描寫,原生態(tài)地保存了一種民俗。或許,正是這些即將要消失的東西,使文字成為一種追憶,從而文字也就帶有史詩的價值,它應(yīng)該是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地域的小歷史。這是對我們生存的一種原始的記憶,作者在盡力將其復(fù)活或者還原,這些東西就是作者過去的生活經(jīng)驗,是存活在記憶中的,是一個人的生命中的,同時經(jīng)過作者內(nèi)化之后,它又是不可復(fù)制的,是原生態(tài)。或許這就是尹馬詩歌的價值及意義。對傳統(tǒng)文化的關(guān)注,同樣是對我們生存的關(guān)注。
一個詩人應(yīng)當(dāng)將民族元素注入自我的寫作經(jīng)驗,這個十分重要,只有這樣,民族元素才會成為一種標(biāo)志,也只有這樣,寫作才會有原生態(tài)價值。只有這樣,寫作才是有根的。這讓人想起詩人希尼在談到他寫作《沼澤地》時說的一句話“需要把記憶與沼澤地和由于找不到合適的詞故不妨稱為我們的民族意識的東西銜接起來。”[3]當(dāng)一個作者擁有了民族意識,在作者的筆下,文字才有獨創(chuàng)的可能,因為,民族意識往往通過一代一代的作者讓文字多元。尹馬的詩中,有時也將帶有原生態(tài)的民俗經(jīng)文字處理成詩歌,這里說的處理,其實就是自我化的處理,他的詩中如《收腳印》、《趕信》等都是對民俗的某種抒寫。
注:文中所選詩歌來自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