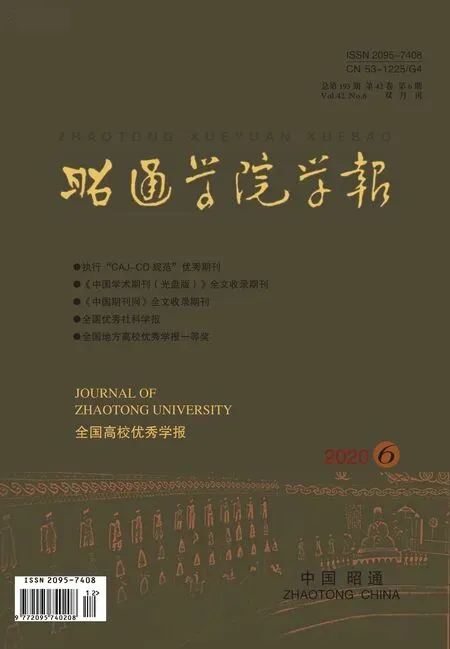母性、巫性、神性的共存與轉換
——論遲子建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劉秀哲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女性作為遲子建文學敘述的母題之一具有多重意蘊。作為女性,她們身上往往閃現著母性的光輝,從《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中的云娘,到《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中的妮浩,再到《群山之巔》中的安雪兒無不如此,她們用自己的溫情關注著世界、人生,將女性所特有的愛給予世間的眾生;同時,通過巫術來通曉世事、預知生死,給苦難者以指引,給奸佞者以懲戒;而這種母性與巫性的融合,又恰恰構成了她們身上神性的光環,使她們神秘卻不詭異,瑰異卻不邪魅。母性、巫性、神性的共存與轉換,使得遲子建筆下的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生命力。縱使她們的人生充滿坎坷,生命有所殘缺,但內心卻是豐盈和完整的。
一、母性——海納百川的包容者
“女性是以母性的特征出現在社會舞臺上的,她應該包含著母性特有的寬容、善良、隱忍、無私的性格特征。”[1]所以在遲子建的作品中,女性更多的指向了母性這一層面,她們接近神性卻又不同于神性,而是人性的獨特展現,是最靠近神性的人性。在遲子建作品中所展現的一系列女性,無不以母性的溫婉善良化解人生的困苦,以博愛無私撫平生活的創傷,以寬闊胸懷包容生命的虛無。縱使她們的人生依舊坎坷,但她們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精神的獨立與自由,而這種獨立與自由又恰恰來自母性醇厚的秉性、溫情與愛意。
“女人長期處于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絕大多數人的女性意識實際上處于一種嚴重扭曲的狀態......;在被迫與婦女傳統命運認同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生成按照男性中心的倫理規范看待外部世界和女性自身的眼光”。[2]遲子建通過自己的作品對這一長久的文化認同進行了改寫,她站在人性的高度對女性表達了由衷的歌頌與贊揚。在她的眼中,女性不再是男權社會下柔弱的附屬品,而是獨立的存在,是一個真正意義的“人”。同時,在女性身上所體現的母性已不是對自我及子女的愛,而是去愛世間的萬事萬物。《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為我們講述了社會底層人們的困苦與對美好生活的期許,而主人公云娘正是人們對美好生活期許的希望之光。她為了滿足一對老夫婦為兒子辦冥婚的心愿,用自己親人般愛犬的生命逼停了快車,撫慰了那對老夫婦內心喪子之痛的創傷。《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妮浩是一個幸福的母親,一生中有很多孩子,但當她知道如果去救別人的性命就會使失去自己孩子的性命,她依舊去拯救那些瀕臨死亡的人們,以致自己的孩子多半死于非命,但她并未因此而懊悔。《群山之巔》中如同精靈般的安雪兒被辛欣來強奸并懷有身孕,然而她并未因這個“不速之客”的到來而懊惱,她滿懷期待的迎接這個新生命的到來,認為這是上天賜個她的禮物。這些愛已遠遠超出作為一個母親對子女的愛,已經從母愛上升到了母性,是一種無出其右的大愛情懷。
自五四以來,中國文壇便極力為女性的獨立自主搖旗吶喊,但更多作者筆下的女性是以一種極端姿態與社會與命運抗爭,從曹禺筆下的繁漪到蘇童筆下的頌蓮,她們無不以一種畸形的方式對抗著壓抑她們的封建社會,正是這種畸形的抗爭使得她們作為女性的自我意識已經完全泯滅,只能使自己在命運的泥淖中苦苦掙扎,最終走向覆滅。正如德國女作家莫爾格納說:“只有學會或者重新學會女性的——這是人性的——自主,才能使這顆行星免遭無法居住的厄運。”[3]而遲子建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便學會了“人性的——自主”,從云娘到妮浩再到安雪兒,無論她們自己的命運多么坎坷,卻始終以母性的溫情來審視這個世界,點燃人生的希望之光,讓游走在這世間的人們不再感到生命中的荒寒。
遲子建小說的母性情懷與其他作家筆下的母性情懷既有共性又有獨特性,所表現的共性在于都以人道主義的情懷、悲天憫人的情感去描摹女性,展現她們的人生畫卷,其中既有詩意的生活也有命運的沉浮;而真正令我們震撼的則在于它的獨特性,她筆下的女性除了具有作為一個女性所特有的溫婉、知性、淳樸外,更具有母性的慈愛、溫厚與善良,她們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包容萬物,為人們尋求精神的皈依。這種近似于神性的人性,雖然時常以自我“犧牲”為前提,但卻蘊含著一種令人感動的力量。正所謂平凡成就偉大,正是對于她們人生的真實寫照,她們沒有顯赫的身份與地位,卻擁有著無限的母性情懷,這種母性情懷往往無需言說,卻已經滲透到了讀者的內心,這也是遲子建作品之所以打動讀者的原因之一。
二、巫性——博施濟眾的救贖者
“巫”古代稱能以舞降神的人,從字形上來講,“巫”上下兩橫代表天地,意指能夠溝通天地之人。“巫”作為一種職業自上古時期便存在。在傳統的認知中,“巫”一般與迷信、鬼神有關;同時,在西方神話中“巫”往往表情兇惡、相貌丑陋,她們詛咒、投毒、散播瘟疫,逐漸被妖魔化。而遲子建筆下的女性所展示出的“巫性”保留了傳統“巫”的職能,但不再邪惡,恰恰相反,她們是善的化身。她們在民族體系上大多屬于阿爾泰語系的通古斯滿語族,在宗教信仰上主要信奉薩滿教,將自然萬物奉為自己的信仰,“以神靈的方式融入信仰者的集體無意識,讓這種萬物合一的規律成為他們觀察和思考世界的心理范式。”[4]到現代薩滿教作為宗教它的功能已經式微,但作為一種習俗仍被廣泛的認同,特別在遲子建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它的足跡。
在遲子建的小說中,除了男性薩滿外,也塑造了眾多的女性薩滿形象,她們擁有神秘莫測的力量,也擁有著濟世情懷。在《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中遲子建塑造了一個年過八旬的老薩滿——云娘。她從父親手中繼承了裝神偶的鹿皮口袋,同時也繼承了父親的法力,她因親切善良而為眾人敬仰。云娘不僅能夠知曉世事、預見未來;而且還能夠做法救人、懲治奸邪。在作品中,云娘出現在順吉客棧,一邊喝酒一邊打盹,看似漫不經心卻對一切事情的前因后果都了如指掌,她準確預知到老齊沒給鐵軌敬煙、佛爺嶺老夫婦的到來、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嘎烏的死去......。她悲憫萬物、匡扶正義,大旱時她用木制的雷神與龍神為百姓祈雨消災;面對邪惡時她用卡穩神懲治壞人。她告誡人們萬物有靈,應常懷一顆敬畏之心。顯然,在整部小說中云娘扮演了一個救贖者的角色,她以自身的“巫性”治愈人們心中的傷痛;以博愛的母性掃除了人們心中的煩惱,讓生活不再苦澀與灰暗。
《額爾古納河右岸》描寫了東北邊陲鄂溫克人在現代浪潮席卷下生活所發生的滄桑巨變,小說對“巫文化”的敘述集中在了兩位薩滿身上——尼都薩滿和妮浩薩滿,但對于后者的“巫性”塑造顯然要比前者更飽滿,因為在妮浩身上除了“巫性”的神秘,還有母性的慈愛。從妮浩身上我們看到了塵世的感動與痛苦,作為部落中的薩滿,她肩負著拯救眾生的使命,而此時在她身上所體現的“巫性”便轉化成了具有極具包容性母性。作為一個母親,她比任何人都要熱愛自己的孩子,當自己的孩子連續離開這個世界,她無比的痛苦與悲傷,但由于自己的職責所在,她又不得不選擇舍子救人。縱使每一次的跳神活動都使她的內心無比的煎熬苦痛,都沒有動搖她對其他生命的救贖,最終只能選擇將避孕的麝香放在口袋中。這種母性與“巫性”的較量,讓我們看到作為一個薩滿的無私與偉大。
同樣在《群山之巔》中,安雪兒也充滿了“巫性”。雖然安雪兒并非像云娘與妮浩一樣是薩滿,但自幼便表現出異于常人的稟賦,她能夠通過望云預知生死,在石碑上刻上誰的名字誰就將死去,當這些在常人看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一一應驗后,人們便認為她身上附著鬼魅,所以對這位“小仙兒”充滿了敬畏。這種“巫性”隨著安雪兒被辛欣來強暴后而逐漸消失,此時“她從云端精靈,回歸滾滾紅塵”,[5]取而代之的是自身偉大母性的彰顯,當她生育毛邊后,便開始享受作為母親的幸福感與饜足感。雖然她有時候會對自己這種不可逆的轉變而沮喪,但她又認為有自己心愛的兒子陪在身邊便是最大的滿足,擁有他便擁有了大千世界。“巫性”的消失填補了母性的缺失,使她不在感到生命的空虛,也讓她的生命更有意義和價值。
在遲子建的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巫性”不是邪惡,而是正義與仁愛,體現在每一位女性身上則指向了對這個萬物有靈世界的救贖。她們用“巫性”來征服邪惡,還人們一份安寧;用母性來感化眾生,讓人們相信美好。縱使在保全自我與救贖他者上會體現出矛盾糾葛,但終將用他者戰勝自我,竭盡全力的去為他者奉獻自己的一切,留下自己默默地舔舐著“傷痕”。
同時,遲子建通過對“巫性”的塑造,也表達出對女性不幸命運的同情與感嘆;也傳達出對這以民俗文化即將消失的憂慮。
三、神性——懷瑾握瑜的指引者
神性是最高的人性,但在遲子建小說中,神性不僅作為最高的人性而存在,同時也是通過母性與“巫性”所彰顯的一種大愛精神。沈從文在《美與愛》中曾寫道:“一個人過于愛有生的一切時,必因此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必覺得那個光與色,形與線,即是代表一種最高的德性,使人樂于受它的統治,受它的處置。”[6]遲子建所塑造的神性便如沈從文所言,是與美最為接近的一種德性,是女性內心的純美與和仁慈顯現。她們用愛與善救贖他人,但又無法避免自身的的痛苦與無助。這種神性的展現引人深思、令人動容。
遲子建認為活生生的人不是被庸常生活所包圍的人,而是被“神靈之光”包圍的人,他們向往自然、貼近自然,散發出“神性之光”,而這種“神靈之光”便源于對真善美的追求,源于愛與被愛。在她的文學作品中一切生命都存在著神性,而對于神性的構建體現在女性身上便是大愛精神的呈現。無論是云娘、妮浩還是安雪兒,她們作為女性、作為母親,本身便散發著神性的光芒;而作為薩滿她們又是最接近“神靈”的人,所以她們憐愛萬物、悲憫眾生。在《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額爾古納河右岸》、《群山之巔》三部小說中,女性的神性擁有著與眾不同的品性,她們指引著眾生尋求生命的真諦,讓處于艱難險阻中的人們走向光明,讓命在旦夕中的人們走向重生。這恰恰與榮格的原型理論相吻合,“在榮格的原型理論中,‘女神原型意象’象征著智慧和引導,它是完備、崇高、真理的存在;是公正、智慧、仁慈的代表;是人類一直在追求,卻一直難以企及的境地;它能讓人類感知到自身的渺小、無知和脆弱,也能讓人類產生敬畏、崇拜和信仰。”這就使得她們所處的高度異于常人,她們是站在高于人的維度俯視眾生,并且能夠為眾生化解苦難,指點迷津,她們飽含屈辱的一生中經歷了無數坎坷,但無論如何被摧殘卻始終屹立不倒。
雖然遲子建筆下的女性大多來自偏遠的鄉村世界,但遼闊的黑土地造就了她們樂天達觀的性格,使他們早已擺脫了愚昧無知的狀態,她們以其善良、無私、博愛的胸懷成為神一樣的存在,從云娘到妮浩再到安雪兒她們無不以舍棄自我的“小愛”為前提去鑄就人間的“大愛”。云娘為了完成老夫婦為兒子辦冥婚的心愿,選擇犧牲陪伴自己一生的愛犬來逼停列車;妮浩為了挽救他人的性命,一次又一次舍棄自己孩子的性命;安雪兒為了不讓毛邊成為孤兒,甚至希望強暴自己的辛欣來不要落網。在別人看來她們是柔弱的女性,但在她們身上有血性、有豪情,人們將尊重與敬仰贈予她們,將神性賦予她們。她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走出生養她們的大山,無法被人們世代銘記,但她們卻給在困苦中踟躕前行的人們以指引,她們獨特的智慧與聰穎已遠遠超越了她們所處的環境。
總而言之,母性與“巫性”的交織鑄就了神性的光輝。同時,這種神性的光輝是未被現代文明所浸染的,保留了它最原始的狀態,那便是對精神家園的守望。無論是《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中云娘對萬物的憐憫,《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妮浩對萬物的體恤,還是《群山之巔》中安雪兒對萬物的哀矜,都因她們自身的神性而讓這個世間顯得詩意盎然。遲子建筆下的女性已是人神合一的超自然存在,對于她們神性的建構,一方面在于母性的博大,母性是每一位女性身上所顯示出的獨特存在,她們以母親般的溫柔滋潤萬物;另一方面在于“巫性”的靈異,她們以異于常人的巫術匡助苦難中的眾生,這種至臻至純的精神守護營造了遲子建筆下溫情真摯的世界;這種母性與“巫性”在遲子建筆下的自然流淌,帶給我們的是溫暖的感動與對待生命的從容。
四、結語
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大部分作者把目光投向了都市生活,而遲子建文學的敘事基點始終沒有游離東北這片廣袤的土地,沒有游離幽靜的村落、 壯麗的山河,這造就了她筆下的生命充滿了靈性。她通過對女性濃墨重彩的刻畫,將母性、巫性、神性置于同一敘事空間內進行切換與轉化,這種獨特的結構和存在方式無限延展文本自身的持久的美學張力。同時,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女性角色書寫,從縱向來看,她顯然對蕭紅的敘述有所繼承和超越,雖然二人對于女性的書寫都以東北大地上的人事為描寫對象,但遲子建筆下的女性比蕭紅筆下的女性具有更加獨立的人格;從橫向來看,遲子建對于女性的書寫比當代文壇上大多作家對于女性書寫更具有平等意識,她筆下的女性已不再是男權社會下的犧牲品,她們往往比男性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遲子建通過對母性、巫性與神性的描繪,展示了她對當代女性的尊崇與敬重,也展現出她不同于其他作家對女性人生觀、價值觀的思考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