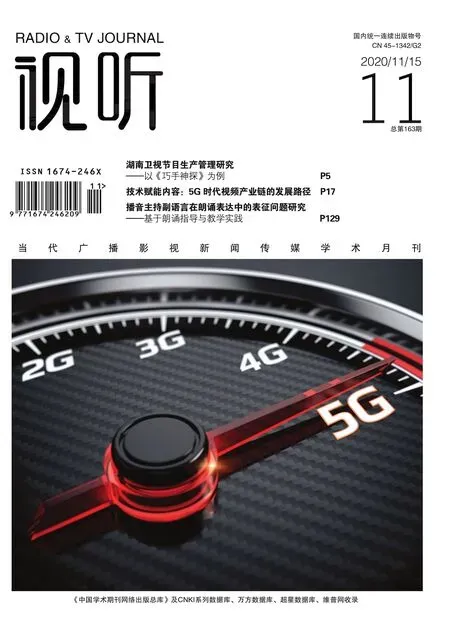身體表征與情感欲望
——《小城之春》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對比論析
□ 魏楠楠
《小城之春》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兩部電影都講述了戰爭之后丈夫身體或者精神上飽受折磨與創傷,此時的妻子都是盡力照顧丈夫、承擔責任、維系情感,然而兩個女性做出的選擇與取舍是大相徑庭的,選擇方式的差異與各自所處的文化土壤有內在的聯系。
一、忠誠克制的愛情規范者和突破禁欲主義的自由者
首先,從兩部電影的空間展示能夠看出截然不同的愛情觀念,在情感的表達上各有不同。《小城之春》這部電影從看到滿目瘡痍的城墻和斷壁殘垣的家園展開敘事,玉紋是不幸婚姻的犧牲品,飽受寂寞煎熬,在戰爭和疾病的雙重打擊下,夫妻感情名存實亡。玉紋只能任憑自己情感消逝在時間的洪流之中,她“發乎情止于禮”,在中國傳統的道德禮教規范下,個人情感壓抑,為家庭、責任、倫理而做出奉獻和犧牲。這部影片中有一個特殊的伴隨物——房子,人物有時候會更多地被放置在屋內的狹小空間之內,雖然影片中還有城墻之上,還有湖內泛舟場景等外部場景的展現,但是這個外部空間沒有使玉紋能夠游出小湖奔向外部。外部空間的展現都是玉紋和章志忱的在場,當他們兩個在一起時,運用景深鏡頭進行限定,他們兩個在外部場景時才能共享生命空間和體驗,而丈夫因身體原因卻并不具備。玉紋糾結于責任道德與情感表達的兩難之中,這部電影與其說是講述了三個人之間的情感糾葛,不如說是玉紋必然的選擇,與其說她心生情感漣漪,不如說是一種永遠的匱乏,一種能夠準確預測的結果,能夠看出玉紋是極其希望和渴望被救贖的,她在被動等待的同時猶豫惶惑終究錯失有可能奔向新生的機會。
其次,在西方電影中,女性對待愛情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康斯坦斯丈夫扭曲的心理壓抑埋沒了浪漫可愛的康斯坦斯。丈夫虛偽、變態,他是資本主義和戰爭異化的產物,他所關注的不是愛情的本質,他只渴望著享有貴族階級的統治權利和榮譽。為了維持名存實亡的婚姻,丈夫甚至允許康斯坦斯與其他男性發生關系,但他決不與妻子離婚,康斯坦斯被擠壓至只剩一副空殼。并不同于《小城之春》中“被封閉的現實空間”,康斯坦斯極度想要逃離室內,這種“外部環境”吸引誘惑著她。她對于一個強壯健康男人的小屋具有極大的欲望,這間接導致康斯坦斯與丈夫的決裂,她毅然決然地選擇一個極具有陽剛之氣的另外一個男性,對其身體特質抱有最大幻想,賦予她內心的強力支撐,強調個體的自由。影片中體現一種現代的女性意識,建構了現代化的女性個體的權力。“欲望取代靈魂,靈魂在肉體中沉睡,已然成了今日藝術所關注的救贖與解放的問題”,女主人公康斯坦斯與切爾斯靈與肉的結合,一發不可收拾。康斯坦斯毅然離婚,與情人離開,她放棄了雍容華貴卻壓抑沉重的上層生活,他們兩個人奔向自由和希望,兩個不同階層的人最終結合。康斯坦斯追隨內心真實本質的情感,反抗絕望的生存空間,在物質利益和資本異化、麻木之下,尋找遺失的自然屬性情感,以男女之情喚起人類原初的身體情感,以此來控訴社會現實。
二、欲望缺席的妥協性和個人主體的樂觀性
提到《小城之春》這部電影時,總會聚焦在影片禮法主題和影片的傳統美學上,影片關于情欲觀和身體的表達,似乎是可以闡釋的又一路徑。在中西方文化中,身體和情欲的話題往往容易被人們所遮蔽,但直到從尼采和福柯開始,身體成為哲學思考的一個嶄新維度。《小城之春》電影原名叫《浴火》,從這能夠看出對于情欲的表達,后來費穆導演給它一個中性的更加人文化的名字。現代女權主義者認為:“婦女的失去自我,首先從失去對自我身體的欲望的感覺開始,她們的覺醒,也就要從身體的覺醒開始。”志忱與玉紋兩人多次目光交匯,在封閉的空間對談偶爾有簡單的身體接觸,加之以玉紋內心的畫外音呈現,表征身體啟蒙的希望,使人感到她含蓄克制的同時又似乎感覺到強烈的內心波瀾。影片中出現了蘭花和月亮的意象,此刻人們都能夠看到玉紋的人性得到蘇醒釋放,看到玉紋試圖喚醒自己被道德和規范束縛的內心意識,但是終究遭遇了失敗和破滅。《小城之春》在封閉破敗的環境里淋漓盡致地呈現了身體的封閉與內向,是一種封閉性的更符合中國傳統的內斂的身體敘事。周玉紋和章志忱雙方難分難舍的微妙矛盾的心情展現得十分細膩,這種情感不逾矩、不熱烈。玉紋終究失去了自我,終究是封閉空間中呈現了身體的絕望與覆滅。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康斯坦斯偶然窺視到沐浴中的護林人切爾斯,對她來說更像是欲望表達的再次喚起。她意識到身體承載著愈發被壓抑和束縛的內心訴求,這預示著康斯坦斯長期壓抑的自我意識的復蘇,預示著她即將沖破軀殼追求自我。身體敘事理論認為,身體不再只是肉體和物質的指代,更加成為了構建社會關系和表達內心情感的重要因素。電影中有體現兩個人性愛的場景,有兩個人撫摸和裸體的呈現,心理都通過身體動作的表達賦予深層次的含義,在這種生命的真諦中,康斯坦斯體會到情感和身體的蛻變。
三、痛切的社會使命和生命自然屬性的意義
馬克思認為,人有兩個基本屬性,一為人的自然屬性,即人的各種生理欲望,包括生存欲望、性欲等;二為人的社會屬性,這是人的根本屬性,指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中,人的各種思想行為總是要受到各種社會關系的影響。在已建立起來的文明社會中,最終康斯坦斯放棄自己男爵夫人的頭銜,與切爾斯私奔;玉紋卻放棄了自己的愛情追求,回到丈夫禮言的身邊來滌清自己的良心與渾濁的內心世界。
首先,從《小城之春》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兩部作品中女性的經歷與走向,呈現出兩個人物不同的愛情抉擇,我們不難解讀出《小城之春》中“發乎情止于禮”的禮教規范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勇敢追求自然感情”的精神內核。《小城之春》拍攝于1948年,家國淪陷、精神創傷,知識分子有難以言喻的痛楚,中國人民身體陷入病態并且負載精神重荷。玉紋其實并沒有被施加社會和家庭的高壓,但是她還是做出了這個個人化的選擇,更能看出中國的儒家道德倫理的影響是無形的、滲透的。福柯認為,社會所有的歷史悲喜劇都是圍繞身體而展開的,身體被精心地規劃,是權力追逐的目標。權力在控制它,生產它,并且“歷史摧毀了身體”,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民族無意識的共性,中國全民族都是沉浸在這種傳統洞穴之中。這里既暗示著傳統文化及其勾連的“家國”共同體的沒落,又矛盾地表現出無力壓制的欲望的傳統倫理規范的掙脫。
其次,《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改編自勞倫斯的小說,創作背景是所生活的那個工業時代,人與自然日漸不和諧,大部分人都被冷漠的機器所控制和裹挾,存在嚴格的階級觀念思想,卻忽視了人最基本的本能需求,使人性漸遭扭曲。西方民族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剝奪了人情人性的欲望權力,兩個具有同樣內核的文本之所以表現出不同是因為社會文化土壤并不相同。西方文化會強調“人”的主體,張揚個性,肯定人的價值,生命終極意義在于對于自然本真的追求。通過對比論析,我們能夠看出兩個人物形象的不同,玉紋是內傾的、深刻的,是一種無法切身體驗的孤獨感,是中國傳統之中“認命”“無動于衷”的人。這種含蓄與內斂正契合了黃土地上的人們的沉思和厚重而并不輕易質疑和反叛。康斯坦斯是外向的,是勇敢的斗士,是反抗怯懦的,是竭力標新立異和積極探索的,暗合的是西方文化中“遵從本心”“沖破桎梏”的自由理念。
通過兩部電影的對比論析,電影中呈現的愛情觀、情欲觀、文化觀構成多重語境,側面折射出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差異,并且以全新維度審視中華民族復興語境中文化觀念的融合與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