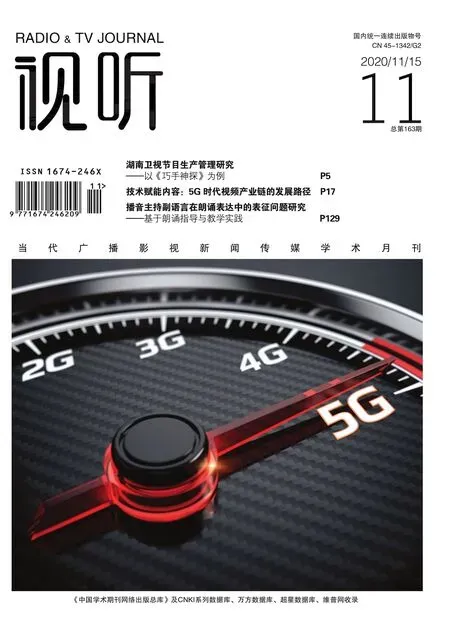流動的現(xiàn)代性視角下“三農”短視頻的鄉(xiāng)村傳播
□ 汪明偉
近年來,作為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一種創(chuàng)新內容展現(xiàn)形式和傳播方式,短視頻因其移動化、易創(chuàng)作、微記錄、可視化、輕傳播、社交化等特點得到蓬勃發(fā)展,其中“三農”短視頻就是不可忽略的一種類型。“三農”短視頻指自媒體人向社交平臺提供分享,取材于農村,反映農村生產、生活,播放時長在5分鐘之內的視頻。“三農”短視頻以真實、接地氣的風格成為鄉(xiāng)村傳播的“軟窗口”。
一、“三農”短視頻興起的背景
(一)政策扶持: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其內容包括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等新興手段推動農業(yè)信息化,提升農業(yè)品牌。“三農”短視頻正是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紅利之下把握互聯(lián)網(wǎng)與“三農”特點的產物。
(二)平臺引流,技術加持
一方面,由于農村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智能手機等新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的快速發(fā)展與普及,技術紅利使得農村與外界的交流溝通插上了翅膀。另一方面,各大平臺也相繼發(fā)力:今日頭條依靠技術優(yōu)勢開辟“三農”頻道作為扶持發(fā)展的內容領域,并在2017年推出“金稻穗計劃”,在激烈的短視頻市場競爭中另辟蹊徑,以差異化的傳播策劃脫穎而出;快手舉行幸福鄉(xiāng)村“家鄉(xiāng)好貨”公益直播,啟動幸福鄉(xiāng)村“5億流量”計劃、“鄉(xiāng)村帶頭人”計劃、“創(chuàng)業(yè)學院”計劃;梨視頻、西瓜視頻、火山小視頻等平臺也積極參與。技術與平臺為“三農”短視頻的孵化、專業(yè)化營造了良好的硬件條件。
(三)內容創(chuàng)作者下沉
截止到2020年3月,我國農村網(wǎng)民規(guī)模為2.55億,占整體網(wǎng)民的28.2%。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觸手可得性以及短視頻的低門檻極大地激發(fā)了三四線農民群體的創(chuàng)作熱情,大批農村青年參與到拍攝“三農”短視頻的隊伍中,通過網(wǎng)絡將自己拍攝的原汁原味的農村生活展示在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頭部“三農”短視頻博主有巧婦九妹、牛不啦妯娌、我是小熙、西北小強、農村四哥等。他們的視頻內容主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記錄鄉(xiāng)村日常生活和風俗人情,比如記錄當?shù)氐幕閱始奕ⅰM月酒、節(jié)日風俗等;第二類是記錄農耕農業(yè),展現(xiàn)勞作過程;第三類是記錄當?shù)剞r村的優(yōu)美風景和自然風光。對于“三農”短視頻博主而言,他們收獲了大批粉絲;在另一層面上,“三農”題材類短視頻也宣傳了農村、農業(yè)、農民的真實立體的形象。
二、“三農”短視頻興起的原因
從人口屬性的角度上來看,“三農”短視頻的受眾可劃分為四個群體:城市人、農村人、由農村遷徙到城市的人、由城市去往農村的人。筆者將從“三農”短視頻的受眾維度分析其興起的原因。
(一)視覺文化的嘗鮮與好奇
城市用戶由于長期居于城市,日常消費的短視頻內容大多為美食、美妝、旅游等“陽春白雪”。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過度美顏、追求拍攝技巧、給用戶營造出“不食人間煙火”的美好意境。長期浸淫在這類短視頻中,容易使用戶產生消費疲勞。而“三農”短視頻沒有任何濾鏡,構圖也非常簡單,這種粗糙的拍攝恰恰給予城市用戶一定的“治愈”功能。同時,這一群體缺乏對農村真實面貌的了解,“三農”短視頻作為展示農村文化的窗口,使得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深入了解到農村、農業(yè)、農民的狀態(tài)。今日頭條、西瓜視頻等線上公共空間將“三農”短視頻博主的私人生活領域搬到互聯(lián)網(wǎng),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消費空間”中的城市用戶群,是人的聚合而不是人的整合。平臺絕大多數(shù)的“公共話題”被降格為對“三農”短視頻博主的私人生活的好奇,城市人觀看視頻的最初意圖在于獵奇以及夾雜著對“底層文化”的審丑心理,而深入觀看后會逐漸放下最初的偏見。例如,有網(wǎng)友在博主“牛不啦”的“麻食菜餃子”短視頻中評論:“真是人生第一次見麻食餃子”“自從來看你們的視頻,看見你們這么搟皮,在家實驗了好幾回都學不會”“麻食,頭一次聽說,沒吃過”。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市與農村兩個群體的心理距離,有助于減少群際隔膜,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二)時空壓縮下的懷舊與記憶
鮑曼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中將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概括為“無固定形態(tài)的,流動的,液態(tài)的,運動著的”。流動的、不穩(wěn)定的時空關系造就了現(xiàn)代人獨特的生活節(jié)奏——匆忙。現(xiàn)代城市經歷著高速膨脹發(fā)展的時期,像裝上發(fā)條一樣,進城務工群體在高負荷的工作中已經變成了加速奔跑的機器。而現(xiàn)代性的核心特征就是不斷漂流,大量人群離開故鄉(xiāng),再也無法歸來。他們只能依賴于媒體、圖像和各種集體活動來存儲、再現(xiàn)集體記憶,觀看“三農”視頻就是其中一種方式。通過對一個理想化的過去和“歸家”感覺的懷念,懷舊模式深度嵌入我們的身份意識,使我們將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聯(lián)系起來,進而理解我們是誰,我們將到哪里去。在社會激變的時代,人們的位置感,以及對意義、歸屬和價值觀判斷的確定性是最脆弱的,而觀看“三農”視頻能夠幫助進城務工群體避免或轉移身份斷裂造成的情緒危機。例如,在“三農”短視頻博主牛不啦的作品中,有網(wǎng)友評論:“一直看你們的視頻,身在廈門,聽著熟悉的家鄉(xiāng)話,眼眶濕潤,想家了!”
(三)共同體的擴張與彌合
近年來,我國城鎮(zhèn)化率持續(xù)增長。2019年,我國城鎮(zhèn)常住人口8484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萬人;鄉(xiāng)村常住人口55162萬人,減少1239萬人。現(xiàn)代社會的急劇流動性一方面加劇了跨區(qū)域人口流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際心理距離的擴張。鮑曼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中引入了“衣帽間式的共同體”概念:人們通過相似的目標和方式,通過他們懷有的觀念和遵從的行為準則聯(lián)結在一起,構成了共同體。共同體鍛造出了團結一致的理念,它將潛在的差異和引起沖突的可能性抹除。在共同體中,人們可以避免互相敵視,和睦相處,它為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的當代社會創(chuàng)造了安全的避風港。以真實、真誠、原生態(tài)為特點的“三農”短視頻在居住在農村的人群和由城市遷移至農村的群體中充當著心理調味劑的角色。
三、“三農”短視頻的鄉(xiāng)村傳播特點
(一)內容傳播:“三農”形象再建構
“三農”短視頻分為美食、農耕、日常生活等幾類,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視頻內容多傳遞正能量。例如,“我是小熙”側重于拍攝農村美食題材,在4分鐘左右的視頻中將鮮為人知的農村美食烹飪方法悉心傳授;“牛不啦”側重于拍攝妯娌、婆媳之間的日常生活,展現(xiàn)了婆媳、妯娌之間的和諧溫馨;“農村會姐”以地道的方言、幽默的“臺詞”吸引了一大批忠實粉絲;“瑩瑩日記”以年輕化的剪輯風格宣傳節(jié)日風俗……透過“三農”短視頻博主的鏡頭,短視頻用戶認識到了一個全新的農村世界:它不再是“臟亂差”的代名詞,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地方。“三農”鏡頭展現(xiàn)了鄉(xiāng)風文明、農耕文明以及農民的精神風貌,作為拍攝背景的田園風光、湖光山色成為吸引用戶的另一大特色,打開了當?shù)氐闹龋瑤恿肃l(xiāng)村旅游。例如,在觀看了“鄉(xiāng)村小喬”的視頻后,來自城市的網(wǎng)友前往小喬的家鄉(xiāng)旅游散心,體驗“慢下來”的鄉(xiāng)村生活。“三農”短視頻的內容傳播打破了人們的刻板印象,傳遞了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等優(yōu)良傳統(tǒng)。
(二)觀看體制:影像符號“喚詢”看客
“三農”短視頻的標題通常帶有“農村”“婆媳”等字眼,每個標題的字數(shù)在15到20之間,采用了“5W”法,讓看客在最短時間內了解到視頻的大致內容。在視頻中,首先由主人公也就是博主本人用原汁原味的方言進行介紹,例如“牛不啦”的“大家好,這里是牛不啦”,“我是小熙”中的“大家好,我是小熙”,進而再由主人公簡潔說明本期視頻的主題。在濃濃的方言中,視頻觀看者逐漸被帶入由拍攝者構造的氛圍中,產生沉浸感。每個視頻的長度為3至4分鐘,迎合了看客碎片化的觀看習慣。標題、時長、內容拍攝模式一方面突出鄉(xiāng)村特點,另一方面很好地迎合了看客的觸屏習慣,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三農”短視頻的用戶黏性。
(三)流量變現(xiàn):平臺打造“三農”網(wǎng)紅
“三農”短視頻博主首先通過拍攝“三農”生活視頻賺得人氣和知名度,進而借助于今日頭條、西瓜視頻、快手等平臺宣傳售賣自家甚至是當?shù)氐霓r產品,將流量有效地轉化為購買力。當農民主播們向都市中見慣了燈紅酒綠的看官們提供一場愉悅的精神“農家樂”,平臺早已為看官們提供了便捷的剁手選擇,為農產品走出大山和農村獻上了完美攻略。例如,快手推出升級改版后的“快手小店”和全新的電商服務市場;西瓜視頻開設小店的同時貼心地為直播間貼上“邊看邊買”標簽,聯(lián)合中國網(wǎng)推出直播專題“鄉(xiāng)野生活”,邀請50位農村創(chuàng)作達人進行了長達6天的集體直播,為農貨山貨打開知名度。2018年,快手發(fā)起“快樂幸福鄉(xiāng)村帶頭人”計劃,為鄉(xiāng)村快手用戶提供商業(yè)、管理培訓,并且整合當?shù)氐奶厣放瀑Y源,打造短視頻網(wǎng)紅,通過“產業(yè)資源+品牌資源+網(wǎng)紅”相融合的方式,促進鄉(xiāng)村經濟發(fā)展。
四、結語
不同社會群體最開始觀看“三農”短視頻往往出于不同的需求:城市用戶群因為好奇,進城務工人員是為了懷舊……然而,隨著短視頻市場逐漸成熟,用戶對內容生產的專業(yè)度與垂直度需求不斷加深,優(yōu)質內容成為各平臺吸引用戶、沉淀流量的核心競爭力。當農村景致與文化自帶的濾鏡消失,表達方式的單一與生硬,固定的內容模式就成為農村網(wǎng)紅的致命弱點。龐大的農村集合想要走出局限的取景框架,農貨想要在農民和平臺攜手之下觸及更遙遠的大眾,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