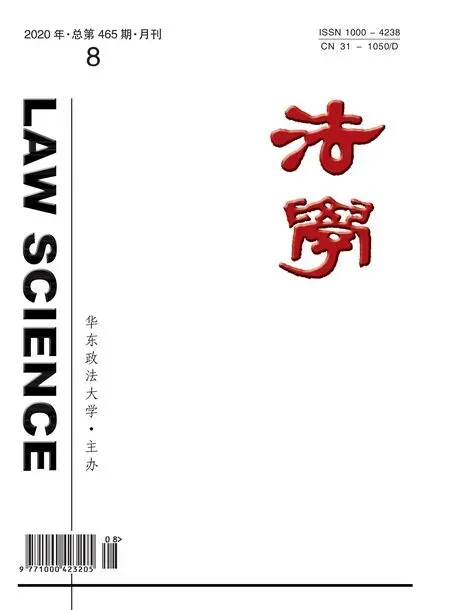單位行政違法雙罰制的規范建構
譚冰霖
進入工業社會以來,以企業法人為代表的單位組織盲目追逐經濟利益而罔顧社會福祉的活動,成為引發環境、健康、安全等公共風險的重要源頭。作為政府規制的重要工具,行政處罰亦圍繞單位行政違法行為(以下簡稱“單位違法”)編織了龐大而細密的法網。傳統上對單位違法的行政處罰主要針對單位本身,不涉及決定或實施違法行為的單位成員。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違法責任主體與行為主體分離,阻滯了行政處罰的威懾效果。對此,現代法律在處罰單位的基礎上,將負有責任的單位成員一并納入處罰范圍。這在理論上被稱為“雙罰制”。〔1〕參見劉曉軍:《一個單位犯罪、兩個犯罪構成——雙罰制理論依據新探》,載《政治與法律》2001 年第1 期,第29 頁;喻少如:《論單位違法責任的處罰模式及其〈行政處罰法〉的完善》,載《南京社會科學》2017 年第4 期,第89 頁。
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尚未對單位違法的處罰制度作出統一規定,〔2〕值得注意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2019 年10 月12 日印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見稿)第15 條曾規定對生態環境、食品藥品等領域的單位違法行為實行雙罰制;遺憾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 年7 月3 日正式向社會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修訂草案)》刪除了該條款。參見《行政處罰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載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flcaw/userIndex.html?lid=ff80808172b5f6e30173138b64742c98&from=timeline,2020 年7 月3 日訪問。但諸如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公共安全等一些特別法領域已經引入雙罰制來提升行政處罰的威懾力度。例如,2019 年10 月11 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引入“處罰到人”的立法思路,通過第75 條規定了附條件的雙罰制,強化了食品生產經營者的主體責任。2020 年4 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也突出強化了單位違法中有關成員的個人責任。〔3〕參見王瑋:《新固廢法新在哪里?》,載《中國環境報》2020 年5 月8 日。
面對單位違法雙罰制的豐富實踐,相較于刑法學對單位犯罪的系統研究,〔4〕代表性成果,參見何秉松:《人格化社會系統責任論——論法人刑事責任的理論基礎》,載《中國法學》1992 年第6 期,第70-72 頁;黎宏:《單位刑事責任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熊選國、牛克乾:《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結構——“新復合主體論”之提倡》,載《法學研究》 2003 年第4 期,第90-97 頁;蔣熙輝:《論公司犯罪的刑事責任構造》,載《中國法學》2005 年第2 期,第160-167 頁;葉良芳:《論單位犯罪的形態結構》,載《中國法學》2008 年第6 期,第92-105 頁。行政法學有關成果并不多見,既有研究雖不乏啟發,但尚未形成體系化的認識。〔5〕參見楊解君:《對法人行政違法的“兩罰”處罰》,載《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4 年第1 期,第38-43 頁;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88-97 頁。這間接導致立法和執法中出現困惑:(1)在立法政策層面,究竟應當對所有單位違法行為普遍適用雙罰制,還是僅對部分單位違法行為局部適用雙罰制?(2)在構成要件層面,單位違法過程涉及單位和成員兩個行為主體,雙罰制的成立是只需統一考察單位維度的構成要件,還是應當對單位和成員的構成要件分別判斷?二者的要件內容為何?(3)在法律責任層面,對單位以傳統財產罰為主的責任模式能否有效抑制單位再犯?對成員處罰的責任邊界何在?本文擬從規范角度對這些問題提出探討。
一、雙罰制立法政策之選擇
不同于“以處罰自然人個人為原則”的刑罰,〔6〕李惠宗:《行政罰法之理論與案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12-13 頁。規制各類市場主體在社會生活中“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所造成的社會負外部性,是現代公共行政的重要任務,故立法者理所當然地將單位和自然人一道作為行政處罰的固有責任主體。〔7〕《刑法》第30 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行政處罰法》第3 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并由行政機關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實施。”也就是說,對單位違法而言,在處罰單位這一固有責任主體的同時處罰成員,并非行政處罰法的邏輯必然,而是基于法律威懾的政策考量。對此,立法者擁有選擇余地。
(一)立法政策之分歧
基于這種邏輯,理論和實踐中對單位違法雙罰制形成了“普遍適用”和“局部適用”兩種不同的立法政策:
1.普遍適用模式,即除法律另有規定之外,凡是單位違法行為均實行雙罰制。例如,我國臺灣地區“行政罰法”第15 條規定,“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并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相似的立法例還有《德國違反秩序法》第30 條。
2.局部適用模式,即僅針對部分單位違法行為設定雙罰制;如法律無特別規定,其他一般性的單位違法行為仍以單罰制為原則。〔8〕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88-90 頁。例如,2017 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第17 條擬規定,“單位違反治安管理的,對單位及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法的規定處罰。本法沒有規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對同一行為規定給予單位處罰的,依照其規定處罰。”〔9〕《公安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的公告》,載北大法寶數據庫,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protocol&Gid=76821c2d3e94dd2a1f9529c77068d6bbbdfb,2020 年7 月1 日訪問。這實際上是肯定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之外實行單罰的立法政策。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的設定和處罰也采用此種模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30、31 條的規定,單位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才負刑事責任,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那么,在這兩種模式之間應當如何取舍?
(二)局部適用模式之提倡
從責任基礎和體系協調兩方面分析,筆者認為單位違法雙罰制的立法政策采局部適用模式更為妥當。
1.就責任基礎而言,隨著法人擬制說的式微和法人實在說得到普遍認可,單位已在行政法上被法律賦予完整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自然人并非單位違法中的必要責任主體。如果要突破法律的一般框架將自然人(單位成員)一并作為單位違法行為的責任主體,就需要更強的論證理由。在刑罰領域,立法者否定單位犯罪全面實行雙罰制的理由是:“由于單位犯罪的復雜性,其社會危害程度差別很大,一律適用雙罰制的原則,尚不能全面準確地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和對單位犯罪起到足以警戒的作用。”〔10〕胡康生、郎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36 頁。行政違法行為作為受到法律責難的行為,其本質也是具有相當社會危害性并破壞法秩序的行為,處罰設定之根本目的在于預防或制裁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11〕參見周海源:《危害性評價應納入行政處罰制度的基本范疇》,載《法學》2020 年第6 期。由此,就可罰性而言,實行雙罰制的正當理由應定位于法益侵害的嚴重性,亦即對于部分社會危害程度極高的單位違法行為,才有必要通過雙罰制強化威懾;否則,單獨處罰單位即可。治安管理處罰領域即是未實行雙罰制的一個典型。《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具有同質性,二者所規范的社會關系、行為性質存在一定重合。〔12〕例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 條規定:“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照本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在刑法理論上,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等行為也被視為典型的行政犯和違警罪。但為何《治安管理處罰法》未沿用《刑法》第31 條確立的雙罰原則,而是反其道對單位違法實行單罰制?理由或許在于:“與單位犯罪相比,單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所造成的后果較小,大多數甚至沒有實際危害后果,只是有發生危害后果的潛在危險性。”〔13〕王宏君:《論單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4 期,第50 頁。
2.從我國現行法律體系觀察,雙罰制目前主要存在于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公共安全、金融監管等部分立法領域,〔14〕如《水污染防治法》第92、94 條,《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108、118 條,《食品安全法》第123、135、139、141 條,《藥品管理法》第118、119、122、123、124、125、126、135、141 條,《反恐怖主義法》83~88 條,《消防法》第65、67、69 條,《網絡安全法》第61~69 條,《商業銀行法》第89 條,《證券法》第180~185 條,《反洗錢法》第32 條,《保險法》第84、87 條。“宏觀來看,我國大部分行政領域對單位違法仍然將單罰制作為基本的處罰方式,并未規定雙罰”。〔15〕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88 頁。相反的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對單位違法行為一般情況下只處罰單位。即便在同一部法律內部,也有不少立法對一些單位違法行為實行雙罰制,而對另一些單位違法行為實行單罰制。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第205 條對證券公司違法為客戶買賣證券提供融資融券的行為規定雙罰制,同法第210 條卻對證券公司違背客戶委托買賣證券、辦理交易事項的行為規定單罰制。這表明,我國實證法已在很大程度上采用局部適用的雙罰制模式。若在行政處罰中重構普遍適用的雙罰制模式,必將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僅將消耗巨量立法成本,還會損及法律秩序的穩定性。
二、雙罰制構成要件之解構
確定立法政策后,雙罰制適用的關鍵就在于構成要件的涵攝。但所謂“雙”罰,究竟是一個抑或兩個構成要件?其構成要件的規范構造又包括哪些內容?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理論和實務上都處于模糊或分歧的狀態,須基于單位違法的形態結構加以分析。
(一)雙罰制構成要件的規范模式辨析
單位違法涉及單位和成員兩個主體及其實施行為。在規范上如何評價這兩個主體和行為,形塑了單位違法雙罰制構成要件的規范模式。
1.在實證法上,我國對雙罰制構成要件的立法規定呈現兩種模式。(1)“重合模式”。即立法對單位和成員規定統一的行政法義務,二者應受處罰行為的成立共享一個構成要件。例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以下簡稱《藥品管理法》)第118 條的規定,生產、銷售假藥的,除依照該法第116 條處罰單位之外,還要對有關成員處沒收違法收入、罰款、終身禁止從業或行政拘留的處罰。在這個條款中,單位和成員應受處罰行為的構成要件完全一致,即“生產、銷售假藥”。諸如此類的立法例還包括《證券法》 第181~185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第83~84 條,等等。(2)“復合模式”。即立法對單位和成員規定的行政法義務不完全相同,二者應受處罰行為的成立要件僅部分重合,除符合單位違法的一般構成要件外,成員應受處罰行為的成立還須滿足其他附加要件。相較于重合模式,復合模式的立法例目前較少,代表之一如《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第75 條規定,對于單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有關成員“故意實施違法行為”“違法行為性質惡劣”或“違法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一并處以罰款。
2.雙罰制構成要件不同模式的背后,是對單位違法形態結構的認識分歧。(1)重合模式對應單位違法形態結構的“單一構造論”。持該論者主張,盡管單位違法表面上存在單位和自然人兩個應受行政處罰的主體,“但自然人成員所應負的行政違法責任的根據,仍是法人違法,而并非其自身獨立的違法行為,他們是作為法人的有機組成部分參與實施違法的”,〔16〕同前注〔5〕,楊解君文,第41 頁。即一個違法行為、兩個違法主體。還有學者走得更遠,認為“單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主體只能是單位本身,單位負責人或其他人員的行為是單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不應成為與單位并列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主體”。〔17〕同前注〔13〕,王宏君文,第48 頁。這實際上否定了單位成員的違法主體資格及法律責任能力。基于這種認識,立法不加區分地對單位違法中的單位和成員規定同一構成要件。(2)復合模式是單位違法“雙重構造論”的實踐映射。持該論者認為,單位違法的形態結構表現為兩個違法主體、兩個違法行為以及內容不同的主觀過錯。在構成論上,單位違法存在兩個構成要件,單位責任與成員責任應適當分離,彼此獨立,是否追究單位的責任并不影響對成員責任的追究,反之亦然。〔18〕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91、95 頁。
3.“單一構造論”為單位違法的處罰提供了一個簡明模型,具有減輕思維負擔的優勢,但其缺陷也顯而易見。(1)在功能層面,無論根據法人實在說還是法人擬制說,單位之權利享有與義務履行,必須由特定的機關來實現,而機關在實現單位目的時,仍要依賴于自然人,〔19〕參見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 頁。“自然人在法人的活動中仍處于主導地位”。〔20〕同前注〔4〕,黎宏書,第 215 頁。公司法學者也指出,“現代公司法理論的依據是把公司經營者視為公司所有者本人即股東的代理人的代理理論,在此背景下,如何監管、監督經營者這個公司治理問題成為公司法中的中心課題”。〔21〕[日]佐伯仁志:《制裁論》,丁勝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0 頁。從特別預防的角度,“單一構造論”忽略成員能動地位及其行為作用的主張失之片面,不利于威懾和抑制單位違法。(2)在規范層面,根據行政處罰法上的“自己行為責任主義”,相對人僅因自己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到處罰,法律不得規定相對人為他人的違法行為承擔行政責任。〔22〕參見陳清秀:《行政罰法》,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76 頁。“單一構造論”認為,成員在單位違法中僅作為單位的組成部分參與實施違法,不具有自身獨立的違法行為。在此情況下實行雙罰制,實際上是在否定成員違法主體資格的同時,又令其為單位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有違自己責任主義。而且,根據包容于單位的同一違法行為及構成要件,分別給予單位和成員兩次行政處罰,也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此外,“單一構造論”認為,成員與單位一道對單位違法行為承擔連帶責任的主張也存在邏輯矛盾。〔23〕同前注〔13〕,王宏君文,第51 頁。從法理上講,連帶責任具有給付的同一性、消滅的整體性、主體的多數性和平等性等本質屬性。一方面,給付的同一性和消滅的整體性固然契合單位作為不可分割整體之單一構造特質。但另一方面,單一構造論認為單位違法行為中只有一個違法主體即單位,成員僅作為單位之手足參與實施違法行為,這與連帶責任的主體多數性和平等性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4.相較之下,“雙重構造論”有助于避免“單一構造論”的缺陷,科學揭示單位違法的形態結構。首先,它客觀反映了成員在單位違法中的獨立地位和能動作用,有助于從源頭上預防和抑制單位違法。其次,它能夠有效克服單一構造論對自己責任主義及一事不再罰等行政處罰基本原則的違拗,從根本上解決成員“代人受過”和對一個違法行為兩次課罰的理論困境。
但應指出,雙重構造論關于“單位責任與成員責任彼此獨立”的主張不能成立。不難發現,此論源于單位犯罪研究中的“單位責任與單位成員責任分離論”,〔24〕同前注〔4〕,葉良芳文,第102 頁。二者內容幾乎如出一轍。但將之套用于單位違法中,則是一種誤區。在單位犯罪中,單位與成員的刑事責任分離的理論基礎是法人擬制說,自然人才是刑罰的固有責任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單位犯罪中的自然人當然能夠脫離單位獨立實施違法行為并承擔刑事責任。而行政法則恰好相反,除了傳統的治安管理違法等少數違法行為外,大部分單位違法行為必須由成員和單位結合完成。譬如,在排污、制藥、消防、證券、網絡等領域,〔25〕參見《大氣污染防治法》第19 條、《藥品管理法》第6 條、《消防產品監督管理規定》第9 條、《證券法》第119 條、《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4 條。從事相關經營必須以單位名義獲得行政許可或行政認可,因而這些領域的許多違法行為屬于純正的單位違法,成員的違法行為依附于單位,在法律行為意義上不可能以個人名義實施。正因如此,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以下簡稱《網絡安全法》)第61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以下簡稱《消防法》)第69 條、《證券法》第184 條等針對單位違法的雙罰制條款,均冠以“網絡運營者”“消防技術服務機構”“證券公司”等主體名稱,這表明很多時候追究成員責任須以單位責任的成立為前提。
綜上,單位違法的形態結構應為雙重構造。在單位違法的場合,雙罰制的成立包含單位和成員兩個層面的構成要件。其中,單位應受處罰行為的構成要件屬于一般要件,成員應受處罰行為的構成要件屬于特殊要件。并且,成員的違法行為依附于單位,對成員責任的追究以單位責任的成立為前提,成員應受處罰行為的構成要件是單位構成要件的邏輯延伸,其規范結構表現為“單位一般要件+成員特殊要件”的復合形態。
(二)單位維度構成要件的展開
由于我國現行《行政處罰法》對應受行政處罰行為的成立缺乏總則性界定,其構成要件體系主要借自刑法學。刑法學關于犯罪構成的主流學說主要包括二階層、三階層和四階層三種見解。〔26〕參見陳興良:《犯罪構成的體系性思考》,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 年第3 期,第53-60 頁。基于行政違法行為的特點,本文采二階層構成要件體系,即犯罪行為(actus reas)和犯罪意圖(mens rea),下稱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
1.客觀要件。在實證法上,單位應受處罰行為的客觀要件一般表現為違反法定的行政法義務,按照規制法學的一般理論,這些義務可提煉為3 類:(1)基于技術或措施的行政法義務,即規定單位應當采用或禁止采用的技術標準或行為措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大氣污染防治法》)第101 條禁止單位采用國家綜合性產業政策目錄中禁止的工藝。(2)基于績效或結果的行政法義務,即規定單位在末端必須達到的產出目標或不得超過的風險閾值。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法》)第124 條規定食品污染物質以及其他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含量不得超過食品安全標準的限量。(3)基于內部管理的行政法義務,即要求單位結合規制目標,制定適合自身的內部經營計劃、管理流程及決策規則等。如《藥品管理法》第126 條要求相關藥品單位遵守藥品生產、藥品經營、藥物非臨床研究、藥物臨床試驗等方面的內部質量管理規范。這些行政法義務大多屬于純正的單位行政義務,客觀上也只能以單位名義實施。
2.主觀要件。單位人格由法律賦予,并無生物意義上的思想。那么,在符合客觀要件的基礎上,單位應受處罰行為的成立是否還需要滿足主觀要件?組織社會學認為,現代社會中的單位已不是單純的資合或人合團體,而是具有獨立意志的“由職位(而不是由個人)組成的行動系統”,〔27〕參見[美]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0 年版,第492 頁。存在具有自身特點的管理制度和組織文化。日本刑法學者藤木英雄指出,單位自身具有犯罪(違法)能力,可以不用考慮單位代表人的主觀意思而直接獨立地把握單位的犯罪(違法)行為。〔28〕轉引自黎宏:《論單位犯罪的主觀要件》,載《法商研究》2001 年第4 期,第54 頁。由此,除了符合構成要件的該當性之外,單位應受處罰行為的成立也須考察單位的主觀狀態,這既是責任主義原則的規范誡命,也是清除組織違法土壤的功能訴求。目前,單位違法的行政法學研究鮮有論及單位應受處罰行為的主觀方面,顯然不夠全面。
參考刑法學的有關研究,美國學者布倫特.費希(Brent Fisse)曾對單位犯罪主觀要件提出開創性探討。他將單位犯罪的主觀要件提煉為4 種類型:(1)“管理性犯意”(Managerial Mens Rea),即把代表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的主觀狀態作為單位的犯意。(2)“復合性犯意”(Composite Mens Rea),即把相關單位成員所掌握的知識集中起來,組成一個復合的犯意結構。(3)“策略性犯意”(Strategic Mens Rea),即單位通過其明示或暗示的政策所表現出來的意圖。(4)“反應性犯意”(Reactive Mens Rea),即單位在犯罪行為發生后未能采取令人滿意的糾正或預防措施,以應對成員的犯罪行為。〔29〕See Brent Fisse, Reconstructing Corporate Criminal Law: Deterrence, Retribution, Fault, and Sanctions, 56 S. Cal. L. Rev. 1186-1204 (1983).此后的相關見解,多少都能歸入這四類。
費希的分類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重要價值,但在單位違法中能否以及如何轉換適用,尚須仔細辨析。其中,管理性犯意和復合性犯意其實都建立在已被摒棄的法人擬制說之上,其本質是將單位的主觀狀態訴諸成員意志,否定了單位的獨立法律人格,并非本來意義上的單位主觀過錯。而且,簡單地把部分特定成員的意志歸咎于單位,不考慮單位作為組織體為阻止行政違法作出的制度努力,也有失公允。相較而言,策略性犯意和反應性犯意將單位意志從成員的主觀狀態中剝離出來,從不同維度構建了單位的固有責任,值得提倡和借鑒。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缺陷,將之引入單位違法時須加以必要改造。
(1)策略性犯意基于“政策”判定單位主觀狀態的依據在于,“法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會通過一定方法,在制定正式規則的同時,還會用增加報酬、晉升職稱或官職等巧妙刺激自然人的目標”。〔30〕黎宏:《論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1 年第4 期,第68 頁。但其缺陷是,“要求控方在犯罪行為發生之時或之前證明公司存在犯罪性質的政策是極端困難的。幾乎沒有公司會付諸明確的政策來支持犯罪行為。”〔31〕同前注〔29〕,Brent Fisse 文,第1191 頁。在單位違法語境下,適用策略性犯意的修正方案是,不將其作為單位應受處罰行為的積極要件,而是將之作為單位反證自己沒有主觀過錯的消極要件:如果單位能夠證明其在違法行為發生前已制定政策明確禁止有關行為,那么單位成員違反政策所實施違法行為的,應視為成員個人行為,不以單位違法論處。這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第30 條第3 款關于過錯推定與允許反證的思路相契合。實踐中,單位犯罪領域已經出現運用策略性犯意的判例,可資行政處罰借鑒。例如,在“雀巢公司員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32〕參見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甘01 刑終89 號刑事裁定書。中,鑒于雀巢公司的政策指示、雀巢憲章及有關圖文指引證實,公司從不允許營養專員向醫務人員支付費用以獲取公民信息,法院認為涉案員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系“違反公司管理規定,為提升個人業績而實施的犯罪為個人行為”,其辯稱屬于單位犯罪的主張不能成立。
(2)反應性犯意認識到對社會有害行為的反應才是對單位加以責難的普遍基礎,其根據是單位從事了不正當的有害或危險的行為后,沒有以負責任的方式作出反應。〔33〕同前注〔29〕,Brent Fisse 文,第1197 頁。但其不足在于,“將行為發生之后的事情作為犯罪成立的要件放進責任之中進行考慮,的確叫人難以理解,因為它有違反英美法中傳統的‘犯罪的成立,以行為的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同時存在為必要’的基本原則之嫌”。〔34〕同前注〔28〕,黎宏文,第47 頁。從合規理念出發,單位的這種反應責任應主要定位于事前責任,而不是待違法行為發生之后再“亡羊補牢”。因此,反應性犯意作為單位應受處罰的主觀過錯,其內容應當修正為:單位盡管可以采取監督、糾正或預防自身及成員違法行為的合規措施,卻沒有采取而給社會造成危害的,在主觀上具有可責難性。以《網絡安全法》第47、68 條的解釋為例。該法第47 條規定網絡運營者發現違法信息后應當立即處置,第68 條規定對違反第47 條者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由此反推,如果網絡運營者已盡到信息管理的合理注意義務,仍未能發現并處置違法信息的,應視為不具有反應性犯意而免除或減輕處罰。至于此處信息管理義務的法律標準,可采用所謂“技術安全港”模式,即限于符合最佳可得標準的技術過濾措施(如關鍵詞過濾、基于統一資源定位符的過濾、基于智能內容分析的識別處理等),而非不計成本的全人工審查。〔35〕參見姚志偉:《技術性審查:網絡服務提供者公法審查義務困境之破解》,載《法商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37-38 頁。此外,在客觀構成要件方面違反技術措施義務或內部管理義務的單位,可直接推定為具有反應性犯意。因為適用法定的技術措施或內部管理制度,本身即是單位應當采取而未采取的反應方式。
(三)成員維度構成要件的展開
在單位違法的雙重構造下,成員應受處罰行為的構成要件既獨立于單位應受處罰行為的構成要件,又與單位行為具有密切的因果關系。這就是,有關單位成員明知自己的行為會使單位陷入違法境地,卻希望、追求或放任該結果的發生。〔36〕同前注〔1〕,劉曉軍文,第31-32 頁。在此,成員應受處罰行為的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呈現出一體兩面的對合關系,兩者相互依存、彼此映證:〔37〕雙層次的犯罪構成體系理論也認為,“犯罪是一個整體, 將犯罪分為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是一種理論上的需要。因而, 犯罪客觀要件與犯罪主觀要件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側面,是對犯罪進行分析的結果。”同前注〔26〕,陳興良文,第59-60 頁。(1)有關成員違法作出指令或參與形成違法決策,既是一種客觀的意思表示行為,也表明其具有違法的主觀故意;(2)有關成員事前疏于管理或事后整改不力,既是一種客觀的不作為行為,也表明其具有疏忽大意的主觀過錯;(3)在單位內部的科層制結構下,成員受單位本身或上級主管意志影響而被迫作出的違法行為,即便具有主觀故意或過失,亦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得以免責。
1.故意行為:意思決定違法。成員作出的違法意思決定,既是直接促成單位違法的客觀行為,也是體現其間接故意的主觀狀態。違法的意思決定大致包括兩種情形:(1)直接指令。單位內部享有命令權的高級管理人員,可以單方直接指示下屬員工執行相關業務操作。按照權責統一的理念,其應當對違法的指令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例如,1986 年原《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15 條曾規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違反治安管理的,處罰直接責任人員;單位主管人員指使的,同時處罰該主管人員。”(2)參與決議。決議行為是一個團體法概念,其根本特征在于采取多數決的意思表示形成機制,決議結果對單位及全體成員具有法律約束力。〔38〕參見王雷:《論民法中的決議行為從農民集體決議、業主管理規約到公司決議》,載《中外法學》2015 年第1 期,第79-81 頁。因此,如果決議行為導致單位違法,參與決議的部分單位成員就應該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但課責應受兩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決議中每位參與人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思單獨行使權利,故在違法決議中投反對票的成員,因不具有違法故意而無責任;另一方面,基于法不責眾的考慮,單位高級管理人員之外的決議參與者,無論投贊成或反對票,也可豁免責任,典型如股東會決議中非單位員工身份的小股東。
2. 過失行為:疏于監督管理。所謂疏于監督管理,是指負有監管職責的有關單位成員未妥善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而導致單位違法。疏于監督管理作為成員應受處罰行為構成要件的依據在于,其間接造成或放任單位違法行為的發生,正是成員主觀過失的客觀表現。
具體而言,監督管理不力包括兩種情形:(1)事前未盡審慎管理義務。例如,《德國違反秩序法》第 130(1)條規定:“作為經營場所的所有人,故意或過失不采取為在經營場所或企業中防止產生違背義務行為而必要的監督措施,并且此種監督義務是作為所有人應當履行的、倘若違背即應受到刑罰或罰款處罰的,則在應為之監督下本可防止的違背義務行為發生時,上述違背監督義務的行為即為違反秩序行為。任命、謹慎挑選監察監督人員也屬于必要的監督措施。”〔39〕《德國違反秩序法(續完)》,鄭沖譯,載《行政法學研究》1995 年第4 期,第91 頁。又如,根據《網絡安全法》第21、59 條的規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不履行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的,可處罰款。這里的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即屬法定的審慎管理標準。〔40〕參見《信息安全技術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2)事后整改不力。對于預防單位違法而言,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通過督促負責人采取避免再犯所必要的組織架構、管理制度、決策程序等,使其不再實施類似的違法行為。因此,如果有關負責成員在單位違法后未積極整改或采取必要的合規措施,則可能再次陷單位于違法境地,從而具有可罰性。
關于如何判定整改合規的妥適性,有學者建議采取二階推定:第一階段,處罰單位時并明確告知負責人要求其采取措施監督單位糾正違法行為;第二階段,若再次查獲單位違法時,其負責人應被視為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該當處罰。〔41〕同前注〔22〕,陳清秀書,第187 頁。這是一種比較公正且務實的思路,并與實證法規定有所契合。例如,《消防法》第65 條第2 款規定,使用不合格消防產品的,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5 千~5萬元罰款,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500~2000 元罰款。類似的立法例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94 條、《網絡安全法》第59 條等。
3. 合法抗辯:期待可能性。所謂期待可能性,是指即使認定行為人具有故意、過失的心理事實,也存在不能給予非難的情形。這是因為,法律規定責任后果,目的是使行為人對違法產生反對動機。雖然一般來說,具有故意、過失就應當或者能夠產生反對動機,但在諸如緊急避險等沒有行為選擇余地的特殊場合,反對動機的設定便失去意義,因為對沒有期待可能性的行為給予處罰,不可能收到預防的效果。〔42〕參見張明楷:《期待可能性理論的梳理》,載《法學研究》2009 年第1 期,第68-69 頁。對于單位而言,其本身就是形成意志并付諸執行的組織體,其在行為過程中可以自負其責地產生反對動機,因而考察期待可能性的意義不大。但是,對依附并服從單位的成員而言卻未必如此,其反對動機的形成可能受制于單位的組織體制,故在判斷其是否成立應受處罰行為時,應對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進行專門考察。
單位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意志的社會子系統,為了實現自身目標,會通過內部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及獎懲規則來影響單位成員的行動,強制或激勵其按照單位的意圖行事。〔43〕同前注〔28〕,黎宏文,第49 頁。基于此,單位成員在單位意志影響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即使造成單位違法并具有故意或過失的主觀狀態,也可能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產生責任阻卻。基于單位內部的科層結構,要對成員進行非難,一般要排除以下兩類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形:(1)單位制定的內部規則(如政策、規章等)違背法律禁止性規范,成員依照內部規則行事導致違法。但兩種情況除外,一是成員違反法律命令性規范不作為的,不得以內部規則未重申法律規定而主張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二是成員基于單位制定的績效獎勵、職位晉升方面的激勵性規則而實施違法行為的,非屬無期待可能性。這兩種情況下,成員完全存在守法的選擇余地。(2)因執行上級不合法的指令而導致違法。基于科層制的組織邏輯,可以借鑒《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60 條進行制度設計,即執行上級主管人員指令時,有關成員認為上級指令違法的,有權向上級提出改正或撤銷指令的意見,上級堅持不改變指令而要求執行導致單位違法的,可以認為該成員不具有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而免責。但是,執行重大且明顯之違法決定或命令的,不得以無期待可能性抗辯。
三、雙罰制法律責任之完善
基于單位違法的雙重構造和構成要件,單位和成員應當分別獨立承擔不同的處罰責任。但從立法現狀來看,目前單位違法中針對單位和成員的處責設置均存不足,亟需結合單位違法的行為特征加以完善。
(一)單位處罰責任的補強
綜觀實證法對單位違法的責任配置,對單位本身的處罰措施以罰款為主,并存在少量諸如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執照等資格罰。〔44〕典型的立法例,參見《水污染防治法》第92、94 條,《食品安全法》第123、135、138、139 條,《藥品管理法》第122-126 條,《反恐怖主義法》83-88 條,《消防法》第65、69 條,《網絡安全法》第61-69 條,《稅收征收管理法》第73 條,《證券法》第180-185 條,《保險法》第160 條以及我國臺灣地區“行政罰法”第15 條。盡管罰款具有易于掌握、責任明確的優點,但在單位違法情境下也存在固有缺陷:(1)威懾困境。罰款效果受到相對人財富的限制。就自然人違法而言,罰款的威懾性的財富瓶頸不會造成嚴重問題,因為法律仍可通過行政拘留乃至刑罰監禁的方式予以威懾補充。但對于沒有肉身且僅承擔有限責任的單位而言,如果罰款超過其資產閾值,就無法實現充足的威懾。〔45〕See Coffee, “No Soul to Damn: No Body to Kick”: An Unscandalized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Corporate Punishment, 79 MICH. L. REV. 390 (1981).(2)溢出效應。單位違法涉及相對復雜的社會關系,罰款的后果可能從兩個方向溢出單位自身界限而造成負外部性。一是,內部溢出,罰款造成的損失可以被單位內部轉嫁、消化,讓沒有實質參與違法的公司投資者、基層成員、單位股東等無辜主體為損失買單。二是,外部溢出,對單位處以巨額罰款可能導致員工失業、物價上漲、供應鏈障礙等社會后果,〔46〕同前注〔29〕,Brent Fisse 文,第1219-1220 頁。某些公共產品供應單位一旦因罰款而倒閉還可能造成關鍵物資的短缺。〔47〕例如,2018 年的疫苗事件中長春長生公司被罰款91 億而宣告破產,從公眾感情上看該企業固然罪有應得;但有關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稱,2019 年百白破疫苗、麻風疫苗等疫苗出現全國性缺貨也與長春長生停產有關。參見朱萍、陶凱倫、肖苗:《百白破等疫苗缺貨調查》,載《21 世紀經濟報道》2019 年7 月19 日。(3)價值虛化。單一的罰款容易被視為“企業違法行為的許可費用”,〔48〕See United States v. Wise, 370 U.S. 409 (1962).給單位造成只要繳納罰款就能違法的錯覺,甚至直接把罰款納入成本收益核算,從而無法體現行政處罰非難違法行為的倫理價值。
除上述外,罰款責任的根本缺陷在于對單位缺乏針對性,不完全符合組織抑制的理念。與自然人違法不同,單位是具有遠超自然人集合的影響力和復雜性的組織體,擁有一套在長期經營管理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及管理規則。這些因素是導致單位違法犯罪的重要內因。〔49〕同前注〔28〕,黎宏文,第68 頁。但罰款責任只能消極體現單位違法的法律后果,未針對單位內部操作規程或合規政策的缺陷,指引或敦促其采取改進措施,因而對單位違法的抑制機制并不明確。這樣一來,即便單位被處以罰款,但是導致單位違法的體制根源卻未革除。可見,單純依賴罰款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責任設計。正如日本刑法學者佐伯仁志所指出的,處罰單位的目的是“通過影響法人組織體的意思決定過程來抑制犯罪……處罰法人的依據不是個人抑制模式,而應該是組織抑制模式”。〔50〕同前注〔21〕,佐伯仁志書,第134 頁。由此,單位處罰責任的改進方向應當是遵循組織抑制的處罰思路,在罰款基礎上設置體系化的合規責任。
1.合規指令。所謂合規指令,是指責令單位建立并實行有效合規體系的處罰責任方式。其作為一種法律責任,源于單位犯罪的刑罰措施。較早在實證法層面將實行合規體系作為一種法律責任的是法國2016 年通過的薩賓第二法案,它將實施合規體系作為法定的刑事處罰,法人一旦被認定構成腐敗犯罪的,就必須在5 年內執行專門的反腐敗合規計劃。〔51〕參見陳瑞華:《合規視野下的企業刑事責任問題》,載《環球法律評論》2020 年第1 期,第30 頁。刑法畢竟只是法律規制的最后手段,在行政執法中及早介入單位的組織管理,責令其根據自身實際和違法漏洞建立合規體系,契合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應成為單位行政處罰責任的重要內容和發展方向。這具體包括合規體系的制定和執行兩個方面。
合規體系又稱合規計劃,“是指企業或者其他組織體在法定框架內,結合組織體自身的組織文化、組織性質以及組織規模等特殊因素,設立一套違法及犯罪行為的預防、發現及報告機制”。〔52〕李本燦:《企業犯罪預防中合規計劃制度的借鑒》,載《中國法學》2015 年第5 期,第177 頁。在規則制定層面,合規體系可作廣義和狹義之分:(1)廣義的合規標準泛指以一般性違法預防為目的,不針對特定組織、特定領域或特定目標的合規體系。廣義的合規體系幾乎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合規場合,對合規管理不提出具體要求,只提供建立合規管理體系的基本環節和建議做法。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制定的《合規管理體系指南》(GB/T 35770-2017)、國資委頒布的《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和國家發改委等七部委聯合發布的《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就是廣義合規體系的典型。一般而言,廣義合規體系應涵蓋“策劃”“支持”“運行”“績效評價”“改進”等基本要素。(2)狹義的合規標準特指行政法上內部管理型規制(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的要求,系針對特定領域的行政目標和預防違法要求,按照法定的框架、要素或技術標準制定的合規體系。〔53〕參見譚冰霖:《論政府對企業的內部管理型規制》,載《法學家》2019 年第6 期,第75 頁。比較典型的如歐盟理事會第1836/93 號條例規定的“生態管理與審核體系”(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我國《食品安全法》第48 條規定的食品安全“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體系”、《網絡安全法》第21 條規定的“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等等。單位在制定合規體系時,既可遵循廣義的合規標準,也可采取狹義的合規標準;但若該領域已有法定的狹義合規標準,則合規體系必須將之納入。
在規則執行層面,欲使合規體系真正內化為單位經營管理機制的一部分,還須課予單位相應的組織保障義務,通過建立或改組專門的合規機構,保障合規體系的有效實施。組織保障義務的建制形式復雜多樣,就廣義的合規標準而言,實踐中已涌現出合規管理委員會、首席合規官、合規部、合規專員等四大機構。〔54〕參見陳瑞華:《企業合規的基本問題》,載《中國法律評論》2020 年第1 期,第184 頁。就狹義的合規標準而言,立法一般會要求單位設置特定業務領域的內部管理專員負責合規體系的實施,如《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第37 條規定的“數據保護官”、我國《網絡安全法》第21 條規定的“網絡安全負責人”等。一般情況下,單位對組織保障義務的履行方式擁有自主決定權,合規機構由單位自行設置,合規人員屬于單位內部雇員。但在單位違法情節嚴重,且行政機關認為單位無力實施良好合規體系的情況下,法律可以授權行政機關直接介入單位內部的組織事務。
當然,基于“人身罰”“財產罰”“行為罰”“警示罰”“榮譽罰”的傳統分類,以及行政處罰通常的制裁性標準,合規指令能否作為行政處罰可能引發爭議。對此可簡要回應如下:首先,就實質而言,面對迅速變遷的現代社會環境,試圖在總則中以完全閉合的類型體系,涵蓋各個規制領域的處罰措施創新,無異于“刻舟求劍”。事實上,“草案”第9 條擬增設的“責令停止行為”“責令作出行為”等處罰種類,就已經超出五分法的涵攝范圍。就形式而言,《行政處罰法》第8 條的兜底規定也已經授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種類。其次,盡管經濟利益是單位(主要是企業法人)追逐的重要價值,但并非唯一價值。組織學和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管理自主權對組織體而言是一種重要的非經濟利益,有時甚至比經濟利益更重要。〔55〕See Robert Aaron Gordon, Business Leadership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45, p.305;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NewIndustrial State,Houghton Miラin Company, 1967, p.77.因此,旨在干預單位內部管理的合規指令是一種具有明顯制裁特征的處罰責任,而不同于一般的責令改正措施。
最后,鑒于合規指令對行政機關和單位而言都有不菲的執行成本,其適用至少應滿足以下條件之一:(1)累犯,反映出單位內部存在違法漏洞或具有再犯的主觀故意;(2)違法行為涉及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生產、衛生防疫等重大公共利益的領域,需要透過合規體系力避再犯;(3)行政機關有證據表明單位的內部管理環節存在明顯違法隱患。
2. 合規激勵。除了把合規指令直接作為一種處罰責任方式外,還可將合規作為一種行政處罰的激勵機制,進一步強化單位推行合規管理的內生動力。這具體包括兩種情形:(1)單位違法時已經建立必要的合規體系的,可以作為免于或減輕/從輕處罰的裁量情節。例如,美國1995 年制定的《自我管理激勵政策:發現、披露、糾正和防止違法行為》規定,如果企業建立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環境管理制度,并在60 日內主動發現、披露和糾正違法行為,環保署將對其免除“基于違法嚴重性的處罰”(gravity-based penalties)或減少該類處罰數額的75%。〔56〕See Incentives for Self-Policing: Discovery, Disclosure, Correction and Prevention of Violations, in Federal Register / Vol. 60, No. 246 / Friday, December 22, 1995 / Notices, pp.66710-66712.《美國聯邦量刑指南》的“組織量刑指南”章節也把有效合規體系的建設作為減輕刑罰的重要情節,減輕幅度最高可達95%。〔57〕See U.S. Sentencing Guideline Manual,§8C2.6.(2015).之所以將具備合規體系作為免除或減輕單位處罰責任的依據,是因其是單位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的一種標識,而是否盡到注意義務是區分違法以及責任大小的重要標準。〔58〕同前注〔52〕,李本燦文,第194 頁。(2)單位違法時未建立合規體系或合規體系存在重大漏洞的,若單位承諾在一定期限內建立有效的合規體系,也可作為減輕/從輕處罰的裁量情節;但行政機關須對其進行跟蹤監控,若期限屆滿單位仍未建立有效合規體系的,可加重處罰。這不僅與當下事中事后監管改革的精神暗合,〔59〕參見盧超:《事中事后監管改革:理論、實踐及反思》,載《中外法學》2020 年第3 期,第783-800 頁。而且實踐中也不乏先例。例如,在震驚證券界的“司度案”〔60〕參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2020〕1 號,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20_370183.htm, 2020 年3 月15 日訪問。中,由于事實不能完全查清而以行政和解結案,涉事企業承諾采取“必要措施加強公司的內控管理”,中國證監會則依據《行政和解試點實施辦法》將原擬作出的40 多億元罰款替代為6.7 億元的行政和解金。〔61〕本案雖以行政和解的方式結案,但企業繳納的和解金大大低于擬處的罰款數額,因而與減輕處罰具有一定的同構性,具有參照意義。從法理上講,基于單位的合規承諾,并通過在考驗期內實施的合規報告和合規監督機制,彌補了單位違法的管理漏洞和組織缺陷,已足以部分實現行政處罰的威懾和矯正目的,從而使單位的可罰性降低。
(二)成員處罰責任的改進
在成員層面,目前雙罰制的責任范圍并不清晰,相關責任的配置也欠科學,需要進一步改進。
1.責任范圍的限縮。基于法不責眾和責任主義的考慮,單位違法中對成員的處罰必須嚴格限定范圍,并非所有單位成員都要與單位“連坐”擔責。因此,除了符合單位違法中成員應受處罰的一般構成要件外,處罰政策上還應從身份層面對應受處罰的成員范圍予以限縮,以免牽連過廣。但何為相關責任人員,仍待從立法論和解釋論上廓清。
在立法論層面,對應受處罰成員的限縮范圍有兩種觀點:(1)將應受處罰成員的范圍限縮為單位的“代表權人”——依公司法、社會組織法等社團法律規范可以代表單位意思和行為的成員,不具有代表權的參與或實施單位違法行為的其他成員被一律排除在外。〔62〕參見陳敏:《行政法總論》(第8 版),新學林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版,第747 頁。我國臺灣地區“行政罰法”第15條的規定就是典型之一,該條將單位違法一并處罰的成員范圍嚴格限定為“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2)在代表權人的基礎上,將應受處罰成員的范圍擴展至在單位業務上負有重要職權的其他責任人員。我國目前關于單位違法的責任規定基本循此思路,《治安管理處罰法》《證券法》《食品安全法》《網絡安全法》等單行法幾乎均將單位違法中應受處罰的成員身份界定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從脈絡上考察,僅處罰代表權人的做法是以對外交易關系為前提的民法觀念為基礎,并未完全體現行政處罰的制度邏輯。在現代單位業務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諸如職能機構主管、業務總監等中層管理人員被授予大幅度的裁量權,代表權人很多時候只是確定基本的方針,并不直接指揮和監督具體的業務。〔63〕同前注〔21〕,佐伯仁志書,第131 頁。因此,從責任主義和特別威懾的角度,立法應當與時俱進地采取第二種觀點,同時追究代表權人和其他責任人員的處罰責任。
在解釋論層面,主要任務是闡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規范內涵,防止行政裁量權濫用導致處罰范圍不當擴張。具體而言:(1)關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認定,理論和實務上爭議不大,基本都將其限定為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在“羅大紅、中山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案行政處罰案”〔64〕參見廣東省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20 行終162 號行政判決書。、“許金福與福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行政處罰案”〔65〕參見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閩01 行終465 號行政判決書。、“楊雄勝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處罰案”〔66〕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1 行初887 號行政判決書。等案件中,法院均認可這一規則。(2)關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刑法學者一般將其界定為奉上級指令具體實施或參與違法行為的單位雇員。〔67〕參見黎宏:《論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載《法學評論》2000 年第4 期,第69 頁。筆者認為這種認定過于寬泛,因為奉命行事的一般雇員實際上僅為單位之手足,其行為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思決定,雖然其對于單位的違法結果有所預見,卻并無防止違法行為的權限和能力,故即便其滿足違法構成要件,也不應成為行政處罰法的評價對象。從責任主義和比例原則的角度,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當定位于單位內部具有決策權或業務領導權的中高層成員,并采取嚴格的職責標準限制其范圍。我國目前的執法和司法實踐也基本持此立場。例如,在“張凌興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處罰案”〔68〕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1 行初1372 號行政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屬于違法行為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邯鄲市公安局峰峰礦區分局〔2015〕0104 號行政處罰決定書中,行政機關查明違法企業地面除塵站存在夜間不正常運行的情況,并認為地面除塵站主任劉某屬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此外,當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范圍涉及多人時,應當秉持個人的可歸責性原則,處罰對象的認定應以單位內部的業務分配或表決意見為準,不得以共同經營或集體決策為由隨意擴大處罰范圍。
2.責任設置的優化。梳理實證法對單位違法中成員處罰責任的規定,主要包括罰款、限制或禁止從業、行政拘留。其中,罰款責任和限制或禁止從業的責任尚有較大優化空間。
(1)關于罰款責任。從立法實踐看,單位違法中成員罰款責任的設置存在立法模式和設定標準的分歧,且未將成員的主觀狀態納入考量,需要在澄清分歧的基礎上予以完善。
第一,從立法模式上看,相對于單位的罰款責任,對成員罰款責任的規定應采取一體模式還是區分模式?所謂統一模式,即對單位和成員設置同等數額的罰款。我國臺灣地區“行政罰法”即采此種模式,該法第15 條規定,“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應并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所謂區分模式,即對單位和個人分別設置不同數額的罰款,對成員設置的罰款數額一般低于單位。如《證券法》第197 條規定,信息披露義務人未依法披露信息的,處50 萬~500 萬元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并處以20 萬~200 萬元的罰款。
相比之下,區分模式更為可取。有刑法學者論及單位犯罪的罰金時主張采取一體模式,核心理由是“不管是單位還是自然人,在實施相同犯罪行為時,對法益的侵犯程度是相同的”。〔69〕張明楷:《犯罪論體系的思考》,載《政法論壇》2003 年第6 期,第30 頁。但法益侵害性只是決定行為可罰性的一個因素,成員和單位可罰性的區分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首先,單位違法的形態結構是一種單位和成員行為相對分離的雙重構造,對二者一并規定法律責任或設置相同的法律責任,在形式上并不妥當。其次,單位違法中雖然存在單位和成員兩個違法行為,但成員行為對單位行為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且不同于刑罰的是,單位本身即是違法行為的固有責任主體。故從可歸責性上講,對單位的罰款應當適度重于成員。最后,較單位而言,成員的法律身份只是單位內部工資再分配的受雇主體,并非單位違法的直接獲益者,且成員財產較單位也相對有限。就此而言,對成員的罰款責任設置也應低于單位。
第二,從設定方式上看,成員罰款責任的數額設定存在數值和倍率兩種方式的分歧。前者如《網絡安全法》第59 條規定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5 千~5 萬元罰款,類似規定還有《證券法》第180~185 條等;后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水污染防治法》)第94 條規定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處上一年度從本單位取得的收入50%以下的罰款,類似規定還有《大氣污染防治法》第122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管理法》(以下簡稱《疫苗管理法》)第80 條等。
面對上述分歧,筆者認為立法對成員罰款數額的設定應統一采倍率方式。理由是:首先,由于數值方式上下限閉合的靜態化特點,極易對成員造成威懾不足或威懾過度。對于收入不菲的單位高管來講,區區數萬罰款可能無關痛癢,無法保證罰款高于違法所得;對于收入較低的普通員工而言,數值式罰款又恐過于嚴厲。其次,單位違法深嵌于市場環境中,單位的盈利狀況、股價漲跌以及成員收入都處于不斷變化中,數值式罰款難以因經濟指數的變化而無法確保動態正義。事實上,單位違法中成員不法行為的根本動機是從單位獲得收入分配,倍率式罰款以成員所得收入作為罰基,使罰款數額直接與違法成員的財產狀況掛鉤,更有利于實現精準威懾。
運用倍率式罰款時應注意,根據威懾原理,罰款設定須足以剝奪行為人從違法行為中獲取之利益,才能使其無利可圖而放棄違法;同時,在執法的查處概率小于100%的現實條件下,罰款必須大于違法所得,才能使預期的懲罰成本等于社會成本,以消除違法者僥幸逃脫處罰的“漏網之魚”心理。所以,對成員設置的罰款倍率系數原則上應當大于1。就此而論,諸如《水污染防治法》第94 條規定的“處上一年度從本單位取得的收入50%以下的罰款”就可能威懾不足。相比之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第75 條對有關責任成員處以其上一年度從本單位取得收入的1~10 倍罰款的規定更為合理。
第三,實證法在規定成員的罰款責任時,普遍采用客觀歸責或過錯推定,未區分故意或過失違法的情形,并不適合單位違法中的成員責任。如前所述,單位違法中成員承擔責任的根據是以自身行為陷單位于違法境地,其中既包括故意行為也包括過失行為,二者的可罰性程度顯然不同,應當在罰款責任上有所區分,否則不利于過罰相當原則及處罰教育目的的實現。對此,在立法論上應區分成員的故意和過失行為并設置不同檔次及幅度的罰款責任;在解釋論上,立足現行法律框架,可借鑒《德國違反秩序法》第17(2)條的規定,〔70〕同前注〔39〕,鄭沖文,第89 頁。在執法中確立如下裁量基準:相關責任成員因過失行為導致單位違法的,可按照法定罰(推定故意)的罰款數額減半量罰。
(2)關于限制或禁止從業的責任。限制或禁止從業責任的典型如,《藥品管理法》第118 條規定的“終身禁止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疫苗管理法》第82 條規定的“10 年內直至終身禁止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等。限制或禁止從業屬于資格罰范疇,相對于罰款和行政拘留,其對單位成員而言更為嚴厲,威懾力也更強。但從實質合法的角度,限制或禁止從業責任涉及公民的職業自由權和勞動權兩項基本權利,需要接受“妥當性”“必要性”“均衡性”三階段的比例原則檢驗。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妥當性階段:限制措施應有助于行政目的的實現。限制或禁止從業措施屬于典型的違法能力剝奪措施,無疑能夠徹底杜絕預防再犯,符合預防違法的的法益保護目的。
第二,必要性階段:必須在能夠實現目的的手段中選擇最溫和的手段, 亦即對基本權利損害最小的手段。首先,限制或禁止從業措施是否屬于最小損益手段無法抽象判斷,而應結合當事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威懾必要性進行綜合考慮。如果無視人身危險因素,對某類單位違法的責任成員“一刀切”地規定限制或禁止從業,無法確保通過必要性要求的檢驗。相對而言,《刑法》第37 條規定禁止從業措施應“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顯得更為審慎。其次,目前單位違法中限制或禁止從業責任甚至明顯重于《刑法》第37 條禁業3~5 年的刑罰處遇措施。“行政處罰與刑罰處罰在性質上有所不同,由于行政不法的不法內涵較低,其立法反映也就較之刑事不法要緩和一些。”〔71〕陳興良:《論行政處罰與刑罰處罰的關系》,載《中國法學》1992 年第4 期,第28 頁。就性質相近的違法和犯罪行為而言,行政責任不宜重于刑事責任,這就如同行政拘留的期限無論如何也不應超過最短的有期徒刑一樣。否則,就不屬于對當事人損益最小的手段而有違必要性原則。〔72〕當然,《刑法》第37 條第3 款已作兜底規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對其從事相關職業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規定的,從其規定。”從形式合法意義上講,行政法設置更嚴的限制執業措施并無障礙。這里主要是從實質正義角度探討其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的最小損害要求。
第三,均衡性階段:應在基本權利限制與該限制手段所欲保護的法益之間進行權衡,只有所欲保護的法益位階明顯高于被限制法益時,這種限制才是正當的。一般來講,生命健康、公共衛生等法益位階的確高于職業自由和勞動權,可以據此對基本權利予以一定限制。但根據“基本權利核心內容不得侵犯”的憲法原則,〔73〕參見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5 年版,第 165 頁。適用終身禁止從業的法律責任因涉及基本權利的徹底剝奪,故需要更強的限制理由,一般應當僅限于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情形。
綜上,筆者建議對限制或禁止從業的責任作如下修正:其一,對于限期從業的處罰責任,可以借鑒《刑法》第37 條的立法技術,根據違法情節和預防再次違法的需要,明確列舉具體的適用條件,主要包括重復違法、故意違法、危害后果嚴重等情形;首次違法、過失違法、危害后果輕微或當事人積極退賠等場合不宜適用從業禁止。而不宜像《藥品管理法》第118 條、《疫苗管理法》第82 條那樣僅抽象規定“情節嚴重”,以免留給行政機關過寬的裁量空間。同時,限制從業責任的期限原則上不應超過《刑法》第37 條規定的3~5 年,以保持最小侵害。其二,對于終身禁止從業的處罰責任,應僅限于在諸如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等涉及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領域設定,不能隨意拓展至其他行業領域,以平衡權利限制的成本收益;同時,終身禁止從業責任的適用應當限于造成實際損害的情形,如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導致不良藥品反應等。
四、結語
傳統行政處罰法由治安管理領域發展而來,以調整自然人的秩序違反行為為主旨。伴隨國家角色從自由法治國到社會法治國、再到風險法治國的變遷軌跡,調整單位違法以規制市場失靈和社會風險,在現代行政處罰中占據日益重要的地位。在此背景下,行政處罰的制度設計應當與時俱進地引入雙罰制,從排除個人違法行為的秩序法向預防組織違法行為的規制法發展。從規范角度,單位違法雙罰制應采用法有特別規定才處罰的局部適用政策,基于雙重構造論分別規定單位維度和成員維度的構成要件,并基于組織抑制的合規理念合理分配單位及成員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