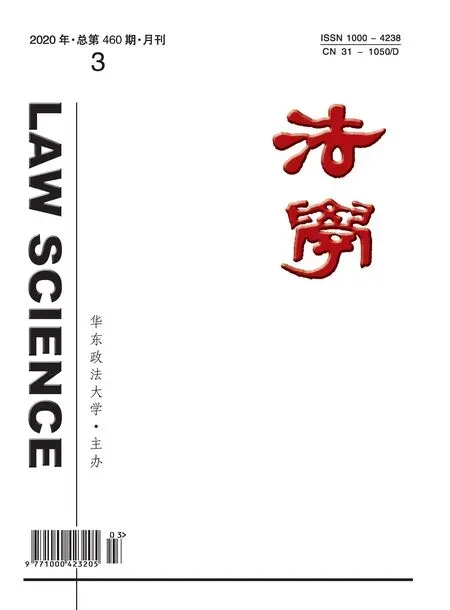重大傳染病危機應(yīng)對的行政組織法調(diào)控
●王 旭
導(dǎo) 論
2020年初爆發(fā)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fā)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1〕參見習(xí)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統(tǒng)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23/c_1125616016.htm,2020年2月23日訪問。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突發(fā)事件”不僅僅威脅到人民生命健康乃至全球健康安全,而且已經(jīng)導(dǎo)致國家,尤其是疫情嚴重地區(qū)一定程度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停擺、次生傷害發(fā)生乃至社會價值觀撕裂,演變?yōu)橐粓龉残l(wèi)生危機。不過,危機往往也是社會學(xué)習(xí)知識的來源,成為社會制度變革與創(chuàng)新的契機。〔2〕See A.Wildavsky: Searching for Safet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Routledge2018,p.7.
從1848年英國通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xiàn)代公共衛(wèi)生法案(The 1848 Public Health Act)明確規(guī)定由中央政府設(shè)立專門機構(gòu),負有包括傳染病防治等職責(zé)在內(nèi)開始,現(xiàn)代國家公共衛(wèi)生治理毫無疑問是一種以政府為主導(dǎo)的組織現(xiàn)象,并規(guī)定到各種法律淵源之中,〔3〕See B.R.Lindsay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2,p.1.盡管模式各不相同。行政法規(guī)范各種行政組織的正式機制,組織法歸根結(jié)底要發(fā)揮影響、形塑行政行為的調(diào)控功能。〔4〕參見[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體系建構(gòu)》,林明鏘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頁。但現(xiàn)代行政組織法必須通過合理解釋提高組織應(yīng)對危機的效率和合法性,避免“組織失敗”,加劇應(yīng)對成本,甚至使得突發(fā)公共事件演變?yōu)楦鼑乐氐墓参C。我們有必要通過法教義學(xué)方法,根據(jù)現(xiàn)代公共衛(wèi)生危機應(yīng)對原理,對我國現(xiàn)行傳染病防治和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yīng)對的相關(guān)規(guī)范做出最佳詮釋,建立起組織結(jié)構(gòu)優(yōu)化的法教義學(xué)目標,才能形成引導(dǎo)實踐的最佳規(guī)范框架,提升我國公共衛(wèi)生危機治理的能力。
一、危機類型學(xué)與重大傳染病應(yīng)對的組織法原理
(一)組織任務(wù)與危機類型學(xué)
行政組織法的建構(gòu)總是與法律觀察社會的特定界面有關(guān),這由組織法是為了促進完成特定行政事務(wù)的要求所決定。〔5〕參見陳愛娥:《國家角色變遷下的行政任務(wù)》,載《月旦法學(xué)教室》2003年第3期。任何行政組織總是在一定社會環(huán)境中、為了完成某種行政事務(wù)而存在,法律必須根據(jù)特定組織所處環(huán)境,分析其要完成的行政事務(wù)特征,才能對組織形式及要素做出最佳安排。〔6〕參見[日]大橋洋一:《行政法學(xué)的結(jié)構(gòu)性變革》,呂艷濱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頁。應(yīng)對公共危機的組織法究竟如何設(shè)計與安排,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共危機”及法律所規(guī)范的危機類型。這是因為:“如果一個人想知道不同類型危機是如何發(fā)展的,圍繞它們的是什么類型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處理它們,那么這種分類法會通過識別不同危機的共同特征提供幫助。”〔7〕Gundel,Towards a New Typology of Crises,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Vol(13),2005,p.106.對于法律來說,我們需要觀察“公共危機”作為規(guī)范對象具體表現(xiàn)出來的不同法律類型(type),準確進行法律解釋的前提就是對不同類型“事物之本質(zhì)”的揭示。〔8〕參見[德]阿圖爾?考夫曼:《類推與事物的本質(zhì):兼論類型理論》,吳從周譯,學(xué)林文化事業(yè)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
重大傳染病公共危機是一種特殊類型,在法律上它來自于《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yīng)對條例》第2條所明確的四種“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yè)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可見,重大傳染病疫情在法律上只是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一種類型,我們需要抓住它的社會條件和因素進行相關(guān)法律解釋,這就是所謂“符合事物之本質(zhì)”的解釋方法。〔9〕同上注,第28頁。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先了解什么是“重大傳染病疫情”,“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是否就是“公共衛(wèi)生危機”?以準確發(fā)現(xiàn)“重大傳染病危機”的社會本質(zhì)。
“重大傳染病疫情”在《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中有明確界定:其是指“《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所稱的傳染病的暴發(fā)、流行。”《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列舉了甲乙丙三類傳染病,實行分類管理,根據(jù)《實施辦法》第73條,“爆發(fā)”是指“一個局部地區(qū),短期內(nèi),突然發(fā)生多例同一種傳染病病人”,“流行”則是“一個地區(qū)某種傳染病發(fā)病率顯著超過該病萬折的一般發(fā)病率水平。”
可見,只有法定傳染病符合“短期突發(fā),且達到一定發(fā)病率”才構(gòu)成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而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又根據(jù)《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3條屬于“突發(fā)公共事件”。〔10〕該條規(guī)定“自然災(zāi)害、事故災(zāi)難、公共衛(wèi)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四種突發(fā)公共事件。
然而,“突發(fā)公共事件”并不等同于“公共危機”或法律上的“緊急狀態(tài)”,這需要我們回到一般危機類型學(xué)上來。
《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法》第3條規(guī)定“突發(fā)公共事件”是指“突然發(fā)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取應(yīng)急處置措施予以應(yīng)對”,包含發(fā)生突然性、危害嚴重性和緊急處置性三個構(gòu)成要件,而這三個要件卻不會必然發(fā)展為一種“公共危機”。按照危機類型學(xué)上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界定,“公共危機”是指“一個社會制度的核心價值或維持運轉(zhuǎn)的功能受到威脅,需要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采取緊急補救行動。”〔11〕Coping with crise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and terrorism,edited by Uriel Rosenthal,Michael T.Charles,Paul ‘t Hart.Springfield 1989,p.19.可見,公共危機是對一個社會整體價值和秩序受到嚴重損害的描述,它不一定是突然發(fā)生;〔12〕Perrow將公共危機分為“日常危機”與“非常危機”,后者是預(yù)見性很弱的突發(fā)性危機,See Perrow,The Next Catastroph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119.公共危機往往造成對社會多個價值的破壞,是一種系統(tǒng)性、綜合性的傷害,是社會問題的全面爆發(fā)。突發(fā)公共事件并不必然導(dǎo)致對社會整體性傷害,例如突發(fā)的大面積火災(zāi)或嚴重交通事故,往往只是對具體利益或局部秩序的臨時沖擊。由此,應(yīng)對公共危機對于組織彈性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好協(xié)調(diào)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組織,并動員更多社會力量;〔13〕See Boin,F.(2008).Crisis Management: Oxford Journals,Volume 63(5),p.549.進而,公共危機往往是一種狀態(tài),相對于突發(fā)公共事件具有較長的持續(xù)性。〔14〕當(dāng)突發(fā)公共事件演變?yōu)橐环N持續(xù)較長的狀態(tài),有的國家可以依照法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tài),但我國《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明確區(qū)分了二者,因此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或國務(wù)院沒有根據(jù)憲法宣布全國或地方局部地區(qū)進入緊急狀態(tài)之前,都可以將公共危機理解為是一種特殊的突發(fā)公共事件狀態(tài),仍然適用《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例如,在宣布某個地區(qū)成為疫區(qū)后,并采取長時間隔離手段,其封閉的社會經(jīng)濟狀態(tài)如何有效管理,如何保持信息、資源等組織要素有效循環(huán)與補給,如何維護封閉社會狀態(tài)下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秩序,都往往超出了突發(fā)公共事件法律的框架性規(guī)定,需要通過解釋抽象法律條款發(fā)展出常態(tài)化的組織安排與措施,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應(yīng)急處置層面;〔15〕法學(xué)和公共管理學(xué)上的深入分析M.Waxman,National Security Federalism the Age of Terror Stanford Law Review (2012)[Vol].64,p.310; Gilpin and Murphy,Crisis management in a complex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p.241-242.最后,公共危機的發(fā)生和加劇往往是內(nèi)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共同作用結(jié)果,可能從情境危機轉(zhuǎn)向由于管理不當(dāng)導(dǎo)致的制度危機,尤其是“組織失敗”。〔16〕See Rhodes and t’ Hart,Puzzling about Leadership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eadership,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63.也就是說,公共組織本身會加劇危機,成為新的危機來源,這需要公共組織通過法律來調(diào)控自身,滿足功能適當(dāng)、民主正當(dāng)與可問責(zé)性等諸多方面要求,其中維持自身的公信力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17〕同上注。
可見,突發(fā)公共事件是一種潛在的危機類型,有發(fā)展成為公共危機的趨勢,二者的轉(zhuǎn)折也沒有絕對清晰的節(jié)點與標準。行政組織法調(diào)控的根本目標就在于通過最佳的組織結(jié)構(gòu)安排與要素流動,盡量防止突發(fā)公共事件出現(xiàn),并阻止其向公共危機演變,同時要準確進行組織裁量,在演變?yōu)槲C后進行法律上的有效管理。
(二)重大傳染病疫情的社會本質(zhì):組織法解釋原理之建構(gòu)
前述危機類型學(xué)的分析告訴我們,公共衛(wèi)生危機并非僅僅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本質(zhì)上是對社會整體面不同程度的沖擊和傷害,而程度大小就與不同危機的社會特征緊密相關(guān)。從法教義學(xué)上來看,即便我們可以通過一部統(tǒng)一的《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或《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條例》來涵蓋或列舉各種危機,但必須根據(jù)它們的具體特征來進行解釋和適用。例如《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條例》第39條規(guī)定“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gòu)應(yīng)當(dāng)對因突發(fā)事件致病的人員提供醫(yī)療救護和現(xiàn)場救援。”重大傳染病與不具有傳染性的重大食物中毒,二者在醫(yī)療人員的專業(yè)構(gòu)成、醫(yī)生自我防護措施與程度、救護場地要求等資源要素方面就會完全不同。對于重大傳染病疫情,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它是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中最容易演變?yōu)樯鐣w危機的類型,其有四個社會本質(zhì)將深刻影響行政組織法的建構(gòu),構(gòu)成解釋具體規(guī)范的基本原理:
第一,重大傳染病疫情是典型的社會外溢性風(fēng)險,極容易構(gòu)成跨界危機。〔18〕See A.Boin,Rhinard,Ekgengren,Managing Transboundary Crises: The Emergence of European Union Capacity,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2014,Vol22(3) ,p.131.所謂“社會外溢性”是指危機的損害后果從來源地或來源因素難以遏制地擴散,它是重要的組織裁量基準。很多國家法律的規(guī)定都與此有關(guān),例如美國《州際應(yīng)急管理互助協(xié)議》(EMAC)即規(guī)定公共危機逾越出一個州是啟動州際應(yīng)急管理互助的法定要件之一,也是根據(jù)《聯(lián)邦災(zāi)害緩釋與危機援助法令》(the Stafford Act)向聯(lián)邦政府請求支持的條件。〔19〕同前注〔3〕,Bruce R.Lindsay文,第 7頁。傳染病的本質(zhì)就是“人傳人”,尤其在人際交互關(guān)系復(fù)雜與全球交通運輸能力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代性條件下,傳染病危機更容易跨越地域、人種、階層、族群,成為一種貝克所講的“跨界風(fēng)險”:“個人的生命史已經(jīng)逐漸被迫向世界性的社會開放”“個人環(huán)境和全球風(fēng)險之間處在交互關(guān)聯(lián)之中”,每一個人和這個世界上另一個人處在“統(tǒng)一的經(jīng)驗架構(gòu)中”,整個世界成為“沒有他者的世界。”〔20〕參見[德]貝克爾:《風(fēng)險社會:新的現(xiàn)代性之路》,張文杰等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37頁。傳染病疫情作為跨界風(fēng)險,不僅僅是指危害跨越行政區(qū)劃甚至國度,本質(zhì)上是一種組織界面的穿越,它催生不同組織的橫向協(xié)調(diào)、溝通與合作機制,甚至在法律上催生新的組織形式,從而打破了傳統(tǒng)理性官僚制所預(yù)設(shè)的專業(yè)化、分權(quán)和任務(wù)區(qū)隔。〔21〕參見[德]馬克斯?韋伯:《經(jīng)濟與社會》第2卷 上,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65頁。應(yīng)對危機的組織架構(gòu)要從縱向科層制走向更多的橫向調(diào)控。〔22〕同前注〔18〕,A.Boin、Rhinard、Ekgengren文,第 140頁。跨界風(fēng)險還意味著貝克所講的“風(fēng)險的回旋鏢效應(yīng)”,危機發(fā)源地將危機擴散開去之后必須警惕被感染地反向再輸入危機,從而給危機解除和重建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第二,重大傳染病疫情是社會無差別性風(fēng)險,既需要提高社會的組織化程度、通過法律創(chuàng)造多元組織形式來動員國家與社會,又需要避免因此加劇組織對個體自由和權(quán)利的限制,確保憲法與法律對組織形式的實質(zhì)控制。所謂“危機的社會無差別性”是指這種危機是“民主分布”,平等概率降臨到每一個人的頭上,每一個人都沒有豁免風(fēng)險的可能。〔23〕See A.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olity Press,1984,p.230.從而,一方面需要通過組織化調(diào)動全社會力量,傳統(tǒng)層級行政的一元結(jié)構(gòu)被動搖。但另一方面也帶來整個社會高度組織化條件下對個體自由的無差別壓制,引發(fā)作為集體現(xiàn)象的組織對個體的不信任與權(quán)利侵犯,從而也給行政組織法的合憲性控制帶來難題。這就出現(xiàn)行政組織在應(yīng)對危機時效率與合法性之間的深刻緊張。
第三,重大傳染病疫情是典型的社會情境性危機,在不同環(huán)境和條件下,危機發(fā)生的原因、概率、表現(xiàn)形式都完全不同,交織著制度、技術(shù)等各種影響因素。〔24〕同前注〔15〕,Gilpin、Murphy書,第 209頁。從最初出現(xiàn)疫情到疫情結(jié)束,存在著各種不確定因素,不同階段之間也缺乏清晰轉(zhuǎn)化的界限,盡管《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都建立起了“預(yù)防與準備”“監(jiān)測預(yù)警”“應(yīng)對與處置”“恢復(fù)重建”等不同階段教義學(xué)體系,但不同階段究竟如何發(fā)揮各種組織的作用,妥善安排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明確其相互權(quán)責(zé),存在較大解釋空間。這加劇了危機應(yīng)對中統(tǒng)一性和分散性、一般性與個別性之間的矛盾。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和第20條分別規(guī)定了國家建立防治的監(jiān)測預(yù)案和應(yīng)急處置預(yù)案,但實際上各地必須根據(jù)自己的情況細化;又如,盡管“早發(fā)現(xiàn)、早隔離、早治療”是傳染病防控的一般原則,但如何做到最早發(fā)現(xiàn),何時預(yù)警與發(fā)布有關(guān)信息才是最佳合適時間,需要考慮各種因素,并依賴多種技術(shù)、制度手段進行理性裁量乃至決斷。因此,應(yīng)對重大傳染病危機首先要求確保組織的彈性,即要允許組織形式多樣、相互關(guān)系靈活,確保組織可以快速反應(yīng);各種組織要素的配置、安排需要根據(jù)具體情況予以調(diào)整;其次,要求尊重組織裁量。組織法規(guī)范需要保持一定的意義幅度,允許適用法律的人根據(jù)具體情況,斟酌現(xiàn)實約束條件對法律條文作出最佳解釋。例如法律規(guī)定了分級響應(yīng)的制度,但如何確定疫情級別,在什么時候調(diào)整級別,就需要理性、精確地裁量。《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起草說明在指出立法必要性的時候就從組織彈性與組織裁量兩個方面指出了現(xiàn)實存在的問題:一是應(yīng)對突發(fā)事件的責(zé)任不夠明確,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靈敏的應(yīng)對體制尚未形成。二是一些行政機關(guān)應(yīng)對突發(fā)事件的能力不夠強,危機意識不夠高,依法可以采取的應(yīng)急處置措施不夠充分、有力。三是突發(fā)事件的預(yù)防與應(yīng)急準備、監(jiān)測與預(yù)警、應(yīng)急處置與救援等制度、機制不夠完善,導(dǎo)致一些突發(fā)事件未能得到有效預(yù)防,有的突發(fā)事件引起的社會危害未能及時得到控制。四是社會廣泛參與應(yīng)對工作的機制還不夠健全,公眾的自救與互救能力不夠強、危機意識有待提高。
第四,重大傳染病疫情容易誘發(fā)社會整體性危機,有一定的時間持續(xù)性和空間封閉性,容易形成危機的日常化狀態(tài),〔25〕同前注〔12〕,Perrow 書,第 119頁。因此,應(yīng)對這種危機需要充分實現(xiàn)各種組織要素的有序流動,發(fā)揮組織合力。例如《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第54條規(guī)定解除緊急措施的條件中,甲類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全部治愈,乙類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得到有效的隔離治療;病人尸體得到嚴格消毒處理;暴發(fā)、流行的傳染病病種,經(jīng)過最長潛伏期后,未發(fā)現(xiàn)新的傳染病病人,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全部治愈”“有效隔離”本身就高度依賴各種組織要素的充分調(diào)動與配合,例如充足的醫(yī)療人員,有效的試劑、特效藥,隔離場所對“應(yīng)收盡收”的保障等。然而,組織要素調(diào)配與安排本身也是國家和全社會調(diào)動力量,需要耗費時間;而“最長傳染期”的設(shè)定更使得危機應(yīng)對措施有一定持續(xù)性。由此,社會整體性危機的本質(zhì)就是由于傳染病疫情的曠日持久使得社會的整體秩序和一般行為模式受到影響,由此會引發(fā)各種次生矛盾與傷害,甚至導(dǎo)致價值觀沖突。在一個持續(xù)性的應(yīng)對危機的社會環(huán)境里,各種組織要素如何有效形成合力,降低沖突矛盾,防止次生傷害所帶來的組織失敗與信任危機,這些都對法律的準確解釋與適用提出考驗。例如,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疫情來源地武漢采取了封閉出城交通管道措施,但封閉后的社會如何運轉(zhuǎn),如何有效隔離健康人與確診患者或疑似患者而不是在物理空間上簡單的“一封了之”,對于健康人如何保障正常生活,對于病患與疑似患者如何保障最充分救治,這些問題引發(fā)的危機已經(jīng)不是最初的生命健康安全威脅,而是社會經(jīng)濟、政治、價值觀的全面危機。〔26〕各種現(xiàn)象描述與反思的綜合性素材可以參見《十六城抗疫記錄》:載《財新》2020年2月17日。
(三)重大傳染病危機應(yīng)對所設(shè)定的組織法目標
重大傳染病疫情是一種特殊的危機類型,我們必須從它自身四個特征,即“社會外溢性危機”“社會無差別性危機”“社會情境性危機”和“社會整體性危機”出發(fā),來構(gòu)建法律解釋原理,形成法教義學(xué)上的體系。
從一般情況來看,行政組織法教義學(xué)建立在雙重功能體系原理之上〔27〕同前注〔4〕,施密特?阿斯曼書,第226頁。:一是建構(gòu)功能,將行政組織建構(gòu)為法律上的人(權(quán)利能力主體),賦予其權(quán)力,明確其責(zé)任。建構(gòu)功能具體又展開為法律形式、組織區(qū)分和實質(zhì)原則三個方面。法律形式是建構(gòu)不同的組織形式,組織區(qū)分則是通過法律區(qū)分組織形式的不同地位,以確定不同權(quán)限和職責(zé)并調(diào)整相互關(guān)系。實質(zhì)原則主要是憲法和法律對行政組織的控制要求與正當(dāng)性證明,例如在德國法上憲法規(guī)定的行政一體性、基本權(quán)利保障和民主正當(dāng)性被認為是三個最重要的控制原則;〔28〕同前注〔4〕,施密特?阿斯曼書,第227頁。二是管制功能,組織法規(guī)范影響具體行政活動的過程及決定。包括如何與其他關(guān)聯(lián)法律規(guī)則相聯(lián)系,來合理建構(gòu)權(quán)限管理規(guī)則、組織間運轉(zhuǎn)協(xié)調(diào)規(guī)則、信息管理規(guī)則、組織與環(huán)境溝通規(guī)則等。〔29〕參見黃錦堂:《行政組織法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86頁。
這個一般框架實際上可以進一步歸結(jié)為組織形式教義學(xué)和組織要素教義學(xué)兩個部分。建構(gòu)功能體現(xiàn)組織形式教義學(xué),聚焦組織形式的法律地位及相互關(guān)系,在我國重大傳染病危機應(yīng)對的法規(guī)范體系中,核心就是處理行政機關(guān)內(nèi)部各種主體的地位及法律關(guān)系,尤其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guān)系,同時還要處理政府與法律創(chuàng)設(shè)的其他組織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也就是一個結(jié)構(gòu)問題。管制功能則體現(xiàn)的是組織要素教義學(xué),也就是如何通過法律有效管制各種組織的工作要素,促進合力形成。
結(jié)合前述重大傳染病危機的四個社會特質(zhì),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對組織形式和組織要素都提出了相關(guān)要求或挑戰(zhàn),“社會外溢性危機”與“社會無差別性危機”更多聚焦組織結(jié)構(gòu)優(yōu)化的問題,例如如何合理、正當(dāng)?shù)卦诜缮蟿?chuàng)設(shè)足以應(yīng)對危機的行政組織,并適當(dāng)?shù)靥幚硭鼈冎g的關(guān)系,這是一種結(jié)構(gòu)優(yōu)化的思維,在行政組織法上則往往在正當(dāng)化原則下加以討論,可以概括為合法性與有效性兩個基本維度。〔30〕參見[德] 漢斯?J.沃爾夫、奧托?巴霍夫、羅爾夫?施托貝爾:《行政法》第3卷,高家偉譯,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第58頁。“社會情境性危機”和“社會整體性危機”更多要求組織要素流動有序,包括在具體情境中合理運用權(quán)力進行組織裁量,建立更加協(xié)同的組織間關(guān)聯(lián)與對話規(guī)則,促進信息報告、通報、發(fā)布,確保應(yīng)對危機所需資源的合理生產(chǎn)布局、調(diào)配使用與供給。
然而,組織要素并不能離開特定組織形式而存在,因此,我們可以組織形式教義學(xué)為框架,通過正確處理組織形式內(nèi)外的結(jié)構(gòu)性關(guān)系實現(xiàn)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終獲得組織結(jié)構(gòu)優(yōu)化的法律框架。
二、組織形式教義學(xué)的基本框架
(一)傳統(tǒng)層級行政模式
層級行政是經(jīng)典的行政組織法結(jié)構(gòu),其背后法教義學(xué)原理在于“行政一體性要求”:第一,根據(jù)憲法和法律明確設(shè)定由專門人員組成的職位體系,形成權(quán)力和責(zé)任明確的效力層級;第二,不同層級的職務(wù)承擔(dān)專業(yè)化行政任務(wù),守土有責(zé),原則上人與職能不交叉;〔31〕參見馬懷德主編:《行政法前沿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頁。第三,不同層級之間形成嚴格統(tǒng)一的命令—服從關(guān)系。權(quán)力,尤其是決策權(quán)奉行“盡可能集中原則”,最終統(tǒng)一于一個機關(guān)或機關(guān)群中的一個首長之中。〔32〕參見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頁。第四,層級行政往往是國家直接行政,要求行政任務(wù)由具有憲法或組織法地位的行政主體代表國家完成,并要求國家機關(guān)應(yīng)該以相同的思考對外做成決定。〔33〕同前注〔4〕,施密特?阿斯曼書,第227頁。
《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的主體結(jié)構(gòu)仍然建立在層級行政基礎(chǔ)上。例如《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4條明確“國家建立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的應(yīng)急管理體制”,第8條和第7條分別規(guī)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領(lǐng)導(dǎo)各自行政區(qū)域里的應(yīng)急工作,第9條規(guī)定了“國務(wù)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工作的行政領(lǐng)導(dǎo)機關(guān)”。〔34〕《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8條:國務(wù)院在總理領(lǐng)導(dǎo)下研究、決定和部署特別重大突發(fā)事件的應(yīng)對工作;第7條規(guī)定:縣級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突發(fā)事件的應(yīng)對工作負責(zé)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由國務(wù)院有關(guān)部門對突發(fā)事件的應(yīng)對工作負責(zé)的,從其規(guī)定。《傳染病防治法》第5條、第6條也明確了各級人民政府領(lǐng)導(dǎo)傳染病防治工作以及衛(wèi)生行政部門主管相應(yīng)工作。〔35〕《傳染病防治法》第5條規(guī)定:各級人民政府領(lǐng)導(dǎo)傳染病防治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傳染病防治規(guī)劃并組織實施,建立健全傳染病防治的疾病預(yù)防控制、醫(yī)療救治和監(jiān)督管理體系。第6條規(guī)定:國務(wù)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主管全國傳染病防治及其監(jiān)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wèi)生行政部門負責(zé)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傳染病防治及其監(jiān)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部門在各自的職責(zé)范圍內(nèi)負責(zé)傳染病防治工作。在整個體系中,以政府及部門主導(dǎo),形成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政府與部門之間三種層級關(guān)系的教義學(xué)結(jié)構(gòu)非常明確。
(二)層級行政教義學(xué)的擴展
然而,在這種傳統(tǒng)剛性結(jié)構(gòu)之外,兩部法律實際上還是在層級行政內(nèi)、外創(chuàng)設(shè)出很多新的組織形式,以滿足應(yīng)對危機的需要:
1.行政機關(guān)內(nèi)部決策、統(tǒng)籌組織與議事協(xié)調(diào)組織
這兩種組織形式仍然在層級行政內(nèi)部,但它改變了由不同政府部門主管某一個行政領(lǐng)域的分散式科層體系,該體系背后理念是理性官僚制預(yù)設(shè)的專業(yè)化分工與分權(quán)原則。〔36〕同前注〔21〕,馬克斯?韋伯書,第629頁。這主要體現(xiàn)在《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8條創(chuàng)設(shè)了“國家和縣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突發(fā)事件應(yīng)急指揮機構(gòu)”(包括軍隊)“國務(wù)院派出的工作組”以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說明中肯定的部門之間“聯(lián)防聯(lián)控”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
法律設(shè)立這三種組織形式的正當(dāng)性在于,危機應(yīng)對往往需要強有力的領(lǐng)導(dǎo)和中央方向,貫穿整個層級制度(官僚制)的指揮鏈條。〔37〕See T’ Hart,Assessing the authority of Politic Office-holder,Western Politics 38(3),2014,p.418.基于此考慮,從世界范圍看,法律上主要建立了三種模式:一是加強部門的專業(yè)協(xié)調(diào),如美國事件指揮系統(tǒng),包括危機中心、聯(lián)邦緊急事務(wù)管理局等;二是通過在中央一級創(chuàng)建和合并更強大的危機管理組織來集中協(xié)調(diào),如美國的國土安全部;三是通過多級組織來促進協(xié)調(diào),如歐盟的多級危機治理模式。〔38〕See A.Boin,M.Busuioc,M.Groenleer,Building European Union capacity to Management transboundary Crisies: Network or Leader-agency Model,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Vol8(4),2014,p.133.我國法律實際上同時糅合了“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架構(gòu)”與“網(wǎng)絡(luò)協(xié)調(diào)架構(gòu)”:
第一種“應(yīng)急指揮機構(gòu)”是為了“建立綜合協(xié)調(diào)的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機制,有效整合各種資源”。〔39〕參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立法草案說明。從法律規(guī)定來看,它是典型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架構(gòu)”,在相應(yīng)行政層級里具有最高決策權(quán)、統(tǒng)籌指揮權(quán)和事項集中權(quán)三項具體權(quán)能。同時第8條規(guī)定,從中央到縣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都可以建立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指揮部,從而是一種很有中國特色的“分散的統(tǒng)一最高權(quán)”模式:首先從人員組成看,它具有層級行政里集權(quán)的必然傾向。《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8條規(guī)定地方應(yīng)急指揮部由“本級人民政府主要負責(zé)人、相關(guān)部門負責(zé)人、駐當(dāng)?shù)刂袊嗣窠夥跑姾椭袊嗣裎溲b警察部隊有關(guān)負責(zé)人組成”,由行政首長組成的人員使得“首長負責(zé)制”邏輯必然延伸到機構(gòu)中;其次,從職能看,第9條規(guī)定其“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協(xié)調(diào)本級人民政府各有關(guān)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開展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工作”,明確了其作為決策機關(guān)和指揮機關(guān)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與協(xié)調(diào)權(quán)”;第三,從保障看,它實際上是中國戰(zhàn)時體制的表現(xiàn),軍隊在其中保障。
第二種“國務(wù)院派出的工作組”。第8條規(guī)定,根據(jù)“工作需要”,國務(wù)院可以派出工作組指導(dǎo)有關(guān)工作。工作組并沒有實際的決策、指揮權(quán),更多是基于貫徹中央政府的意圖,防止危機應(yīng)對中的地方主義而設(shè)計,與其他法律里的督察組織、工作檢查小組均不同。〔40〕例如《土地管理法》第6條規(guī)定:國務(wù)院授權(quán)的機構(gòu)對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以及國務(wù)院確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況進行督察。在法教義學(xué)上值得進一步考慮的是指導(dǎo)的形式、效力,與其他地方組織形式的關(guān)系等等問題。
第三種“政府部門間的聯(lián)防聯(lián)控工作機制”則是一種典型的網(wǎng)絡(luò)協(xié)調(diào)工作架構(gòu),其本身并不享有決策和指揮權(quán),更多是行政組織法上的議事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這種模式在我國公共事件應(yīng)急法治傳統(tǒng)中由來已久,在《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出臺前,中國分成不同專業(yè)領(lǐng)域來應(yīng)對各自的突發(fā)事件,建國初期即成立“中央救災(zāi)委員會”以協(xié)調(diào)各個相關(guān)部門的防疫、防災(zāi)工作。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我國還成立了國務(wù)院抗震救災(zāi)指揮部、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國務(wù)院安委會等“虛權(quán)”的議事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明確了由各級政府統(tǒng)一負責(zé)應(yīng)急處置,實踐中各級政府設(shè)立應(yīng)急辦公室作為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直到2018年黨和國家機構(gòu)改革設(shè)立綜合性、統(tǒng)一性的應(yīng)急管理部。〔41〕參見鐘開斌:《從強制到自主:中國應(yīng)急協(xié)調(diào)機制的發(fā)展與演變》,載《中國行政管理》2014年第8期。聯(lián)防聯(lián)控機制具有臨時性和非實體性,這種協(xié)調(diào)組織的關(guān)鍵作用在于通過協(xié)調(diào)促進橫向機構(gòu)之間的合作,而不是實際做成決定,網(wǎng)格化的架構(gòu)有助于權(quán)力配合、信息溝通與資源配置。〔42〕同前注〔38〕,A.Boin、M.Busuioc、M.Groenleer文,第 141 頁。因此在法教義學(xué)上必須區(qū)分它與同樣具有組織聯(lián)合功能的指揮部,并思考有無必要通過法律解釋發(fā)展出層級行政之外的網(wǎng)絡(luò)架構(gòu)。另外,聯(lián)防聯(lián)控機制與應(yīng)急管理部本身享有的綜合協(xié)調(diào)職能是什么關(guān)系也值得透過法教義學(xué)進一步思考。
2.科學(xué)支持與技術(shù)運用組織。
各國在組織法上普遍賦予傳染病防治中科學(xué)支持和技術(shù)運用組織一定的法律地位,這是由這類危機應(yīng)對的本質(zhì)特征所決定的,那就是它需要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和醫(yī)療診斷治療,并借助傳統(tǒng)公務(wù)員之外的專業(yè)隊伍才能有效遏制危機。在我國有《傳染病防治法》第7條規(guī)定的“各級疾病預(yù)防控制機構(gòu)”“醫(yī)療機構(gòu)”、《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26條規(guī)定的“國家綜合性應(yīng)急救援隊伍”三種典型組織形式,《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jiān)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第19條還規(guī)定了“專家工作組”這種形式。〔43〕該條規(guī)定“接到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相關(guān)信息報告的衛(wèi)生行政部門應(yīng)當(dāng)盡快組織有關(guān)專家進行現(xiàn)場調(diào)查。”如何規(guī)定這類組織的權(quán)力、責(zé)任,正確處理它們與政府的關(guān)系是法教義學(xué)要關(guān)注的重點。概括來說,在法律上這類組織可以分為獨立-權(quán)力型,獨立-非權(quán)力型,非獨立-權(quán)力型三種,其本質(zhì)涉及到如何在危機應(yīng)對中正確處理科學(xué)與政治、專業(yè)獨立與權(quán)力控制之間的關(guān)系。〔44〕See D.Resnik,Playing Politics with Science: Balancing Scientific Independence and Government Overs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88.獨立-權(quán)力型的組織以美國聯(lián)邦疾控中心為典型,它獨立于政府系統(tǒng),但享有對疫情的獨立判斷權(quán)和發(fā)布權(quán)并可采取相應(yīng)的危機應(yīng)對措施,不受聯(lián)邦政府控制,具有直接向總統(tǒng)報告的權(quán)力。〔45〕參見《高福領(lǐng)導(dǎo)的CDC為何遭遇信任危機》,載《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20年第937期。2001年中國公共衛(wèi)生體制改革后實際采取了類似“獨立-非權(quán)力型”的模式,作為最重要的監(jiān)測和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機構(gòu)CDC不再具有行政執(zhí)法主體地位,CDC從衛(wèi)生防疫站模式中脫離后,其衛(wèi)生執(zhí)法監(jiān)督權(quán)被取消,2008年開始的事業(yè)單位分類改革更明確其為“公益一類”事業(yè)單位,由財政全額撥款,可以進行研究調(diào)查,但依據(jù)《傳染病防治法》第18條賦予疾控中心的八項職能,其并不享有發(fā)布信息、制定措施與執(zhí)法等各種權(quán)力。〔46〕參見胡大一:《彌合裂痕,應(yīng)對挑戰(zhàn)——論全面實施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健康中國戰(zhàn)略》,載《黃河科學(xué)學(xué)院學(xué)報》2019年第1期。
3.基層群眾自治組織
《傳染病防治法》在第9條賦予“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參與疫情防控與危機應(yīng)對的權(quán)力,法教義學(xué)上值得關(guān)注的是它們在防疫中的權(quán)力清單,并如何與其他法律規(guī)定的組織工作程序保持銜接和一致。
4.“中間行政”組織
《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還創(chuàng)造出組織法上的“中間行政組織”,它是指承擔(dān)了一部分行政任務(wù)、但并不是具有公法上完全權(quán)利能力的主體,往往基于行政委托、協(xié)議、合作等方式而分享了一部分行政事務(wù)管轄權(quán),“中間行政組織”是否具有獨立的地位在行政組織法上存在較大爭議。〔47〕同前注〔32〕,翁岳生主編書,第204頁。《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guī)定的“依靠群眾”原則是此類組織形式得以存在的教義學(xué)根據(jù)。《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條例》第37條就具體規(guī)定了“群防群治”的組織形式,從而在危機應(yīng)對實踐中帶來了很多“中間行政”現(xiàn)象,例如社區(qū)、物業(yè)管理部門、企事業(yè)單位(例如學(xué)校)等,它們都分享了應(yīng)對危機的管理權(quán)和監(jiān)督權(quán)。值得討論的是,依組織法定主義原理,“中間行政”組織的權(quán)力必須經(jīng)過組織法或程序法的規(guī)定,通過行政委托等教義學(xué)類型明確取得并受到法律控制,〔48〕參見[日]鹽野宏:《行政組織法》,楊建順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但“群防群治”的各種具體形式并沒有組織法委托或其他行政事務(wù)管轄規(guī)則的規(guī)定,它本質(zhì)上是對戰(zhàn)時體制下社會動員與全民皆戰(zhàn)模式的制度模擬,與民主正當(dāng)性原則與法治國原則下控制的理性官僚制有極大不同,因此如何將“群防群治”組織形式納入法治軌道,接受法律保留與法律優(yōu)先等法治國原則拘束并恪守尊重基本權(quán)利的消極規(guī)范品格,這是此類法教義學(xué)要建構(gòu)的重點。
5.危機應(yīng)對中的社會自組織系統(tǒng)。
傳染病疫情危機的社會外溢性和無差別性必然導(dǎo)致危機應(yīng)對系統(tǒng)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這意味著法律應(yīng)盡力促成一個自我組織的反應(yīng)系統(tǒng),如此才能提升危機應(yīng)對的效率。〔49〕同前注〔38〕,A.Boin、M.Busuioc、M.Groenleer文,第 137 頁。法律也創(chuàng)設(shè)出各種社會自組織系統(tǒng),它們自我設(shè)定危機應(yīng)對的措施,形成閉環(huán)。根據(jù)《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6條“國家建立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第55條“組織群眾開展自救和互救”,實踐也存在各種社會互助組織、社會自助組織,這類組織的活動邊界、行為方式與其他組織的互動關(guān)系,就是法教義學(xué)要討論的重點。
總之,層級行政在傳染病危機應(yīng)對法教義學(xué)上已經(jīng)被打破,行政組織在法律上成為容納了很多形態(tài),既被不同規(guī)則所區(qū)隔,又在功能上互相滲透,多樣復(fù)雜而又被共同組合的整體。
三、組織結(jié)構(gòu)優(yōu)化:中央與地方
(一)“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與“屬地管理”的法律解釋
傳統(tǒng)層級行政仍然是應(yīng)對重大傳染病危機的主導(dǎo)力量,它所涉及的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問題主要體現(xiàn)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不同層級之間權(quán)責(zé)的合理劃分,從法教義學(xué)方法來看,必須通過恰當(dāng)?shù)姆山忉尳?gòu)最佳的劃分方案,解釋的基本對象就是《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4條“國家建立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綜合協(xié)調(diào)、分類管理、分級負責(zé)、屬地管理為主的應(yīng)急管理體制。”解釋的重點就在于“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分級負責(zé)”“屬地管理”究竟如何作最佳之理解。
“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首先是危機管理中的基本原則,如何建構(gòu)一個兼顧權(quán)威與效率的高層級統(tǒng)一指揮機構(gòu)應(yīng)對危機,是很多國家和區(qū)域性國際法律改革的方向,〔50〕同前注〔18〕,A.Boin、Rhinard、Ekgengren文,第 132頁。同時它也是中國強調(diào)“全國一盤棋”的行政組織文化特色。然而這種“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又是建立在“分級負責(zé)”基礎(chǔ)之上,呈現(xiàn)出一種“分級的統(tǒng)一模式”,立法者試圖通過此兼顧“快速反應(yīng)、明確各級政府職責(zé)與有效整合資源”多項價值。〔51〕同前注〔39〕,《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立法草案說明。為此,法律將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分為“特別重大、重大、較大和一般四級”,并在立法草案中進行了原意解釋:一般和較大事件的應(yīng)急處置工作分別由縣級和設(shè)區(qū)的市級政府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重大和特別重大事件的應(yīng)急處置工作由發(fā)生地省級人民政府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其中影響全國、跨省級行政區(qū)域或者超出省級政府處置能力的特別重大的應(yīng)急處置工作由國務(wù)院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52〕同上注。可見,“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意味著我們不能在任何時候都將“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解釋為“中央政府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從權(quán)力最終來源角度可以作如此解釋,但在具體法律適用時則必須根據(jù)“危害級別對應(yīng)行政級別”的教義學(xué)原則加以解釋。只有構(gòu)成全國蔓延的危機或超出省級政府能力的危機才能適用“中央政府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的規(guī)則。這體現(xiàn)了立法者一個明確的意圖:公共危機應(yīng)該盡量控制在地方,地方則盡量將之控制在基層,從而在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基層之間進行合理的事務(wù)管轄劃分,避免危機蔓延與高昂行政成本。
“屬地管理”則可以通過解釋發(fā)現(xiàn)是一種“發(fā)生地管轄”規(guī)則,以滿足快速反應(yīng)的要求。首先,《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法》將“屬地管理”解釋為“縣級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突發(fā)事件的應(yīng)對工作負責(zé),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后,發(fā)生地縣級人民政府應(yīng)當(dāng)立即進行先期處置”;〔53〕同上注。其次,通過體系解釋我們發(fā)現(xiàn),《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與常規(guī)行政立法不同,它先規(guī)定地方政府應(yīng)急職能(第6條),后規(guī)定中央政府職能(第7條),強化屬地負責(zé)的規(guī)范意圖非常明顯。
然而,上述解釋需要結(jié)合重大傳染病危機的社會特征作更具體、最佳之解釋。例如,在傳染病防治中,尤其是疫情爆發(fā)后,由于其強烈的社會外溢性,非常容易成為全國蔓延的危機,當(dāng)我們判斷疫情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蔓延,會不會從一個縣到一個省乃至到全國,何時發(fā)生這種跨行政區(qū)域的情況,往往需要中央政府根據(jù)信息來統(tǒng)籌全局、綜合決斷。“一般”“重大”等表述本身就是不確定法律概念,需要結(jié)合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根據(jù)病毒感染指數(shù)大小(reproduction值,RO)、變異情況、易感人群特征等作具體分析,并應(yīng)對隨時發(fā)生的變化。如果我們認為“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意味著消解中央政府的責(zé)任,將職責(zé)逐級下放,則極容易出現(xiàn)不利后果。同時,“分級領(lǐng)導(dǎo)”的確切含義在傳染病危機應(yīng)對中如何具體解釋?哪些職能應(yīng)該屬于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哪些應(yīng)該屬于地方或下級政府,也存在進一步解釋空間。“屬地管理”同樣如此,對于傳染病疫情危機來說,這種屬地負責(zé)應(yīng)該進一步限縮解釋為“最近發(fā)生地負責(zé)”,因為傳染病防控基本要義在于“早發(fā)現(xiàn)、早隔離、早治療”,因此《傳染病防治法》第33條明確規(guī)定“疾病預(yù)防控制機構(gòu)……接到甲類、乙類傳染病疫情報告或者發(fā)現(xiàn)傳染病暴發(fā)、流行時,應(yīng)當(dāng)立即報告當(dāng)?shù)匦l(wèi)生行政部門,由當(dāng)?shù)匦l(wèi)生行政部門立即報告當(dāng)?shù)厝嗣裾保颂幰?guī)定的即為“當(dāng)?shù)亍倍恰翱h級衛(wèi)生行政部門”。
由此,本文要緊扣重大傳染病疫情危機應(yīng)對的主題,從最壞角度設(shè)想,在已經(jīng)構(gòu)成全國蔓延或可能蔓延的條件下,應(yīng)該如何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能才能構(gòu)成對法律的最佳之解釋。
在本文看來,中央政府應(yīng)該根據(jù)“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原則”,重點履行五項職能:第一,建構(gòu)標準;第二,合法性控制;第三,階段轉(zhuǎn)折點變化的內(nèi)部判斷與決策;第四,組織要素網(wǎng)格化搭建;第五,獨立干預(yù)與監(jiān)督。地方政府則根據(jù)“屬地管理原則”重點履行:第一,組織裁量;第二,信息管理;第三,預(yù)警管制與應(yīng)急管制;第四,危機狀態(tài)下的公共服務(wù);第五,在地協(xié)調(diào)與異地協(xié)作這五項職能。
(二)中央政府職能的法律解釋
第一,建構(gòu)標準。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結(jié)構(gòu)化存在與“抽離化的機制”治理(disembedding mechanism)。所謂結(jié)構(gòu)化,也就是現(xiàn)代社會關(guān)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xiàn)一種模式化的特性,通過將這種模式從具體情境中抽離出來加以穩(wěn)定保障,就能實現(xiàn)“遠距離的治理”(governance at distance)。〔54〕See A.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olity Press1984,p.285.而有效的遠距離治理對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避免“天高皇帝遠”,確保無論何級地方政府都按照標準化、抽象化的行為模式統(tǒng)一行動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因此,一個有權(quán)威的中央政府必須通過事前建立標準并在恰當(dāng)時候發(fā)出具體指令,確保各級政府按照規(guī)定動作和模式行為。我們討論的這兩部法律就都遵循“預(yù)備”“監(jiān)測與預(yù)警”“反應(yīng)與應(yīng)對”(信息管理與應(yīng)急措施)“恢復(fù)與重建”基本結(jié)構(gòu)來規(guī)范各級政府行為,然而每一個階段具體的指標必須要靠中央政府來建設(shè),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規(guī)范性框架。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規(guī)定“按照國務(wù)院規(guī)定的或者國務(wù)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規(guī)定的內(nèi)容、程序、方式和時限報告”就是將屬地信息報告責(zé)任標準化、結(jié)構(gòu)化。又如該法第60條規(guī)定“國務(wù)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會同國務(wù)院有關(guān)部門,根據(jù)傳染病流行趨勢,確定全國傳染病預(yù)防、控制、救治、監(jiān)測、預(yù)測、預(yù)警、監(jiān)督檢查等項目。”盡管該法規(guī)定傳染病防控經(jīng)費屬于地方政府責(zé)任,但具體收費的項目卻是由中央政府來設(shè)定。《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yīng)急條例》第10條也規(guī)定“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jù)全國突發(fā)事件應(yīng)急預(yù)案,結(jié)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本行政區(qū)域的突發(fā)事件應(yīng)急預(yù)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預(yù)案成為各地預(yù)案的框架性規(guī)定。中央政府這種組織功能本質(zhì)上是一種調(diào)控行政,〔55〕同前注〔4〕,施密特?阿斯曼書,第205頁。通過綜合性地適用法律,來形塑具體政府可能的行為空間,確保個別性的機制被大型的制度框架所設(shè)定。
在中國的法律里強調(diào)這種職能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意義,就是因為“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體制存在,非常容易出現(xiàn)危機防控中的地方碉堡化與地方割據(jù),最后因為各自為政的地方保護而阻礙危機有效應(yīng)對。這種地方碉堡化與割據(jù)表現(xiàn)在如下方面:第一,“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容易帶來權(quán)力清單不明確、管控處置標準隨意。例如,根據(jù)《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法》第8條,從中央到縣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都可以設(shè)立指揮部,集中行使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最高權(quán)力,這樣必然會影響制度設(shè)計初衷,出現(xiàn)權(quán)力效應(yīng)遞減和應(yīng)對標準分化。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就出現(xiàn)了有些地方指揮部隨意發(fā)布命令,設(shè)定差異極大的管控標準等亂象;〔56〕參見《疫情防控越吃勁,越要堅持依法防疫》,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10/c_1125555129.htm,2020年2月10日訪問。第二,“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誘發(fā)狹隘的地方利益至上,導(dǎo)致本應(yīng)互相協(xié)同的危機應(yīng)對成為各自為政的惡性地方競爭;〔57〕本次疫情防控中發(fā)生的云南大理州政府截留其他省份的救災(zāi)物資引發(fā)媒體軒然大波正是地方割據(jù)引發(fā)惡性競爭的典型表現(xiàn)。參見《大理截留防疫口罩危害防疫大局此風(fēng)不可長》,http://news.chengdu.cn/2020/0206/2098012.shtml,2020年2月6日訪問。第三,“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客觀上不利于整體防控疫情,統(tǒng)籌兼顧。傳染病在全國沒有被控制前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從整體形勢出發(fā)進行資源調(diào)配,根據(jù)全國中位水平合理厘定管控措施的種類、幅度、廣度和強度并要求地方動態(tài)調(diào)整,防止地方治理能力和公共保障能力差異帶來的顧此失彼,否則必將出現(xiàn)中心疫區(qū)的波浪式接替,疫情高峰在各地此起彼伏,結(jié)束疫情變得曠日持久。
第二,合法性控制。由于重大傳染病是一種社會無差別性危機,防治既要依賴每一個人,又須監(jiān)管每一個人,《傳染病防治法》的起草說明非常好地揭示出這個悖論式關(guān)系:“傳染病威脅的對象是整個社會,因而防治傳染病也應(yīng)當(dāng)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zé)任。為此,對防治傳染病這項社會性很強的工作,必須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確公民、社會有關(guān)組織和政府有關(guān)部門的責(zé)任,并依法進行社會管理。”〔58〕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的《傳染病防治法》起草說明。為了克服原子式的個體不好被監(jiān)管的弊端,防疫期間整個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必然提高,每個人都被編織、包圍到各種危機應(yīng)對的組織之中,疫情之下幾乎沒有“原子式個人”的存在,這必然加劇組織社會學(xué)上早已洞察到的“組織及寄生于其上的科層制對個人自由與權(quán)利的壓制”。〔59〕[法]克羅齊埃:《法令不能改變社會》,張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在“屬地管理”的規(guī)則下,這種壓制與侵犯必然主要出現(xiàn)在地方政府。美國法上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國家安全名義下對公民權(quán)利的侵犯不僅僅表現(xiàn)在聯(lián)邦機構(gòu)的行為,各州政府和地方管理機構(gòu)都會通過立法性規(guī)則、行政指令侵犯憲法上的公民權(quán)利。〔60〕See M.Waxman,NATIONAL SECURITY FEDERALISM IN THE AGE OF TERROR,STANFORD LAW REVIEW (2012)[Vol].64,p.291.很多州政府在啟動相應(yīng)級別響應(yīng)后會為了更有效地實施應(yīng)急方案而對公民的人身、場所、行動采取各種嚴厲的限制措施。〔61〕See Bruce R.Lindsay: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 Brief Introduction,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2,p.11.我們會發(fā)現(xiàn),重大傳染病危機應(yīng)對極容易讓社會籠罩在福柯和阿甘本所謂的“生命政治”之下,每個人成為潛在的“赤裸之人”。〔62〕參見[法]米歇爾?福柯:《規(guī)訓(xùn)與懲罰》,劉北成等譯,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27頁;參見[法]米歇爾?福柯:《領(lǐng)土、安全與人口》,錢翰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6頁;參見[意大利]吉奧喬?阿甘本:《例外狀態(tài)》,薛熙平譯,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頁。由此,中央政府的重要職能就是嚴格根據(jù)憲法和法律對地方政府的應(yīng)急管制行為進行合法性控制,必須通過發(fā)布或督促省級政府制定統(tǒng)一的行政手冊、指南,建立公開發(fā)布的行政裁量基準,并啟動有效問責(zé)機制對地方政府進行監(jiān)督。〔63〕例如司法部即2月24日出臺《關(guān)于推動嚴格規(guī)范公正文明執(zhí)法 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意見》加以規(guī)范。
第三,階段轉(zhuǎn)折點變化的內(nèi)部判斷與決策。危機管理學(xué)告訴我們,政府對于危機處在何種階段的判斷非常重要,有必要采取一定分析手段確定不同階段趨勢變化的轉(zhuǎn)折點。〔64〕See Karl.Weick K.M.Sutcliffe,Managing the Unexpected: Assuring High Performance in an Age of Complexity,Jossey-Bass2001,p.109.《傳染病防治法》在法教義學(xué)上實際上確立了三種依次出現(xiàn)的狀態(tài):日常預(yù)備與監(jiān)測的潛在出現(xiàn)狀態(tài)(第二章預(yù)防)、疫情出現(xiàn)與確認狀態(tài)(第三章報告、通報和公布與第四章的常規(guī)應(yīng)對措施)、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狀態(tài)(以甲類、乙類傳染病爆發(fā)、流行為轉(zhuǎn)折節(jié)點)。由此,政府需要根據(jù)信息,基于各種考慮作出處于何種狀態(tài)的決策,尤其是判斷出現(xiàn)爆發(fā)、流行情況后,就進入到《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的規(guī)范領(lǐng)域,需采取各種更加強硬的應(yīng)急措施。這里涉及到兩個重要的組織法因素:第一,確立特定組織成立、變更乃至撤銷(對于臨時指揮機構(gòu)和議事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的法律狀態(tài);第二,確定組織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根據(jù)《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yīng)對條例》第3條和第4條,國務(wù)院應(yīng)急指揮部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yīng)急指揮部的成立時間要件是“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發(fā)生后”,如何判斷重大傳染病疫情發(fā)生?信息應(yīng)自下向上迅速流動,地方各級政府也可以履行報告、互相通報等職能,但內(nèi)部決策程序則應(yīng)該集中在中央政府,對疫情是否構(gòu)成爆發(fā)、流行,甚至蔓延到其他省級行政區(qū)劃的判斷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內(nèi)部決策。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政府的決策在這里是一種內(nèi)部程序,它不會必然對外發(fā)生直接法律效力,我們需要區(qū)分內(nèi)部判斷—決策權(quán)和下級政府據(jù)此決策行使的決定與宣布權(quán);同時,中央人民政府及有關(guān)部門享有決策權(quán)也不能豁免地方政府的預(yù)警和信息管理義務(wù)。
第四,組織要素網(wǎng)格化搭建。中央政府第三個重要職能就是促進權(quán)力、信息、資源各種組織要素的有效傳遞、流動,形成四通八達,互通有無的國家應(yīng)急網(wǎng)絡(luò)。從行政法學(xué)上來說,中央政府促成組織要素合作與有機整合的職能是一種“轉(zhuǎn)介行政”,〔65〕同前注〔6〕,大橋洋一書,第217頁。政府通過搭建平臺,創(chuàng)造條件,傳遞信息來促成分散的組織要素有機流動與整合。例如《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法》第26條規(guī)定的“國家救援隊伍”,以及國務(wù)院聯(lián)防聯(lián)控機制在全國范圍對醫(yī)療人員、物質(zhì)裝備的布局、安排、調(diào)整,都是轉(zhuǎn)介行政的表現(xiàn)。中央政府履行這項職能的正當(dāng)性就在于它的“高位協(xié)調(diào)”能力與宏觀洞察能力,能夠超越局部利益和視角,通過分析全局來作出最優(yōu)的安排。當(dāng)然,這種工作在組織社會學(xué)上也經(jīng)常被提醒要注意組織的“有限理性”問題,中央政府并不是全能的,因此好的轉(zhuǎn)介行政應(yīng)該盡量避免直接干預(yù)要素流動,是為流動創(chuàng)造條件,促成合作,〔66〕同前注〔38〕,A.Boin、M.Busuioc、M.Groenleer文,第 133 頁。而不是回到計劃經(jīng)濟的指令模式之下,這就需要中央政府應(yīng)該更多運用市場的手段或為市場手段發(fā)揮要素配置功能提供好的政策環(huán)境。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中央政府提出防疫與恢復(fù)經(jīng)濟社會秩序需要統(tǒng)籌兼顧,尤其是優(yōu)先允許生產(chǎn)經(jīng)營醫(yī)用防護物質(zhì)的企業(yè)復(fù)工、復(fù)產(chǎn),就是為市場配置要素提供政策保障的轉(zhuǎn)介行政之典型表現(xiàn)。
第五,獨立干預(yù)與監(jiān)督。為了緩解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效監(jiān)管地方應(yīng)對危機的行為,尤其是督促地方按照標準化和合法性要求來行動,中央政府還必須具有獨立干預(yù)和監(jiān)督的職能,在行政法學(xué)上表現(xiàn)為它可以創(chuàng)造出一些“獨立行政空間”,跳脫出層級行政規(guī)定的權(quán)力逐級流動規(guī)則和嚴格行政隸屬關(guān)系。〔67〕同前注〔4〕,施密特?阿斯曼書,第227頁。“獨立行政空間”是為了克服權(quán)力和信息傳遞效率逐級遞減的理性官僚制弊端而出現(xiàn)的,在理想的組織狀態(tài)里,權(quán)力應(yīng)該至上而下地高效傳遞,以確保高層意圖準確執(zhí)行;信息則應(yīng)該自下而上高效流動,以確保高層掌握實際情況、形成正確決策意圖。然而,單一制框架里的中央-地方關(guān)系總是存在“委托失靈”,地方政府懸置中央法律與政策,隱瞞信息,對上級決策陽奉陰違,都難以避免,這在危機應(yīng)對情況下必然嚴重干擾大局。中央政府建立垂直的獨立干預(yù)和監(jiān)督體系就非常重要。例如,《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43條規(guī)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宣布有關(guān)地區(qū)進入預(yù)警期,同時向上一級人民政府報告,必要時可以越級上報”,《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jiān)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第19條規(guī)定“獲得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相關(guān)信息的責(zé)任報告單位和責(zé)任報告人……具備網(wǎng)絡(luò)直報條件的要同時進行網(wǎng)絡(luò)直報,直報的信息由指定的專業(yè)機構(gòu)審核后進入國家數(shù)據(jù)庫。”這里規(guī)定的“越級上報”和“網(wǎng)絡(luò)直報國家數(shù)據(jù)庫”都是“獨立行政空間”,有意打破層級行政的秩序,創(chuàng)造出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直接干預(yù)和監(jiān)督。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中央政府還借助新媒體,例如在騰訊微信開辟群眾在防疫期間生活困難的線索提供功能,在人民網(wǎng)上直接開通地方防疫中問題線索舉報專欄。
(三)地方政府職能的法律解釋
第一,組織裁量。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中央標準化要求與合法性控制前提下結(jié)合本地實際情況進行組織法上的精準裁量,避免危機應(yīng)對中的“消極裁量”。危機管理學(xué)研究者即提出:“一方面,危機增強了在戰(zhàn)略層面上強有力的領(lǐng)導(dǎo)和中央控制的必要性;另一面,它凸顯了在操作一級地方自治和靈活性的需求。地方當(dāng)局在處理危機方面有多大的自主權(quán)是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中央限制很大,只允許地方當(dāng)局擁有有限的回旋余地,地方組織的即興發(fā)揮就很困難。當(dāng)下面臨的挑戰(zhàn)是如何在不削減中央責(zé)任的情況下形成一套分散式響應(yīng)機制。”〔68〕同前注〔38〕,A.Boin、M.Busuioc、M.Groenleer文,第 142 頁。
在我國“中央統(tǒng)一管理”與“屬地負責(zé)”的雙重要求下,如何建立統(tǒng)一部署下的地方“分散式響應(yīng)機制”,尤其需要解決如下問題:第一,賦予地方各級政府在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應(yīng)急預(yù)案形成空間,但必須符合國家的基本標準和框架;第二,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確定和調(diào)整本行政區(qū)域應(yīng)急響應(yīng)級別的裁量權(quán),但必須接受中央政府監(jiān)督或取得同意;第三,根據(jù)各地實際情況確定組織形式及介入危機的程度。例如根據(jù)《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條例》第37條規(guī)定的“群防群治”,各地社區(qū)、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社會管理服務(wù)機構(gòu)(如物業(yè)公司)這些沒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組織都分享或參與到危機應(yīng)對中,但必須根據(jù)地方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需要啟動這些組織以及委托它們的具體公共任務(wù),也就是說對于社會的組織化程度需要地方政府根據(jù)裁量來具體判斷,以確保既有效應(yīng)對危機,也不會因為組織化程度過高而不可避免限制公民的權(quán)利與自由;第四,合理進行組織要素的裁量。例如是否根據(jù)法定權(quán)力對外發(fā)布本行政區(qū)域的預(yù)警信息,是否請求其他地區(qū)或國家的資源支持以及具體的內(nèi)容。
地方政府的組織裁量也必須受到控制,得到治理,基于三個理由:一是民主正當(dāng)性要求。憲法規(guī)定的民主原則尤其可以約束那些沒有明確行政法主體地位的組織、未經(jīng)民主程序作出、尤其涉及到對公民權(quán)利義務(wù)處分的行為,防止危機應(yīng)對演變?yōu)榈胤焦杨^政治;〔69〕參見[英]克雷格:《英國和美國的公法與民主》,畢紅海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頁。二是可問責(zé)性。問責(zé)的本質(zhì)是負責(zé)公共事務(wù)的組織必須就決定或措施作公開說明,〔70〕See M.Bovens,“Analyzing and Assessing Accountabil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European Law Journal,vol.13,no.4,2007,p.450.也就意味著組織裁量可以通過聽取意見、說明理由、公開透明等正當(dāng)程序加以治理,危機狀態(tài)并不是取消程序,相反是要通過法律和制度將例外規(guī)范化,危機治理常態(tài)化與程序化;三是治理有效性。不受控制的裁量往往無法有效實現(xiàn)行政目的,要么導(dǎo)致消極裁量,要么導(dǎo)致裁量濫用,在裁量收縮為零的時候也會出現(xiàn)違法裁量。因此,有必要建立由省級政府制定和發(fā)布的裁量基準,編制有關(guān)手冊或指南,理性引導(dǎo)地方和基層政府正確運用裁量權(quán)。
第二,信息管理。“屬地管理”的核心是信息管理,因為疫情發(fā)生在地方,盡管往往決斷在中央。地方政府有效的信息管理不僅對于在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落實“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具有重要意義,是統(tǒng)一作出監(jiān)測預(yù)測、預(yù)警、應(yīng)對等決斷的基本依據(jù),也對于中央統(tǒng)籌安排全國防疫,準確判斷危機所處階段及轉(zhuǎn)折節(jié)點具有關(guān)鍵意義,因此《傳染病防治法》《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及相關(guān)法規(guī)、規(guī)章都對地方政府的信息管理進行了詳細規(guī)定。在法教義學(xué)上值得重點討論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信息管理權(quán)限,重點需要解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quán)限劃分和地方政府內(nèi)部信息管理的權(quán)限劃分兩個問題。
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quán)限上,傳統(tǒng)單一制理論認為地方權(quán)力來源于中央,但地方政府的信息管理權(quán)卻具有固有性和當(dāng)然性,未必是中央權(quán)力的委托行使。這是因為對于傳染病疫情來說,沒有抽象意義上的“中央信息”,疫情信息一定是散點出現(xiàn),從而具有集成的特點,而集成也就意味著是“邊緣決定中央”而不是相反。〔71〕同前注〔5〕,Gilpin、Murphy書,第 75頁。因此,法律應(yīng)賦予地方政府在信息管理上相當(dāng)?shù)男纬勺杂桑荒鼙粍咏邮苤醒胫噶畈拍苄惺剐畔⒐芾淼臋?quán)力。在地方政府內(nèi)部信息管理權(quán)力劃分上,根據(jù)我國傳染病防治規(guī)范體系,地方政府享有如下信息管理權(quán)力:(1)信息采集、分析與監(jiān)測權(quán)(《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第18條第二項,《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37條到第41條)。信息采集、分析與監(jiān)測屬于日常風(fēng)險預(yù)防手段,在很多國家應(yīng)急法律中屬于“危機緩釋”階段,緩釋意味著對各種可能出現(xiàn)的風(fēng)險(與物理因素易受潛在破壞性事件影響有關(guān))進行更高層次的認識和更為系統(tǒng)的分析。〔72〕同前注〔3〕,Bruce R.Lindsay文,第 10頁。這毫無疑問要以信息采集和監(jiān)測為前提,且應(yīng)該是各級地方政府都擁有的權(quán)力。(2)信息預(yù)警權(quán)(《傳染病防治法》第19條省級政府的權(quán)力、《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42、43條)。預(yù)警屬于風(fēng)險交流,它對遏制傳染病爆發(fā)、流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必要仔細區(qū)分各級地方政府的具體職責(zé)。根據(jù)《傳染病防治法》第19條規(guī)定“國務(wù)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和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jù)傳染病發(fā)生、流行趨勢的預(yù)測,及時發(fā)出傳染病預(yù)警,根據(jù)情況予以公布”,這里區(qū)分了“預(yù)警發(fā)出”和“預(yù)警公布”。后者是面向公眾,前者結(jié)合第20條規(guī)定“地方人民政府和疾病預(yù)防控制機構(gòu)接到國務(wù)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發(fā)出的傳染病預(yù)警后……”進行體系解釋可知,“預(yù)警發(fā)出”屬于內(nèi)部風(fēng)險交流。這兩項權(quán)力根據(jù)該法都屬于國務(wù)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和省級人民政府,但《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43條“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fā)布相應(yīng)級別的警報,決定并宣布有關(guān)地區(qū)進入預(yù)警期”卻賦予了縣以上各級地方政府均有預(yù)警發(fā)布和宣布進入預(yù)警期的權(quán)力,二者是否沖突?在本文看來,二者并不沖突,《傳染病防治法》第19條只是對省級政府的預(yù)警權(quán)作出規(guī)定并沒有明確排除縣級地方的預(yù)警權(quán),而《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43條規(guī)定的“發(fā)布相應(yīng)級別警報”“宣布有關(guān)地區(qū)”的限制性規(guī)定說明縣以下政府只對于“一般級的突發(fā)事件”在“縣級行政區(qū)域”內(nèi)享有預(yù)警發(fā)出和發(fā)布權(quán),它無權(quán)發(fā)布其他級別事件、其他行政區(qū)域,更不能發(fā)布全省的預(yù)警信息,與省級政府統(tǒng)一發(fā)布本省的預(yù)警信息并不矛盾,相反正符合我國突發(fā)公共事件“分級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和傳染病防治需要最大程度“切斷傳染源”之目的解釋要求。縣級政府應(yīng)盡最大可能合理履行該項職責(zé)。(3)信息報送、通報權(quán)(《傳染病防治法》第35條、《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第43條),信息報送是在政府上下級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通報根據(jù)法律則是橫向各級政府部門之間,以及不同地域之間的政府進行信息交流。(4)重大傳染病疫情發(fā)布權(quán)(《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這項權(quán)力定位于“傳染病爆發(fā)、流行時”,它與預(yù)警權(quán)不同,預(yù)警只是對一種可能趨勢的警告,而此條規(guī)范的是已成為現(xiàn)實的突發(fā)公共事件,因此這個時候省以下地方政府不能再依據(jù)《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yīng)對法》第43條規(guī)定的預(yù)警權(quán)來發(fā)布信息,只能依據(jù)《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由國家衛(wèi)生行政管理部門或授權(quán)的省級政府發(fā)布本行政區(qū)域的疫情。我們要區(qū)分兩種發(fā)布權(quán):預(yù)警發(fā)布權(quán)和疫情宣布權(quán),前者按照“分級的統(tǒng)一管理”可由縣以上人民政府在各自區(qū)域里發(fā)布,最大程度提醒民眾注意防護,將潛在危機扼殺于萌芽中;后者只能集中于中央政府部門或省級人民政府。如此制度設(shè)計體現(xiàn)出立法者既要最大程度防備風(fēng)險,又要最大程度避免社會恐慌的如履薄冰心態(tài)。
第三,預(yù)警管制與應(yīng)急管制。不同國家的應(yīng)急法律都規(guī)定了地方政府的管治權(quán),例如在美國,以各個州是否宣布“緊急狀態(tài)”為界限,州政府享有的管治權(quán)在種類、強度、持續(xù)程度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宣布緊急狀態(tài)之前,管制手段更多基于信息搜集、重點人群和場所管理,在進入緊急狀態(tài)后就包括更嚴格的區(qū)域管理、行動和隱私限制、資源調(diào)動與分配、各種專業(yè)人才的啟動等。〔73〕同上注。我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律體系也可以分為預(yù)警管制和應(yīng)急管制兩項重要的地方職責(zé)。預(yù)警管制主要體現(xiàn)在《傳染病防治法》第二章所規(guī)定的日常監(jiān)測、預(yù)防接種、公共場所設(shè)施衛(wèi)生改造和各種專項防治。《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也規(guī)定了監(jiān)測、分析、通報等措施。應(yīng)急管制則在兩部法律里都規(guī)定為傳染病出現(xiàn)疫情或突發(fā)公共事件確實發(fā)生以后的各種手段。從組織法上來考慮,有必要明確不同組織的權(quán)限,例如各種中間行政組織,社區(qū)、村民小組、保安公司、物業(yè)部門,各種企事業(yè)單位,是否能夠獨立行使強制權(quán),如何明確其權(quán)力清單,恐怕還必須在法教義學(xué)上鏈接到《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作體系化思考,以避免管制碎片化和對公民權(quán)利的侵犯。
第四,危機狀態(tài)下的公共服務(wù)與一般秩序維護。重大傳染病危機作為一種典型的社會整體性危機,其損害的法益遠遠不止是人民的生命健康權(quán),而是在疫情持續(xù)期間對社會經(jīng)濟秩序的全面沖擊和破壞,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履行在此期間的公共服務(wù)和一般秩序維護的職能,這往往是中央政府無法直接行使的權(quán)力。在危機管理學(xué)上,這種公共服務(wù)與秩序維護在危機管理學(xué)上又被稱為“善后政治”,它強調(diào)政府必須在應(yīng)對危機的同時維持或重建社會秩序,在根本上說是民主正當(dāng)性原則和善治理念的必然要求。〔74〕See Perrow,The Next Catastroph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159.因此,地方政府在確保社會正常生活用品供應(yīng),交通醫(yī)療用水用電等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社會治安管理維護,打擊哄抬物價、假冒偽劣等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地協(xié)調(diào)與異地協(xié)作。危機應(yīng)對的系統(tǒng)性還必須強化地方政府的在地協(xié)調(diào)與異地協(xié)作職能。這里既包括地方政府不同組織形式之間的協(xié)調(diào),也包括屬地政府與在地建制的軍隊,地方政府與中央在地的機關(guān)、企業(yè),政府與屬地企業(yè)、社會組織的協(xié)調(diào)。例如在《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法》的框架里,我們就必須妥善處理地方人民政府與屬地指揮部的關(guān)系,該法從第48條到第53條賦予了地方各級政府“履行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職責(zé)或者組織處置突發(fā)事件”的職能,并具體規(guī)定了其針對人身、場所、物質(zhì)、信息的應(yīng)急措施甚至強制措施,那么同級指揮部是否也享有這些權(quán)力?如二者權(quán)力行使發(fā)生沖突,內(nèi)容程序不一致情況下如何處理,本文認為,指揮部更多應(yīng)該定位于決策和統(tǒng)籌機構(gòu),應(yīng)該盡量減少微觀管制權(quán)力的運用,因其畢竟缺乏明確的組織法上授權(quán),各種具體管制措施應(yīng)該依照單行法交由政府及工作部門分別實施。對于其發(fā)布的管制公告等文件,嚴格說屬于行政法上的計劃行政,是綜合運用多部法律對相關(guān)問題在同一主題下作出的一攬子決定,也應(yīng)該要接受合法性審查,其在存續(xù)期間的行為引發(fā)法律爭議,應(yīng)該以指揮部自身作為行政復(fù)議的被申請人、訴訟被告和行政賠償?shù)牧x務(wù)機關(guān)。若在撤銷后引起法律爭議,則應(yīng)該由宣布撤銷它的地方行政機關(guān)來承擔(dān)相應(yīng)法律后果。
地方政府還應(yīng)該履行異地協(xié)作職能,聯(lián)邦制條件下,聯(lián)邦成員單位可以根據(jù)固定或臨時約定、協(xié)議等方式尋求互助,〔75〕同前注〔3〕,Bruce R.Lindsay文,第 10頁。我國體制里主要是定位于中央高位協(xié)調(diào),例如本次疫情防控中采取“省包市”的方式進行對點支援,將來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發(fā)展出在教義學(xué)上更為穩(wěn)定、成熟、權(quán)利義務(wù)責(zé)任明確的法律類型,充分運用區(qū)域互助協(xié)議等制度框架來實現(xiàn)異地協(xié)作的規(guī)范化與常態(tài)化。
四、組織結(jié)構(gòu)優(yōu)化:政府與社會
(一)層級化與網(wǎng)格化
組織形式結(jié)構(gòu)優(yōu)化除了涉及傳統(tǒng)層級行政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劃分,還涉及政府與社會的組織形式關(guān)系。在重大傳染病疫情應(yīng)對中,由于組織形式的分化,層級行政的動搖,這個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也非常重要。縱觀我國的相關(guān)法律,這個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主要體現(xiàn)為兩個類型:層級化與網(wǎng)格化,理性官僚制與戰(zhàn)時體制。
傳統(tǒng)行政法認為,危機應(yīng)對主要是政府職責(zé),而政府是按照層級架構(gòu)自上而下形成的組織,形成穩(wěn)定的命令-服從關(guān)系,是一種縱向結(jié)構(gòu)。但現(xiàn)代社會理論告訴我們,公共危機應(yīng)對在現(xiàn)代性條件下,必然會催生以橫向平等尊重,又互相合作、協(xié)同與依賴的網(wǎng)格化結(jié)構(gòu)。
按照吉登斯、貝克等社會理論家的認識,工業(yè)文明催生的現(xiàn)代社會具有反思理性的特征,所謂反思理性是“一種有條理的懷疑”之理性,它是跨越各個社會組織的政治聯(lián)結(jié),〔76〕同前注〔23〕,A.Giddens書,第 257頁。確保社會組織之間處在互相監(jiān)測、學(xué)習(xí)的狀態(tài)。每一個人都保持了反思的特性,尤其是信息社會的到來,政府壟斷資訊與知識被打破,層級行政必然被沖擊。危機應(yīng)對網(wǎng)格化的第二個重要原因在于以科學(xué)話語為代表的“次政治(sub-politics)”現(xiàn)象出現(xiàn)。〔77〕同前注〔20〕,貝克文,第 239 頁。專家系統(tǒng)在危機應(yīng)對中具有特殊的話語權(quán),類似于重大傳染病防控,不借助社會中的專家系統(tǒng),包括疾控、醫(yī)療、專業(yè)救援隊伍等資源,政府根本無法開展相應(yīng)工作。
社會網(wǎng)格化的存在則意味著去等級制,更松散與靈活,強調(diào)知識、信息、資源的共享、互補、協(xié)同和對話,由此,兩種組織形式必然會產(chǎn)生摩擦,以政府為代表的層級組織經(jīng)常會吸納網(wǎng)格結(jié)構(gòu),將其成為附屬和補充,導(dǎo)致網(wǎng)格化社會組織被嵌入到“等級制度的陰影”中。這里我們尤其需要關(guān)注的是政府與專家系統(tǒng)在疫情防控中的關(guān)系。
政府是權(quán)力系統(tǒng),但需要借助獨立的專家系統(tǒng)在疫情監(jiān)測預(yù)警、確診救治、特效藥疫苗開發(fā)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專家系統(tǒng)具有專業(yè)研究能力,但很多時候缺乏影響公眾的權(quán)力,如何有效平衡二者是憲法學(xué)和組織學(xué)都要共同關(guān)注的課題。美國在司法審查發(fā)展出一個基本框架:需要區(qū)分對“科學(xué)家自主權(quán)的限制”還是“對科學(xué)組織或機構(gòu)自主權(quán)的限制”,是“對科學(xué)內(nèi)容的限制”還是“對科學(xué)過程的限制”,是微觀管理VS普遍監(jiān)督。〔78〕See D.Resnik,Playing Politics with Science: Balancing Scientific Independence and Government Overs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8.對科學(xué)家自主權(quán)的限制會被認為嚴重侵犯《憲法修正案》第1條保護的言論自由,而如果基于特殊國家安全考慮且經(jīng)受住成本-收益風(fēng)險,則可能正當(dāng)化對科學(xué)組織的限制。對科學(xué)內(nèi)容的限制也是比較嚴重的,但如果按照有關(guān)法律出于保護生物安全、大眾健康等法益而限制科學(xué)的過程則也可能不違反憲法。對具體科學(xué)活動與環(huán)節(jié)的監(jiān)管也比制定一般性約束條件要更有可能冒犯憲法。因此,限制的對象、理由、方式、程度實際上構(gòu)成了政府是否干預(yù)獨立專家系統(tǒng)的四條法教義學(xué)標準。
在中國的危機應(yīng)對中,法律并沒有對專家個人作出明確限制,但也存在限制機構(gòu)、限制過程和進行具體干預(yù)的情況。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規(guī)定“疾病預(yù)防控制機構(gòu)、醫(yī)療機構(gòu)和采供血機構(gòu)及其執(zhí)行職務(wù)的人員發(fā)現(xiàn)本法規(guī)定的傳染病疫情或者發(fā)現(xiàn)其他傳染病暴發(fā)、流行以及突發(fā)原因不明的傳染病時,應(yīng)當(dāng)遵循疫情報告屬地管理原則,按照國務(wù)院規(guī)定的或者國務(wù)院衛(wèi)生行政部門規(guī)定的內(nèi)容、程序、方式和時限報告”,《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jiān)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第19條規(guī)定“接到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相關(guān)信息報告的衛(wèi)生行政部門應(yīng)當(dāng)盡快組織有關(guān)專家進行現(xiàn)場調(diào)查”、第23條規(guī)定“各級衛(wèi)生行政部門應(yīng)當(dāng)組織疾病預(yù)防控制機構(gòu)等有關(guān)領(lǐng)域的專業(yè)人員,建立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隊伍”,可見從文義解釋來看,專家系統(tǒng)并沒有獨立的調(diào)查權(quán)、判斷權(quán)和發(fā)表權(quán),給實踐中政府基于各種考慮過濾信息、錯誤判斷、遲延發(fā)布等帶來了可能。〔79〕相關(guān)事實披露參見《投資7.3億打造的傳染病網(wǎng)絡(luò)直報系統(tǒng)為何失靈28天》:載《財經(jīng)》,2020年2月27日。
我們應(yīng)該根據(jù)限制對象是機構(gòu)而不是個人,尊重個人在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和科研探索自由,對專業(yè)人士發(fā)表的提示予以法律保護;通過目的解釋要基于重大正當(dāng)公共利益考慮才能限制專業(yè)機構(gòu)的研究過程,“組織研究”不能吸收“獨立研究”,研究過程和結(jié)論應(yīng)該保持一定范圍、程度和方式的獨立性與發(fā)表自由,政府應(yīng)該采取更多橫向合作而不是縱向命令的方式來優(yōu)化與專家組織的關(guān)系。
(二)戰(zhàn)時體制與理性官僚制
政府與社會需要優(yōu)化的第二個結(jié)構(gòu)是“戰(zhàn)時體制”與“理性官僚制”間的關(guān)系。《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法》和《傳染病防治法》既建立了嚴格的理性官僚制,強調(diào)政府層級有序、專業(yè)分工;又通過“鼓勵社會動員”“依靠群眾”“群防群治”等條款建立起戰(zhàn)時體制,二者存在很大差異與緊張關(guān)系:第一,“力量下沉”與“機關(guān)化”之間的矛盾。戰(zhàn)時體制強調(diào)基層和一線力量,屬于全民動員,必然強化社區(qū)、街道責(zé)任,而官僚制以綜合管理為主,執(zhí)法隊伍力量不足,這在疫情防控中必然導(dǎo)致基層力量薄弱而疲憊不堪,而機關(guān)運轉(zhuǎn)則鞭長莫及;第二,有效作戰(zhàn)與專業(yè)劃分之間的矛盾。戰(zhàn)時體制強調(diào)打破專業(yè)分工,統(tǒng)一號令,理性官僚制則強調(diào)守土有責(zé),專業(yè)分權(quán)。防疫中的戰(zhàn)時體制是對專業(yè)分工的極大摧毀,“干部下社區(qū)、沉一線”成為必然;第三,社會組織化與自發(fā)秩序的矛盾,戰(zhàn)時體制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組織化程度,這也是對理性官僚制恪守政府與社會邊界,給社會保留自發(fā)秩序有效應(yīng)對危機帶來矛盾。
更嚴重的是,戰(zhàn)時體制與官僚制之間也會出現(xiàn)組織共謀和組織趨同,那就是地方政府默許基層組織進行模仿,建立自己科層制,制定規(guī)則、發(fā)布措施、組織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就必然加劇標準泛化、濫用權(quán)力、地方利益至上演變?yōu)楦髯愿顡?jù)的基層單位利益至上,打亂了組織形式之間的統(tǒng)籌兼顧與穩(wěn)定秩序,破壞了應(yīng)對危機的整體合力。
因此,戰(zhàn)時體制與官僚制之間應(yīng)該保持平衡,建立起合理區(qū)隔又互相協(xié)作的結(jié)構(gòu),政府應(yīng)該通過開放一定的社會自助、互助空間進行社會動員,同時要起到托底責(zé)任和監(jiān)督責(zé)任,對社會動員機制下的各種組織進行規(guī)模、權(quán)力、行為的有效合法性控制。
五、結(jié)語
重大傳染病危機應(yīng)對是現(xiàn)代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從行政組織法上來思考,我們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以組織形式為解釋對象,通過合理處理組織關(guān)系來有效配置組織要素的過程,從而實現(xiàn)行政組織的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對于法律來說,它從來不是白紙黑字的顯白語言,而具有意義深度,需要我們對其在特定標準下進行詮釋。我們也不能寄希望通過修改法律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在指導(dǎo)危機應(yīng)對的過程中,組織法作為具體行為的調(diào)控框架,必須結(jié)合具體的危機類型,在合法與有效的雙重價值觀指引下對組織規(guī)范作出最佳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