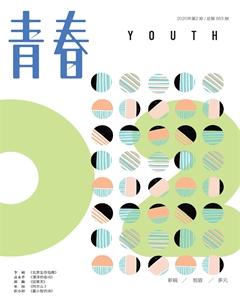懺悔錄
李麗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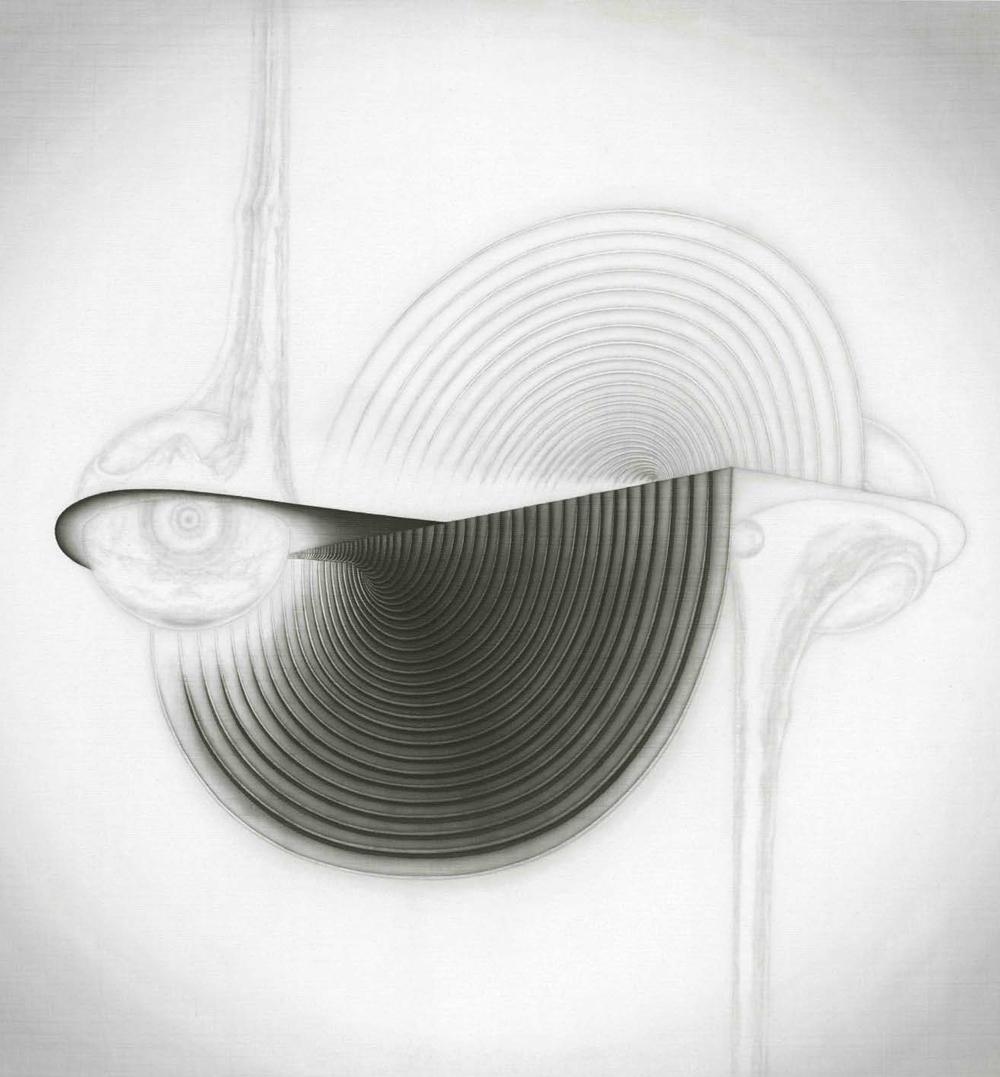
河池學院堆云文學社
廣西河池學院堆云文學社成立于2004年3月14日,前身是中文系團總支學生會主辦的《中文前沿》,該文學社是河池學院文傳院主辦并直接指導的純文學社團,曾獲得“全國人文百強社團”的稱號。自立社以來,有多名社員的文章發表在《廣西文學》《河池文學》《南丹文學》《丹鳳文學》《宜州文學》《麒麟》等刊物上。
人生總是被無數個有形的無形的洪流推著走,一旦泄洪,就沒有回旋的余地。我再也找不到能夠表達我歉意的方式,無數個夜晚,我躲進暗沉的夢里,當我開始懺悔,便偶爾有光亮透進來。那些光,并不敞亮,但柔和有如月光,我便知道,我的靈魂需要這樣一束光照耀。
寫給父親
我并不是一個擅長懷舊的人,除了刻骨銘心的,大體都模糊了。有關魚塘與竹排的記憶,多半是溫暖的。我的生命由水而來,母親懷我的那一年,為躲避抓超生的人,情急之下跳進村里的一汪魚塘,在水中憋著氣,就在母親以為撐不住時,那些人終于離開,我和母親逃過一劫,這才有了現在的我。我出生后,父親便承包了魚塘,它陪我走過人生最初的十三年。
每年夏天,是父母緊張而又忙碌的日子。因為農村的夏天經常停電,池塘里的魚在煩悶的夏季容易缺氧。為此,父親動手做了一條大大的竹排,每日空閑時就劃著竹排在魚塘中轉悠。我站在岸邊,望著竹排推著水波,水波又推著竹排。
“丫頭,上竹排來,我撐著你轉轉。”
“爸爸,我不敢。”他很少主動叫我,所以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拒絕了。
“不怕,有爸爸在。”父親固執地喊我,我還低著頭,夏天的熱風吹在我弱小的身體上。我記憶中是這樣的,傍晚的余暉與水交融著,波光蕩漾,有魚跳出水面,充滿了誘惑。
“好!”我鼓足了勇氣,跳上竹排。這是我少有的一次與父親一起撐竹排。
年復一年,它仿佛永遠年輕,而我,分分秒秒不同。
我喜歡走魚塘的石階,有時候蹲坐在泥上,有時候站著發呆。扒開雜草,它還是記憶里的老樣子,當我仔細聽著,仿佛還能聽見一些瑣碎的聲音:早點回來啊。曾經小小的我隔著一汪池塘,對經常外出的父親喊話,可是,這樣的生活我還能再過一遍嗎?
童年的日子,生活總是不富裕,但我們三兄妹卻沒有感到艱辛。父親常常一碗飯幾棵青菜果腹,長期勞累的生活和嚴重的營養不良使他患上了肝病,好在他一直按時喝草藥,每天還能生龍活虎地訓斥我們,我總以為他會一直這樣罵我們,直到老了說不動。但他還沒老,便得了肝癌,四十二歲就離開了。一夜之間,池塘就跟著荒廢了。
父親開始病重,是我讀初三那年的年三十,我們一家人窩在房間里看電視,我不記得當初看的是什么節目,只記得陸陸續續聽到父親咳嗽。我忙著看電視,沒有回過頭問候他一句。直到父親咳了血,家人才手忙腳亂地送父親去醫院,之后,我才開始陷入無盡的恐慌。
第二天父親終于回來了,大抵是看到了我的不安,不擅長微笑的父親伸出大手揉了揉我的頭發,笑笑說:“爸爸沒事,醫生說我的肝壞了,再換一個就可以了。”大抵是因為年輕,又或許是父親說沒事時的眼神過于淡定,他也從沒有說過謊,我便相信了他的話。
父親不善言辭,在最后的半年里,他換了一種方式與我告別。他開始變得挑剔,每每買回的果蔬,他總苛刻地讓我遵照先泡上半個小時、然后認認真真地洗上三遍的準則。他不允許我喝飲料,買了一箱箱的礦泉水堆在家里逼著我喝。我頂嘴,他便暴躁地吼我:“你已經不小了,這些東西都不健康,別讓我看到你生病,好嗎?”大概是因為父親最后那卑弱又無奈的兩個字,我開始服軟。但后來發生的一件事,讓我切實恨了他許久。父親放在桌面上的一張五十塊錢人民幣不見了,那天我剛好進過他房間拿東西。
父親認定是我拿的錢,問我:“為什么拿錢?想買什么東西,你可以先問我,我明明說過沒有經過別人同意之前,不要亂拿東西。”
父親不分青紅皂白地責問,使我氣昏了頭,我沖他大喊:“你憑什么認為是我拿的,你這個自以為是的偏執鬼。”
父親氣得直喘氣,他最看不慣孩子偷錢,小時候總是反復和我強調“小時偷針大時偷金”的老話。父親罰我在祠堂前跪下,但錢確實不是我拿的,我擔心他的身體,只能順從地跪著。直到母親回來,誤會才解開,是母親早上拿的錢,去集市買了些東西。知道真相的父親局促地和我道歉,他充滿希冀的目光看著我,等我的原諒。我扭過頭,回避了他。父親為了討好我,給我買了心心念念的兩條褲子,還買了從不允許我吃的零食。他不想把最后的時光浪費在跟我生氣上。
第二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晚,而我也漸漸地察覺出父親身體的異樣。化驗單、檢測報告可以藏得住,可是一個人的消瘦是真真切切表現出來的。端午節放假,我回到家時,太陽將要落盡。我清楚地記得那個傍晚,父親坐在院子里那個吱吱作響的椅子上,他削弱的身影,被風吹起的衣襟,在血紅的背景下,猶如一幅殘忍的畫影。
父親揮手示意我過去,我假裝沒看到,轉身跑上樓。跨上最后一級階梯時不小心摔倒,我的鼻血和眼淚同時流下來。我知道自己的舉動一定深深傷害了他,但不見他是我花了許多勇氣才做出的決定。我習得了父親身上所有的優點,樂觀、堅強、執拗,唯獨沒學會勇敢,我無法接受曾經偉岸的男人,此刻形同槁木的樣子。
爸爸彌留之際,留給我們兄妹三人一人一張五十元的人民幣,它很新,應該是剛從銀行取出來的。在生命僅存最后一點意識時,他留了一句話:作為父親,對不起。
我無法原諒自己。
那張五十元人民幣被我沉沉地壓在鐵皮盒里,每晚都會打開望一眼,它在我的指尖發出清脆的聲音。
一天晚上,我回房間躺著,照例打開鐵皮盒,眼前的景象讓我崩潰,幾近發瘋——它不見了。第二天找到“兇手”,是九歲的堂弟拿走了它,到街上換了零食和玩具。我沖九歲的堂弟咆哮,可那實際上是我的錯,是我沒有藏好它……
我去問店主,店主一臉茫然,得知那張五十元人民幣對我的特殊意義后,他決定幫我回憶。
“好像是一個拿著一百塊的小女孩換走了那張五十元人民幣。”
“好像是?”
“嗯……嗯,抱歉,我也記不大清了,來買東西的人比往常多一些。”
店主模糊不清的記憶使我泣不成聲,望著茫茫的街道和來往不息的人群,最終我妥協了。
沒有了那張人民幣,鐵皮盒還原為鐵皮盒,靜靜地躺在桌面上。白天我聽不到它的聲音,在寂靜的夜里,它輕輕地叫一聲,像是在向我哀求。這樣想著,后來便總是失眠,像是要證明什么,我決定把鐵皮盒鎖起來了。
一放就是一個夏天,緊接著是秋天,最后冬天也過去了,鐵皮盒再沒有打開過。數數日子,爸爸離開我們已經六年了。偶爾有人問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后,有沒有覺得自己的人生軌跡受到了影響?
我很茫然,父親走后,家人們都心照不宣地生活著,閉口不提與父親有關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和同學們聊起家人,我脫口而出“我爸爸也是這樣”時,我才明白父親原來真的不在了。
父親啊,你種在池子旁的葡萄樹已經結果了,你要是還在,該多好!
寫給母親
母親不是傳統的母親,她的嗓門極大,總是連名帶姓地喊我名字,做事雷厲風行,她有時候粗鄙、小氣、沒有見識、藏著農村母親的縮影。但無論生活多么不如意,母親一樣熱愛生活。
母親算得上是一個美人,外婆總和我提起,“你媽年輕的時候啊頭發烏黑又直,兩只眼睛像一潭水,可多人追嘞。”在那個年代,每家每戶的兄弟姐妹都很多,我母親排行第一,底下有兩個弟弟和三個妹妹。母親聰明能干學習好,可家境貧寒,小學沒畢業就輟學了。不滿十歲的母親就開始扛著鋤頭種菜賣菜,幫著外婆送弟弟妹妹上學。十六歲時,母親一個人跑去廣東打工,在她的堅持下,弟弟妹妹都完成了學業。母親的好,舅舅和姨媽總記在心里,后來父親生病,叔叔和姑姑從未問過,只有舅舅和姨媽們辭掉工作,一直陪伴母親度過了那段日子。
爺爺出生在沒落的地主家庭,遺留著“女孩讀書無用”的觀念,不肯送姑姑讀書。母親十八歲便嫁到我們家,爺爺拗不過性格剛烈且脾氣又大的母親,最終同意讓姑姑讀書。母親每天騎一輛破爛的自行車走街串巷地賣豆腐,賺得的錢一邊補貼家用,一邊供姑姑讀書。只是姑姑不是讀書的料,考不上高中,初中畢業后便去廣東打工了。奶奶一直不待見母親,奶奶的偏見在于,她認為女人應該賢良恭順,伺候公婆,料理家務。然而母親偏離了這種期望,后來賢惠溫和的小嬸進門了,一對比后,奶奶的偏見愈演愈烈,直到大哥出生,婆媳的矛盾才逐漸緩解。
母親是一個能干的女人,與父親結婚后兩人勤勤懇懇,白手起家,日子漸漸富裕起來。童年時代,母親說一不二的性格使我產生了恐懼。我更愿意呆在嬸嬸家,看著嬸嬸溫和地呼喚她的孩子,一遍遍不厭其煩地講故事時,我的腦海中便會浮現這樣的想法:“要是我媽也和嬸嬸一樣就好了,為什么我的媽媽不是嬸嬸。”母親從來不曾這樣溫柔地待過我,可是長大后想起抱有那樣想法的我,總是感到愧疚。因為無論我犯多大錯,多么不優秀,她從不曾說過“我的孩子和某某某一樣就好了”這樣傷人的話。
我對黑夜充滿恐懼,但母親堅持讓我一個人睡。看到月光照耀的樹梢閃閃發亮,我總疑心它們會從窗口伸進來,把我夾走。我睜著眼遲遲不敢睡去,天越來越黑,月亮也不見了蹤影,這樣的情景使我發抖。母親的房間在隔壁,我哭著喊她,卻始終等不到母親。哭到筋疲力盡,我才帶著對母親的憤恨入睡。我曾多次控訴她的無情,然而后來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母親一直站在門外聽我的動靜,直到我睡著后才走開。如今再和她提起,母親卻覺得難為情,很快掛掉了我的電話。
和母親通話的時間很少有超過五分鐘,即便是我上了大學,每次主動給她打電話,總是聊不到幾句便掛了電話。有一段時間我忙著社團的事情,很久沒有和她聯系。母親竟破天荒地給我打電話:“最近很忙嗎?你已經兩個周末沒有打過電話了……”
“最近事比較多,而且每次給你打電話總說不到五分鐘你就掛了。”我小聲地和母親解釋,得知我在忙的事情,而且常常熬夜,母親很不解,說道:“你是在糟蹋自己的身體還是在糟蹋我?做這些有意義嗎?”母親的接連發問讓我有些發怒,沖她喊:“你什么都不懂,我已經長大了,我在做什么我清楚。”
我的蠻橫在母親面前屢屢表現得淋漓盡致,母親沉默了很久,母親生氣了,卻不知道該說些什么緩和氣氛。很久母親才回我話:“隨你自己吧,我的路已經走到這了,我沒有什么文化,不懂你想走什么樣的路,我只求你健健康康……”
我突然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話,直到母親掛掉電話,我才意識到我說的話有多傷人。回想到這二十年來對母親的愧疚,以及此刻說她“什么都不懂”的罪過,我恨不能就此站在她面前,向她請求寬恕。細細想來,就是這樣一個年華漸逝、言語粗鄙的婦人,獨自對抗著周圍人的冷言嘲諷,將三個孩子送進大學。在人生旅途中,母親賦予我的深度和廣度,沒有任何一本書能比她更周全。
我是一個怯懦的孩子,怕出頭露面,搞砸事情,但母親勇敢且強大的個性影響了我。在我的記憶中,母親終年忙碌著,每晚夜里兩點半,我們還在做著香甜的夢時,母親已經起床了。到市里的路有十多公里,我無法體會一個女人在駭人的黑暗中是如何克服恐懼,日復一日地從市場帶回貨品,為我們換取生活費用的。母親做事永遠不敷衍,在忙碌之中,門前那株葡萄樹依然被照顧得很好,隔年結著誘人的果肉,正如我們兄妹三人一樣。母親說,每次覺得自己撐不下去的時候,看到這株葡萄,便會想到父親,想到三個可愛的孩子,便覺得內心一陣溫暖,就想著還能再硬著頭皮撐一段時間。于是,母親就這樣過了一年又一年。
母親啊請你原諒,在旁人面前永遠游刃有余的我,卻笨拙地不知如何表達一個女兒對你的情感。這個世界并不完美,但我真的愛它。
寫給阿才、阿福和胖小貓
我不知道狗和貓是帶著什么使命來到人間的,在農村,它們能活到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小時候我們家養有兩條狗,它們出生后不久大母狗便死掉了,大伯父和叔叔們將它剝皮燉了肉,在他們眼里,狗的使命只有兩個,一是看家護院,二是作為盤中肉。
我和哥哥喜歡狗,于是為活下來的兩只小狗搭了一個窩,秉持著“賤名好養活”的原則,我們為小狗起了名字,大的叫阿才,小的叫阿福。它們越長越大,越來越高,身強力壯的狗狗掌握了一項技能――捉老鼠。每每捉到一只老鼠,便會額外得到一塊骨頭。這更激起了它倆逮老鼠的興趣,心甘情愿地身兼多職,以表達對主人家的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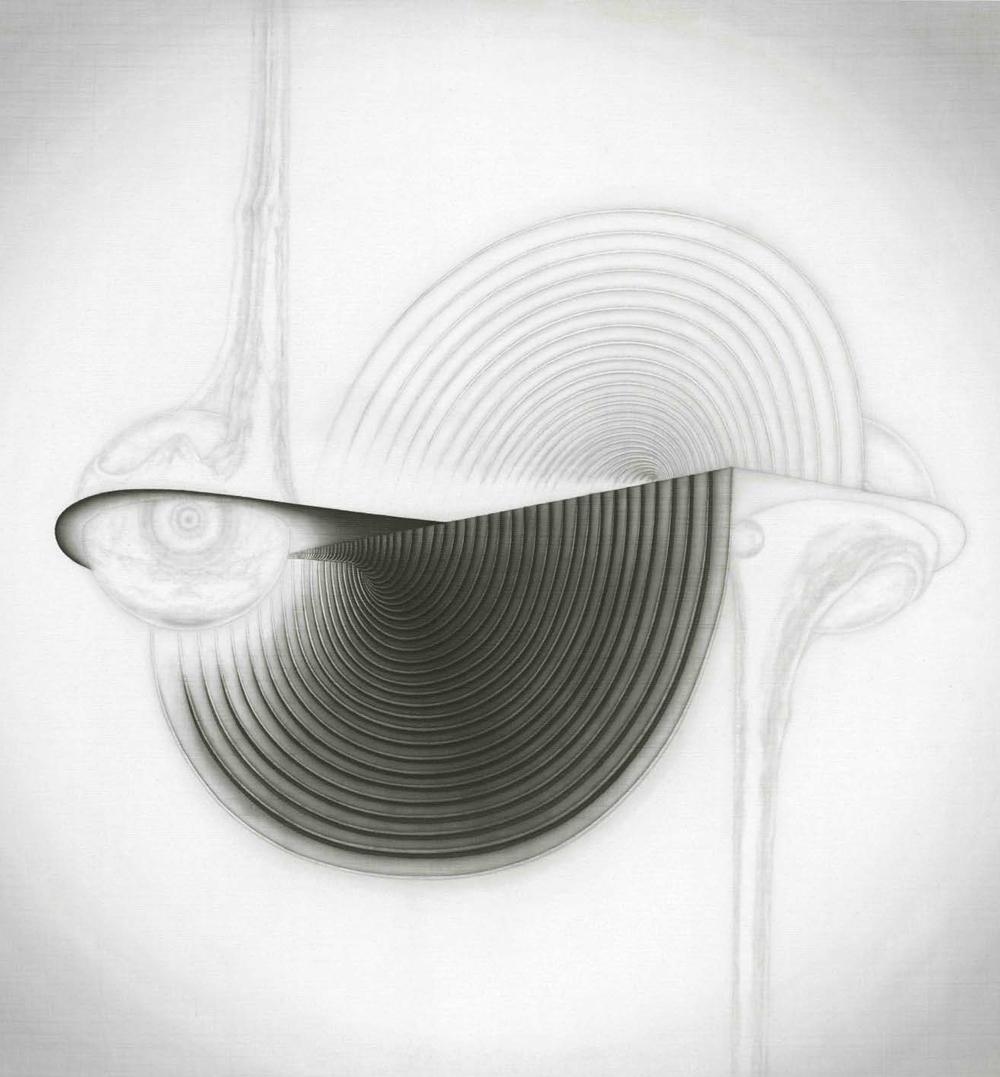
然而阿才阿福受到的待遇與付出是不對等的。突然有一天,阿福被路過的摩托車撞斷了腿,嘴上的血不停地往下流。鄉下沒有給狗醫治的地方,我只能心疼地給它綁上碎布。過了一個月,阿福死在了它的小窩里。失去了兄弟的阿才開始不愿意進食,它越來越不想回家,終日伏在門前的樹下。我心疼地摸著它的腦袋,我和它說:“別難過,我會一直陪著你。”興許是聽懂了我的話,阿才的眸子又亮起了光,很乖巧地往我身上蹭。
一日放學回家,遠遠地便看見叔叔、伯父和爺爺們聚在門口,我走近一看,卻發現阿才被繩子捆著吊在鐵桿上,嘴上殘留著血跡,早就斷了氣息。原來他們趁著狗沒有餓瘦,打算早早把它打死吃掉。我氣得發抖,只能崩潰地大哭。大人們被嚇了一跳,卻還是笑著說話:“你小孩子懂什么,狗沒用了只能這樣唄。”大人的語氣平淡得好像只是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螞蟻,我不知該如何控訴大人殘忍的罪行,我曾信誓旦旦地向狗允諾,卻沒有踐行。
日子過去將近十來年,我還是很喜歡狗,路上見到也會偶爾逗逗,但家里再沒有養過狗。阿才死去后,奶奶開始養貓,貓比狗精明,更懂得討主人的歡心。貓也會撒嬌,當大人們坐在院子里曬太陽閑聊時,就會爬上主人的膝蓋,蹭著手臂,千嬌百媚。因為它的到來,家人們輕而易舉地忘記了曾給家里帶來快樂的阿才阿福。因此我格外憎恨那只貓,我憤恨地喊它“死小胖”,假裝不小心踢翻它的食物,或者不經意地踢它一腳。但小胖似乎毫不介意我怎么評價它,我這些小把戲在它看來,估計太過可笑和幼稚。之后因為一次意外,它的腿被門重重夾了一下,走路就有些一瘸一拐。不久奶奶又養了一只貓,新來的貓白凈、勤快、動作迅速,很快取代了小胖的地位。我竟表示愉快,隔三差五地在它面前揶揄它,它也不惱,我才想到,小胖聽不懂人類的語言。
當我決定停止這無聊的玩笑后,小胖離家出走了,再沒有回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