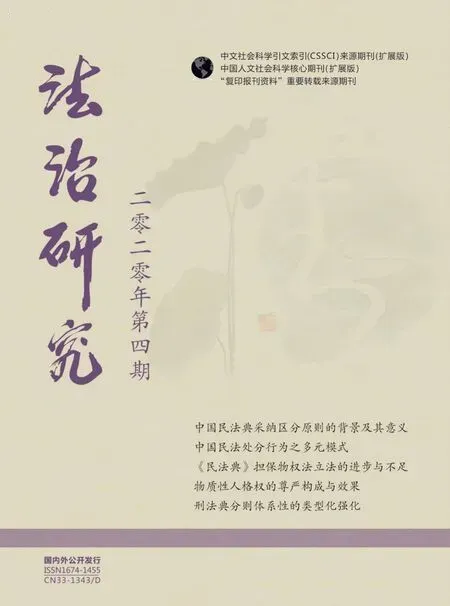《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的進步與不足
董學立
作為民法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擔保物權法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又以新的面孔問世了。①1995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2007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其中包含擔保物權法;且上述兩個擔保物權法同時適用。2020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其中有擔保物權法,與此同時,《民法典》明文廢止了前述包括擔保物權法的兩部法律。此后,我國的擔保物權法就是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的擔保物權法。在民法典的編纂過程中,學界普遍認為,在物權法中,相比較于所有權法和用益物權法,擔保物權法是最應該也最有可能發生一些質變的部分。之所以說它最應該發生質變,是因為我國的擔保物權法制與域外的擔保物權法制演進路線不同,由此形成的缺陷頗多頗重:我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始,其中的動產擔保物權法制就走上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由此產生了一些結構性立法缺陷。②動產上得以設立抵押權的法典法制度植入,使得我國動產擔保物權法制出現了結構多元并規范多元,由此導致了我國的動產擔保物權法制出現了同一規范的重復、不一致、矛盾和漏洞等諸多結構性的立法缺陷。詳細內容請參見拙作《我國意定動產擔保物權法的一元化》,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6期。因此有必要借此次民法典編纂之良機,予以進行結構性的修改與完善;又之所以說它最能夠發生質變,是因為擔保物權法制與所有權法制和用益物權法制不同,擔保物權法多屬于技術規范,少有本土特色,少受其他制度影響,完全可以借助于比較法的研究,借鑒域外成熟法制經驗予以修改和完善。
如同民法典的其他領域在此次民法典編纂中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一樣,擔保物權法領域雖有一些改善,但也沒有發生根本改善,與期待的應然進步尚有不小的距離。在民法典編纂“三個非不可”原則的指導下,我國的擔保物權法制又失去了一次絕佳的修改和完善機會。③我國此次民法典編纂,是在現有民事立法基礎上的民法典編纂,政界與學界都自覺的固守了“非增加不可的才可以增加,非刪除不可的才可以刪除,以及非改變不可的才可以改變”的民法典編纂原則。因此,面世的民法典與原有立法相比,沒有顯著變化實屬情理之中。相比較于《擔保法》《物權法》中的擔保物權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中的擔保物權法有一些進步;相對于域外先進的擔保物權法制,《民法典》中的擔保物權法尚存有明顯不足。研究《民法典》中擔保物權法的進步與不足,眼下目的在于解釋好、適用好《民法典》中的擔保物權法;遠期目的在于為再修改、再完善擔保物權法做足理論準備。④民法典頒布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應該不會有民法典某一部分如擔保物權法的修改、完善乃至重新編纂,但從擔保物權法的獨立性、落后性以及重要性來看,不排除在某個時間里對其進行單獨的修善,乃至將其從民法典中抽離出來而頒布擔保物權單行法。
一、《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的進步
所言《民法典》中擔保物權法的進步與不足,是比較研究的結果。說其有進步,是以《民法典》中的擔保物權法制與我國原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中的擔保物權法制相比較得出的結論。經認真細數,與《物權法》中的擔保物權法相比,《民法典》中的擔保物權法制,共計有47處修改或完善。按照這些修改或完善方面變化程度和變化意義的不同,我們將《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的進步分為如下三個方面:可有的進步、需有的進步和須有的進步。
(一)關于“可有的進步”
所謂“可有的進步”,實指“可有亦可以無的進步”。也就是說,修改后的《民法典》擔保物權法在此一方面相比較于《物權法》,雖說并非是沒有意義,但也可以說是沒有實質的意義。這一方面修改集中表現為將《物權法》擔保物權編中使用的“但”一字修改為“但是”一詞或者“但是,”:如《民法典》第386條、第388條、第399條第2項、第407條、第409條第2款、第417條、第421條、第422條、第430條、第435條、第443條、第444條、第445條以及第448條等,分別修改《物權法》第170條、第172條、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94條第1款和第2款、第197條、第200條、第204條、第205條、第213條、第218條、第226條第2款、第227條第2款、第228條第2款以及第231條中的“但”一字,就被修改為《民法典》中相關條款中的“但是”一詞或“但是,”;⑤唯《民法典》第422條使用了“但是,”,其他都使用了“但是”。另《民法典》擔保物權法中增加的第416條也使用了“但是”一詞,以及刪除了《物權法》包含“但”一字的第191條。⑥增加的一條即“購買價款擔保物權及優先受償權規則”,其最后一句是“但是留置權人除外”。我們建議刪除此句,若要保留,也應該是“但是留置權除外”,而非是“但是留置權人除外。”合計以上“改”“增”“刪”各方面,《民法典》擔保物權法共有17處使用了“但是”一詞或者“但是,”。
相比于后文言及的《民法典》擔保物權法“需有進步”和“須有進步”兩個方面,將《物權法》擔保物權法中的“但”一字修改為《民法典》擔保物權法中的“但是”一詞或“但是,”,其修改的必要性和法規范價值雖非全無,但也確實意義不大。因為這一修改,并沒有對相關的法規范有任何實質內容上的改變。因此,這一方面的修改可以說是“可有可無的進步”。既然是“可有可無的進步”,在民法典編纂任務如此繁重,需要用心修改的方面如此眾多的情況之下,為何還要花費時力對“可有可無”方面進行修改?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國《物權法》頒布于2007年,此后于200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印發了《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一)》,其中關于“法律常用詞語規范”方面認為:“但是”“但”二者的含義相同,只是運用習慣不同。法律中的但書,一般用“但是”,不用單音節詞“但”。“但是”后一般加逗號,在簡單句中也可以不加。從發文時間上看,在《物權法》頒布之后的2009年發文的《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一)》,成為此次《民法典》編纂“法律常用詞語規范”的試驗田。這一判斷從《民法典》全文皆使用了“但是”一詞或者“但是,”,可得證明。
也正如該《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一)》中所言,“但是”“但”二者的含義相同,只是運用習慣的不同。所以,將《物權法》擔保物權編中使用的“但”一字,修改為《民法典》擔保物權法中的“但是”一詞或“但是,”,性質上僅屬于文字使用習慣的修改,對于立法的規范實質內容沒有任何修改。但既然對《物權法》擔保物權編的修改和完善,都觸及到了用詞習慣的地步,則是否可以因此說對《物權法》中的擔保物權法的修改與完善,應該到了至善至美的地步?結局已如大家所知,其實不然,此為后話。
另外,從《物權法》頒布實施后的十余年時間來看,有沒有關于因《物權法》擔保物權編的法律規范使用了“但”一字,而造成法律適用困惑的案例?筆者是聞所未聞。使用“但”一字與使用“但是”一詞乃至“但是,”之間,如果其區別僅是“運用習慣的不同”,而沒有其他方面不同的話,則將“但”一字修改為“但是”一詞或者“但是,”這一立法完善方面,相比較于“需有進步”和“須有進步”方面,就可以說是屬于“可有”的進步,亦即“可有可無”的進步——有其雖好,缺其無妨。
(二)關于“需有的進步”
所謂“需有的進步”,是指《民法典》擔保物權法對《物權法》擔保物權編的修改或完善,或者緣起于其賴以存在的制度環境發生了變化,或者緣起于其立法政策發生了轉向,或者緣起于其原有的詞句不夠準確等,從而使得保持或延續某一規范不合時宜,因此需要以修改或完善而與時俱進。
首先,是起因于制度環境的改變。如《民法典》刪除了《物權法》第178條規定的“擔保法與本法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本法”。《物權法》之所以有此條規定,起因于《物權法》擔保物權編得以實行的同時,并未廢止《擔保法》中的擔保物權制度。因此,就有了這一條關于《物權法》中的擔保物權制度與《擔保法》中的擔保物權制度都有效適用的情況下,兩個法律如何協調適用的規范。其含義是:《物權法》與《擔保法》同時有效實施的情況下,“擔保法與本法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本法”;其言外之意是“擔保法與本法的規定一致的,可擇其一適用”。但在《民法典》頒布之后,依據《民法典》第1260條的規定,原有的《物權法》以及《擔保法》都要廢止,《民法典》因此就無需保留《物權法》中的第178條了。《民法典》中與此相類似的修改還有:如因正在進行的農地三權制度改革所導致的農地承包權、經營權等權利屬性的暫不確定,《物權法》第180條第3項規定的“以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物權法》第201條規定的“依照本法第110條第1款第3項規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或者依照本法第183條規定以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筑物占用范圍內的建設用地使用權一并抵押的”,以及《物權法》第184條規定的“耕地”等,或被《民法典》第395條修改為權利屬性確定的“海域使用權”,或被《民法典》第399條刪除,或被《民法典》第418條修改為“以集體所有土地的使用權依法抵押的”;如《物權法》第181條中規定的“經當事人書面協議”,也因《民法典》第400條中規定了“設立抵押權,當事人應當以書面形式簽訂抵押合同”而被刪除,且該條中的“債權人有權就實現抵押權時的動產優先受償”一語,亦因與該法第196條的規范用語需要相協調,而被《民法典》修改為“債權人有權就抵押財產確定時的動產優先受償”;如因《民法總則》對訴訟時效制度的修改,使得《民法典》第410條修改《物權法》第195條“其他債權人可以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該協議”為“其他債權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該協議”;如因未來動產擔保物權統一電子登記制度的采用,將不會出現“同時登記”的情形,因此《民法典》第414條刪除了《物權法》第199條的“順序相同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如因抵押權經公示后得以產生的對抗效力,《民法典》第405條刪除了《物權法》第190條中的“抵押權設立后抵押財產出租的,該租賃關系不得對抗已登記的抵押權”;如《物權法》第226條規定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以基金份額、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登記的股權出質的,質權自證券登記結算機構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以其他股權出質的,質權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也因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機構即將于《民法典》外設置而無需規定,《民法典》因此需要將其修改為“質權自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以及如《物權法》第228條規定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信貸征信機構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也是因為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機構即將于《民法典》外設置而無需規定,《民法典》因此也需要將其修改為“質權自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等。
其次,是緣起于立法政策的改變。如因對擔保物特定性立法政策的放寬,即允許在擔保合同中概括描述擔保物,《物權法》第185條中的“抵押財產的名稱、數量、質量、狀況、所在地、所有權歸屬或者使用權歸屬”,被《民法典》第400條第3項修改為“抵押財產的名稱、數量等情況”;以及《物權法》第210條第3項中的“質押財產的名稱、數量、質量、狀況”,被《民法典》第427條第3項修改為“質押財產的名稱、數量等情況”;如因立法政策對抵押權人處分抵押物的放寬,《民法典》第406條修改《物權法》第191條為“抵押期間,抵押人可以轉讓抵押財產。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按照其約定。抵押財產轉讓的,抵押權不受影響。抵押人轉讓抵押財產的,應當及時通知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能夠證明抵押財產轉讓可能損害抵押權的,可以請求將轉讓所得價款向抵押權人提前清償或者提存。轉讓的價款超過債權數額的部分歸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債務人清償”;如因立法政策對“流抵”和“流質”禁止政策的反轉,《物權法》第186條規定的“抵押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不得與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以及《物權法》第211條規定的“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不得與出質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質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分別被《民法典》第401條、第428條修改為“抵押權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與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財產優先受償”,“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與出質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質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質押財產優先受償”。
再次,是緣起遣詞造句的不夠準確。如關于動產抵押權的設立,《民法典》刪除了《物權法》第188條和第189條中規定的“抵押權自抵押合同生效時設立;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以增加“第四百零三條”即“以動產抵押的抵押權自抵押合同生效時設立;未辦理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方式,避免了同一規范內容的重復;⑦在刪與增之間,體現了法律制度的抽象性表達。《物權法》有兩條關于動產抵押權設立的規范,屬于規范性重復;《民法典》中只有一條關于動產抵押權設立的規范。合如《物權法》第196條規定“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設定抵押的,抵押財產自下列情形之一發生時確定:(二)抵押人被宣告破產或者被撤銷”,其中的“被撤銷”,因法律用語不夠準確,《民法典》將其修改為“需要解散清算的”;如《物權法》第206條規定的“抵押財產被查封、扣押”,因其不便于適用,而被《民法典》第423條修改為“抵押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抵押財產被查封、扣押”;如《物權法》第210條兩次規定的“質權合同”一詞,因用語不當而被《民法典》修改為“質押合同”;如《物權法》第184條中的“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因用詞外延過于狹隘,而被《民法典》第399條修改為“醫療機構等以公益為目的成立的非營利法人”;如《物權法》第220條規定的“因質權人怠于行使權利造成損害的,由質權人承擔賠償責任”,因用詞缺乏準確,而被《民法典》修改為“因質權人怠于行使權利給出質人造成損害的,由質權人承擔賠償責任”;如《物權法》第223條規定的“應收賬款”,因被認為用語不夠準確,而被《民法典》修改為“現有的以及將有的應收賬款”等。⑧將原有的“應收賬款”修改為“現有的以及將有的應收賬款”,猶如畫蛇添足,所有的擔保物,都是分為現有的和將有的兩種,且用“以及”也是錯誤的。“以及”有和或并的意思,此用語在原《物權法》第181條規定的浮動抵押中被使用。但在本條中,使用“以及”就不合適了,應當使用“或”。
總之,或因《民法典》頒布之后擔保物權法制賴以存在的制度環境發生了變化,或因立法政策發生了改變,或因遣詞造句需要進一步精準,借此次《民法典》編纂時機,《物權法》擔保物權編中的上述這些條款共有26處得到了修改或完善。《物權法》中這些被修改或完善的法律規范,在賴以存在的原有的制度環境中或者是正確的,或者是不夠準確的。因此,對它們的修改只是因為時過境遷、與時俱進需要修改而已。
(三)關于“須有的進步”
所謂“須有的進步”,是指因起始于《擔保法》中的動產抵押權的法典法植入,以及這一植入狀態在《物權法》乃至《民法典》中的延續,導致了我國動產擔保物權法的結構模式與規范表達方面的結構性立法缺陷。對此結構性立法缺陷,在《民法典》中經四處修改或完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如針對擔保物權類型法定過于狹隘,《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增加規定“擔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擔保合同擴大到非典型擔保合同,使得我國擔保物權法的氣質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使得擔保物權法的調整范圍和調整能力大幅度提升。盡管在確立區分原則的制度背景下,這一條規定擴大的是擔保合同而非是擔保物權,但鑒于擔保合同的名稱類型與擔保物權的名稱類型的密切關聯,我們也可以認為其是擴大的擔保物權類型。再如針對擔保物權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的不足,《民法典》在抵押權一章第一節第414條第2款增加規定了“其他可以登記的擔保物權,清償順序參照適用前款規定”。增加這一條規定,是因為我國《物權法》在“抵押權”一章較為周到、細致、科學地規定了“抵押權”包括動產抵押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但在“權利質權”一章,我國擔保物權立法向來都是缺失“權利質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的。《民法典》當然可以在“權利質權”一章增加關于“權利質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但這樣一來,就會造成“抵押權”一章的優先受償次序規范與“權利質權”一章的優先受償次序規范的規范重復。因此,抵押權一章上述增加的一款,就解決了權利質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缺失問題。但稍帶遺憾的是,在“抵押權”一章規制“權利質權”一章的問題,有一種在自留地里為別人家種菜的“多管閑事”之感,完全不符合法典法邏輯性和體系性要求。⑨抵押權法中應該只能“管轄”抵押權的事宜,而不應該長臂“管轄”動產質權或權利質權的事宜。正確的姿態應該是在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中添加準用規范,準用動產抵押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另如針對同一動產上抵押權與質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缺失,《民法典》第415條增加規定了“有同一財產既設立抵押權又設立質權的,拍賣、變賣該財產所得的價款按照登記、交付的時間先后確定清償順序”。⑩2019年《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65項對動產抵押權與動產質權的競存作了說明,認為:同一動產上同時設立質權和抵押權的,應當參照適用《物權法》第199條的規定,根據是否完成公示以及公示先后情況來確定清償順序:質權有效設立、抵押權辦理了抵押登記的,按照公示先后確定清償順序;順序相同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質權有效設立,抵押權未辦理抵押登記的,質權優先于抵押權;質權未有效設立,抵押權未辦理抵押登記的,因此時抵押權已經有效設立,故抵押權優先受償。《物權法》有關這一內容的缺失,導致法學理論界眾說紛紜,司法實踐中也矛盾重重。[11]參見曹明哲:《芻議動產抵押權與動產質權競存的優先順位》,載《南方金融》2019年第1期。還如針對購買價款抵押權及其超級優先受償制度的缺失,《民法典》第416條增加規定了“動產抵押擔保的主債權是抵押物的價款,標的物交付后十日內辦理抵押登記的,該抵押權人優先于抵押物買受人的其他擔保物權人受償,但是留置權人除外”。《民法典》增加的這一條,就是大名鼎鼎的“購買價款擔保物權及優先受償規則”。《物權法》對這一規則的缺失,導致了立法漏洞。但《民法典》給出的這一條規范尚不夠嚴謹科學,易生歧義。[12]詳細論述見后文。
動產抵押權的擔保物權法典植入,導致的動產擔保物權法結構模式與規范表達立法缺陷,應是以及事實上也是全方位、各層次的。但《民法典》關于擔保物權法“須有的進步”方面,卻僅限于修改或完善擔保物權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的內容。因此,“須有進步”的實然完成程度,與應然完成程度之間,距離還很大。這些還沒有完成的應然進步,就是我們下述關于《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的立法不足的方面。
二、《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的立法不足
相比較于我國原有的擔保物權法制,新頒布的《民法典》在擔保物權法制編纂方面有上述“可有、需有以及須有”等方面的進步;當我們轉換視角,將《民法典》中的擔保物權法制相對比于國外先進的擔保物權立法時,則我國頒布的《民法典》在擔保物權法制建設方面,顯有《民法典》編纂應該有所進步但卻裹步未進的不足方面:
(一)“須有而沒有”的立法不足
“須有而沒有”的立法不足,表現在《民法典》擔保物權法制的調整范圍仍然狹窄,整體性制度的缺失以及同一規范的重復等。
首先,盡管《民法典》已經擴大了調整范圍,將“所有權保留、融資租賃和保理”圈入自己的調整范圍,但仍顯狹窄,如實踐中大量存在的讓與擔保以及理論上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擔保形式等,則完全不在此法的調整范圍之內。緣于對物權法定原則的理解不到位,我國擔保物權立法一直堅守著物權嚴格法定原則,或者逐步放寬到了物權法定基礎上的物權緩和原則。但至今學界還沒有普遍認識到物權法定原則適用于擔保物權法,與適用于所有權法和用益物權法的確有不同。有研究認為,物權法定原則不應是“競存論”基礎上的物權法定原則,即物權法定原則要么是物權嚴格法定原則,要么是物權法定緩和原則,以及要么是物權自由原則,且每一項被選定的物權法定原則普適于所有權法、用益物權法和擔保物權法;物權法定原則應該是“并存論”基礎上的物權法定原則,即物權嚴格法定原則、物權法定緩和原則以及物權自由原則得以并立并存,并且各自有特別的適用領域,即物權嚴格法定原則限適用于所有權法,物權法定緩和原則限適用于用益物權法以及物權種類自由原則限適用于擔保物權法。[13]董學立:《論物權法定:從宏觀敘事到微觀求證》,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0年第2期。但我國擔保物權法制,向來采取擔保物權嚴格法定原則,在擔保物權類型上,采取封閉的類型體系,擔保物權限指《民法典》物權編中規范的擔保物權類型即意定擔保物權限指“不動產抵押權、動產抵押權、動產質權、權利質權等”,即使我國民法典將擔保物權的類型范圍擴展到了合同法中規定的所有權保留、融資租賃和保理等非典型擔保物權類型,但對于合同法中沒有規定的讓與擔保等其他當事人依合意創設的擔保物權類型,則沒有規定。對于未來經濟活動中當事人以其他名稱設立的內容為擔保物權的合意,則不能納入到民法典擔保物權法中接受調整。
擔保物權是不同于所有權也不同于用益物權的物權類型。所有權在立法中沒有被分類,所有權其實也沒有分類的社會需要。所以,所有權需要實施嚴格的物權法定原則,以此方可保護所有權的歸屬安全和交易安全,并以此為基礎得以建立起用益物權體系和擔保物權體系。用益物權有分類,其分類的標準是對他人不動產的使用內容的不同,因此才有了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以及居住權等。因此,用益物權是法定基礎上的緩和。唯有擔保物權,雖其也有分類,但其分類的依據卻不能夠依據其核心內容方面,即擔保物權是“在受擔保債權數額限度內,對擔保物變價的優先受償權”,而是依據其非核心內容的不同方面如擔保物類型、擔保物權公示方式等。就擔保物權的核心內容方面,類型不同的擔保物權的核心內容都是一樣的。擔保物權核心內容的同一,決定其不同僅在于或擔保物的不同以及因擔保物的不同而導致的不同,或擔保物權公示方式的不同以及因公示方式的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等。既然如此,那些所謂的非典型擔保如合同法中規定的所有權保留、融資租賃以及保理等,以及現有法律制度中沒有規定的擔保物權類型如讓與擔保等,它們的核心權利內容都與法定擔保物權類型無異。因此,擔保物權法的調整對象應該開放如通過或開放擔保物權的定義,或明確現有擔保物權規范準用于非典型擔保物權在內等,以使得擔保物權類型包括非典型擔保物權類型。有學者建議稿曾提出如下方案:【擔保物權內容法定種類自由原則】擔保物權的內容,由法律規定;擔保物權種類名稱,當事人可自由約定。【探究真實意圖】判斷當事人是否以合意設立了擔保物權,不應拘泥于當事人使用的文字,而應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圖。[14]董學立:《擔保物權法編纂的理論基礎》,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291頁。
其次,基礎性制度的缺失。為確保動產擔保物權的善法良行,有賴于兩項制度的支撐,一是動產擔保物權的統一登記制度,二是動產擔保物權的統一優先受償次序規則。前者被譽為動產擔保物權法良行的基礎設施,即此猶如高鐵要跑得快,有賴于良好的軌道基礎設施一般。如果沒有與高鐵的高速運行相適應的軌道,再好的高鐵都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相較而言,再好的動產擔保物權制度,如果沒有統一登記制度的支撐,都不會發揮出其應有的制度功效。而建立在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基礎設施之上的動產擔保物權優先受償次序規則,則是擔保物權法的核心規則。所謂核心規則,就是指擔保物權法的其他制度方面,要么是以統一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的建立健全為目的,要么是以健全的統一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為前提。也可以說,沒有建立健全的動產擔保物權統一優先受償次序規則,則擔保物權法的其他規則方面,要么就失去了建設的意義如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公示制度,要么就沒有了有效實施的制度前提如擔保物權的實現等。
因動產擔保物權被立法切分為動產抵押權、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這一結構模式雖非是必然導致但極容易導致立法者因過分關注立法的局部、細節而忽視掉整體性制度設計,如動產擔保物權的統一登記制度設計,以及動產擔保物權的統一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的設計等。所以,本次民法典編纂,一如前述,對過去立法中忽視了的動產擔保物權優先受償次序規則予以極大的關懷,增加的數條規范都是關于優先次序的規范,極大地彌補了過去立法的不足。但即使如此,《民法典》仍沒有徹底解決動產擔保物權的統一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的問題,如缺少對金融債權質押的控制公示制度,以及以此種公示制度為基礎的特別優先受償次序規則。關于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制度,《民法典》更是沒有擔負眾望,在刪除原有立法分散登記規范的情況下,卻沒有勇氣明文規定建立動產擔保物權的統一登記機構,將這一歷史性的規范功績讓渡給了國務院《改善營商環境條例》這一規范性文件。[15]《改善營商環境條例》第47條第2款規定:國家推動建立統一的動產和權利擔保登記公示系統,逐步實現市場主體在一個平臺上辦理動產和權利擔保登記。納入統一登記公示系統的動產和權利范圍另行規定。
再次,同一規范的重復。在擔保物權核心內容同一的情況下,立法將動產擔保物權切分為動產抵押權、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的結構模式,導致動產擔保物權法規范在擔保物權的定義、擔保物范圍、擔保合同,擔保物權設立、公示、效力、次序、實現、消滅等九個方面規范群,在動產抵押權、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之間被重復,并在規定重復基礎上次生出規范不一致、矛盾和漏洞等問題。雖然此次《民法典》編纂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在優先次序規范群方面有顯著進步,如前述《民法典》編纂注意到了動產抵押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與權利質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的同一性,因而有了《民法典》第414條第2款關于“其他登記的擔保物權,清償順序參照適用前款規定。”但《民法典》卻沒有將這一模式復制到擔保物權其他的重復規范群方面。也可以說,對于動產擔保物權的規范重復,以及因規范重復導致的規范不一致、矛盾和漏洞等立法缺陷,并沒有上升到一種理論,并以此理論指導《民法典》的編纂。
在擔保物權的定義規范方面,既然有了“一般規定”中的“擔保物權”定義,為何還需有 “一般抵押權”一節中的抵押權定義,以及“動產質權”一節中的動產質權定義,尤其是動產抵押權定義與動產質權定義,除了其之間公示方式的不同外,兩者沒有任何其他區別內容,因而形成了定義規范重復;[16]在立法規定了“擔保物權”的定義之后,關于“一般抵押權”定義應該突出規定其用以區別于“動產質權”的登記公示,同理,“動產質權”定義應該突出規定其用以區別“一般抵押權”的占有公示。至于“擔保物權”定義中規定的“到期不履行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抵押權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擔保財產優先受償的權利”,則無需在“一般抵押權”和“動產質權”的定義規范中重復。同時在既有的立法模式下,我們也未對“權利質權”作出定義,導致規范缺失。在擔保物的范圍規范方面,抵押權既有關于擔保物范圍的積極規范又有消極規范,從而導致積極規范失去規范價值;動產質權只有消極規范,從而導致其與抵押權同一問題的不同立法模式;抵押物的范圍擴大到法不禁止的財產都可以抵押,則權利質權的質押物即權利,也可以規制到動產抵押權范疇中,則權利質權因此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意義;對于抵押物實施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立法政策,但對質押權利則實施法不授權即無權的立法政策,兩者之間在同一部法律中形成政策相背;對于擔保物權的收益,現有立法僅僅規制了其消極收益即擔保物損毀的保險金、賠償金等消極代位物,但沒有規定因擔保物物理形變的收益如林木經砍伐變為木材,木材經加工變為家具,家具經銷售變為貨幣等的積極代位物。在擔保合同,現有立法承繼過去立法的規范,既有抵押合同,也有質押合同,形成規范重復;在擔保物權設立方面,立法承繼過去立法的規范,既有擔保物權設立的意思主義,也有擔保物權設立的形式主義;在擔保物權的公示方面,既有公示對抗主義,也有公示生效主義,導致在同一部法律里面的設立規范以及公示規范不統一;在擔保物權的效力方面,民法典編纂修改了抵押期間抵押物的處分規范,但立法沒有對權利質押物質押期間的處分如《民法典》第444條關于以注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其出質后的處分行為進行了限制,以及該法第445條關于以應收賬款出質的,其出質后的處分權亦做了限制等,由此形成了擔保物權存續期間,擔保人對擔保物的處分權的不統一;在擔保物權的實現方面,立法沒有充分表達擔保物權作為物權實現上的直接支配屬性,在當事人關于抵押權的實現方式協商不成至請求人民法院變價之間,尚有一段得以直接支配的距離;在擔保物權的消滅方面,對于同樣有著訴訟時效問題的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立法沒有做出如抵押權的訴訟時效的同樣規定,形成了法律漏洞。[17]2019年《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59項規定:抵押權人應當在主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內行使抵押權。抵押權人在主債權訴訟時效屆滿前未行使抵押權,抵押人在主債權訴訟時效屆滿后請求涂銷抵押權登記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登記作為公示方法的權利質權,參照適用前款規定。該項規定沒有將動產質權的參照適用列入其中,這是錯誤的。《民法典》第437條、《物權法》第220條規定:出質人可以請求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及時行使質權;質權人不行使的,出質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拍賣、變賣質押財產。既然有“出質人可以請求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后及時行使質權”的規定,則當有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可能。
上述這些問題的存在,與我國過去的擔保物權立法中,以及剛剛頒布的《民法典》擔保物權法制中,沒有明文規定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準用抵押權(動產抵押權)的規定,直接有關。也就是說,過去以至現在,我國的擔保物權立法,一直是在缺乏系統理論指導下的個別規范的修改或完善操作。[18]動產抵押權的擔保物權法典法機械植入,導致了擔保物權法制九個方面規范群的全面規范重復、不一致、矛盾或漏洞。這次《民法典》編纂,僅在擔保物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方面有“須有的進步”,但在其他八個規范群方面,則幾乎無進步。
(二)“需有而沒有”的立法不足
首先,對于究竟是擔保合同從屬于主債權債務合同,還是擔保物權從屬于受擔保債權,《民法典》延續了以往立法的錯誤規定,即《物權法》第172條規定的“設立擔保物權,應當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訂立擔保合同。擔保合同是主債權債務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的,擔保合同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依據《物權法》確立以及被《民法典》承繼的“區分原則”,擔保合同以及主債權債務合同是獨立的法律行為,因此兩者之間根本就談不上主從關系。依據擔保協議產生的擔保物權與依據主債權債務合同產生的主債權之間,按照擔保物權產生和存續的目的,有擔保物權對受擔保債權的從屬性關系,即擔保物權從屬于受擔保的債權。因此,《民法典》第388條應該將《物權法》第172條修改為“設立擔保物權,應當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訂立擔保合同,擔保物權從屬于受擔保的債權。受擔保債權無效的,擔保物權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其次,對于抵押權的設立,《民法典》將《物權法》第188條與第189條合并修改為“以動產抵押的,動產抵押權自抵押合同生效時設立;未辦理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但對于不動產抵押權的設立,《民法典》卻延續了《物權法》第187條的規定,即“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的財產或者第五項規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應當辦理抵押登記。抵押權自登記時設立”。如果動產抵押權的設立,可以做如上的修改的話,則不動產抵押權的設立亦應該做如下的修改:以不動產抵押的,應當辦理抵押登記。不動產抵押權自登記時設立。[19]當然,對于《物權法》第187條、第188條規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上抵押權的設立,《民法典》也應該明確其需待在建物這一未來物成為特定物之時才得以設立。
再次,對于增補的購買價款擔保物權及優先受償規則,《民法典》第416條規定“動產抵押擔保的主債權是抵押物的價款,標的物交付后十日內辦理抵押登記的,該抵押權優先于抵押物買受人的其他擔保物權人受償,但是留置權人除外。”經認真的研究,我們認為該條應該修改為“在購置物上設立的動產抵押權擔保的是購置物的價款,購置物交付十日內辦理抵押權登記的,該抵押權優先于買受人在購置物上設立的其他擔保物權。”,之所以做這樣的修改,是因為原有規范表述存在重大缺陷:一是表述不清,原規范過于抽象,不利于理解,如“動產抵押權擔保的主債權是抵押物的價款”,這樣的表述,不要說是一般人士,就是專業人士,如果對此沒有專門的研究,對其理解也會摸不著頭腦。購買價款擔保物權來自于所有權保留買賣,也就是分期付款買賣。所以,如果將其修改為“在購置物上設立的動產抵押權擔保的是購置物的價款”,就清晰明了多了;二是表述錯誤,即“該抵押權優先于抵押物買受人的其他擔保物權人受償”的表述存在錯誤,抵押權的優先受償次序,是同一抵押物上的數個抵押權之間的優先受償次序,因而不是“抵押權”優先于其他“擔保物權人”,且“抵押物買受人的其他擔保物權人”未必就全部是同一買受物上的擔保物權人,若不是同一購買物上的擔保物權人,因此就沒有優先受償次序的法律問題;三是表述重復,即關于留置權的超級優先受償地位,既然《民法典》第456條已經承繼了《物權法》第239條規定的“同一動產上已設立抵押權或者質權,該動產又被留置的,留置權人優先受償。”則可以通過體系解釋得出購買價款抵押權的情況下,留置權也優先于購買價款抵押權。因為購買價款抵押權是抵押權的一種類型。
(三)“可有而沒有”的立法不足
一如前述,對于抵押物的規范,《民法典》延續《物權法》的立法模式,既有可抵押物的積極規范,也有不可抵押物的消極規范,即所謂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從立法技術方面看,有關于不可抵押物的負面清單即足矣。所以,《民法典》可以刪除可抵押物的正面清單規范,當然,留著它也無所謂——既然它已經留在那里很久了。從司法實踐來看,既規定抵押物的正面清單,也規定抵押物的負面清單的模式,與只規定抵押物的負面清單的模式,只是立法技術的高低,對司法實踐沒有直接影響。因此,刪除立法對可抵押物的正面清單規范,就是一個可有而沒有的立法操作。刪除是立法技術的提升,不刪除對司法實踐也不會有影響。因此,未刪除可抵押物的正面清單,即成為“可有而沒有”立法不足。
三、對《民法典》擔保物權法“進步與不足”研究的價值
在《民法典》剛剛頒布之際,談論其進步,或皆大歡喜;議論其不足,則有不敬之嫌。法典是用來崇拜的,只有崇拜才能自覺遵守、敬畏而用。法典不是用來批評的,批評導致法典威信掃地,又談何被崇拜以及被自覺遵守和敬畏適用。但學術工作都是以批評促進步為業的。所以,筆者應景習作,選“進步與不足”為題。但這樣的情懷,應是來自于躬身完善每一條擔保物權法規范中培養起來的家國情懷——每一位民法人都最終擁有的情懷。質言之,筆者道出擔保物權法的進步與不足,是為了擔保物權法的盡善盡美——更好的立法完善以及更好的司法適用。
(一)關于《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立法進步方面的研究價值
對于“須有的進步”方面而言,購買價款擔保物權及其超級優先受償規范的增加,不僅以此彌補了過去立法的不足,也因此使我們認識到了所有權保留制度與抵押權制度之間可以相互轉換——現有的購買價款擔保物權制度是由非典型擔保物權類型即所有權保留制度轉換而來的。不同的擔保物權類型之間可以相互轉換,這一現象恰是不同類型擔保物權的核心內容同一的表征。而不同類型擔保物權的核心內容同一,則是擔保物權可以實施規范一元化立法的理論基礎。[20]從比較法方面分析,現有的擔保物權立法,有三種立法模式:德國不動產擔保物權法的多元結構與一元規范模式、美國《統一商法典》第九編動產擔保物權法的一元結構并一元規范模式,以及我國的動產擔保物權法的多元結構又多元規范模式。由此又可以推導出,在擔保物權的多元結構里,也可以實現擔保物權的規范一元。再好的法學理論如果沒有實證法的佐證,都是蒼白無力的。而所有權保留得以轉換為抵押權并得以植入擔保物權法典,則強而有力地說明了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也可以轉換為抵押權,這尤其在“法不禁止的財產都可以抵押權的”法制環境下,權利質權制度整體性融入抵押權更是如此;動產質權與動產抵押權之間則僅存一步之遙——兩者之間僅限于公示方式的不同。由此,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不必糾結于當事人使用的擔保物權類型概念,如當事人合意創設權利質權,但沒有辦理登記公示手續,此時,我們是解釋為權利質權因而無效呢?還是可以探究當事人的真實合意解釋為權利抵押權呢?我們認為,這種情況下,可以將名義為權利質權的擔保物權設立,解釋為動產抵押權的設立,即使之有效的司法操作。在抵押權一章規定抵押權的優先次序規則準用于其他登記擔保物權,雖有其不合宜之感,但卻因此讓人們嗅到了避免規范重復以及避免重復規范的不一致、矛盾和漏洞立法技巧的味道。如果可以糾正其地宜不適的不足,并且可以放大開來,并施以準用規范立法技術的側入,則擔保物權法九個方面規范群,因我國特有結構模式的規范表達的缺陷,就可以大概率地迎刃而解。所以,我們認為,對于擔保物權規范一元化的應然結局而言,《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的進步,只是其通向終極目標的一小步。我們應該珍惜這一小步的進步。因為它的方向是正確的。既然方向正確,就無需再擔心路途遙遠,那只是時間和機緣的問題。
對于“需有的進步”方面而言,不論是制度賴以生存的環境發生了改變,還是立法政策發生了改變,乃至遣詞造句更加精準,總之,時過境遷、與時俱進,乃是法律保持其生命力的王道。但這屬于就事論事的微觀操作事業,當撐不起推進法制蛻變的重任。任何一條法律規范都不是孤獨存在的,其必是受制于周遭的制度環境,當周遭制度環境發生變化之后,原有的制度必然隨之應變,求得規范自身的安穩。如擔保物的范圍圈定,如抽象規范的增加或地位提升導致的規范省簡,如統一登記機構的建立對分散登記規則的刪除等;立法政策的變化也使得一些規范搖身一變,如對流抵押和流質押的承認,導致原有的規范變身;如對擔保物特定性的政策放寬,導致對其限制的描述表達被刪除等。遣詞造句的完善,使得立法的語言更加精準,便于法律的學習和適用。這一點告訴我們,在司法過程中,因為擔保物權法制賴以存在的制度環境始終處于變化狀態,司法就不能抱緊成文法本身不放,還應觀察其賴以存在的制度環境的變化,適時對法律規范本身做出隨變調整。但對于“可有的進步方面”而言。將“但”一字修改為“但是”一詞或“但是,”,形式意義大于實質價值,且與擔保物權法的整體進步程度不相匹配:讓人誤以為《民法典》擔保物權法有了徹頭徹尾的舊換新顏,但其實不然。
(二)關于《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立法不足方面的研究價值
首先,針對《民法典》擔保物權法調整范圍的不足,我們在司法實踐中要善于識別當事人依合意創設的擔保物權類型,尤其是非典型的擔保物權類型,如所有權保留、融資租賃、讓與擔保、保理以及借款買房、以物抵債,等等。只要當事人依合意創設了“在擔保債權數額限度內對擔保財產變價的優先受償權”,不論其使用了什么樣的名稱概念指代其法律關系,都可以判定當事人依合意創設了擔保物權,因而可以接受擔保物權法的調整。[21]《民法典》第642條第2款規定:出賣人可以與買受人協商取回標的物,協商不成的,可以參照適用擔保物權的實現程序;第745條規定:出租人對租賃物享有的所有權,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768條間接規定了保理的登記制度等。合同法里的這些規范,彰顯了所有權保留制度、融資租賃制度以及保理制度等的擔保物權屬性。如對于“借款賣房”交易,當事人很有可能使用了買賣合同的概念,但如果當事人約定了購房款退還后房產退還的約款,以及借款若不能按期歸還則購房人獲得房產所有權或獲得對房產所有權變價的優先受償權等,則此以買賣合同之名所表達的法律關系實質,就是以房屋所有權讓與擔保借款債權的償還;還如租賃關系,也有真租賃和假租賃之分,真租賃就是在租賃物的使用壽命期限以內,通常是遠低于租賃物的壽命期限,租用租賃物并支付租金,租期結束歸還租賃物給出租人的法律關系;假租賃就是以租賃之名,行租買之實,如租賃合同約定的租賃期限通常等于或接近租賃物的使用壽命,且在租賃合同中約定租賃到期,承租人可以以名義價格購買租賃物,或者租賃物直接歸承租人所有等。這樣的租賃,就是融資租賃,就是以租的名義購買租賃物,出租人以保留所有權的方式擔保租金支付。其實質,就是一種非典型擔保物權。尤其隨著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制度的實施,名稱各異的擔保物權類型若想獲得交易安全的保護,就需要在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平臺上實施擔保物權的登記。登記本身反過來也驗證當事人設立擔保物權的真實意思,即凡是自主到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平臺實施登記的,就是動產擔保物權登記,而不論其在合意中使用了什么樣的名義。
其次,針對《民法典》擔保物權法整體制度的不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現有立法缺少統一登記制度的規范。但這一制度因為已經規定在國務院《改善營商環境條例》中,且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正在抓緊組織落實,隨著《民法典》頒布后擔保物權法實施的背后推動等,相信動產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制度很快就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其次是統一優先受償次序規則雖有完善但尚不足,即此次民法典編纂增加了抵押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且增加了動產抵押權優先受償次序規則被準用的規范,這樣一來,擔保物權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就基本建立健全了。但與國外制度相比,因為我國的擔保物權制度沒有設置動產擔保物權的“控制”公示制度,也就沒有設置與控制公示制度密切相關的優先受償次序規則。這應是其不足之處。
再次,針對《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的重復規范不足,首先是在理論上明確擔保物權的類型劃分標準不是依據擔保物權的核心內容,因為擔保物權的核心內容都是同一的,不能作為擔保物權分類的依據。劃分擔保物權類型依據的恰是擔保物權的非核心內容如擔保物類型不同、擔保物權的公示方式不同等。擔保物權的核心內容同一,是擔保物權實施規范一元化的理論基礎。其次是在理論上明確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得以準用動產抵押權的規范,因此需要在擔保物權法中增加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準用動產抵押權的準用規范。在現有法律缺少此類準用規范的情況下,司法應該可以有所作為,以司法的助力來彌補擔保物權立法的不足。針對規范的重復、不一致、矛盾或漏洞,司法活動可以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物權法的基本原則以及擔保物權的基本原則或者法律精神,做出適恰的司法解釋,以有利于法律目的的達成,也尊重了當事人的內心意思,有利于物盡其用等。
四、結語
我國的擔保物權法制,走過了一段與國外的擔保物法制不同的發展道路,表現在我國在1995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的時候,將動產抵押權植入進了擔保物權法典。域外的擔保物權法制,則是先有其民法典,后再以民法典之外的特別法——或以判例法,或以單行法,確立動產上設立非移轉占有的動產擔保物權類型如動產抵押權,彌補民法典缺失動產抵押權的不足。國外這一“基本法-或單行法或判例法”的結構模式,不會引起法體系的負面效應,因為基本法中的動產擔保物權制度與或單行法或判例法的動產擔保物權制度的適用對象不一樣。但我國走的是一條通過動產抵押權的擔保物權法典植入,解決傳統擔保物權法制缺少動產抵押權的立法缺陷,這一動產抵押權的法典法植入模式導致了動產上設立的擔保物權類型之間,即動產抵押權、動產質權和權利質權之間的規范重復、不一致、矛盾和漏洞。理論分析結論如此,實證研究證實亦不二。所以,這才是此次擔保物權法編纂的理論基礎和發力基點。但遺憾的是,我國學界對此沒有形成統一的認知,我國的擔保物權法制也無緣此次民法典編纂的良機得以脫胎換骨。
在學術理想與立法實踐之間,此次民法典編纂使得許多民法學者有失落感——自己的學術主張沒有被立法采納,而每一位民法學者又堅信他的主張至誠至善,完美無缺。僅從擔保物權法的編纂來看,筆者認為,現在呈現在大家面前的擔保物權法,就是其恰好的應有狀態。法學是學術行為,求真求善;立法是政治行為,在力量博弈中求得均衡。這其中的底色,就是我國人民現有的法律素養,這是立法民意基礎的最大公約數。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基礎還有待提高。所以,學者路遠且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