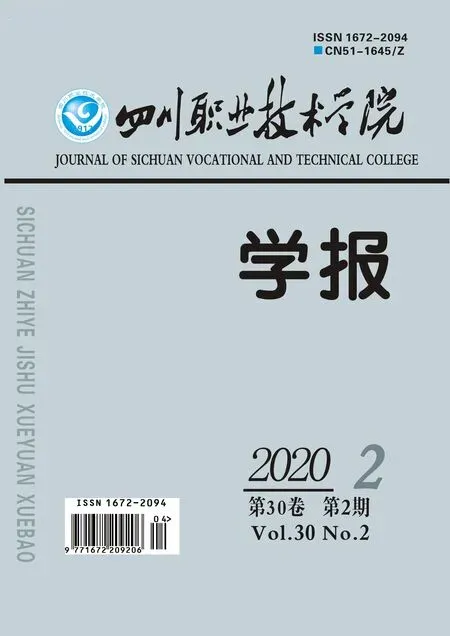論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中的道家思想
楊 梅
(廣西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廣西 桂林 541006)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屬四川遂寧)人。陳子昂是初唐詩文大家,去世后文集由好友盧藏用收集整理,成《陳子昂集》。《感遇三十八首》是陳子昂代表作之一,盧藏用在《故陳子昂集序》中說道:“至于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三十八首》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骎骎,方將摶扶搖而凌泰清,獵遺風(fēng)而薄嵩、岱,吾見其進(jìn),未見其止。”[1]2在這里可以看出,陳子昂《感遇詩》“微顯闡幽”、“接天人之際”即蘊(yùn)含著許多道家思想。下面將詳細(xì)分析,以祈方家指教。
一、陳子昂與道家的淵源
要探索陳子昂與道家的淵源,需要闡明兩個(gè)問題,一是道家和道教有何區(qū)別與聯(lián)系?二是為何陳子昂《感遇詩》中體現(xiàn)是道家思想而不是道教思想?
第一個(gè)問題,學(xué)術(shù)界歷來有爭議。二者自古便有聯(lián)系,道教來源于道家,以道家尤其是老莊哲學(xué)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方法論為其養(yǎng)生學(xué)的基礎(chǔ)理論和實(shí)踐規(guī)范。但古人對道家和道教的區(qū)分并不嚴(yán)格,在東漢以后講道家時(shí)是將道教包括在其中的。如著名學(xué)者陳攖寧就在其《道教與養(yǎng)生》中主張道家、道教不可分[2]。但二者實(shí)有區(qū)別。有學(xué)者表示:“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一般都認(rèn)為:道家和道教這兩個(gè)概念在歷史上雖有混用的情況,還是加以區(qū)別為宜。理由是兩者雖存在盤根錯(cuò)節(jié)的關(guān)系,但道家屬于學(xué)術(shù)思想流派,道教屬于宗教。”[3]13兩者具有一定的區(qū)別,目前在學(xué)術(shù)界是統(tǒng)一的觀點(diǎn)。
道家和道教主要有以下五種區(qū)別。第一,鬼神觀。作為宗教的道教,更多強(qiáng)調(diào)的是鬼神,而道家卻講天道自然,否定神秘的存在,有無神論的傾向。第二,崇拜物。道家以“道”作為最高思想范疇,但并無崇拜物,而道教卻神化“道”,并且把它“人格化”后加以“神圣化”,如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被認(rèn)為是“道的化身”①,而且道家人物如老莊都被稱作“神”。第三,信仰觀。道教作為宗教,它要求教徒保持宗教信仰,而道家無此要求。第四,組織形式。道教有相應(yīng)的宗教活動場所(宮、觀、廟)以及一定的教團(tuán)組織等形式,而道家人士卻更多以隱士的身份隱居。第五,修行方式。道家不相信法術(shù)巫術(shù),但也有自己的“修行之法”,以“養(yǎng)氣”、“養(yǎng)精”等養(yǎng)生之法來修行;而道教吸收了道家養(yǎng)生論,兼收了神仙家、醫(yī)家和自己的創(chuàng)造,在養(yǎng)生之法上有更多的途徑和方式。
第二個(gè)問題,陳子昂因家族緣故曾受到過道教的影響,但對他影響更大的是道家思想,在詩歌中他曾對道教煉丹術(shù)表示過懷疑,如《感遇詩》(三十三):“金鼎合還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峨眉。變化固非類,芳菲能幾時(shí)。疲痾苦淪世,憂悔日侵淄。眷然顧幽褐,白云空涕洟”②就流露出這種傾向。在鬼神觀方面,陳子昂認(rèn)為有神仙世界的存在,而且在詩中也有很多求仙訪道之言;但他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向神仙世界尋求寄托,在實(shí)際行動上并沒有如道教徒一般加以操行,所以我們在此認(rèn)為他詩歌中體現(xiàn)的是道家思想。在他苦悶時(shí),思想上更多與超凡脫俗的道家精神契合,如《陳氏別傳》中有“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1]1563
探討陳子昂道家思想的淵源,需從家族和時(shí)代影響爬梳。陳子昂出身道教世家,他的五世祖(一說四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袐書》《白虎七變法》,遂隱于郡武東山。”[1]910,其父陳元敬好神仙之術(shù),“山棲絕榖,放息人事,餌云母以怡其神。”[1]911(《府君有周文林郎陳公墓志文》)“絕榖”就是道教之“辟谷術(shù)”,“云母”是道教仙藥之一,“絕榖”、“餌云母”,這兩種都是養(yǎng)身長生之術(shù)。其父對他任俠好游的性格也產(chǎn)生了影響,記載曰:“父元敬,瑰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xiāng)人阻饑,一朝散萬鐘之粟而不求報(bào),于是遠(yuǎn)近歸之,若黽魚之赴淵也。”[1]1562(《陳氏別傳》)陳子昂少時(shí)學(xué)縱橫術(shù),其詩說“少學(xué)縱橫術(shù),游楚復(fù)游燕”(《贈嚴(yán)倉曹乞推命祿》),這使他養(yǎng)成了豪俠任氣之性,并始終伴隨他一生。陳子昂青年時(shí)期在“金華觀”(后改名為玉京觀)讀書,這是一座著名的道觀。從上述介紹可以看出陳子昂青年時(shí)期家族中道教色彩對他的影響。
陳子昂道家思想的淵源還有來自于時(shí)代的影響。道家自老莊學(xué)派之后有黃老學(xué)派,“黃老”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后來黃老學(xué)派不斷發(fā)展。在漢初,黃老理論應(yīng)用于政治,成為治國的主要指導(dǎo)思想,而后漢武帝大興儒學(xué)獨(dú)尊儒術(shù),黃老失勢,與老莊合流。發(fā)展到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道家一方面向玄學(xué)演變,一方面與道教合流。初唐時(shí)期,道教因老子姓李的緣故受到李唐百般推崇,道家思想盛行于世,還被執(zhí)政者應(yīng)用于政治上。特別是唐太宗任用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采取清靜無為的政策,對內(nèi)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外少動干戈,和平穩(wěn)定,故而成就了初唐“貞觀之治”的局面。處于道家思想盛行時(shí)代中的文人,自會受到時(shí)代風(fēng)潮的影響。
二、《感遇三十八首》中的道家思想
陳子昂人生經(jīng)歷坎坷,仕于武后朝,其才初被武后所稱贊,“地藉英華,文稱暐曄。”[1]1585(《唐才子傳》)但是他政治思想多與武后不合,經(jīng)常產(chǎn)生矛盾,所以居官之日,也常遭疏遠(yuǎn),思想較為苦悶。他的《喜馬參軍相遇醉歌》中序曰:“吾無用久矣,進(jìn)不能以義補(bǔ)國,退不能以道隱身”[1]470說出了自己的尷尬處境。
《感遇三十八首》不是作于一時(shí)一地,多數(shù)作于晚年,就其思想脈絡(luò)來看,貫穿其中一條清晰的主線便是道家的思想。對現(xiàn)實(shí)的強(qiáng)烈不滿、對前途的渺茫、對人生的憂患而產(chǎn)生的出世之感是該組詩歌中的主要內(nèi)容。下面從政治觀、人生觀、宇宙觀三個(gè)方面來分述之。
其一,政治觀。陳子昂在政治上推崇儒道并存的觀念。他有著儒家“窮則獨(dú)善其身,達(dá)則兼濟(jì)天下”(《孟子·盡心下》)的濟(jì)世情懷。其父陳元敬說:“吾家世雖儒術(shù)傳嗣,然豪英雄秀,濟(jì)濟(jì)不泯。”[1]1005(《堂弟孜墓志銘》)這里表明陳子昂家世雖然有著道家的根底,但也受儒家思想影響積極入世。然陳子昂在政治上的對策更多采用道家的政治觀念。老子主張“無為而治”,“在政治方面,他用人道主義和民本思想為武器批判現(xiàn)實(shí)政治的人性淪喪。”[3]71人道主義,體現(xiàn)就是一個(gè)“慈”,“夫慈,以戰(zhàn)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wèi)之。”[4]176(《道德經(jīng)》第67 章)老子的“慈”比孔子的“仁”范圍更廣,孔子的“仁”區(qū)別善與不善,這樣必會使得愛有所偏倚,而老子的“慈”卻是“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134(《道德經(jīng)》第49 章)其含義與墨家的“兼愛”類似。民本思想,體現(xiàn)就是“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4]109(《道德經(jīng)》第39 章)老子認(rèn)為,王侯等統(tǒng)治階級也必須以百姓的存在作為基礎(chǔ),他們是“本”、是“基”。
陳子昂在政治上,富有理想,好才能,提出“息兵”、“措刑”等主張,而且同情民生疾苦,反對武后窮兵黷武。這便是老子“無為而治”的主張。《感遇詩》(其三)“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是對武后開邊戰(zhàn)爭的不滿和對人民的深切同情;《感遇詩》(其二十九)“圣人御宇宙,聞道泰階平。肉食謀何失,藜藿緬縱橫”表明對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的向往;《感遇詩》(其十九)“圣人不利己,憂濟(jì)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凈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為尊。云構(gòu)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贊揚(yáng)無為而治的政治方針對人民有利,批評武后大興佛寺是勞民傷財(cái)?shù)谋渍瑹o益于人民;《感遇詩》(其二十六)“荒哉穆天子,好與白云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耽瑤池樂,豈傷桃李時(shí)。青苔空萎絕,白發(fā)生羅帷”以及其二十七“豈茲越鄉(xiāng)感,憶昔楚襄王。朝云無處所,荊國亦淪亡”都有借歷史教訓(xùn)來警告執(zhí)政者的意思。
其二,人生觀。陳子昂在《感遇詩》當(dāng)中有許多鞭撻人心叵測、人情多偽的詩,這與老莊思想的“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fù)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4]48的思想一致。在道家看來,生命的本質(zhì)是自然所賦予的,所以要保持純潔樸實(shí)的本性,需要減少私欲雜念,拋棄圣智禮法的浮文。道家認(rèn)為正是智慧出來了,人民才陷入偽飾中,“智慧出,有大偽”,認(rèn)為知識會妨礙精神自由和生命自由,只有沒有任何功利的、未經(jīng)人偽飾的真誠才是自由。而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更多是“以利相合”,一旦利益產(chǎn)生糾葛,便趨利求榮,這就使得人生痛苦。
《感遇詩》(其五)言: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傾奪相夸侈,不知身所終。曷見玄真子,觀世玉壺中。窅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作者在這首詩中諷刺了世俗之人如同集市商販一樣爭名奪利,而不知神仙世界的超脫自在,可以看出作者對現(xiàn)實(shí)世界的不滿與對神仙世界的向往。
在《感遇詩》(其十)中,陳子昂說:
深居觀群動,悱然爭朵頤。讒說相啖食,利害紛 。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wù)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shí)。
作者指斥人們爭名奪利互相誹謗傷害,在利益的誘惑下紛紛用謊言來羅織罪名構(gòu)陷他人的丑惡世道,見到這樣的世道,莊子說:“人心險(xiǎn)于山川,難于知天。”(《莊子·雜篇·列御寇》),而陳子昂說:“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其十八)、“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亡禍?磨滅成塵埃”(其三十五),都抒發(fā)了作者面對丑惡現(xiàn)實(shí)無法排解而歸于求仙訪道以及憂讒畏禍的心理。而在現(xiàn)實(shí)中,陳子昂兩次被人構(gòu)陷入獄也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映,最后憂憤而卒。
陳子昂《感遇詩》還有一部分詩歌抒寫壯志難酬的悲憤和憂生之嗟。《感遇詩》(其二)言: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dú)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裊裊秋風(fēng)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借山林芳草詠嘆歲月之嗟;其三十一“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借道家的瑤臺之樹詠嘆壯志難酬的感傷。其三十六: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云期。時(shí)哉悲不會,涕泣久漣洏。夢登綏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觀群化,遺世從云螭。婉孌將永矣,感悟不見之。
作者托道家仙游之夢表達(dá)避世隱居而不能的悵惘,也是作者化解人生痛苦的方式。
其三,宇宙觀。在道家的思想體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對宇宙起源、世界構(gòu)成問題的思考,這也是道家體系重要組成部分。老子揭示了萬物生生滅滅的全過程,那就是“夫物蕓蕓,各復(fù)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fù)命。”[4]39(《道德經(jīng)》第16章)實(shí)際上,萬事萬物的發(fā)展變化都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從生長到死亡、再生長到再死亡,生生不息,循環(huán)往復(fù)以至于無窮,皆循著這個(gè)運(yùn)動規(guī)律。這里老子抽象出“歸根”、“復(fù)命”兩個(gè)概念,主張回歸到根源,回到虛靜的本性,去探索“道”的奧妙。老子還建立了宇宙模型,以“道”作為宇宙之起源,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fù)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4]120(《道德經(jīng)》第42章)道家認(rèn)為,世界源自于道,“一”、“二”、“三”是萬物產(chǎn)生的過程,這體現(xiàn)了由少變多、由小變大的思維邏輯。“萬物負(fù)陰而抱陽”就是道本身包含著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相交,萬物便在這種狀態(tài)中產(chǎn)生。
陳子昂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對宇宙的來源做過探討。他在《感遇詩》(其一)說: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征?
首兩句言日月交替之景,《禮記·祭義》中言“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5]407詩三四句是說月圓則虧,暗含陰極則陽生之理,《周易》坤卦上六爻經(jīng)文為“上六,龍戰(zhàn)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zhàn)于野’,其道窮也。”上六爻是乾卦最上面一爻,此時(shí)陰氣已達(dá)至頂峰,然而物極必反,此刻正處于陰極陽生之時(shí)。東晉郭璞《游仙詩》有言“晦朔如循環(huán),月盈已見魄”也是這個(gè)道理。詩五六句所言即為天地萬物創(chuàng)始之初與萬物興廢之理。《易·系辭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孔穎達(dá)疏:“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dú)饣於鵀橐弧<词翘酢⑻灰病9世献釉啤郎弧创颂珮O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5]三元,指的是“天元、地元、人元”,為循環(huán)更替之理,《史記·歷書》記載:“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huán),窮則反本。”[6]詩末兩句是說,天之大道是長存的,因此三正周行,不斷循環(huán),而人卻不能窮極其中之奧秘,這是詩人對宇宙萬物規(guī)律的認(rèn)識。
《感遇詩》(其八)言:
吾觀昆侖化,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構(gòu),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空色皆寂滅,緣業(yè)亦何成?名教信紛籍,死生俱未停。這首詩探索了宇宙人生的根源,前面兩句是說天地變化,日月幽遠(yuǎn),宇宙混沌;其次說陰陽交會而生萬物,仍然是說宇宙的生成,明代鐘惺在《唐詩歸》(卷二)中言:“‘精魄相交會,天壤以羅生’,《陰符》袐語”③;后面四句是作者表明態(tài)度,作者推崇孔子尊《易》和老子尚無,對西方的佛教進(jìn)行了批評。佛教的教義是因緣論,作者認(rèn)為佛教既然說空與色都?xì)w于寂滅,則所謂的前世因緣如何完成?最后,作者對魏晉以來的名教之繁雜庸俗的情況也進(jìn)行了批評。
除了這兩首詩歌外,陳子昂還在詩中闡釋了萬物循環(huán)變化的規(guī)律,并且抒發(fā)了作者身處亂世而無力回天的無奈。《感遇詩》(其三十八)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yùn)自盈縮,春秋遞來過。盲飇忽號怒,萬物相紛劘。溟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這里對“孤鳳”所處環(huán)境的描寫,是作者對于自身環(huán)境的感受與反映,為孤獨(dú)者的“自白”宣言。清代陳沆曰:“‘仲尼探元化’、‘微霜知?dú)q晏’、‘玄蟬號白露’三章,皆事亂世思遺身遠(yuǎn)患之詩。”[1]149(《詩比興箋》卷三)可謂中肯。
三、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中道家思想表現(xiàn)特點(diǎn)及文學(xué)史意義
其一,化用道家之語。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中有許多化用道家故事的地方,用道家之語,或表達(dá)歸隱之情,或?qū)ΜF(xiàn)實(shí)進(jìn)行諷喻。在《感遇詩》(其五)中,作者寫道:“曷見玄真子,觀世玉壺中。窅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這里用仙人能自由出入天地抒泄對現(xiàn)實(shí)的不滿。《感遇詩》(其六)有“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蒙識,誰能測沉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jīng)。昆侖有瑤樹,安得采其英。”這里的“仙道”、“丹經(jīng)”、“昆侖”、“瑤樹”都是道家之語,表達(dá)了詩人向往神仙世界的歸隱之情。
針對這一傾向,明代譚元春說:“子昂《感遇》諸詩,有似丹書者,有似《易》注者,有似《詠史》者,有似《讀山海經(jīng)》者,奇奧變化,莫可端倪,真又是一天地矣。”④通過道家之語來表達(dá)作者之思,言淺而意遠(yuǎn)。但有人也對這種表現(xiàn)展開了批評,如清代的賀貽孫便說:“凡《感遇》《詠懷》,需直說胸臆,巧思夸語,無所用之。正字(注:即陳子昂)篇中屢用‘仲尼’、‘老聃’、‘西方’、‘金仙’、‘日月’、‘昆侖’等語者,非本色也。”⑤他認(rèn)為寫感遇詩就得抒發(fā)內(nèi)心感情,而且語言須得本色自然,絕無門面,他推崇如張九齡那般的感遇詩,莫不是一種觀點(diǎn)。
其二,運(yùn)用比興,托物寄托,塑造鮮明的自我形象。比興是《詩經(jīng)》以來中國詩歌的大傳統(tǒng),是陳子昂《感遇詩》藝術(shù)特色的突出表現(xiàn),也是他在《修竹篇·序》中標(biāo)舉的“興寄”和“風(fēng)骨”在他自己創(chuàng)作中的體現(xiàn)。詩中的比興,也多與道家之物有關(guān)。“寶鼎淪伊谷,瑤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其十四)之寶鼎、瑤臺,“去去行采芝,勿為塵所欺”(其二十)、“夢登綏山穴,南采巫山芝”(其三十六)之靈芝,“瑤臺有青鳥,遠(yuǎn)食玉山禾。昆侖見玄鳳,豈復(fù)虞云羅”(其二十五)之青鳥玄鳳,這些在道家看來,都是些縹緲悠遠(yuǎn)、瑰麗美好的仙人之物,與世無爭,自由自在,它們寄托了陳子昂在黑暗的社會中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志節(jié),同時(shí)通過這些意象的展現(xiàn),也使得詩歌豐滿圓潤,富有道家情趣,形成了沉郁剛健、婉而多風(fēng)的藝術(shù)特色。宋代朱熹有云:“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jié)豪宕,非當(dāng)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shí)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7]正是道家意象在詩歌中的比興,使得詩歌詞旨幽邃,余味悠長,此論莫不如是。
陳子昂在《感遇詩》中還塑造了鮮明的自我形象,“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及“多材固為累,嗟息此珍禽”(《感遇詩》其二十三),借美麗的翡翠來表達(dá)對才識之士不為人知的憂慮;“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jīng)世道,遺身在白云”(《感遇詩》其十一)塑造了高士鬼谷子的形象,也是作者自我精神的體現(xiàn)。而他自己的身世,在詩中也有反映:“本為貴公子,平生實(shí)愛才。感時(shí)思報(bào)國,拔劍起蒿萊。”(《感遇詩》其三十五)陳子昂本也是一位熱血男兒,有著杜甫一般濟(jì)世之懷,然而沉重的現(xiàn)實(shí)讓他痛心,《資治通鑒(卷二〇三)》有云武后事:“太后自徐敬業(yè)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nèi)行不正,知天下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8]武后擅權(quán)以來,不少人擠破腦袋想得到高官厚祿,遂酷吏肆虐,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萬馬齊喑,唯陳子昂挺身而出,于垂拱四年上《諫用刑書》,揭露嚴(yán)刑峻法的真實(shí)情況,但這并沒有什么作用。他在三十六歲時(shí)被陷冤獄,“誰言未亡禍,磨滅成塵埃”(同上詩),后產(chǎn)生隱居之志,也是對現(xiàn)實(shí)無力的反叛。但他這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氣度,這種敢于直諫的勇氣,被后世的杜甫極力推崇,詩有“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9](《杜工部集》卷五《陳拾遺故宅》),稱他為忠義之士。
其三,文論觀方面之復(fù)變思想。道家思想就在一個(gè)“變”字,宇宙生成變化是變,陰陽對立統(tǒng)一是變,而陳子昂處于齊梁文風(fēng)和盛唐文風(fēng)之間,創(chuàng)新求變,為唐詩健康發(fā)展掃盡頹風(fēng),為唐詩大盛、李白杜甫登上詩國頂峰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這在燦爛的中國文學(xué)史上書寫下濃墨重筆的一頁。他在著名的《修竹篇·序》中寫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fēng)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xiàn)有可征者。仆嘗暇時(shí)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fēng)雅不作,以耿耿也。”[1]163面對形式主義嚴(yán)重的齊梁文風(fēng),他求變革新,推崇“風(fēng)雅”和“興寄”,主張恢復(fù)“漢魏風(fēng)骨”,而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則充分體現(xiàn)他的詩歌革新理論,前人就認(rèn)為他創(chuàng)作的《感遇》詩“出自阮公《詠懷》”(唐皎然《詩式》卷三),實(shí)際上阮籍就是陳子昂在《修竹篇·序》里所說的“正始人物”,而陳子昂的《感遇詩》較之《詠懷》內(nèi)容要更為豐富充實(shí),思蘊(yùn)更為深沉。高步瀛說道:“唐初猶沿梁、陳余習(xí),未能自振,陳伯玉起而矯之,《感遇》之作,復(fù)見建安、正始之風(fēng)”[10]正是對陳子昂文學(xué)史之功做出的評價(jià)。
注釋:
①《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jīng)注》中有:“本玄之一氣,凝結(jié)至高曰天,上有主宰謂之帝,道居帝之先,故為元始。”
②文中所有《感遇詩》,皆引自:彭慶生著,陳子昂集校注[M],合肥:黃山書社,2015(3),以下不作說明。
③④[明]鐘惺,譚元春著,唐詩歸(卷二)[O],明君山堂刻本。
⑤賀貽孫著.詩筏[O],嘉業(yè)堂刊《吳興叢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