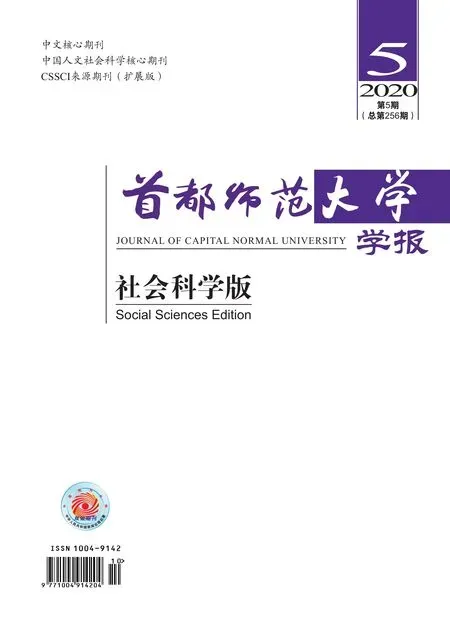“本性美學”如何可能?
——兼與左劍鋒先生商榷
劉建平
長期以來,在中國哲學和美學研究中存在著簡單比附、不求甚解的傾向,似乎一研究中國傳統美學,就是天人合一、回歸自然;一談到某位美學家的思想,就是儒道互補、三教合一……事實上,這些僅憑經驗和感覺建構起來的美學觀點乃至美學理論大多是站不住腳的。對傳統美學命題進行細致的辨析和嚴謹的界定,對傳統思想進行系統梳理和澄清,是和傳統美學資源現代轉化同樣重要的工作,本文對“本性美學”的批判和商榷,也正是立基于此的。左劍鋒在《中國古代本性美學及其對現代美學的影響》①左劍鋒:《中國古代本性美學及其對現代美學的影響》,《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以下簡稱“左文”)一文中,認為傳統的儒釋道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強調發揮人的本性力量去觀照世界”,他進而將這種“有關本性體驗的思想及受其影響的藝術理論”稱為“本性美學”,在“本性”“本性體驗”的概念界定和“本性美學”的立論基礎上都存在諸多問題。“本性”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儒家有“修身之根本在返歸本性”的觀念嗎?“本性美學”如何可能呢?本文認為:一、儒家的修身之根本并非返歸“本性”。二、“本性”并非先秦儒家的“心性”,以“本性”來詮釋“心性”是宋明理學家對先秦儒學詮釋的結果,而非先秦儒家自身的思想,二者不可混同。三、儒釋道對“本性”有著不同的解釋,儒家的心性、道家的自然無為、禪宗的“自性”概念差異頗大,“本性體驗”并沒有揭示出中國古代美學的特質,它既不是理想的人生境界,也不是審美方式,只是一種“工夫”的手段,不能把人格修養、道德實踐和藝術創造、審美體驗混為一談。
一、儒家修身之本并非返歸“本性”
為了更好地理解“本性美學”的概念,我們先探討一下“本性”的概念。首先,儒家所謂的“本性”,并沒有固定的意涵。孔子、孟子、荀子所講的“本性”皆不相同,但基本上沒有否認人的“本性”存在動物本能的一面,“中國古代所言之性,天然地包含著一切與動物共有的本然之性”①張江:《“理”“性”辨》,《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 9期。。孔子沒有講本性之善惡的問題,《論語》中講“性”主要有兩處:一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二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孔子的“性”一方面包含生理感官之欲求,另一方面它又并非形而上的、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有待塑造、自我實現的生命存在;孟子雖言性善,但也沒有否認人的本性中包含著生理本能之欲求;至于荀子,則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多欲”等“生之所以然者”(《荀子·正名》)。可見,孔、孟、荀諸子的“本性”,皆非儒家修身所要達到的理想境界。左文談儒家“本性”思想多以《孟子》為例,為了讓論證更具針對性,本文也主要以《孟子》為例,來辨析一下儒家的“本性”概念。
首先,生理欲求是儒家“本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是在“人禽之辨”的背景下談“本性”的,對“本性”的理解涉及人禽之別,《孟子·離婁下》云:“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本性而言,人和動物的差別很小。然而人畢竟不是動物,這“幾希”的差別在哪里呢?那就是《孟子·公孫丑上》所講的“四端之心”。可見,孟子的“本性”概念并沒有完全排除人禽相通的那些本能欲望,張江認為,本能是“中國古代‘性’之語義核心之點。性為本能,人之質也”②張江:《“理”“性”辨》,《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 9期。。葛瑞漢(A.C.Graham)也說:“孟子主張道德傾向是唯獨屬于人的自然沖動,這并不是說它們就是人性的全部;相反他明確說色聲香味的欲求和身體的舒適也是性。”③A.C.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0,p.27.歸結起來,《孟子》中的“本性”概念至少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生理層面的感官欲求,人在生理上都有追求美味、美服、美色的本能,“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盡心下》)。孟子把這種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作為本性的內涵,這在先秦哲學中是比較普遍的用法,人在生理層面上的“本性”都是相似的(性相近也),具有普遍性,這種感官欲求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把它斥之為動物本性,而與人性無涉。二是精神層面的心之欲求,它是建立在感官欲求相似基礎上的“心”之欲求,“心之所同然”。“心”本有善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郭店楚簡》更是直接指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①涂宗流、劉祖信:《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譯》,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44頁。不同于感官欲求的外在性、他律性,“心”之欲求是主體內在的、自主性的追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孟子·盡心上》)《孟子》的“本性”概念是以上二者兼而有之的,這兩者的發用都是人性正常的呈現。
其次,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是圣人,不是返歸本性,更不是自然人性,而是“工夫論”人格。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②《禮記·中庸》,《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先秦部分》(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96頁。君子所具有的智、仁、勇三德,都不是所謂的“本性”。“智”不是天生的,孔子說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智”是后天努力學習的結果,《論語》中孔子多有“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之語;“仁”的基本含義是“愛人”,但本性意義上的“愛”還是基于生物本能的、狹隘的親情之愛,它需要經過一個由親子手足之愛向社會群體之愛、先天血緣之愛向后天生命之愛的擴充和努力的過程,君子的博大情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都并非是人天生的“本性”所有,而是“修己”的結果;至于“勇”,也絕非是逞能撒潑的匹夫之勇,而是“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勇”是以“義”為基礎的。同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勇”是和獨立的人格聯系在一起的,這才是君子之“勇”,君子人格顯然不是一種“本性”,“(‘君子’和‘仁人’)都是個人成長的不同方面而論,它們對學習和修身養性的熱衷卻是共同的”。③郝大維、安樂哲:《孔子哲學發微》,蔣戈為、李志林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頁。至于孟子獨創的“大丈夫人格”,更是需要經過艱苦的修養工夫和不斷學習才能達到的精神境界,在《孟子》那里,充實則可實現善,不充實則為不善。陳澧明確指出:“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④陳澧:《東塾讀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頁。這是合乎孟子原意的。左文從“以善說性”的視角來詮釋先秦儒家的思想,將《孟子》對人性的分析“邏輯上的可能性”混同于“真實的可能性”(real possibility)⑤SHUN K,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18.,這是對先秦儒家人性論的一大誤解。
孟子之后,荀子更沒有“修身之根本在返歸本性”的觀念。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路德斌認為“生之所以然”乃人之天性,是就“性”存在層面而言的,是指人與動物共通的屬性;“不事而自然”則是此本性之發用——好利、好聲色,也即欲的層面,⑥路德斌:《荀子與儒家哲學》,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111頁。我亦贊同此論。荀子強調人的“本性”是一種“善的缺乏”,如果順著人的本性發展,易流于性情之欲而產生各種亂象和紛爭,“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荀子·性惡》)。圣人和常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圣人能夠“化性起偽”(《荀子·性惡》),什么是“偽”呢?“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在荀子看來,本性是生命存在和延續的基礎,但并不美,也不是美得以成立的依據。“偽”是人后天工夫和努力學習的結果,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社會化,⑦參見Winnie Sung,Eth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Xunzi:A Partial Explanation,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2016,no.13,p.71.無論是“性惡”說還是“性樸”說,荀子都堅持“化性起偽”,主張“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偽”的目的不是認識人性,而是改造人性。⑧參見佐藤將之:《荀學與荀子思想研究:評析·前景·構想》,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年版,第203頁。按照荀子的理解,理想人格不僅包含完美的品格,還有其現實的社會功能,自覺地擔負并完成各種社會歷史使命,“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宋代張載更是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格理想,顯然,這種人格境界不是“本性”概念所能涵蓋的。
再次,我們不能將先秦儒家的人性理想化、抽象化詮釋而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孟子》的性善不是指人的“本性”就是具足善的、完美無待于外的,而是指人性有向善的維度,《孟子·告子上》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這是說仁、義、禮、智等“善端”是人所本有的。《孟子·公孫丑上》云:“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見,這里的“善端”還只是為善的種子,種子不是果實,并非是完滿成熟之德,①Chong K,Early Confucian Ethics:Concepts and Arguments,Chicago:OPEN COURT,2007,p.52.而是有待于生長、擴充、完善,才能臻于“善”的境地;如果人“旦旦而伐之”,讓四端之心“陷溺”,久而久之也會喪失掉為善的可能而淪為動物。就人具備向善的潛能這一點而言,即使是主張“性惡”的荀子也是無法否認的。二程認為:“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②《程氏遺書》卷25,《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1頁。劉述先也認為:“仁心也并不存在于虛渺的彼岸,每個人都可以體驗到它的根芽,問題在于是否能將之擴充到自己全面的生活。能夠擴充則生活的意義飽滿,不能夠擴充則生命的意義感到虛歉。”③劉述先:《生命情調的抉擇》,臺北長榮書局1974年版,第34頁。可見,《孟子》所謂的“本性”只是確立了人性向善之可能的依據,也只是一種“可以為善”的潛能,而不是已經實現了的、完滿的“善”。儒家的修身之本是通過“工夫”的過程使有限的生命生發出無盡的道德價值,而臻于完善的境地,這才是“善”的實現。
二、“本性”并非“心性”
如前所述,“返歸本性”并非是先秦儒家的修身之本,那么為何會產生“一切修身之根本在返歸本性,發揮本性力量”這種說法呢?從中國哲學史來看,宋代理學家如二程、朱熹等不乏以“天理”釋“性”的說法,將“性”分為氣質之性和義理之性,這種以“本性”來詮釋“心性”的模式是宋儒對先秦儒學過度詮釋的結果,而非先秦儒家自身的思想。
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的宋儒對《孟子》的人性論進行了發揮,直接用“天理”來詮釋“性”,強調“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④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5頁。朱熹進一步把“養氣”的目的解釋為“復初”,“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這里的“復”氣之“初”,也即是復性之初,也可稱之為“本性”。在《孟子》中,“氣”還只是一種“工夫”論上的環節,而朱熹則賦予“氣”以道德的意涵,“孟子養氣一段,某說得字字甚仔細,請仔細看”。⑤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第231頁。在朱熹看來,《孟子》的“氣”即是一種源自“本性”之善氣,它原本就具有道德的屬性;而“本自浩然,失養故餒”之說更意味著這種“氣”是生命的本體,并不需要“工夫”和學習而本來就“浩然”。在《朱子語類》中,朱熹還進一步指出“至大至剛”就是氣的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氣的發用,“塞乎天地之間”是氣的效果。⑥朱熹:《朱子語類》卷五十二,第四冊,黎靖德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53頁。朱熹這里確立的不是“性”之本體,也不是“心”之本體,而是“氣”之本體,正如黃俊杰指出的,“它一方面指生理的事實(氣,體之充也),另一方面又指道德的原則(其為氣也,配義與道)”。⑦黃俊杰:《孟子思想史論》卷二,臺灣“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版,第212頁。“氣”是性和理的具體化。⑧事實上,張載早就指出“性”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差異,兩者是相互獨立的,而朱熹試圖打通“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孟子集注》曰:“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認為“氣”是“性”的具體呈現。但他同時又認為“氣”又不同于性、理,性、理是必然之善,它是不會改變的;而“氣”則是可以變化的,在“心”的作用下,“氣”可善可惡,“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圣愚之異”。(《朱子語類》卷四,第一冊,第76頁)在此意義上,《孟子》的哲學可以稱得上是“氣的哲學”,《孟子》的美學是“氣的美學”。問題在于,朱熹對《孟子》思想的詮釋,是否符合《孟子》的原意呢?事實上,孟子并沒有講“氣”具有生理和道德的雙重屬性,也沒有說“浩然之氣”是“本性”所生,而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公孫丑上》)朱熹賦予“氣”以道德的屬性,在“復”氣之“初”上下工夫,這種詮釋方法偏離了先秦儒家以“心性”釋人性的傳統,“本性”難免失之于粗糙、混沌,“心性”才是精神的自覺、道德主體的確立。朱熹在詮釋《孟子》時在“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還是先天具足上游離不定,其思想上的這種矛盾在文本中也有體現,他一方面認為“氣”是本自浩然,“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叚本如是也”①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第231頁。;另一方面又承認“‘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集義以生之者”。②“氣”在運轉過程中會有不同的人性呈現。參見朱熹:《朱子語類》卷五二,第四冊,第1259頁。“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個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③朱熹:《朱子語類》卷五二,第四冊,第1243頁。這里對“浩然之氣”和初稟之氣之間的區別解釋得很清楚了。由此可見,以“本性”來論人性,把“本性”看作理想的人格、完滿的道德實體是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對先秦儒學詮釋的結果。不可否認,這種詮釋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并非正解。盡管朱熹宣稱自己解經是緊扣文本詮釋經典,“大抵某之解經,只是順圣賢語意,看其血脈通貫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也”。④朱熹:《朱子語類》卷五二,第四冊,第1249頁。他的《四書章句集注》《朱子語類》等終不免有刑求古人之嫌。
左文認為“本性”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事實上,《孟子》的核心概念恰恰是“心性”而非“本性”,“心”在孟子的整個哲學思想中處于中心的地位。據統計,《孟子》全書提到“心”的次數高達117次,而《論語》中只有6次。《孟子》中有“四端之心”“不忍人之心”“赤子之心”“盡心”“養心”“求放心”“不動心”“慎其心”等說法,“心”是真正的自我之所在。學界一般稱儒家美學為“心性美學”,而幾乎沒有人稱之為“本性美學”,原因就在于“本性”不是“心性”。那么,儒家的“本性”和“心性”究竟有何差異呢?“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盡心上》)這里的“性”并非天生的,而是通過“心”的工夫和修養過程建構起來的,因而稱之為“心性”,把《孟子》的“性”解釋為“本性”、把“天”解釋為“天性”都是一種誤解。⑤孟子的“性”不僅沒有排除生理欲望,而且也不同于先驗的、抽象的道德實體,是一種“心性”。牟宗三特別指出,孟子性善作為具有內在道德性的“性體”,是一種具有實踐動力的“性能”,是一種能活動、創造的“創造實體”,不同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本質”只是一種到處可以應用的“類概念”,指涉事物某種抽象的形式特征。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版,第39-40頁。“養氣”的工夫就是用天地自然的“正氣”滌蕩內心、淘汰沉渣,實現人與自然的能量交換,只有確立了道德的主體性,內在的“充實”才能顯現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莊嚴氣象。故而史華慈(B.I.Schwartz)指出:“(孟子)問題意識的中心實際上并不是本性(性)而是人心/心靈(心)。”⑥史華慈:《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程鋼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頁。牟宗三也認為“心”在孟子思想中具有本體論的意義,⑦牟宗三:《康德的道德哲學》,《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04頁。徐復觀更是明確指出,孟子的思路就是“以心善言性善”,⑧徐復觀認為,孟子所言的性善的“性”,并非“本性”的“性”,只是生而即有內容中的一部分,這一部分通過“心”的作用而當體呈現,是為“本心”(切勿望文生義地認為“本心”就是“本性”),孟子實是以“心”統性、情、才。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162頁。其內在的原因不言自明。
左文對先秦儒家的基本理解之所以出現諸多偏差,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宋儒對先秦儒學的詮釋(也有過度詮釋)取代了對先秦儒學思想本身的研究。左文認為:“在儒釋道的本性體驗中,人回歸本性。而本性是先天稟有的,是天道下貫于人的結果。因此,回歸本性亦即返歸一切價值的最終源頭——天道。于是,在本性體驗中發生了一種‘位移’,由小我、私我進入大我、無我。”事實上,以孟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價值根源并非來自于“天道”,而是來自精神自覺的主體之“心”,也就是徐復觀說的“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價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話、迷信的力量,使每一個人,能在自己的一念自覺之間,即可于現實世界中生穩根、站穩腳”。①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自敘),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心”的發用方式,也絕非是由“天道”上往下貫,而是由“心”下往上溯。這里的“位移”是個物理學/數學上的概念,意味著在一個平面上物體的位置變化。照此邏輯,似乎本性體驗“由小我、私我進入大我、無我”是一個平面推移的過程,這是根本不符合《孟子》思想的。孟子的存、養、充、擴皆是“心的作用”,而非所謂的“本性力量的觀照”;存、養、充、擴的過程,也并非“本性”的復制、推移,而是本性的純化、升華,是動物性向人性主體的躍進。儒家上溯升華、躍進的目的地,并非是一個什么抽象的“天道”,也不是那個理想化的“本性”,而是生命共感的養成。孟子的“怵惕惻隱”之心即是你的心和小孩子的心產生了關系,它意味著人在精神深處開始對生命的某種共同價值產生了體認和向往之情。不僅是小孩子將要掉入井中,即使見到有人虐待小狗、小貓,我們的心靈也會產生類似的感覺,甚至看到一朵花被雨打落、一片樹葉在風中飄零,也會喚起我們對生命同樣的感觸,這種由內而外、由感而通的情感共鳴和生命共感,也就是牟宗三所言的“儒家的悲憫,相當于佛教的大悲心,和耶教的愛,三者同為一種宇宙的悲情(cosmic feeling)”。②牟宗三:《中國哲學的重點何以落在主體性與道德性》,項維新等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總論篇,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頁。人的“心”通過自覺、自證、自知的覺悟、認識所達到的精神境界卻不是人本性所有,而是由生活的情感體驗而擴展到群體的生命情感,進而達到陸象山所言的“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的“天道”層面一氣貫通的結果。在此意義上,“本性”并非是生命的理想境界,愛美人、愛美食還難脫離實用功利之愛,愛自己、愛親人還是一種狹隘的血親之愛,這都可以說是一種本性。儒家的修養“工夫”就是要超越個體一己之限制,從有限的世界出發而向無限的宇宙價值的發現邁進的努力,進而養成一種民胞物與、萬物一體的偉大的生命共感。“返歸本性”“本性覺醒”等說法把“本性”看作一抽象的道德實體或永恒的人性假設,它既排除了人性的生理基礎,又抽空了人性的社會基礎,從而背離了先秦儒家“心性”的本質。先秦儒家所講的“性”,是以“心”作為主宰的,孔子講“我欲仁,斯仁至矣”。這里不是“天道”欲仁,不是“本性”欲仁,而是“我”欲仁。對“仁”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天道”,也不是“本性”,而是確立了道德主體的“我”。沒有“心”之主體,就沒有什么“本性覺醒”“本性力量”。所以孟子也說:“仁,人心也。”忽略了“心”對身的主宰性,“心”對“性”的主宰性,就不可能理解先秦儒家的人性論。
三、“本性體驗”不是中國古代美學的本質特征
左文將中國古典美學稱為“本性美學”,認為“本性體驗”是中國古代美學特色的“根本體現”,這是不符合美學史的常識的。
首先,“本性體驗”不是一種審美體驗。左文認為“本性”是先天稟有的,一方面“本性體驗”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覺等感性因素于一身,另一方面又認為“就古代本性美學而言,本性覺醒只有在擺脫情欲的束縛之后才有可能”,這里在邏輯上是矛盾的,情欲恰恰是推動藝術創造和審美的重要動力,“生命、本能、情欲非絕對生物性的,非簡單的生命欲求,而包含深刻的人性和道德訴求”。③張江:《“理”“性”辨》,《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 9期。本能、情欲、直覺是“本性”的重要構成,是人對各種現象產生的神經感應的生物基礎,尤其是審美的感觸與沖動,都是起于這些神經性、生理性反應,正如張江所言,“中國古代之性,天然地與情及欲相融而生,由情及欲,是高于器官之本來感覺,并為具有深刻浸潤性、塑造性的重要因素”。④張江:《“理”“性”辨》,《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 9期。因此,“本性”在擺脫了情欲之后,究竟是“覺醒”了還是“泯滅”了呢?擺脫了情欲的“本性”究竟在什么意義上能成為藝術創作的“基礎”和“前提”呢?
我們再看看“本性體驗”這個概念。“本性體驗”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對“本性”的感受和體驗,還是達致本性的“工夫”過程呢?左文對“本性體驗”提出了諸多模棱兩可的解釋,“本性體驗”一會兒是“超出個人利害計較”,一會兒是“和諧的生命情趣”,一會兒是“溫厚的道德情感”,一會兒又是“理想的審美化生存方式”,一會兒又變為“‘樂’的體驗”,類似的說法,在左文中還可以找出很多。這種解釋好像面面俱到,無懈可擊,但結果是“本性體驗”看起來無所不包,實際上是一個沒有任何實際內涵而淪為意義“內爆”的空泛概念,也就是說,“本性體驗”因為被賦予了過于豐盈的意義而超出了其自身的承載能力,從而淪為一個無意義的概念——似乎什么都是,其實什么也不是。左文以“孺子將入于井”為例,提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四端之心”就是儒家的“本性體驗”,孟子所講的作為“本性”的“四端之心”還只是“善端”,還處于粗糙、本能的初始階段,它既有待于內在提升、擴充、純化,同時還要呈現為外在的形象,也就是“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審美體驗不僅是一種生命的體驗,而且還是一種生命的創造,是新的人生境界的開拓,是對以往生存經驗的升華,絕不是左文中所講的“本性覺醒”或“返歸本性”那樣的心理活動。因而,先秦儒家的“工夫”過程只是人格修養的體驗,而非審美體驗;它所養成的主要是一種道德情感,而非審美情感。若將二者隨意混同,那倫理學就是美學,道德就是藝術了。
其次,“本性體驗”缺乏“踐形”的維度。左文認為儒釋道都以“返歸本性”作為修身之本,這無論對先秦儒家、道家還是后來的佛教、禪宗,都是一種不夠準確的論斷。①道家的本性中的“無知”,和后來經過“心齋”“坐忘”后達到的“忘知”,能說是一回事嗎?佛教的“自性”概念能和左文的“本性”簡單等同嗎?本文主要以先秦儒家“本性”概念的辨析為主,其他兩家的“本性”待另文論述。事實上,無論是孔子的“里仁為美”,孟子的“充實之謂美”,還是荀子所謂的“性偽合”,都不是所謂的“本性體驗”,而是人通過修煉和選擇(擇不處仁、集義所生)的結果。
“本性體驗”也好,“返歸本性”也罷,大都是指向內在的、心理的活動,還只是一種靜態的、理想化的人性描述,缺乏外在的形式呈現,缺乏“踐形”的維度,更缺乏在社會實踐層面落實和拓展的依據,它又如何可能具有生活改造的功能指向呢?左文提出“本性美學則向內深化了感性”,這是很令人費解的說法。如何是“向內深化了感性”?是閉目塞聽式地“內化”為心理活動,還是化感性為理性呢?儒家的“心性”不僅有向內的開拓,也有向外的展開和落實;不僅有個體內在精神上的升華,還要有在社會生活層面上的“踐形”和“踐行”,“確切地說,孟子的盡心,必落實到踐形上面。能踐形才能算是盡心。踐形,乃是把各官能所潛伏的能力(天性)徹底發揮出來;以期在客觀事物中有所作為,有所構建”②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172頁。。這里的“各官能所潛伏的能力(天性)”意味著儒家的“工夫”不僅不否認生理感官之本性的存在,同時還是對這些本性的解放,這恰恰不是“向內深化”,而是向外拓展,是人的身體和精神向外擴充、達于天地外物的過程。《孟子·告子上》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要經歷一個推己及人、存—養—充—擴的過程,“擴是放開,充實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③朱熹:《朱子語類》(二),《朱子全書》第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3頁。。這里“擴充”“充實”的過程絕對不只是李明輝所謂的只有量(應用范圍)上的擴展,而是德性的完滿,是境界的提升,是善的實現。④參見劉建平:《生命本真氣象的呈現——論孟子的“充實之謂美”》,《哲學與文化》2019年第7期。愛自己的孩子是本性、自然的本能,愛別人的孩子是人性、非自然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需要經過后天的“工夫”過程才可能實現,絕非是一種先驗的本性。如果“四端之心”就是“本性”,就已經是完滿自足的善,那還有什么“擴充”的必要呢?“推己及人”正是為了克服“善端”最初的有限性、差等性,“本性”是“推”的源頭和基礎,但并不是結果和終點;“推己及人”并非是生命自然而然的演進過程,而是要經過主體“克己”的人格修煉和不斷學習、創造、開拓的精神努力,因而在儒家思想中,內在的人格修煉和外在的學習、教育就成為純化情感、轉化個性的重要途徑,“‘學’意味著獲得和擁有先輩們投注到文化傳統中的意義”⑤郝大維、安樂哲等:《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頁。。真正的“仁”和“善”,一定不是本性,由“本性”向“心性”躍進的“工夫”過程,才能“具體引導中國社會、中國人生活現實的改造”,①王德勝:《功能論思想模式與生活改造論取向——從“以美育代宗教”理解現代中國美學精神的發生》,《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這是由個體層面向社會層面的擴大,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私愛”向以生命關懷為基礎的“博愛”的升華,這才是“泛愛眾,而親仁”“民胞物與”的真正含義。
再次,“本性體驗”與感物論的關系。從“本性體驗”對中國藝術的影響來看,左文認為立基于人格修養的儒家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對文藝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前者在詩學中發展為感物說,后者往往與前者交織在一起,使感物之情更為深厚廣博,表現為富有悲憫和同情意味的生命共感”,感物說強調的是由生活閱歷所構成的人生感受對文藝創作的重要性,例如“詩窮而后工”說、“憤書”說等,但我們首先應該區分“本性美學”能否成立是一回事,而它在后世的文藝創作中能否產生影響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必要條件,并不能證明前者存在的合法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健認為是“物”而非“本性”才是審美創造和審美體驗的感發之源,“在感物興情的過程中,物、情的律動都是物所主導的”②李健:《中國古代感物美學的“感物興情”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對物的感應并非是“本性”的發用,更不是由“本性”推動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物在情先、物在“性”先才是文藝創作的規律。劉勰云:“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③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5頁。這種心物交融的藝術創作過程和所謂的“本性體驗”之間很難說有什么直接的關系。
四、“本性美學”:一個空泛的命題
在中國美學中,“美”不能被定義為經驗,它只能被定義為對存在的體驗,因為生命存在本身無法界定,“美”就是體驗生命存在的重要途徑。④Cheng Chung-ying,A Study in the Onto-Aesthetics of Beauty and Art:Fullness and Emptiness as Two Polarities in Chinese Aesthetics,Edited by Ken-ichi Sasaki,Asian Aesthetic,Kyoto:Kyoto University Press,2010,p.133.然而,“本性”并不是生命存在本身,“本性體驗”也不能說是一種審美體驗。西方哲學史上有美是事物本身的完善的說法,奧古斯丁曾提出過“美在完善”的命題,克羅齊也認為“用把那個完善歸于感性認識的辦法,使得一些混亂的東西變成了不再是否定而是肯定的東西”⑤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王天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頁。。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性”并不是美學意義上的“完善”。左文引用傅佩榮的觀點認為“善性”是一趨向,是一等待被實現的潛能,這也說明了“善性”并非是自然而然實現的,在此意義上,“本性體驗”還是一種初始的、不明朗的情感體驗,是一種生理本能、日常功利欲求、情感欲求與道德心性需求相混雜的狀態,并非理想的人格境界。在《孟子》中,美不是“善”而是對“善”的超越,它是充實了的“善”并賦予“善”以情感、溫度和“氣象”,使其得到情感的浸潤而成為可“擴充”的精神養分,而非冰冷的道德原則。孟子正是通過“養氣”“立志”“盡心”的工夫,讓“善端”擴而充之成為“充塞于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并由此成就“大丈夫人格”,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儒家美學是一種由身把握心、由性而“踐形”的“身心合一論”。
同時,左文在文中多次強調“本性美學”在古代哲學中占有核心地位,對古代美學和藝術創造起著導向作用,并反復強調人格修養和“本性覺醒”在藝術創作中的核心地位。中國美學史、藝術批評史上有“文如其人”“畫如其人”之類的說法,形成了以人品來評價藝品的批評傳統,即藝術家人格修養的境界越高,他就越能將藝術作品提升到一個高超的境界,所以徐復觀指出,“在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中,總認為做人的境界與作品的境界分不開”⑥徐復觀:《傳統文學思想中詩的個性與社會性問題》,《中國文學精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藝術家的人品與藝術創作之間存在關系確實不假,然而,將人格修養的境界與藝術作品的境界作一一對應的“文與人合”“跡與心合”的思維模式,未免顯得有些機械。首先,人生經驗和藝術經驗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人格修養和藝術造詣也是不能直接等同的,由人格修養、“本性覺醒”而得到的只是一種倫理體驗,而藝術修養不僅有賴于豐富的生活經驗的積累,更有賴于藝術體驗的積累、藝術技巧的練習及審美經驗的豐富等。左文雖然注意到了人品與藝品不一致現象的存在,但他仍然堅持“本性體驗及修身工夫均為藝術創作的前提條件”“理想藝術創作需以本性體驗為基礎”等觀點,這就有失偏頗了。無論是古代畫家鄭板橋的“必技工而后能寫意”,還是當代畫家劉國松的“先求異,再求好”等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藝術創作理論,都沒有把人格修養看作是藝術創作的前提。單純的“本性體驗”、人格修養并不能成就偉大的藝術作品,也不能成就偉大的藝術家,正如單純的技巧訓練一樣,不宜過度夸大人格修養對藝術創作的影響。①可參見劉建平:《徐復觀與二十世紀中國美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其次,將人品與藝品一一對應的批評方式往往容易造成對偉大藝術作品的“誤讀”,似乎我們只要把藝術家的生平了解一番,對藝術家的人格和品行有所把握,就可以判定藝術作品的價值了,甚至無需去欣賞藝術作品本身,這顯然是不夠客觀的。另外,從藝術批評史上看,將人品與畫品、文品相聯系并在藝術實踐中得到了體現,是宋、元以后的畫家進行理論總結和詮釋的結果,與所謂的“本性美學”實際上沒有直接的關系。
綜上,本文結論如下:
1.孔、孟、荀諸子修身所要達到的理想境界并非“本性”。“本性”既包括人與動物同類并存的生理本能,同時又包括異于禽獸而獨有的道德潛能。道德上的“善”與人的“本性”之間是存在緊張關系的,“善”一方面要通過后天的“工夫”修身克己,將“善端”加以擴充;另一方面,這種向善的追求也是符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然而它并不是善本身,不能說“本性”就是“善”,就是完滿自足的存在,孟子的“性”指的并不是某種普遍相同的性質,②參見李巍:《“性”指什么——孟子人性論的起點》,《現代哲學》2016年第5期。不是一種先驗的、抽象的道德實體。儒釋道的“本性力量”都沒有否認生理本能等感性欲求的意義,都沒有否認身體和感性在生命安頓中的重要價值。本能、情欲、直覺是“本性”的重要構成,也是審美發生的生理學基礎,擺脫了情欲、本能的“本性”及“本性體驗”不是審美體驗。
2.“本性”并非“心性”,以宋儒的對先秦儒學的詮釋取代了對先秦儒學思想本身的理解,這是左文詮釋先秦儒家“本性”概念錯誤的根源。先秦儒家價值根源是來自“心”的一念自覺反省,其發用方式絕非是由上往下貫,而是由身而心的“身心合一論”,是由下而上的“心性論”。同時,儒釋道“工夫”的過程各不相同,如何能用“本性”一詞“一言以蔽之”呢?按照這個邏輯,我們是否可以炮制出“心齋美學”“坐忘美學”“克己美學”“禪定美學”等概念呢?“本性美學”這一概念既沒有人性論的堅實根基,也缺乏君子、圣人的人格理想維度,更缺乏明確的“工夫”和方法,只是一個空泛的概念。
3.審美和藝術在“本性美學”中居于什么地位呢?左文認為“由人格修養到本性體驗,再到藝術審美,最后又返歸人格修養、本性體驗,從而使得整個生活得以改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本性美學的整體性”。這里說的“整體性”恰恰是闡釋學上的死胡同。“本性”既然是天生(先天稟有)的,人從一開始由人格修養已經獲得了“本性體驗”,我不知道通過藝術審美繞了一大圈又回到“本性體驗”的意義是什么?是回到了原點呢,還是升華了“本性體驗”的層次呢?如果后面的“本性體驗”只是回到了原點,那么藝術審美并不是人格修養和生活改造的必須途徑,因為通過“本性體驗”就可以實現對狹隘的現實人生利害的超越,取途于審美和藝術豈不是走了一個大彎路?審美反倒成了人格修養的累贅;如果后面的“本性體驗”升華了前面“本性體驗”的層次,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此“本性”還是彼“本性”嗎?“本性”難道可以從獸性、人性到神性劃分很多等級嗎?這究竟是“本性”還是“心性”呢?如此一來,這樣的“本性”概念就不是生之秉性,而是失之“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