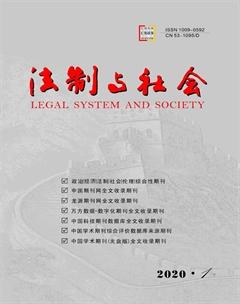論未成年人監護相關制度的構建與完善
沈鵬程
摘要 未成年人監護關系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和社會秩序維護,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關于未成年人監護,雖已通過立法、司法等手段予以規范,但關于監護人及其他相關主體法律責任,僅僅停留在監護人資格的撤銷、終止等方面,未能有效規制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構建與完善相關制度,以此督促監護人及其他相關主體履職盡責。
關鍵詞 未成年人 監護 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2.7 文獻標識碼:A DOI: 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1.254
一、問題的引出
2013年6月,南京幼女餓死事件發生,舉國嘩然,聞者無不震驚。其后,雖相關當事人伏法受誅,卻無法挽回兩條幼小的生命。有人或謂,此案實屬家長疏于照料且人性泯滅所致,與社會其他主體無涉;有人卻主張追究相關主體責任。對此,筆者認為拋去社會公眾道德批判不論,僅從監護法律關系角度而言,該案實際上反映出家庭監護缺失、負有監護職責的部門未能履職盡責等問題,這無疑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如何通過有效制度設計,明確未成年人監護領域各方主體權利義務,進而不斷強化未成年人監護利益保障。
在現今社會發展語境下,未成年人監護主體構成早已超出家庭親權主導時代,而逐步過渡到傳統家庭親權和國家親權協力發展時期。監護不再是特權,而是義務;監護不完全是家庭內部事務,也是社會公共事務,這早已成為當今社會共識。因此,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領域,社會各方主體均應發揮其應有作用。以往基于家庭親權所構建的監護制度不能完全滿足當今社會發展需要,國家親權理論逐步發展并與家庭親權理論共同影響著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構建及完善。
二、相關制度構建的理論基礎
關于傳統監護理論,最早出現于古羅馬法。其主要以家長主義為支撐,以家父權關系為基礎逐步發展完善的,其后伴隨國家出現及法學理論發展,其概念范疇和規范內容不斷擴張豐富。我國古代也存在類似監護的制度。如《宋會要>記載:“元豐令,孤幼財產,官為檢校,使親戚撫養之,季給所需。”這主要是講,宋神宗時期頒布詔令,針對雙親已亡之孤兒財產,官府設置檢校一職或部門,命令親戚撫養孤兒,并按季度供給撫養所需。較之于古羅馬,我國古代類似規定雖顯匱乏且未成體系,但其在封建時代為未成年人特別是孤兒利益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據,具有其時代意義。
所謂國家親權,是指國家對兒童和其他法律上無行為能力人享有一般的監護權。該理論肇始于英格蘭,其發展與完善具有顯著的時代需要和特點。早期行使國家親權,表面上看是對普通民眾的撫恤,實質上便于國家對未成年兵力的支配與控制,或基于維護封建領主土地附屬權益的需要。其后伴隨司法審判文明進步,國家親權的福利性質才逐步得以彰顯。從上述定義看,國家親權具備幾個顯著特征:一是國家親權具有福利性,以國家干預形式充當監護人角色,保障未成年人相關權益,具有顯著的社會福利傾向,這無疑是社會福利理論向未成年人監護領域延伸的重要表現;二是國家親權具有補充性,從傳統親權理論向國家親權理論演變的歷史進程中不難發現,國家親權的發展在于不斷彌補并解決因傳統親權缺陷造成的諸多侵犯未成年人監護權益的問題;國家親權具有強制性,國家親權的啟動和實施由強制性立法規范和司法程序保障,具有強制性特點;國家親權具備有責性,基于國家親權理論發展所創設的種種制度包括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實現,無一不是國家權力向私法領域的延伸,無論基于何種利益考量,根據當代社會主流觀點,國家權力的行使特別是對私人領域的干預均應秉持審慎態度,根據有權必有責原則,因其不當行使造成私人權益侵害,亦應承當相應責任,自不待言。
結合前揭案例,樂某系虐死幼女之生母,追究其刑事責任自不必言。但從案發前推至月余,作為負有相關職責的居民委員會、派出所民警等其他主體未能盡到合理關注義務,致使慘案發生,其是否對此應承擔相關責任,值得我們思考。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他人盡其所不能承擔之過分義務,但也并不能據此便斷定各涉案主體(除樂某外)與此案無關,實屬牽強。因此,有必要通過立法手段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制度,按照國家親權理論,探索構建侵權、行政主體責任承擔、未成年人公益訴訟等制度規范,以此明晰各方主體權利義務,從而為未成年人監護權益保障提供更為全面有力的支撐。
三、相關立法規范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欲構建和完善未成年人監護相關制度,首先應對我國相關立法規范現狀進行梳理,并通過將其與實踐相印證,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而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此為基礎構建和完善相關制度。
關于未成年人監護的規定,主要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青少年犯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以下簡稱《民法總則》、《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青少年犯罪法》、《侵權責任法》、《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法規中。201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通過了《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規制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提供了有力遵循。但縱觀上述規定,不能否認,由于立法規定的時代性、法律條文表述的局限性、社會發展的快速復雜性等原因,在未成年人監護秉持國家親權主義的今天,以往某些規范內容已漸現匱乏無力,亟需構建或完善相關制度。具體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缺乏規范家庭、教育機構以外的其他相關主體責任規定
《民法總則》第十六條至第三十九條依次對未成年人監護人、監護人身份的確定、監護人的權利義務、監護人身份的撤銷與終止等作出規定,但對于監護人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責任承擔未作相關規定,這抑或在于調和《民法總則》原則性規定與《侵權責任法》等其他具體規定之間的沖突;考察《侵權責任法》,僅通過第三十八條至四十條對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等主體責任予以規范,缺少對除上述負有監護職責主體以外其他主體侵犯未成年人監護權益的規范;同樣,作為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專門法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僅僅在其第六章即法律責任部分作出籠統規定;《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主要傾向于婦女權益保護、《義務教育法》主要傾向于規范義務教育實施主體與受教育者權利義務關系的規定,對其他相關主體責任也少有規范。根據國家親權理論,未成年人監護是一項社會公共事務,除上述法律規定所涉主體以外的其他主體同樣享有權利,亦同樣應承擔相應義務,對侵犯未成年人監護權益的行為同樣負有責任。因此,有必要通過修訂相關規定,進一步明確其他主體責任承擔形式,從而為未成年人監護權益保障提供充分依據。
(二)缺少針對未成年人監護公益訴訟的規定
縱觀上述及其相關法律規定,雖賦予了未成年人近親屬等主體請求法院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權利,但未成年人監護領域并未設立公益訴訟制度,這無疑剝奪了其他主體提出正當請求的權利,顯然不利于未成年人保護。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可以拓寬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法律途徑,加大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力度。目前,關于公益訴訟主要集中于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領域,且已發揮良好作用。未成年人權益(包括監護權益)保護同上述領域相較,具有同等保護意義。
(三)缺乏統一未成年人保護立法
從頂層設計上來說,現行未成年人保護并未形成整體性、長期性、獨立性、時代性的立法體系。未成年人保護(包括監護)立法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保護的專門性法律、設有未成年人保護專章的法律、附有未成年人保護條文的法律。不難發現,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立法規定散見于各實體法及程序法之中,因獨特的立法歷史背景,未能形成法律用語規范、法律體系健全、法律邏輯統一連貫的立法規范;同時,與以規制成人行為為基礎和視角構建起來的立法規范不同,未成年人保護具有其獨特性,這是由未成年人獨特的身心發展和認識程度決定的;另外,獨特的時代發展階段也決定了未成年人保護統一立法規范形成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信息爆炸時代深刻影響并改變了未成年人觀察、認識及反饋世界的方式,由于未成年人認識和判斷事物能力較弱,極容易受到不良信息誘導,從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因此,亟需根據未成年人獨特發展特點制定相應統一立法規范。
四、相關制度的構建與完善設想
(一)監護監督人的設立及其責任承擔
《德國民法典》第1792條、第1799條、第1833條對監護監督人身份的取得、監護監督人的權利和義務作出明確規定。其中第1833條規定:“(1)監護人有過錯的,對因義務之違反而發生的損害向被監護人負責任。監護監督人亦同;(2)一人以上一同對損害負責任的,他們作為連帶債務人負責任。”這些規定無疑具有借鑒意義。反思前揭案例,雖在案件審判進程中律師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聯名向其他相關政府部門請求公開其職責履行情況,但因對相關實際上負有監護監督義務的其他主體缺乏有效規范,最終被其以各種無理理由拒絕公開,也因此無法令其承擔應負之責任。倘若通過立法明確其他相關主體監護監督人職責及其承擔責任的方式,則在其他主體未履行監護監督義務時,便可據此追究其相關民事責任。因此,有必要引進監護監督人制度,為未成年人監護權益維護提供制度保障。
(二)構建未成年人公益訴訟制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有利于強化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通過構建和完善未成年人公益訴訟,賦予前述作為未成年人監護監督人及其他相關社會主體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可以拓寬未成年人監護權益維護法律救濟渠道。
(三)探索構建未成年人統一立法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具備構建未成年人保護統一立法的各方面基礎。如前所述,已形成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青少年犯罪法》等專門法律為基礎的多方位、多角度立法規范。同時,結合解決司法實踐中產生的各種法律適用問題經驗和多年來積累的立法實踐經驗,未來在整合相關法律規定的基礎上,逐步形成體系完整、邏輯連貫、內容成熟的統一的未成年人立法規范,從而為未成年人監護權益保護保駕護航。
五、結論
未成年人監護關系其身心健康發展和社會秩序維護,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當前,因相關立法、司法制度缺失,在監護人和其他主體侵害未成年人監護權益時,無法根據相應規范進行有效規制。雖然我國已制定了大量關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規定,但由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及其自身發展的獨特性與復雜性,很多立法規定未能充分發揮其規制作用。同時,在傳統家庭親權和國家親權協力發展的當今時代,未成年人監護早已無法由家庭個體主導,而是需要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方可為未成年人監護提供有力支撐。當然,在賦予家庭、教育機構等以外主體監護權利時,也應該明確其相應義務和責任。這都需要通過構建和完善相關立法、司法制度予以實現。未來,隨著未成年人保護統一立法出現,必將能夠為未成年人監護提供更為充分的法律制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