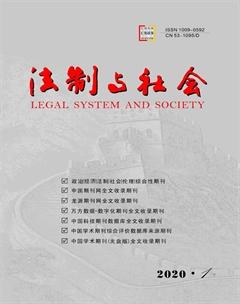新《土地管理法》對小產權房問題的規制
何家成 何杰
摘要 原《土地管理法》規制下的城鄉二元土地管理模式是小產權房形成的根源。我國近十幾年來對小產權房問題的態度經歷了由“堵”轉“疏”的變化。新《土地管理法》正式確立城鄉一元土地管理模式,為小產權房問題提供切實可行的入市流通路徑。
關鍵詞 小產權房 商品住宅用地 規制
中圖分類號:D922.3 文獻標識碼:A DOI: 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1.265
城鎮居民住房壓力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問題。伴隨近十幾年來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高溫,我國城鄉結合部分地區出現大量由農村集體成員出資建設,并轉賣于城鎮居民居住使用的“小產權房”。“小產權房”并非法律術語,受原《土地管理法》限制,因該類房屋只能在農村集體成員間流通,城鎮居民無法以購買形式獲得房屋產權,更無法得到不動產登記證書,而被稱之為“小產權房”。
一、小產權房問題的由來
原《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集體所有土地用作建設用地的,只能在鄉鎮企業、村民住宅建設或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的范圍內,而其余范圍的建設項目需使用土地的,應當申請使國有土地。若社會資本需要使用集體所有土地,必須走“由當地政府征收集體土地,再由開發商向政府購買集體土地使用權”的道路。這一條文是我國城鄉二元制土地管理模式的根源所在,也使得政府在建設用地的管理上具有壟斷性權利。政府作為“中間商”在社會資本與集體間賺取征收差價,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起到了穩固政府財政控制力,集中資源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城鄉經濟建設差異的日趨明顯,鄉村反哺城市的經濟發展模式遇到新的挑戰。部分鄉村集體不甘受制于政府征收土地的低廉價格,憑借手中的土地所有權向社會資本發出要約,本意在于加快社會資本流入農村的進程,為農村經濟建設尋找新的出路。而社會資本苦于國內房地產市場高企的建設用地使用出讓費已久,雙方一拍即合,開始在城鄉結合地帶發展工業、商業、商品住宅等建設項目。部分房地產開發商通過直接與村集體簽訂合作開發協議,在未經當地政府審批、征收轉變土地性質的情況下,將集體所有土地用于經營性建設。一方面,房地產開發商免于向當地政府交納巨額的土地使用權出讓費,在城鄉結合部地區興建商用住宅帶來的巨大利潤使得房地產開發商趨之若鶩;另一方面,農村集體成員以高于政府征收價的條件出讓土地使用權,往往還能得到開發商低價置換房屋的承諾。經濟利益驅使下,城市周邊一幢幢無產權證的小產權房拔地而起,而農村耕地紅線則一再被突破。
由于開發商未按照政府規劃進行工程建設,無法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此類小區無法定性為城市居民住房,更無法取得房產證。然而此類住房進入房產市場流通的不在少數。購房者迫于城市附近房屋房價高起的原因,甘冒無產權證書的風險,購買農村居民用房。這一方面片面的緩解了城鎮居民住房壓力,另一方面,也在司法實踐中帶來諸多問題:小產權房的購買、使用合同如何定性?購房者權益如何保護?違規建設的房屋應當如何處理?堵不如疏,想要根本性的解決小產權房問題,必須從城鄉二元制土地管理模式入手。
二、土地政策的轉變
從2007年徹底禁止小產權房的交易到今時今日改變城鄉二元制土地管理模式、科學引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我國政府在小產權房問題上經歷了從“堵”到“疏”的態度轉變。新《土地管理法》的定稿與施行,也標志著新的集體土地流轉模式的初步建立。
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規定:“其他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必須是符合規劃、依法取得的建設用地,禁止入市后土地用作商用住宅開發”,這一通知從根本上否定了小產權房交易的合法性。當時我國正面臨嚴重的農村集體土地濫改濫用問題,18億耕地紅線處于被突破的邊緣,從政策形成的角度做理解,政府為了防止農村集體擅自改變土地用途,將小產權房交易“一刀切”為違法的判定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通知》本身并沒有對如何防止小產權房的開發建設、已經建成的小產權房作何處理等問題做出回答,可見《通知》是時代壓力的產物,我國正迫切需要一條切實可行的土地管理新政策。
2008年,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陳錫文曾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到:絕對禁止開發商興建小產權房,但對于已經在城鄉結合部購買了小產權房的買受人,政府應當對他們合法的利益進行保護。此時,中央城府已經明確意識到,一味禁止絕不是小產權房現象的解決途徑,通過適當途徑加以疏導,權衡保護小產權房購房者的利益、緩解城市居民住房壓力,才能既治標又治本。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農村宅基地問題改革中提出:“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2015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33個試點縣試點改革。這是黨中央在農村土地政策導向上的一次重大轉變,此后,全國紛紛開展試點工作,圍繞“農村集體土地入市交易”的核心命題進行開創性的實驗。
2019年8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土地管理法》把黨中央、國務院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決策部署和試點成功經驗上升為法律,在充分總結試點成功經驗基礎上,做出了多項重大突破,標志著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新《土地管理法》將原《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刪除,并在第二十三條和第六十三條規定“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依法登記,并經三分之二以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意的情況下,可以出讓、出租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個人使用,使用者還可以通過轉讓、互換、抵押的方式進行再次轉讓。”這一規定從根本上打破了政府對建設用地的壟斷,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流通提供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案,城鄉土地二元化管理產生的差異也將因新《土地管理法》的施行而逐漸被抹平。
如前文所言,小產權房的出現,源于原《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帶來的城鄉二元土地管理模式。新《土地管理法》旨在建立城鄉一元土地管理模式,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納入市場流通領域的做法必然包含商品住宅建設用地的流轉。至此而言,小產權房建設似乎迎來合法化的曙光。
三、新法中對小產權房建設的調整
(一)商品住宅建設內含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并經依法登記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可以……”其中的“經營性用途”是否包含商業住宅建設用的?對比《物權法》第一百三十七條關于“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方式”的規定,該法律條文中對“經營性用地”做了“工業、商業、旅游、娛樂和商品住宅等”的列舉,可見從《物權法》的角度而言,經營性用途應當包括工業、商業、旅游、娛樂和商品住宅等。
其次,新《土地管理法>實施的目的在于探尋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入市流通的方法,改變城鄉土地二元化管理模式。商品住宅類建設用地在經營性用地的占有相當的權重。禁止商品住宅類用地在市場流通,將無法有效的緩解城鎮居民住房壓力,更與修法目的相背離。從本次法律修訂的目的統一性與法律體系間的完整性上解釋,將新《土地管理法》解釋為允許商品住宅類經營性用地入市流通的更具有合理性。
(二)小產權房的權屬
新《土地管理法》中第十一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舊法也有類似的規定。本次修法并未改變農村集體的所有成員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地位,亦再次明確了集體土地入市流轉后所得的收益應當歸屬于全體所有權人。在小產權房的歸屬問題上,奉行房隨地轉的政策,不變更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人地位,而將土地使用權及土地上的附著物的所有權交于購房人即可完成小產權房的權屬關系變更。
(三)集體土地流通方式的轉變
相較于舊法,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并應當簽訂書面合同,載明土地界址、面積、動工期限、使用期限、土地用途、規劃條件和雙方其他權利義務。”第三款規定“通過出讓等方式取得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或者抵押,但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或者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權人簽訂的書面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農村集體直接與社會資本簽訂合同,轉讓一定年限內建設用地的使用權能,使得建設用地的供給市場不再由政府壟斷。從正向關系而言,房地產開發商為尋求更大的利潤空間,將向廉價的集體所有建設用地示好。大量社會資本流入農村,必然對當地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形成良性影響。同時由于已經取得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后續轉讓、抵押,也避免了社會資本的資金壓力,降低了入門門檻,使得市場環境趨向于充分競爭。而從反向關系而言,集體所有土地國有化路徑不再是集體所有土地入市的唯一通道。因此,從今往后政府的征地價格將必然因為社會資本的競爭而上升,通過買賣土地所有權改善地方財政狀況的問題也將得到改善,而農村集體成員也能享受到因征地價格提升而帶來的利好。
(四)地方政府對集體土地流通的監管
新《土地管理法》中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用“計劃管理”的模式對建設用地的總量進行控制,并編制“土地利用年度計劃”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做出合理安排。出于社會穩定性的考慮,新《土地管理法》并未承認完全市場化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通模式。政府仍然應當秉承科學引導,合理計劃,適當干預的方針,既要放開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手腳,讓集體土地順利的流入市場,又要在市場調節過程中細心監管,在出現問題時及時解決。
四、結語
長久以來,原《土地管理法》規制下城鄉二元化土地管理模式已經積聚了太多矛盾與糾紛。農民利益因征地、土地入市限制等因素而被閹割,社會資本也缺乏正常流入農村的渠道,小產權房問題不過是這些利益博弈下的外在問題表現形式。想要根治小產權房問題,可謂“華山獨徑”,即改變城鄉二元土地管理模式。新《土地管理法>即將于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此時正是新舊交替之際。新法確立的一元城鄉土地管理模式、集體經營性土地入市規則、“簡政放權、讓利于民”的工作原則方是根治農村土地問題的治本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