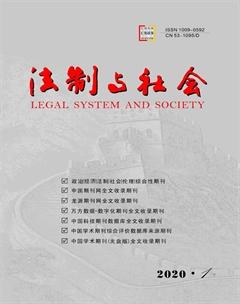淺析遺贈扶養協議的解除
洪丹霞
摘要 我國的人口結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已步入了人口高度老齡化的階段。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尚在建設中,家庭和公民個人仍舊是贍養老年人的中堅力量。但現實情況是有部分老年人沒有法定贍養義務人或者雖有法定贍養義務人但贍養義務人基于各種原因沒有時間照顧老年人。為了能夠安享晚年、擺脫孤獨,老年人選擇與法定贍養義務人以外的公民簽訂遺贈扶養協議。遺贈扶養協議履行期限較長,在此期間容易發生一方反悔要求解除協議的情形。鑒于遺贈扶養協議兼具有人身性和財產性,我國現行法律對于遺贈扶養協議的解除尤其是當事人有無任意解除權沒有明確的規定,本文將從遺贈扶養協議制度的設立初衷、協議履行的特點來分析當事人有無任意解除權以及如何完善有關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規定。
關鍵詞 遺贈扶養協議 解除 任意解除權 傾斜性保護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 87/j .cnki.1009-0592.2020.01.344
一、遺贈扶養協議的概念、特征及有關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立法、司法現狀分析
(一)遺贈扶養協議的概念、特征
遺贈扶養協議是指遺贈人與扶養人簽訂的,由扶養人承擔遺贈人的生養死葬的義務,遺贈人的財產在其死后歸扶養人所有的協議。遺贈扶養關系是一種平等、有償和雙務的民事法律關系。簽訂遺贈扶養協議目的在于使那些沒有法定贍養義務人和雖有法定贍養義務人但基于各種原因實際上無法讓無法得到贍養的孤寡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規定,扶養主體必須是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公民和集體組織,由此可見扶養人與遺贈人通常沒有親密的血緣關系。此外,遺贈扶養協議約定扶養人取得財產的時間為遺贈人去世以后,即扶養人是延遲獲得財產的,在此之前扶養人需要履行扶養義務且該履行期限往往比較漫長。
(二)有關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立法、司法現狀分析
基于上文提到的遺贈扶養協議的特點即扶養人履行扶養義務的時間比較長以及協議雙方通常沒有親密的血緣關系,所以雙方極易產生矛盾。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即便是親生子女也可能因為工作、照顧子女等客觀因素對父母的耐心逐漸減少。而一旦耐心的減少發生在沒有親密血緣關系的遺贈人和扶養人之間,遺贈人對扶養人就會產生猜忌,維持遺贈扶養關系的情感基礎就會受到沖擊,于是就出現一方或雙方提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情形(司法實踐中遺贈人提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占絕大多數)。而我國法律有關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規定較少,僅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十六條中規定到“扶養人或集體組織與公民訂有遺贈扶養協議,扶養人或集體組織無正當理由不履行,致協議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遺贈的權利,其支付的供養費用一般不予補償。遺贈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致協議解除的,則應償還扶養人或集體組織已支付的供養費用”。
因對該條規定的理解不同,司法實踐中對協議雙方尤其是遺贈人提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處理結果也大相徑庭。除了協議雙方均同意解除遺贈扶養協議或者遺贈人有證據證明扶養人未履行扶養義務而被判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外;對于一方沒有違約的情況下另一方可否要求解除遺贈扶養協議(即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權)判決結果卻大不相同。有部分判決認為“因扶養關系屬于身份關系的一種,具有極強的人身屬性,因此遺贈扶養協議不應適用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雙方當事人均應有任意解除權”,持此種觀點者認為遺贈扶養協議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被扶養人的權益而非強調協議的契約性、公平性,所以當遺贈人從內心上不認同扶養人的扶養,法院不能維持遺贈扶養協議的效力,因此應當賦予協議雙方在被扶養人死亡前的任意解除權③。但是更多的判決認為“雙方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是其真實意思的表示,沒有違反法律規定,簽名后即具有法律約束力,任何一方非依法律規定或者取得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遺贈扶養協議屬于繼承法律規范,屬于財產關系協議,當事人并不具有任意解除權”。由此可見,司法實踐中對于遺贈扶養協議的當事人是否具有任意解除權爭議頗大。
二、筆者認為現行法律規定未賦予當事人任意解除權
(一)任意解除權的行使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任意解除權是指不需要以對方違約為前提就可主張解約的解除權。通說認為任意解除權是法定解除權,僅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才可適用。司法實踐中亦僅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中有明確規定的合同主體可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行使任意解除權。即便是對《合同法》明確規定任意解除權,有部分學者仍認為“適用范圍過寬,應當進行限縮解釋”。所以,筆者認為不應隨意擴大任意解除權的適用范圍,在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情形下,任何一方不得隨意解除遺贈扶養協議。
(二)《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并未賦予當事人任意解除權
比較《合同法》中任意解除權的規定和《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可知,該條并未明確賦予當事人任意解除權。例如,《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條明確規定“定做人可以隨時解除承攬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五條明確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而《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并未寫明協議雙方或者其中一方可以隨時要求解除合同。筆者認為如果將第五十六條理解為賦予協議雙方任意解除權,將會導致人們認為法律對協議方尤其是扶養人背信棄義的違約行為(即條文中的“無正當理由”不履行扶養義務)不作否定性的評價,這不僅有違立法初衷更是違背了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故將該條理解為遺贈扶養協議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更為符合立法本意。
(三)通過賦予當事人任意解除權無法實現對遺贈人的傾斜性保護
有一種觀點認為賦予協議雙方尤其是遺贈人任意解除權,便于鞭策或監督扶養人履行扶養義務,任意解除權是遺贈人唯一的“武器”,筆者卻認為此種觀點未免太過“單純和美好”。
第一,遺贈人的意愿是主觀且波動的,其意愿可能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尊重遺贈人一時的意愿并不一定能夠真正地最大限度地保障遺贈人的權益。據筆者對部分可查詢得到的判決文書的分析,遺贈扶養協議糾紛中除了遺贈人和扶養人外往往也有其他人牽涉其中,除了小部分確實是因為扶養人不履行扶養義務導致遺贈人主張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絕大多數的遺贈人要求解除遺贈扶養協議往往與第三人的介入脫離不了關系。比如,部分第三人得知遺贈人尚有財產從而故意討好遺贈人并挑撥遺贈人與扶養人的關系,或者未履行贍養義務的法定繼承人挑唆遺贈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而隨著年齡的增大,老年人的是非判斷能力逐漸下降,遺贈人與扶養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后能否得到更好地照顧根本無法確定。所以一味地尊重遺贈人的“意愿”極有可能使其陷入紛爭甚至是陷阱當中。
第二,鑒于遺贈扶養協議中扶養人取得財產在后,履行扶養義務在前,否認遺贈人的任意解除權并不會使遺贈人的利益受損。遺贈人提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如果扶養人不愿意與遺贈人解除的,其應當繼續照顧、關懷遺贈人,修復、維系雙方之間的關系,以獲得遺贈人的認可。否則,遺贈人的拒絕接受扶養將會給扶養人履行義務帶來很大難度,從而可能導致扶養人無法獲得遺贈的財產。若扶養人在遺贈人已因其未盡扶養義務提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情形下依舊不積極履行義務,遺贈人完全可以以扶養人未履行遺贈扶養協議為由要求解除協議,而無需依據任意解除權。即遺贈扶養協議中有關扶養人義務以及違約責任的約定就是遺贈人的“武器”。
第三,筆者認為不宜因遺贈扶養協議的人身屬性較強為由而賦予當事人任意解除權。相較于遺贈扶養關系,婚姻關系的人身屬性應該更強,但即便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亦沒有賦予婚姻雙方任意解除婚姻關系的權利。
三、關于完善遺贈扶養協議解除問題的思考
(一)筆者認為可通過制定具體細則或是發布遺贈扶養協議范本的方式指導當事人細化遺贈扶養協議中扶養人的義務,以便更容易判斷扶養人有無違約
目前我國法律對于扶養人義務的規定是“生養死葬”,這一規定過于籠統。關于“養”如何“養”沒有明確規定,以致于各地法院認定扶養人有無全面履行“生養”義務的標準不統一。客觀上來說,隨著經濟和精神文明的發展,老年人需要的不僅是經濟上的供養還有精神上的慰藉,所以如果不細化“養”的標準將不利于保障遺贈人的利益。
(二)筆者認為可明確規定可以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特定情形以及解除的方式
遺贈扶養協議確實具有較強的人身屬性,遺贈扶養協議目的的實現依賴于扶養人與遺贈人之間的感情基礎,扶養人需自愿長期如親人般地照顧遺贈人的生活,給予遺贈人精神上的安慰;同時遺贈人對扶養人也要有一定的信任和寬容,雙方能夠進行良好的溝通。而一旦雙方之間的信賴關系和感情基礎破裂,就不宜強迫任何一方繼續履行遺贈扶養協議。我國《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中對于哪些情形下可認定為“感情卻已破裂”有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成為了判定是否需要解除婚姻關系的重要依據。所以,筆者建議可以參考解除婚姻關系的條件即認定感情確已破裂的情形,詳細列出當事人可要求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幾種情形,比如遺贈人與扶養人因發生矛盾已分開居住達到一定期限,或遺贈人已由其他人實際贍養達到一定期限等具體情形。通過規定具體的可以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情形(對這些特定情形的設置可以更傾向于考慮遺贈人的意愿和權益保護),給予遺贈人一定的解除權利,而并非只有在遺贈人舉證證明扶養人不履行扶養義務的情形下遺贈人才可解除協議。如此便給遺贈人解除遺贈扶養協議提供更多的可能,在任意解除權與扶養人不履行扶養義務才可解除協議之間找尋一條折中之道。
四、結語
遺贈扶養協議制度是我國繼承制度的重要補充,也是緩解國家和家庭養老責任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妥善處理遺贈扶養協議糾紛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先從任意解除權的角度出發探討現今法律框架下解除遺贈扶養協議的難點,進而提出兩點建議以便當事人尤其是遺贈人在發現簽訂遺贈扶養協議的目的無法實現時可以順利地解除協議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以上淺薄意見,望對遺贈扶養協議制度完善能稍有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