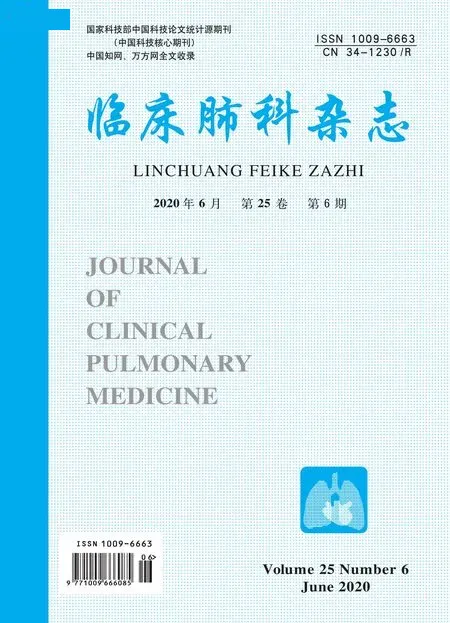ARDS基因組學相關生物標志物及臨床研究現狀
左海濤 陳永青 楊志華 李雪飛 謝建軍 胡曼青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多種病因引起的肺泡毛細血管內皮細胞和肺泡上皮細胞損傷,造成彌漫性肺間質及肺泡水腫,以進行性低氧血癥和呼吸窘迫為臨床特征[1]。ARDS是重癥監護病房常見的危重癥,臨床死亡率極高,早期發現并積極干預對于改善ARDS預后非常重要[2]。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個體遺傳基因突變涉及ARDS的發病過程,對ARDS基因突變標志物的檢測有助于預測疾病易感性,便于對死亡風險進行分層,并可能揭示新的治療靶點[3]。本文就近年來ARDS基因組學相關生物標志物及臨床研究現狀予以綜述。
ARDS病理生理學的分子研究
ARDS涉及多種復雜的病理生理學改變,臨床特征的異質性可能與潛在的生物遺傳學差異有關。在多種危險因素作用下,ARDS肺組織發生廣泛的炎癥反應,導致肺泡上皮細胞和內皮細胞釋放多種炎癥分子和炎癥介質。II型肺泡上皮細胞損傷和內皮細胞的活化可導致肺血管阻塞,引起肺泡中蛋白質沉積以及炎癥性肺水腫形成,使肺組織的通透性增加[4]。研究發現,ARDS患者肺組織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水平明顯降低,VEGF是一種可影響血管通透性的糖蛋白,具有復雜的多效生物活性。VEGF可維持正常的肺泡結構,促進血管內皮細胞遷移、增殖和血管形成,通過上皮再生參與肺損傷后組織修復。VEGF也可促進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損害肺泡-毛細血管屏障的完整性,導致肺水腫形成[5]。因此,VEGF對ARDS肺組織的病理生理改變具有雙向調節作用。
ARDS除了肺泡毛細血管內皮細胞屏障出現功能障礙外,肺組織嗜中性粒細胞聚集和多種炎癥因子異常表達也影響ARDS的病理生理學過程[6]。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是病原體賴以生存而變化較少的主要部分,使病原體很難產生突變而逃脫固有免疫的作用。例如:PAMP中的革蘭氏陰性細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可激活多種信號通路,觸發炎癥介質釋放,導致肺泡-毛細血管屏障功能障礙。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TLR)是參與非特異性免疫的一類重要蛋白質分子,可識別壞死組織與細胞碎片,誘導炎性介質表達,引起炎性細胞浸潤到肺泡腔,進一步導致肺部炎癥反應并損害呼吸功能。游離線粒體DNA和線粒體肽屬內源性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在調節對肺損傷的反應中也發揮關鍵作用。DAMPs是宿主來源的分子結構,具有調節病原體識別及受體激活的作用。DAMPs來自受損和死亡細胞、細胞外基質或作為免疫調節蛋白存在于細胞間質中。DAMPs既可以充當TLR激動劑或拮抗劑,又可以調節TLR和NOD樣受體信號級聯。這種多樣化的分子類型可能作為ARDS的重要治療靶標[7]。
ARDS易感基因研究
目前,ARDS相關基因及生物標記物研究,多集中在鑒定生物學候選基因編碼中的遺傳變異風險方面,涉及細胞生長和發育、組織通透性、血管代謝、氧化應激及凝血反應等[8]。與ARDS易感性相關的基因類型,與不同的種族遺傳有關。例如:以歐洲人為研究對象的ARDS患者,Egl-9家族低氧誘導因子1基因變異與30 d內ARDS死亡風險增加獨立相關。該因子和低氧誘導因子降解脯氨酰羥化酶,是人類對低氧環境適應性反應的關鍵調節劑,在組織低氧和炎癥反應之間提供聯系。目前,Egl-9家族不同基因突變狀態對ARDS易感性的影響尚不明確[9]。
ARDS早期即存在肺血管收縮和纖維增生,53%的ARDS持續機械通氣超過5 d可出現纖維化病變[10]。有研究報道了特發性肺纖維化常見風險基因變異與ARDS易感性的關聯。粘蛋白5B(Mucin 5B,MUC5B)基因啟動子的多態性顯示與特發性肺纖維化的臨床相關性較大。MUC5B等位基因變異純合子有中等程度的ARDS發生風險(OR:1.47;95%CI:1.02~2.1)。研究支持在ARDS和特發性肺纖維化之間可能存在共同的遺傳風險[11]。另外,晚期糖基化終產物(Advanced glycosylation end-products,AGEs)特異性受體基因變體,可表達編碼肺上皮細胞損傷的標記物。有研究分析了AGEs可溶性受體和內源性分泌性AGEs的血漿水平,AGEs基因變異與ARDS風險增加和AGEs可溶性受體血漿濃度升高相關。根據血漿AGEs可溶性受體水平有助于確定ARDS易感目標人群[12]。
在對ARDS的實驗動物模型研究中,也將miRNA作為為治療靶標,以降低炎癥性細胞因子,如白介素-1(Interleukin-1,IL-1β)和腫瘤壞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 alpha-α,TNF-α)的表達,減少細胞凋亡及肺損傷。細胞凋亡異常可觸發肺損傷,涉及與凋亡相關的多種蛋白質,包括Bax、Bcl-2和裂解半胱天冬酶-3等,也被稱為肺損傷生物標記物,在ARDS的早期階段即可出現明顯變化[13-14]。Fang等[15]研究了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作為潛在的miRNA調節劑,對暴露于LPS的肺微血管內皮細胞進行功能獲得和功能喪失研究,以確定miRNA在LPS誘導的細胞凋亡和炎癥反應中的作用。研究發現,LPS(1μg/mL)可明顯誘導內皮細胞中miRNA的表達。miRNA沉默可以阻斷LPS誘導的ACE2抑制,并伴有凋亡減少以及IL-1β和TNF-α的產生。ACE2的過度表達可削弱MiRNA介導的內皮細胞凋亡。miRNA耗竭則減弱LPS暴露小鼠的肺部炎癥反應、中性粒細胞浸潤和血管通透性,并恢復ACE2表達。研究表明,miRNA介導LPS引起的肺內皮細胞凋亡和急性肺損傷,與對ACE2的抑制作用有關。ACE2被認為是miRNA的靶基因。
其他有關ARDS易感基因的研究,涉及免疫應答、炎癥因子、血小板功能異常等方面。例如,防御素是生物免疫系統中的重要調節分子,有學者研究了防御素β1基因變異與ARDS易感性和存活率的關系。研究表明,rs1800972點的G等位基因攜帶者更易發生ARDS且預后不良。防御素β1基因轉錄及轉錄后RNA的穩定性異常,與ARDS風險增大和預后較差有關[16]。由于有絲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1調節與炎癥和凋亡有關的細胞內信號傳導途徑,發生遺傳變異后可能影響與ARDS相關的炎癥和轉錄修飾過程[17]。同樣,血小板可通過參與炎癥反應和血管內凝血來影響ARDS的發病過程。富含亮氨酸重復序列的16A基因的遺傳變異,可影響血小板形成,與ARDS風險降低有關[18]。盡管ARDS相關候選基因研究尚存在局限性,初步研究結果提供了遺傳基因變異與ARDS易感性具有較強的關聯性。
ARDS與全基因組關聯研究
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可在全基因組層面上驗證基因與疾病的關聯,目前已經揭示數百種涉及多種復雜疾病易感性和不良預后的基因變異。對歐洲人群與創傷相關ARDS患者GWAS的關聯研究,使用Illumina公司的人Quad 610芯片進行全基因組基因分型,在B淋巴母細胞系中采用定量性狀基因座分析進行功能驗證。單核苷酸多態性功能評估顯示,rs471931在11q13.3上對酪氨酸磷酸酶受體F型多肽相互作用蛋白α-1基因中的mRNA表達產生順式調節作用。該基因編碼脂蛋白-α,參與細胞粘附、整聯蛋白表達和細胞-基質間相互作用,編碼基因突變參與了創傷相關ARDS的發病過程。研究支持對ARDS發病風險進行多中心GWAS研究的可行性,初步確定了潛在的候選風險基因[19]。
Rautanen等[20]分析了因嚴重膿毒癥、肺炎或腹腔內感染性休克而入住ICU的歐洲成年ARDS患者的28 d死亡率。在三個獨立的隊列研究中完成了GWAS評估。研究確定了FER基因的一個常見變異,與肺炎引起的敗血癥死亡風險降低有關。該基因編碼的蛋白質是FPS/FES非跨膜受體酪氨酸激酶家族成員。具有調節細胞與細胞間粘附,并通過生長因子受體介導從細胞表面到細胞骨架的信號傳導。生存分析結果顯示,與非攜帶者相比,具有FER變異的ARDS患者90 d內死亡風險更大。FER變異可以作為肺炎引起嚴重ARDS患者生存的預后因素。另一項獨立的GWAS研究發現,有14個基因位點與ARDS 28 d死亡率增加相關,這些基因編碼空泡蛋白13同源物A和富含半胱氨酸分泌蛋白LCCL結構域2。前者含有有害的錯義變體,編碼分子通過反式高爾基體網絡進行蛋白質循環控制,在自噬降解中起重要的調節作用。后者的蛋白質產物與先天免疫有關,在敗血性休克中減少,與降鈣素原水平的變化有關,是膿毒癥最有效的生物標記之一[21]。
總之,對具有ARDS發病危險個體進行相關基因及生物標記物檢測,有助于識別疾病易感性,便于對患者進行危險分層,以確定治療目標及分析預后。由于大多數GWAS是在歐洲人群中進行的,不同種族ARDS的基因易感性可能存在差異,因此有必要在不同人群中進行研究,以發現更多的特異性ARDS易感基因。不同人群中大樣本的GWAS研究,將增進對ARDS遺傳基因突變的認識,有助于改善ARDS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