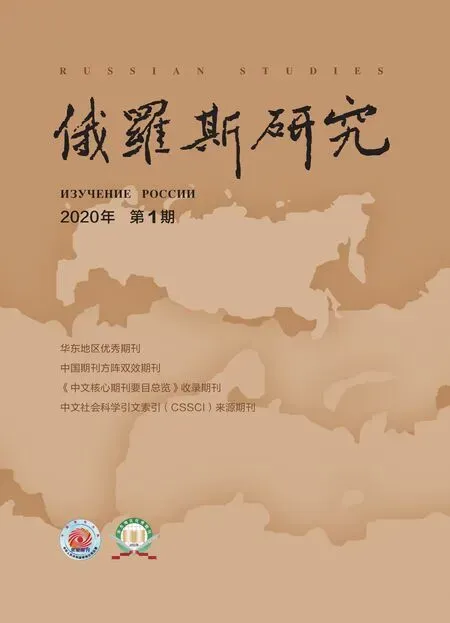“自由國際秩序”、多極化與俄羅斯的“2024議程”*
馮紹雷
【內容提要】在國際秩序構建問題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國際秩序”理論、普里馬科夫的多極世界思想、基辛格的國際秩序演變觀,是三種來自不同思想譜系、取向與功能各異、對國際秩序延續和轉型有著各自思考的理論。雖然三種立場之間有時看似對立,存在著相互沖突與逆轉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開對話,乃至探尋共識的空間。從物理學意義上的外在結構,或簡單引用歷史先例,來尋找未來世界秩序演進的軌跡,顯然已經不夠。關注上述不同立場間的爭議與各自在互動中的調整,研究各大國間很不相同的國內進程與“全球轉型”之間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2020年初俄羅斯開啟了“2024議程”。俄羅斯政府改組和普京提出憲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部署與相關的廣泛討論,不僅旨在解決社會經濟的緊迫挑戰,同時也指向2024年現總統任期屆滿之后的中長期政治經濟安排。像俄羅斯這樣將當下困難問題的處理與長遠發展戰略部署加以聯系,將本國內部事務的轉型與未來世界發展的潮流相互銜接的做法,值得學界關注。
引言
21世紀以來,引發國際熱議的重大議題之一,乃是世界秩序的延續和轉型,以及這一背景下主要大國內部演進及其相互關系將如何發展的問題。本文的寫作意圖在于,針對世界秩序問題的若干關鍵性范疇——如“自由國際秩序”、多極化(或多極世界)的認知正在發生的變化,探討東西方各種不同認知之間的復雜互動如何影響實際的進程。筆者試圖提出的關鍵問題是,在當下紛亂的世界中,是否還有可能在未來世界秩序構建這樣的關節點上,通過對話,探尋利益和觀念的交織與互補,推動各方立場的接近。本文的初步體認是:從中長期角度看,來自不同思想譜系的具有代表性的核心理念,在國際秩序構建問題上,有時看似針鋒相對,但并非沒有可達成共識的空間。形成共識非常艱難,也必定會出現以對抗取代合作的歧見和倒退。但無論從觀念、利益和戰略、政策運作這幾個方面看,都存在著從相互交織重疊的領域出發,一步步探尋合作的可能性。作為一種實例,本文也試圖展示俄羅斯作為全球變遷中的一個關鍵大國,如何應對全球轉型背景下國內與國際事務的相互作用,提升大國地位與影響,也謀求內外兩種轉型的大步推進。
首先,對于近年來學界和媒體有關世界秩序問題的爭議,本文并不打算做面面俱到的引介,而是選擇最具代表性的關鍵性范疇,包括其中的爭議和反思,進行介紹、分析,以尋求走向共識的路徑。本文擬側重介紹伊肯伯里的“自由國際秩序”理論、普里馬科夫的多極世界思想以及基辛格對國際秩序演變歷史的系統總結。在這三位中,伊肯伯里作為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他所闡述的“自由國際秩序”理論,是對已有百年實踐積累的美國與西方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的成敗得失及前景,所做的系統分析。這一模式現在雖然遭遇巨大爭議,但若想對此作正本清源式的解讀,伊肯伯里的理論還是可以作為對話的思想資源。普里馬科夫的多極化思想,并非獨創,但顯然是針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表現出的衰落,而提出的因應改進之道。多極化思想雖暫不具備那種具有全面替代性的結構模式,但已局部地轉化為當今國際秩序實際運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基辛格作為當今政學兩界最有資格對世界秩序問題進行評說的戰略大家之一,反倒顯得立場超脫,似乎并未特別力挺任何一種類型的世界秩序主張。但他通過總結歷史,對于國際秩序延續和轉化的機理、原則和方法等問題的見解,特別是對于“合法性與權力的平衡”這一關鍵點的強調,給人們帶來不少啟發。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胡利平、林華、曹愛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序言。
因為這三種理論具有各不相同的內容與功能,而且有著各不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更不用說他們背后還有迥然相異的政治立場,所以,我們期待這種敘事角度的反差,能打破既定范式,或是超越就事論事式的慣性,有助于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理解和感悟。本文試圖在有限的篇幅內,將世界秩序之爭和俄羅斯“2024議程”②俄羅斯的“2024議程”這一提法,乃是筆者對于2020年初以來圍繞著普京總統提出的俄羅斯憲法修改草案,將2024年以后俄羅斯國內的憲政安排、經濟復興計劃(包括巧妙地將這一安排與當前改善經濟的短期措施相結合)以及俄羅斯外交戰略的調整,這幾件大事的長遠規劃和統籌部署的統稱。筆者認為,這是在當前全球轉型的背景下,俄羅斯內政外交與之互動的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重要進程。這兩個看似并不直接關聯的過程,放置在一起加以觀察分析,希望能找出這兩者之間客觀存在著的、同時也是內在互相深刻關聯的動態演進邏輯,為理解未來世界構建與俄羅斯的互動的可能取向,提供哪怕是非常初步的思考。為此,筆者較傾向于使用“全球轉型”這種新的表述,來描述世紀之交以來、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以來的世界整體性改變。③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019, No.1.這種改變不僅是全球性的、地區層面的、發生在各國相互之間的,而且特別不可避免地發生在主要大國內部。
總體來說,由力量結構改變所導致的這種內部和外部關系的重組和制度規則的變遷,以及因現代信息科技這樣的外部條件的變更,所促使的觀念、心理、行為范式的變化,正以或是激進式的突變,或是累積式的演進,推動著全球意義上的轉型。俄羅斯作為當今世界一個主要大國,無論人們對其現有影響力和未來可能的潛能,及其內外政策的實施,有多少不同的評價,但多少都能感受到,這個被眾說紛紜的大國正在積極因應著上述這樣一個全球轉型的深刻過程。
一、“自由國際秩序”的爭論及其啟示
“自由國際體系”在很多年中是美國兩黨共識和美國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受到新老自由主義者的多年辯護,與美國霸權地位的盛衰息息相關。毫無疑問,這是討論未來國際秩序問題時最核心的范疇之一。即使在既有的國際秩序風雨飄搖之際,這一范疇還是會受到強勁的辯護。
(一)伊肯伯里的“自由國際秩序”理論
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是在國際秩序研究方面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學者之一。2006年,由他領銜撰寫、并成為民主黨競選綱領的“普林斯頓報告”發表后,伊肯伯里率高級學術代表團在中國各地訪問交流,當時曾參與京滬一系列學術活動的中國國際問題學者可能還對此記憶猶新。①馮紹雷:“普林斯頓報告的背景、內容與評估”,《中國戰略觀察》,2007年第 3期。2009年,伊肯伯里發表“3.0版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美國和關于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爭論”的長篇報告。該報告闡述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歷史沿革,全面勾畫了其內容框架,深入分析了國際秩序演進的各種愿景。雖然此報告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剛剛發生過后作者的思考和表述,帶有深重的理想主義色彩,經過十年來各種前所未見的國際沖突和激進演變之后,該文寫作時的背景也已經時過境遷,但仍不失鮮明的當下針對性。在未來國際秩序構建這一問題上,無論懷有怎樣的意愿和構想,也無論形勢變化如何令人眼花繚亂,都還有必要回到國際秩序構建——既是一個現實的國際政治議題,同時也是一個智識領域——的原則和設計構架本身,進行有根有據的全面系統的思辨和討論。伊肯伯里的報告可以作為討論這一問題的一個基礎性的文本。②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n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9, Vol.7, No.1, pp.71-87.
1. “自由國際秩序”的歷史性沿革
伊肯伯里的研究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自由國際秩序”的歷史性沿革,另一個方面則是這種歷史性變化邏輯中所包含的各種維度。
伊肯伯里提出,歷史地看,“自由國際秩序”有 1.0、2.0、3.0等各種版本。所謂1.0版“自由國際秩序”,乃借助于伍德羅·威爾遜的思想而產生。威爾遜主義起源于民族國家涌現、民族主義興盛的年代。威爾遜主義雖主張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治原則,但在20世紀20到30年代的復雜國際背景之下,“自由國際秩序”并未被真正實施。美國自己也不想執行有關和平和戰爭的協定,而是回到19世紀早期運用國際仲裁方式來解決爭端的狀態。因此,當時的國際秩序只能算是一個0.5版的“自由國際秩序”。
伊肯伯里認為,2.0版“自由國際秩序”大體上是冷戰時期的國際體制。20世紀40年代,羅斯福像威爾遜一樣,希望建立大國合作與強制下實現和平的體制。美國通過重建歐洲、對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實現一體化、確認承諾、開放市場、提供安全保障、遏制蘇聯,奠定了國際秩序的基礎。在冷戰陰影之下,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的國際秩序邏輯也宣告形成。
戰后第一個十年,“自由國際秩序”原是由西方主導、多層次、有多種機制加以保障的。但是,局勢的變化逐漸使得美國開始行使直接的政治和經濟管理。此后十年,歐洲孱弱、蘇聯抗爭,建立秩序的各種復雜需求,使美國主導的市場、美元、冷戰同盟等機制,成為戰后國際體制的關鍵所在。美國不僅覺得自己是國際秩序的領導者和支持者,而且是一個所有者和行動者。于是,自由主義的、但同時是霸權式的國際體制出現了。
伊肯伯里認為,以下因素大大推進了3.0版“自由國際秩序”的問世:(1)冷戰的終結,對手的消失,同時也使美國式的霸權邏輯客觀上趨于終結;(2)支配式的等級制關系,逐漸變成了討價還價;(3)究竟是美國式的單邊行動還是聯合國更具權威,日益成為問題;(4)國際主體大幅度增加,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崛起。①馮紹雷:“普林斯頓報告的背景、內容與評估”。伊肯伯里認為,3.0版的“自由國際秩序”,也即后霸權式的“自由國際秩序”,目前只是部分地出現,其完整的面貌和邏輯還處于遠不確定的狀態。
2. “自由國際秩序”階段性演進的特點與路徑②為使讀者確切理解“自由國際秩序”演進中的結構性要素,也避免正文過于冗長,茲將伊肯伯里提出的有關國際秩序轉型的五個關鍵向度置于注釋中,便于查閱:(1)可供參與的范圍:這里指的是,國際體制參與者僅允許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排他性集團,還是對全球所有國家開放。(2)主權獨立程度:亦即,國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領土范圍內宣示其權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國際承認的范圍內顯示其統轄國內事務和執行職責的合法權利,包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向超國家體制割舍主權,或者通過協議降低自主決策的程度。(3)主權平等水平:是指在國際秩序內等級制的實現水平。自由體制主張平等,但自由體制也可以在具有等級的情況下被組織起來。(4)法制規范性:指秩序運行中,在多大程度按照法制原則辦事。“自由國際秩序”的法制狀況呈多樣性:國家間互動可以嚴格恪守法律條文,但也可以討價還價。(5)政策實施的寬度和深度:國際秩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國家間推行共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人權、安全政策。能夠實施更多共同政策,顯然也具有更多功能,包括在國家間實行干預、監督、規制、保護等舉措。
伊肯伯里認為,“自由國際秩序”的三種版本各有其特點。就1.0版本而言,按照國際法的秩序,威斯特伐利亞式的主權觀念被確認,國家獨立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得到尊重。該體系的政治層級較為均等。該體系按照國際法來執行規則和規范。同時,當時僅有很少的政策空間,可以用來限制各國間的開放性貿易和建立集體安全體系。在2.0版本當中,出現了以西方為主導性取向的安全和經濟體系,對威斯特伐利亞主權觀念也出現了修正。該體系中的新型等級體制的特征表現為:美國霸權提供公共產品,以美國式規則為導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確立起了保護人和委托人式的關系,但各自仍具有相互作用、討價還價、表達意愿的機會。該體系強調經濟規制、保護人權等領域的政策運作,政策空間也獲得擴展。在未來的3.0版本中,非西方國家前所未有地可以被擴展成為核心治理機制的成員,該秩序覆蓋全球范圍。后威斯特伐利亞式的主權觀念成為主流,同時,伴有干涉性、相互依賴性的經濟與安全體制。出現后霸權式的等級制度,各種不同的具有領導地位的國家組成了不同的集團,占據著國際治理體制中的各種崗位。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得到擴展,與諸多網絡型合作的新領域相互匹配。該體系的政策運作空間進一步得到擴展。
那么,當下有哪幾種國際秩序演進的路徑呢?伊肯伯里認為,至少有三種與前一階段“自由國際秩序”2.0版本不同的路徑。而每一種路徑都包含著主權、規則、機制、權威等要素的不同組合。
第一種路徑,就是“自由國際秩序”3.0版本。這種理想中的模式與以往美國霸權式的自由國際秩序相去甚遠。美國將會在這一體制中丟失不少支配性和監控性的規則和機制。以往由美國通過北約等組織所提供的西方一家在多邊機構中的主導性,將讓位于“公共的”治理規則和機制。在3.0版本里,國際治理中的權威崗位將轉向吸收整個國際社會的成員。同時,威斯特伐利亞式的主權也將受到進一步的侵蝕。后霸權時代的等級制度將由若干主導國家所組成的群體來奠定基礎。他們將會在聯合國安理會、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各國際治理機構取得關鍵崗位,提供以前由美國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并確保市場開放和提供安全保障。美國將會把自己的傳統霸權讓位于加強合作,將會在非正式和網絡式的協議中得到自己的份額。這是一個與美國和西方霸權較少聯系的秩序,但是,將會更依賴共同規則和強化集體行動。
第二種路徑,將會是“自由國際秩序”的2.5版本。聯合國將會和先前十年那樣,保持與各方之間的協調與討價還價,但是將作為霸權體制的領導者。在2.5版本里,美國將會讓出部分特權,但會保留其余部分。美國將與伙伴共享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權威,但是美國無論如何會保持在軍事戰略領域的霸權。美國可能不參加國際法院。
第三種路徑,如果“自由國際秩序”變得封閉和法制消失,那么該秩序將會被打破。“自由國際秩序”2.0版本中的政治、經濟、軍事戰略等各種因素將會變得碎片化,轉化成為競爭性的地緣政治集團。這樣的全球秩序的崩潰不一定是指原有秩序的完全瓦解,然而,只要停止開放貿易,終止以法治為規范,否定以多邊決策為基礎,那么既有的國際秩序就告結束了。這時的國際秩序就會演變成一個較少合作、地區層面更加分裂、各方更加互不往來的競爭性地緣政治環境。
3. 美國可能的幾種選擇及其條件
伊肯伯里提出,究竟選擇這三種路徑中的哪一種,取決于在國際秩序沿革過程中主要參與者的意愿及其能力,這里還存在著幾種可能的選擇。
首先,美國主動放棄壟斷特權,讓渡給國際共同體。即使是國際權力分配出現急轉彎,美國在未來幾十年當中依然還是世界舞臺上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世界上還是有不少國家希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可能也會認為,這樣一種協商式的“自由國際秩序”,比起任何別的選擇要來得更好。問題是,美國是否愿意做出這樣的選擇?如美國轉向2.5版本尚且困難,那就不用說轉向3.0版本了。如果出現更加分散化的趨勢,那么,很可能只是留下少數幾個關鍵伙伴國家與美國保持著安全領域的聯系。
第二種可能,美國的安全能力可以轉化成為廣泛的經濟和政治協議。美國具有極其強大的軍事力量,美國一國的軍事開支甚至遠超過其他所有國家軍費的總和。問題在于,美國的軍事力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構建全球規則和體制的談判能力?如其他國家指望進行安全對峙,那就正好給予美國一個機會,重新返回霸權體系。
第三種,選擇未來國際秩序的多種可能性。如果若干個領導國家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各奔東西,歐洲將會繼續樂意削弱威斯特伐利亞主權。但是,如果非西方國家,像中國和印度,一旦傾向于尋求完全不同的國際秩序,他們未必一定傾向于“自由國際秩序”的開放和法制。但是,另一種可能是,他們確實認為:他們的利益可以在“自由國際秩序”之內得到關照。如果第二種可能成為現實,那么從“自由國際秩序”2.0引申出來的路向,應該是側重于“自由國際秩序”內的參與和分享權威,而不是“自由國際秩序”原有的實質性特征被改造。
在上述不同方向的選擇中,伊肯伯里提出了對“自由國際秩序”未來演進的兩個判斷:
第一,在沒有戰爭和經濟災難的情況下,“自由國際秩序”看來不會被徹底打破或者消失。就像過去一樣,“自由國際秩序”將會不斷地演進。國際治理的特征將會隨著各國共享并實踐權力與威權而得到改變。重要的是,領導國家和新興國家并沒有想推翻“自由國際體系”的基本邏輯和法制秩序。壓力和動機來自于治理方式和處于該系統中的責任承擔狀況的改變。
第二,美國是“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倡導者和支持者,今天的問題在于,這一體制如何演進?美國在主導性不如以往的情況之下,如何繼續支持這一體制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美國還要繼續成為穩定并且發揮“自由國際秩序”作用的領導者?美國如何在較少特權的前提下支持這一體制?美國正處在深刻的動搖和猶豫當中——美國的力量可能提升,也可能衰落。但美國必須適應這樣的新局面,即,擴大和深化“自由國際秩序”,乃是當今的現實。①馮紹雷:“普林斯頓報告的背景、內容與評估”。
伊肯伯里的基本立場無疑是力求維持“自由國際秩序”的生存與發展。值得關注的是,伊肯伯里的構想生動反映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之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難以自保,期待通過對原有秩序的修正和轉型,包括國際決策機制中領導權的有限重組,來適應國際格局急劇變化的立場。問題在于,伊肯伯里報告之后所發生一系列重要變化,包括烏克蘭危機、敘利亞戰爭、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中國崛起等現象的出現,究竟是否意味著原有考量的基礎不復存在?這需要從進一步拓展視野的思辨中去尋找答案。
(二)“自由國際秩序”的全球性爭議
伊肯伯里發表這篇長篇報告之后,有關國際秩序的爭論有增無減,特別是近三四年,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成為國際學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為便于把握從伊肯伯里報告直到最近這一領域爭議的發展,筆者提供以下關于國際秩序辯論中諸多觀點的一些不同的分類,至少可以劃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第一類,中國旅美學者、美國威登堡大學于濱教授在《俄羅斯研究》雜志上撰文提出,目前的辯論主要發生在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立場之間。其一是自由主義派別內部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之爭。悲觀主義者認為,因出現中俄等現體制的“修正主義者”,或因西方內部反建制勢力的打擊,“自由國際秩序”已經“壽終正寢”;樂觀主義者則認為,西方主導的國際體制依然有回天之力。其二是現實主義質疑派批評“自由國際秩序”“既不自由、又非一統天下、鮮有秩序井然”。①于濱:“中俄與‘自由國際秩序’之興衰”,《俄羅斯研究》,2019年第1期,第23-26頁。尤其是主張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社會”、提出大國爭霸必有一戰的“超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稱“自由霸權體系注定失敗,美國決策者應該理智地拋棄對自由霸權的追求”。②J. Mearshi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其三,注重東西方歷史差異的學者,批評現實主義派別錯誤地認為,任何新興力量的崛起似乎都是在破壞現有秩序,他們尖銳地指出,對現行國際秩序進行最大修正的不是別人,而正是美國自己。經過綜合比較,于濱教授的意見是:盡管“‘自由國際秩序’困難重重,這需要國際社會的集體努力來修復、修改和完善。在沒有全球性危機的情況下,如果把‘嬰兒’(自由國際秩序)和臟了的‘洗澡水’一起倒掉,沒有人會從中獲益”。③于濱:“中俄與‘自由國際秩序’之興衰”,第52-53頁。
第二種分類,由英國肯特大學國際與歐亞問題教授理查德·薩科瓦(Richard Sakwa)在《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上所發表的文章中提出。①Richard Sakw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odels of Global Ord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3.在他看來,有四種類型的爭奪霸權模式。第一種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但冷戰后西方主導的“民主國際主義”激進擴張正在引起普遍反對。第二種是變革性(革命性)國際主義:冷戰時蘇聯陣營革命性對抗已是過去,但當下面臨著以氣候變暖、恐怖主義、分裂主義、種族主義等期望國際秩序發生質變的左右激進社會運動。第三種是美國式重商主義的民族主義:以美國第一、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民族主義來否定國際秩序效能。第四種是保守的(或主權的)國際主義:以中俄為代表,伸張主權與新區域建構、堅持在無霸權的國際主義基礎上改革而不是顛覆現有國際秩序。薩科瓦的分類,顯然受到了英國國際問題研究學派的影響,強調社會向度;同時把中俄列為國際秩序演進中的一大主題,凸顯當今國際社會多樣化、多極化、多元化的現實。薩科瓦的結論是,比起霸權主義,一個在多個模型之間進行競爭的國際體系可能更加平衡、有序和創新,并可更加協調地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②Ibid.
第三種分類,旅美俄羅斯學者、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安德烈·齊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側重于對國際秩序的轉型問題上所出現的各類觀點進行歸納和劃分。按照他的劃分:其一是“警世危言派”,比如,“2018年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報告”強調,美國改變力量平衡的企圖正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一系列的國際機制和次結構正在加速走向解體和衰朽的全球趨勢”,“該趨勢不可逆轉,也不可能在全球規制的基礎上得以重新恢復”;此外,俄羅斯的卡拉加諾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美國的科恩(Stephen Cohen)、萊格沃爾德(Robert Legvold)等著名學者也都持類似觀點。其二是“支持穩定派”,如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包括伊肯伯里在內,這派觀點不僅認為國際秩序的危機被夸大了,“現行國際秩序在后冷戰時期出現被改變后的留存,不但可能而且應該”;“現行國際秩序的問題只是執行中的問題,而不是其生存原則出現了問題”。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主任科爾圖諾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提出:“雖然美國和西方急劇削弱,但依然是政治、科技、經濟各領域的世界領袖的美國和西方能夠在不遠的將來恢復力量,現有國際秩序不需要根本改造,而只是需要改善。即使美國不如預期,俄羅斯也會寄希望于歐洲,視之為與其一體化的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其三是“雙重趨勢派”,齊甘科夫本人認為:“‘警世危言派’忽略了現有國際秩序同時存在著建構和解構兩種過程,而‘支持穩定派’過于悲觀地看待非西方力量克服技術差距、創建穩定國際政治機制的能力”。在他看來,當今始終同時存在著破壞性和創造性進程兩種態勢,因此,大體上也屬于支持國際秩序穩健轉型的一派。①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019, No.1.
第四種分類,“西方缺失”主題下“自由國際秩序”的問題與挑戰。這是 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就國際秩序爭議提供的另一種不同分類方式。作為影響力廣泛的世界級國際論壇,該報告基于歐洲立場,每年選擇一系列重要問題進行針對性的分析,探究大變局之下如何維護自由國際秩序。《慕尼黑安全報告》醒目地提出了“西方缺失”這一范疇,認為對西方內部分裂的焦慮是慕尼黑安全論壇關注的重點。報告提出,“西方”作為一個相對緊密的地緣政治體走向衰敗和“西方精神分裂”的局面,原因首先在于西方本身“出現了一個非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陣營”。該陣營中的人認為,“西方不是一個對所有持自由民主價值的人都開放的共同體。相反,它是一個由種族、文化或宗教標準組成的社區。”該派別認為“(白人基督教)的西方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外來者’的威脅”。其中較溫和者主張拒絕難民、封閉邊界、反對“政治正確”;較激烈者將伊斯蘭世界視為敵人;其中最極端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則訴諸襲擊、謀殺不同信仰的公民和政治家。《報告》點名批評作為執政者的特朗普和歐爾班“反對自由國際主義、主張新的民族主義的立場”;稱“西方內部的非自由主義勢力可能成為外國非自由主義勢力在西方的‘特洛伊木馬’”;并直指,“北約最大的危險,既不是其他大國的崛起,也不是其周邊地區的不穩定,而是內部非自由主義的崛起和西方集體身份的不穩定。”《報告》自我批評道,西方盲目自信,對中俄終將采取自由價值觀過于樂觀,聽任危機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損害,承認對此“還無法找到應對挑戰的答案”。《報告》還提出“西方領導的聯盟”任意發動“軍事干預”和“在國際沖突中的軍事優勢”已不復存在;西方主要國家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機構的支持在減少,中國等對國際機構的關鍵影響力在增長;作為“自由國際秩序”支持者的北約與歐盟“苦苦掙扎”,“面臨巨大挑戰”。《報告》指出,美國收縮產生的政治效應、過度使用經濟武器導致盟友與伙伴疏離、以及國內的分裂,將會使美國進入一個“戰略停滯”時代;而歐盟在全球定位、內部政治與戰略上的分歧、包括在 5G等問題上既與美國脫鉤、又無法達成內部一致,都“阻礙了歐盟全球競爭力的提升。”《報告》稱,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關于緩和與俄羅斯關系的提議,“招致了幾乎全歐洲的批評”;美歐之間、歐洲內部圍繞北溪2號管道的激烈爭論;大多數歐洲國家在美俄、美中之間發生沖突時不會選邊站,而會采取中立態度。《報告》認為,在此背景下,西方需要應對大國戰略的“雙軌戰略”是:“在符合其最佳利益的情況下與專制國家合作,同時加強西方的凝聚力”。《報告》最后得出的結論是:自由主義的吸引力、民主國家占世界GDP總量的57%,這些原因使“西方應該能夠捍衛自由國際秩序,同時承認全球權力轉移將帶來自由秩序必須與之共存的競爭模式”。①“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Westlessness”, Feb.16, 2020,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
通過對當前關于“自由國際秩序”的辯論的簡要介紹,人們不僅看到了有關的各種觀點,同時也感悟到了這些觀點背后紛繁復雜的思想譜系的激烈博弈。盡管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辯論不會在一個短時間中落幕,但是,第一,總體而言,來自各方的多數專家傾向于認為:與“自由國際秩序”密切相關的當前國際體制需要經過改革才能留存。而其關鍵問題,正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哈斯所言,“不是一個國家、兩個國家來統治全球,而是由占有行使各種各樣權力的多重主體來實施統治”。②柯貴福、陶慶梅:“新型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載于《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與大流動時代》,汪暉、王湘穗、曹錦清等著,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鑒于“解構”與“創新”兩種趨勢同時存在,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博弈一時還難分高下。比較多的意見傾向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有關國際秩序構建的合作還勢必與競爭互相交織而同時存在。第三,與此同時,在關于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挑戰究竟來自內部還是來自外部的爭議中,至少在《慕尼黑安全報告》發表之后,認為西方內部分裂、包括美國自身與多邊體制“脫鉤”才是削弱“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原因的觀點,與主張挑戰主要來自外部的立場,互成掎角之勢。
二、“多極世界”構想的演進
世紀之交,國際新興力量崛起,傳統西方大國出現衰落趨勢。要求維持二戰以來的基本國際秩序,主張維護國際社會的穩定,反對霸權,支持多極化發展和多邊主義,同時也要求改革現有國際體制不合理方面的立場,可歸為“多極世界”與追求多極化的思想流派。換言之,多極、多元、多樣化乃是其基本發展趨勢,而支持現有國際秩序在穩定運作前提下的改革,是其基本的戰略路線。這一流派反映了當今新興經濟體、轉型國家、重要的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立場。中國與俄羅斯被認為在這一流派中最具代表性。
(一)普里馬科夫的“多極世界”思想
“多極世界”的思想乃是該陣營的主要理論淵源。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是這一理論立場的主要發起人。普里馬科夫是一位長期從事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的高級專家,同時又是一位多年擔任大國總理和外長、有著豐富從政經驗的世界級政治家,這樣的背景使得他在推動“多極世界”觀念發展的進程中發揮了特殊作用。雖然“多極世界”并沒有像“自由國際秩序”的敘事那樣,有著以西方政治理論為背景的完整系統的學理闡述,但這是基于冷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邏輯的自然產物,有著以新興力量崛起為背景的國際變局的強勁支持。普里馬科夫對“多極世界”理論要點的歸納大致如下:
第一,在普里馬科夫的闡述中,多極世界始終有一個重要的對立面,那就是美國所追求的單極化的趨勢。他認為,“從歷史上看,已經表現出的世界秩序有兩種類型:多極化和兩極化。理論上講,我們還可以補充另外一種類型,叫作單極化。然而,單極世界秩序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不過,這種幻覺還是有過的。況且,建立單極世界的目的又成為一些意識形態學說的基礎。許多戰略設想、政治和軍事行動均從屬于這個目的。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這樣說:某些人追求單極世界的欲望一直沒有泯滅,不過客觀上的先決條件卻不曾存在,因此這種欲望壓根就沒有轉化為歷史現實。”“冷戰后美國極力推動的單極化不僅與可能導致人類自我毀滅的兩極化對立起來,而且還與‘井噴式出現的’多極化對立起來。”①[俄]普里馬科夫:《沒有俄羅斯,世界會怎樣?》,李成滋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第二,普里馬科夫認為,“多極世界”的基礎,在于世界以市場經濟原則的“同質化”為基礎和意識形態不再占主導地位的趨勢。他說:“冷戰剛一結束,世界上便出現構建單極世界的傾向。不過,此時在國際關系構成中意識形態因素已不再具有決定性意義。在形式上,世界變得同質了,因為市場機制成為全球共同的發展模式。”②同上,第2頁。
第三,普里馬科夫說:追求單極世界秩序是出于對蘇聯解體這一重大問題的偏頗認識。他直言:以為“美國贏得了冷戰而蘇聯輸掉了冷戰”,是一種“不符實際的認識”;“蘇聯解體不能歸結于其在冷戰中敗北”;美蘇共同努力才結束了對抗;因此,美俄仍應該具有平等權利。雖然普里馬科夫的這一認知遠遠沒有被美國精英普遍接受,但他堅持認為:“2008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給‘單極世界’致命一擊。正是這場危機,使美國‘單極’金融中心的作用蕩然無存”。③同上,第7頁。
第四,普里馬科夫強調,在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之下,世界形成若干中心是客觀事實。現階段世界多極化的特性是,美國在各極之間排名獨特,依然是經濟和軍事上最強大的國家,但這不等于單極世界的存在。在世界各力量中心發展不均衡的前提下,多極化體系本身相當穩定。多極化世界是建立在全球化某一階段基礎上的,不僅建立在強化了的各力量中心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上,而且還建立在這些中心在經濟與科技相互隔絕的條件下無法生存的基礎之上。④同上,第3-12頁。
(二)西方語境下的“多極世界”
與“自由國際秩序”的理論所發揮的實際功能和歷史地位相比較,“多極世界”并沒有像前者那樣已有了從理論構想的提出、實施、修正、包括受到嚴峻挑戰這樣百多年時間的經久積累。在二戰之后,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自由國際秩序”成為西方和美國主導世界事務的制度基礎。而到20世紀60年代的后期,基辛格以多極化的趨勢為依據,調整大國關系;到冷戰后的90年代中期,普里馬科夫不僅重提,而且推動“多極世界”的構建,“多極世界”的實踐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無論如何,“自由國際秩序”是一種實際運行了多年、其影響力遍及全球的基本制度。而“多極世界”還只是一種可供未來選擇的方向,目前還只是一種相對局部和補充性的制度構建的嘗試。這兩者有著基本的區別。問題在于,正當“自由國際秩序”面臨嚴峻挑戰的關鍵時刻,西方對于“多極世界”作何反響。
鑒于“多極世界”這一范疇所具有的高度現實政治含義,毫不奇怪,首先會有來自競爭對手的批評。2003年,美國當時基于“單極世界”理念,大力推行單邊主義戰略。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曾聲明道,“多極化——這是一種競爭對抗的理論,用最糟糕的表述是,這是一種價值競爭”。換言之,按照賴斯的說法,多極化會導致大國間新一輪類似于冷戰的、包含有意識形態競爭的對抗。①[俄]普里馬科夫:《沒有俄羅斯,世界會怎樣?》,第2-3頁。然而,同樣來自保守派陣營,但經驗更為豐富的、被普里馬科夫稱為“才華橫溢”的老資格戰略家基辛格,在世紀之初所撰寫的著作《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一書中,就這樣寫道,“美國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優勢在哪里,但與此同時,推行政策的時候應該意識到:世界上似乎還存在其他一些力量中心”。用普里馬科夫的話來說,基辛格根本無法忽視現存的多極世界秩序這個事實。②同上,第10頁。
(三)“新兩極世界”的爭議
隨著國際局勢的迅速變化和“多極世界”的實踐推進,人們開始對這一理論進行進一步的思考,俄羅斯核心層精英對此也做出了自己的反應。
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出現了筆者稱之為“新兩極世界”的辯論。本文認為,沒有必要對一部分極端鼓吹重回對抗、漫無節制地挑動東西方對立、過于意識形態化、也缺乏理論深度的輿論再去作詳細介紹。盡管這部分言論甚囂塵上,但實際上,學術界和媒體界還是有很多學者認為,時過境遷,無論從國際環境、國際力量結構、還是國際主體的意愿來看,冷戰時代的那種全面結盟、軍事對抗、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局面并不那么容易被輕易重復。
但是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確還是有不少非常資深的學者,傾向于“新兩極世界”正在來臨的觀點。2008年金融危機前,老資格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提出過“G2”的觀點。知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也提出過“中美國”的新詞,以此描摹即將來臨的中美共同發揮重要作用的新階段。而近年來,比如來自俄羅斯的權威國際問題學者謝爾蓋·卡拉加諾夫提出,“世界從多極走向兩極的趨勢開始形成,一極以美國為中心,另一極在歐亞。中國看起來是后者的經濟中心。然而只有在中國不謀求霸權的情況下,歐亞中心才能形成”。①馮紹雷:“大歷史中的新定位——俄羅斯在敘事-話語建構領域的進展與問題”,《俄羅斯研究》,2017年第4期,第29頁。卡拉加諾夫在這里指的是一個基于中俄合作的新力量中心正在出現。另一位美國資深專家、歐亞集團主席克利福德·庫普錢(Clifford Kupchan)最近在北京舉行的專業會議上還論證道,“世界正在走向以中國和美國為核心的兩極化。其中一個經得起實證檢驗的依據是,中美兩家與排在后面的其他比較重要的政治經濟大國間,在實力規模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凸顯出中美兩國地位的遙遙領先”。②參見克利福德·庫普錢在2020年1月11-12日在清華大學國際安全研究中心所舉行的高端國際研討會上所做的發言。盡管各國學界還有很多人并不認為所謂“新兩極世界”就是當今的現實,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認為世界正在走向兩極化的觀點和輿論,一直在激起人們的思考和辯論。
(四)以“多邊主義”取代“多極世界”?
與上述觀點有類似之處的另一種主張來自俄羅斯。但該主張一方面強調要克服兩極思維的慣性,同時又強調,應由多邊主義來取代“多極世界”。這方面已經較為系統公開表達意見的,是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主任安德烈·科爾圖諾夫。2018年6月26日,這位俄羅斯資深學者在《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網站發表了題為“為何世界不會多極化”的長文。隨后該雜志2019年第一期在首篇位置全文刊登了科爾圖諾夫撰寫的“在多中心和兩極之間”一文,再次表達對普里馬科夫“多極世界”構想的不同視角的闡述。
科爾圖諾夫認為,“至少在俄羅斯,多極化的概念依然是一種用來表達總體性的政治聲明和對全球發展趨勢所作判斷時的折中性混合物”。他認為:在后蘇聯時期,俄羅斯關于世界秩序演變的敘事,是從兩極(冷戰時期)逐步過渡到“單極時刻”(20世紀90年代中期),并進一步向多極或多中心世界過渡。國際體系向多極化演變,在俄羅斯是被普遍公認的事實。從科濟列夫一直到普里馬科夫,“‘多極’和‘多中心’這兩個詞在俄羅斯的官方和專家辭令中最常交替使用,前者比后者更常見。含義上有細微差別,但這兩個術語都強調現代世界的‘權力中心’”(兩極和中心),而不是它們之間的溝通(如“多邊主義”)。①A. Kortunov, “Between Polycentrism and Bipolarity: On Russia’s World Evolution Narrative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1, pp.10-11.
科爾圖諾夫的認識是,其一,在過去的20年中,多極化的概念未能成為一種具有組織和總結知識、聚焦、解釋、觀察、啟發、交流、規范等成熟功能的科學理論②S.W. Littlejohn,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lif.: Wudth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p.28-29.;也并沒有可靠衡量國際體系向多極化過渡的進展(或者倒退)的指標體系;更沒有何時能完成從單極世界向多極世界過渡的可靠預測。其二,因社會歷史條件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深刻差異,以往多極體系(主要是1814-1913年歐洲大國關系體系)的歷史經驗,已經完全不能作為現代多極理論的基礎。科爾圖諾夫認為,一個關鍵的區別是:當年維也納會議之所以達成妥協,主政者都是專制君主,而近百年來民意波動對政治家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兩百年前亞歷山大一世的寬容和梅特涅的遠見,已經不大可能再被今人仿效。③Andrey Kortunov, “Why the World is Not Becoming Multipola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9 June 2018, https://eng.globalaffairs.ru/book/Why-the-World-is-Not-Becoming-Multipolar-19642其三,多極系統內“極”的聚合驅動力,并沒有得到經驗性的證明。在科爾圖諾夫看來,設想中的以地區大國為力量中心的國際架構,實際上并不成功。相反,地區大國的周邊中小國家有著太多的離異、尋租、博弈,或者干脆是以鄰為壑。其四,科爾圖諾夫甚至自問:“我們是否真有足夠理由相信,世界的確在向多極化方向發展?能否斷定,歐盟與十年前相比變得更加接近獨立的一‘極’?十年來非洲、中東或拉美更接近全球一‘極’了嗎?……我們無法斷言世界正穩步向多極化方向邁進”。①Andrey Kortunov, “Why the World is Not Becoming Multipolar”.其五,科爾圖諾夫明確表示,倘若我們贊同國際體系中各國平等的原則,就應當放棄多極化構想的基礎概念,從“多邊化”尋找出路,以“多邊”取代“多級”。“多極化世界由勢均力敵的多個集團組成且尋求平衡,而多邊化的世界則由兼容互補的多種制度組成”②Ibid.。
科爾圖諾夫的意見,可能并不僅代表他個人偏于“自由主義”立場的看法。另一位代表更為主流意見的學者、俄羅斯瓦爾代國際俱樂部學術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俄羅斯外交與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認為,“我們翹首以待的多極化模式雖然給俄羅斯帶來了機遇,卻未提供任何可靠保障,不確定性倒是成倍增長。換言之,我們需要從頭再來,首先是要明確,將謀求何種地位,在這場競爭中究竟需要采取哪些不可或缺的方式(軍事、政治、外交、信息)。我們是否具備上述所有工具。與此同時,在冷戰期間為我們帶來成功的方式,如今已具有明顯的局限性。畢竟如今的世界已經迥異。”③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Дом, который построил кто?// Огонёк. 24 декабря 2018. С.22.
(五)“單極世界”向“多極世界”的過渡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
當今俄羅斯學界出現了關于多極化問題的另一種方式的修正。這一種意見認為,多極化進程還會延續,但這是一個延宕時間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表述并非一般學者。有人甚至引用普京的表述來強調這一修正,認為雖然普京一直強調“多極世界”的重要性,但在2016年瓦爾代會議上,普京曾說,“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今天它可能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我們承認這一點”。④Путин В.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 Октября 2019.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151科爾圖諾夫對此的解讀是,這意味著盡管多極世界是俄羅斯設想的一種未來秩序模式,但是現在要說“單極時刻”已經被完全消除,還為時過早。2017年,俄羅斯外交部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談到向多極化過渡時,也預計這種過渡將長期地持續下去。⑤Лавров: многие политики являются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теории управляемого хаоса. 11 августа 2017. https://tass.ru/politika/4477015遵循普里馬科夫20年前的總體邏輯,拉夫羅夫提出,“……時代的變化總是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在最近一次講話中,拉夫羅夫再次強調,向多極世界的過渡將需要“幾十年”,而且其最終結果并不能被預先確定。①“Lavrov notes polycentric world will take decades to establish”, TASS, 25 Feb. 2019,https://tass.com/politics/1046245有關俄羅斯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若干官方文件都指出,經單極性從兩極向多中心過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并不是一個既成事實。例如,2016年頒布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指出,“現代世界正經歷一個重大變革時期,其實質歸結為多中心國際體系的形成……但是,向多極化的普遍運動并不排除舊的、主要是單極體系所具有的‘暫時穩定’的時期”。②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640.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普里馬科夫本人曾具體地預言,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末或者在第三個十年之初,多極世界將普遍確立。③A. Kortunov, “Between Polycentrism and Bipolarity: On Russia’s World Evolution Narratives”.顯然,普里馬科夫對多極化前景的判斷并未變成現實。對此,齊甘科夫提出的修正意見是,向多極世界的過渡將成為一個歷史性的長期過程,比如,“后華盛頓體制的轉型可能要延續到2050年。”④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這一判斷,與上述俄羅斯官方的表達比較相似。
值得思考的是,有關多極化進程將會持續很長歷史階段,即“多極世界”可能是若干個十年之后才會出現這一判斷,是否僅僅是一個關于過渡階段的持續時間問題?是否意味著對多極化現象本身有了更為深切的洞察?抑或是對向未來國際體制的轉型這一件事本身有了更新的理解?無論是從多極化轉向“新兩極世界”,還是轉向另一方向的“多邊主義”,不管怎么說,這至少意味著人們希望更從容地思考和應對這一重大而復雜、又從未經歷過的全球性變局。
三、重回基辛格?
“自由國際秩序”雖然飽受批評,但這一西方觀念形態已經成為在廣大范圍內實際管理世界事務的基本制度和規范。“多極世界”思想雖然并未占整個國際格局的主導地位,但也已經局部地轉化為新興國家群體參與當今國際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相比之下,基辛格對世界秩序思考的意義何在呢?從形式上看,雖然沒有伊肯伯里“自由國際秩序”那樣一類制度化的敘事,當年提出的“多極化”也僅是基辛格對國際發展趨勢的一種描述,但問題在于,基辛格通過對于數百年來世界秩序構建跌宕起伏的復雜歷史的思辨和總結,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的原則、路徑、功能、取向等關鍵問題。其鋪陳之老到,思想之深刻,恐怕當今學界難出其右。尤其是當“自由國際秩序”和“多極世界”理念都沉浸于當下的無盡爭議、又折射出其后五花八門的思想譜系和利益背景而難得要領之時,有必要重新回到基辛格,從他那幾乎身兼國際史專家而又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決策者這種獨一無二的特殊積累中,從他既是一位公認的現實主義均勢的崇尚者,又被認為是一位理想主義者的思想考量中,①[英]尼爾·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義者》,陳毅平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從他毫無疑問是美國主導世界這一理念的推動者,但又極力主張當今世界需要多元包容合作的超越折中的立場中,去尋求借鑒。概括地看,了解基辛格眼中的世界秩序問題,應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基辛格眼中的“世界秩序”及其當今特點
在《論世界秩序》一書中,基辛格提出了“三個層面的秩序問題”。首先是“世界秩序”。他認為:“世界秩序反映了一個地區或一種文明對它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正安排和實力分布的本質特征所持的理念。”基辛格這里所指的“世界秩序”,并不是一個已成為全球大一統規制系統的實際格局,而是西方和非西方地區各方有關國際社會未來發展模式的構想,是一種觀念形態。這種觀念形態來自各方,因而它是復數,而不是單數。其次,關于“國際秩序”,他認為,“國際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區——大到足以影響全球均勢——應用這些理念。”與“世界秩序”不同,基辛格這里所說的“國際秩序”,反倒是指已經形成的、未必覆蓋全部但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均勢結構基礎上的體制性秩序。然后是“區域秩序”,這里的“‘區域秩序’指同樣的原則用于某一具體的地理區域”。換言之,基辛格所指的“世界秩序”范疇,是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在內的各主要權力中心所追求的理想秩序模式。而“國際秩序”、“地區秩序”則是上述觀念和經驗在全球和地區層面的實際制度與規范構建。這樣一種劃分至少表明,在“世界秩序”這一問題領域中,尚有主觀的理想模式和客觀上已經實際形成的模式之間的復雜博弈。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胡利平、林華、曹愛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XVIII頁。
基辛格認為,當今國際秩序的構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在于,第一,“世界混亂無序,各國之間卻又史無前例地相互依存”。②同上,第9頁。他對“種種不受任何秩序約束的勢力是否將決定我們的未來?”的這一發問,表明了他對“失序”的深重擔憂。③同上。其次,基辛格敏銳地察覺,當今時代“不顧一切地追求一個世界秩序的概念”,但是又存在著“不同類型的世界秩序”的訴求④同上。。在他看來,世界的無序,并不在于秩序的缺失,而恰恰在于追求“不同類型的世界秩序”的訴求之間的競爭。他深深質疑:“具有不同文化、歷史和傳統秩序理論的各個地區,能夠維持任何共同體系的合法性嗎?”基辛格指出,“國際社會”一詞使用頻率之高超出以往任何時候,但從這一詞語中“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標、方式或限制”。⑤同上,序言,第VIII頁。其三,基辛格指出,越是“在一個即時通信和政治劇變的時代”,越是要“采取一種既尊重人類社會異彩紛呈的特點,又尊重人與生俱來對自由的渴望的做法”。沒有自由的秩序,“最終也會制造出自己的反對派”,但另一方面,“沒有一個維持和平的框架,就不會有自由,即使有也難以長久”。在基辛格眼中,秩序與自由是“人類體驗的兩個極端”。⑥同上,序言,第XVII頁。他對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1814年維也納體系的高度肯定,正是基于這兩條原則的兼顧。而他對于威爾遜主義的批評,也恰恰在于威爾遜“創立了一個僅靠呼吁遵守共同原則來維持的國際體系”,而“權力諸要素要么無人理睬,要么混亂不堪”,因而“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爾賽和約》那樣在達到自己的目標上如此失敗”。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第97-98頁。他認為,二戰以來美國歷任領導人對于構建世界秩序的貢獻,都是“權利與合法性相平衡”的體現。②同上,第16頁。
(二)合法性與權力的平衡——國際秩序延續和更替的核心
在基辛格看來,“合法性與權力之間的平衡”是一項核心原則。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首先,何為“秩序”?他認為,“求得秩序兩方面(權力與合法性)的平衡是政治韜略之本”。基辛格強調,“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特點”。③同上,第3頁。他指出,歷史上歐洲國際秩序“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對絕對價值做出判斷,轉而采取務實的態度接受多元世界,尋求通過多樣性和克制漸漸地生成秩序”。④同上,序言,第XI頁。也就是說,在基辛格眼中,多元化前提下的價值包容,是形成秩序的重大原則。但在另一些地方,他也把“世界秩序的最終本質”視為是由“大國間雄心碰撞所決定”的,認為“只有取得地緣政治的勝利,人類價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維護”。⑤同上,第332頁。似乎把現實主義的實力原則置于突出地位。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基辛格還是非常欣賞梅特涅的見解:“秩序與其說產生于對國際利益的追求,不如說產生于把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相結合的能力”。⑥同上,第85頁。比起簡單化地強調權力關系,基辛格更重視各國之間的“均勢”;而多元化的價值包容也需要以均衡的權力配置為基礎,這才能形成秩序。
第二個問題,基辛格一再使用的“權力與合法性”,指的究竟是什么?在基辛格的語境中,“權力”這一范疇不僅是指實力、暴力、軍事力量等含義,有時還指實力的均衡和實力的多樣化、多極化這樣的含義。“合法性”這一范疇的使用更值得關注。除了一般將“合法性”理解為被確立的意識形態原則、得到共識的制度規范這些含義之外,基辛格在描述羅斯福對國際秩序的看法時,比較明確地提到羅斯福“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即基于個人之間的信任、對國際法的尊重、人道主義目標和善意。”可見,基辛格對于“合法性”的理解,還是不同于一般人的見解。包括像國家元首間的私人信任、伙伴關系、普遍善意這樣一些范疇,也被他視作為“合法性”的應有內容。有時,他把“合法性與權力”,表述為“道德懲戒”與“暴力使用”兩個方面,強調需要均衡二者,不可走極端。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第481頁。
基辛格強調,“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的微妙平衡”。他強調,任何一種秩序離不開“原則”與“均勢”:“一套明確規定了允許采取行動的界限且被各國接受的原則,以及規則受破壞時強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種均勢”。②同上,第18頁。
(三)“權力與合法性的均衡”為何不能夠輕易實現?
基于多年實踐,基辛格深知“合法性與權力之間的平衡極其復雜”。③同上,序言,第XIX頁。他指出,合法性和權力均衡的建立,都是有條件、而非自動形成的。他說,當今世界不會“在某一時刻自動地融入一個平衡、合作的世界,甚至融入某種秩序”。在基辛格看來,國際秩序變更或危機只能發生在兩種情況之下:“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勢發生重大變化”。他指出,“當支撐各種國際安排的價值觀被根本改變時(或是被負責維護這些價值觀的國家遺棄,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會出現第一種傾向”。“盡管這些挑戰以武力為基礎,針對的是資源分配的不公,但是,其核心是指向觀念和心理層面的價值體系。”第二種情況,則是權力關系的重大變化。基辛格說,或是原有權力關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塌陷,如蘇聯崩潰;或是新興大國“不愿扮演它未曾參與設計的體系分配給它的角色,現存大國也許無力對這一體系的平衡做出調整,以包容它的崛起”。他不無擔心地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即由此而起;當今大國關系急劇變化也預示著這樣一種權力關系的重組。④同上,第481頁。目睹了當代國際社會的合法性與權力關系的嚴重失衡,基辛格警告說:“一種國際秩序的生命力,體現在它在合法性和權力之間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別給予兩者的重視程度。無論合法性還是權力,都不是為了阻止變革,兩者相結合是為了確保以演進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較量實現變革……一旦這一均勢被打破,種種束縛隨之消失,各種貪得無厭的訴求和狂人就會紛紛出籠,繼而天下大亂,直到建立一個新的秩序體系。”基辛格的警示值得三思:“當今世界,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一些歷史上素不相干、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只是彼此保持距離而已)、只認自己實力的實體,更有可能帶來沖突,而不是秩序。”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序言,第XIX頁。
四、國際秩序爭議的啟示、挑戰及其未來路徑
從本文所介紹的這三種來自不同背景和立場的國際秩序理念,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之間并非沒有若干趨于接近的,或者是可以作為對話的空間。但是,又必須承認,達成共識何其艱難。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一)西方和新興國家間在關鍵決策領域合作的可能性
伊肯伯里闡述“自由世界秩序”理念,以及普里馬科夫“多極世界”思想的重要內容,就在于探討:在秩序延續與轉型過程中,關鍵決策領域的西方與新興國家間能否合作共存。這一假設在當時的實踐中并非沒有重要反映:就在伊肯伯里寫作這份美國版世界秩序報告的差不多同時,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與法國總統薩科奇一起,經過與中國等新興國家領導人的磋商,在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之下,將協商世界經濟政治重大問題的重要國際機制,從G7改為G20。從而完成了國際秩序轉型中決策程序的一個重大演進。究其原因,一方面,基辛格說得明白:“建立具有建設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現在沒有哪個國家,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能夠像美國在冷戰剛剛結束、在物質和心理上獨步全球的時候那樣,單獨擔負起領導世界的責任”。基辛格主張,“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建立世界秩序”。②同上,第486頁。而在筆者看來,另一方面的客觀背景在于,在全球化進程欲罷不能的背景下,與其說當今世界是一個“極化的世界”,亦即人們常說的“單極”、“兩極”、“多極”,諸如此類,還不如說,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科技和信息條件之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代世界前所未有地變成了一個“網結式世界”。“極化世界”與“網結世界”的區別在于,當代世界的各個“極”,雖然依然是一個觀察實力變化的重要向度,而且以實力競爭實現價值和利益目標仍然是各國的基本戰略選擇,但是已遠遠不像四五十年前那樣,各“極”之間可以互相隔離而不相往來。相反,產業、價值、信息、人文等各種各樣的“鏈接”已使得各國、各地區、各種文明相互間的關聯性,遠比實際上難以真正計算的各個“極”的力量消長狀態,要來得更為重要。也因此,任何一個國家想輕而易舉、來去自由地“脫鉤”,也都會不那么簡單和容易。
(二)歷史借鑒與現實經驗可以為秩序轉型提供路徑
鑒于國際秩序的延續與轉型高度復雜艱難的特點,基辛格說,“重建國際體系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家才能的終極挑戰”。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第486頁。但是,歷史與現實依然是未來國際轉型的最好的老師。第一,多元共存的主張,實際上是得到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一直到冷戰后的國際體系發展的歷史所見證的重要經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乃是17世紀歐洲內部的多元化過程的一次實現。法國大革命后所出現的1814-1815年維也納體系,乃是當時歐洲擁有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國力的幾個大國的一次合作共存,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后來恩格斯所說的“百年和平”的長期相對穩定。②國際關系史界對此有爭論,有的認為19世紀60-70年代德國統一戰爭期間已經打破均勢,也有的認為,早在19世紀50年代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局勢已被打破。但是,19世紀的國際格局因維也納體制而維持較長時期的穩定,乃是歷史事實。而雅爾塔體系更是二戰后不同意識形態大國之間合作的一次重要實踐,盡管冷戰對抗破壞了多元合作,但是多極化、多樣化、多元化發展的格局一直深刻影響著國際局勢。第二,歷史上曾經經歷過的多種國際秩序,無不為我們留下關于秩序延續和轉型中各種有效功能機制的歷史借鑒。比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安身立命的一個關鍵,按照基辛格的提示,在于其將國際規范視為復雜利益交織中的“中立性”的體現,這幾乎是一個被當代人所遺忘的重要功能。“中立性”這一原則至少能避免為所謂的“互相對立的價值標準”而相互殘酷搏殺。又比如,維也納體系后的大國協調機制,雖然今天大眾參與的局面大大影響了外交決策,“秘密外交”已不可能如同當年般存在,但是大國間協調的原則,特別是通過政治領導人會晤的形式進行交往溝通、密切磋商、甚至不同程度的互相承諾,仍然是轉型期一項非常重要的機制。再比如,雅爾塔體制確立的大國政治決策,安理會猶如世界警察般的作用,盡管眾說紛紜,卻依然實用。伊肯伯里提出的等級制留存的可能性,還是取決于整個國際體系的設計,而并不是僅僅拘泥于形式上是否平等。包括冷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盡管在今天面臨尖銳挑戰,但是,這一秩序轉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產生于和平、而不是出現在大規模戰爭條件之下,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所提供的一筆寶貴遺產,迄今值得世人珍惜。在“權力與合法性的均衡”這一原則之下,有太多歷史遺產依然可以供今人發掘使用。
(三)文明多樣性基礎上可能形成秩序共識嗎?
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基辛格并非沒有保留。一方面,他主張,“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價值的同時,還需要有一種全球性、結構性和法理性的文化,這就是超越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視角和理想的秩序觀。”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第486頁。但是,他具體回答這一問題時,含蓄地提到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成功簽署,得益于當時兩百個來自歐洲各方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共同努力:“他們之所以克服了重重障礙,是因為他們都經歷了慘烈的‘三十年戰爭’,決心不讓戰爭重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前景更加嚴峻,必須應勢而動,否則就會被挑戰吞沒。”②同上,第490頁。但是,當年歐洲在有限的范圍內,而且在近似的文化基礎上達成的政治妥協,能否在今天各種距離遙遠、甚至經歷了上千年互相敵對的歷史悠久而十分輝煌的文明之間重現?今天人類能否重現當年的克制、寬容、理智和遠見?基辛格在表達對當今國際秩序深切擔憂之時,對此并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
可能正是基于這種擔憂,基辛格并沒有忘記提醒,“美國的領導作用始終不可或缺”。他甚至強調,“除了美國,沒有其他大國能把改善人類境遇作為戰略目標之一”;③同上,第430頁。但他在強調美國的領導作用時,還不忘發出警告:雖然美國“一直尋求保持穩定和普世價值之間的平衡,但這種平衡并不總是與不干涉主權或尊重他國歷史經驗的原則相吻合。”①[美]亨利·基辛格:《論世界秩序》,第486頁。在這里,人們看到一個智者在向世界提供建議的同時,并沒有忘記提醒美國會向國際社會索要的代價。然而,美國究竟能否擔當這一角色?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冷戰結束之初,當時執政的共和黨提出“單極世界”的主張,明白地表露出美國想成為構成“同心圓式”的世界秩序的中心。而2008年金融危機后,民主黨的奧巴馬也提出了美國還要領導世界一百年的豪言壯語。但是,特朗普上臺后退出國際多邊合作機制,視中俄為最大的競爭對手(有時近乎“敵人”),以美國利益至上的口號取代作為領導者國家的國際責任,強調單邊主義、重商主義、民粹主義,刻意淡化意識形態原則。似乎與現行國際體制“脫鉤”,才是美國的選擇。正如基辛格所說,“在塑造當代世界秩序方面,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發揮了如此決定性的作用,也沒有哪個國家參與世界秩序的態度令人如此難以參透。美國篤信自己的道路將塑造人類的命運,然而在歷史上,它在世界秩序問題上卻扮演了矛盾的角色。”②同上,第305頁。
面對如此矛盾的局面,既然已經不能重回歷史老路聽憑一個互相殘殺的國際無政府狀態重現,也不能夠相信任何救世主、抑或世界霸主會拯救人類,那么就只能相信,經由人類的良知,事在人為,去爭取實現一個和諧安寧的世界。從悲觀論的、反思的立場來看,可能還應回到基辛格,即人類只是在面臨災難與毀滅的深淵面前才會懸崖勒馬,去尋求共存之道。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是由于可怕的三十年戰爭;維也納協議的誕生是出于反對拿破侖發動的顛覆歐洲秩序、推廣革命的全面戰爭;雅爾塔體系的確立是由于 20世紀人類飽嘗兩次大戰的斷崖式悲劇;而晚近冷戰格局的終結,則是出于人類從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造成巨大傷害中,預感到的核恐怖時代全面對抗性沖突可能帶來的災難。換言之,幾乎任何一次國際秩序的重大轉型都源自于當時人們對戰爭或災變的恐懼。
從樂觀主義的國際演進的觀念來看,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元共存思想是每一次國際秩序演進中積累起來的寶貴財富。第二,“權力與合法性的平衡”基礎上構建國際秩序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非排他性規則,如規則的中立性、價值標準的非絕對性、程序的漸進性、行動規劃的務實與可預見性、以及唯有人類才有能力構建的平等對話的公平性等等,明智的政治家可以借此推進多元文明的合作與團結。俄羅斯與西方歷經多年沖突對峙后正在醞釀對話突破,中美經過艱難談判終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些都表明,即使在當前一片朦朧混沌的國際格局中,依然可以對多元并存的前景抱有謹慎樂觀的期待。2017年,筆者在瓦爾代論壇上曾有幸請教普京總統,在經歷了人類社會諸多國際秩序模式之后,如何看待未來的國際秩序模式。普京充滿自信地回答說:“當今世界面臨著如此豐富復雜的變化,經濟科技如此高速的發展,我們怎么能夠想象,今后國際秩序還是以前任何一種國際體制的簡單重復?我認為,今后的國際秩序一定是和以前任何一種國際秩序不一樣的重新構建。”①在2017年瓦爾代會議上筆者與普京總統的對話。筆者以為,對未來世界無限發展與變化前景的敬畏和預期,以及對人類參與構建未來秩序的豐富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堅定信念,是對多樣性文明能夠形成秩序共識的一個難以撼動的總體理性基礎。誠如魯迅所言:“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五、“全球轉型”背景下的俄羅斯“2024議程”
安德烈·齊甘科夫是提出“全球轉型”這一問題的重要學者之一。他認為,關于大規模全球性變化的討論雖然非常活躍,但始終沒有取得共識。他從幾個方面來觀察已經展開的辯論過程:一些學者從現有國際秩序的延續或更新改造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比如,前面提到的伊肯伯里、基辛格、林德(Jennifer Lind)和沃爾福斯(William Wohlforth)等。但是,這些來自不同地區與文化的不同力量之間的關系具有怎樣的動態性質?他們之間的相互認知多大程度上會導致沖突,抑或反過來趨于取得共識?特別是各大國間很不相同的國內進程正在怎樣作用于“全球轉型”?所有這些問題都還沒有能夠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而關鍵在于,倘若只是從外部結構,或簡單地引用歷史先例來尋找未來世界秩序發生與演進的軌跡,比如就像聳人聽聞的“修昔底德陷阱”這類話題那樣,是否能夠如愿以償?同時,齊甘科夫在研讀了關于俄羅斯和當代全球性轉型進程相互關系問題的文獻后說,盡管近期以來薩科瓦、卡拉加諾夫、雷丁(Andrew Radin)和里奇(Clint Reach)等所提供文獻,已經和近30年來國際學界的所謂“轉型學者”所寫的關于向自由民主體制過渡的“轉型研究”作品有了很大區別;但是既有研究還是非常有局限性。特別是在西方民主體制本身已經出現一系列問題、而原有的轉型研究一向以西方為楷模的背景下,顯然再也不能像30年前那樣,盲目地堅持以“逆轉科學共產主義模式”為目標的所謂“轉型研究”,而全然不顧當今“轉型中”的國家與地區的現實已經發生的深刻改變。于是,齊甘科夫認為,應該在(1)總體國際秩序轉型;(2)秩序轉型背景下的國際關系;(3)國內制度變遷與上述兩者的相適應,這三者相互結合的視角下,展開對問題的討論。在他看來,對俄羅斯而言,有賴于以下三個方面的綜合:為建立新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為維護在這個世界上的巨大利益所做的非對稱性抗衡;以及為實現上述兩個目標在國內必須推進的改革。①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實事求是地說,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國可以輕松自如地應對當今世界的種種內外挑戰,對俄羅斯而言尤其如此。2020年初,圍繞著俄羅斯政府改組和普京提出憲法修正案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和廣泛討論,顯然首先旨在著手解決當下社會經濟的緊迫挑戰;同時,又順理成章地指向2024年現總統任期屆滿之后的中長期政治經濟安排。本文將這一進程命名為俄羅斯的“2024議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像俄羅斯這樣將當下困難問題的處理與未來長遠發展的部署巧妙地加以聯系,將本國內部事務的轉型與未來世界發展的潮流相互銜接,的確值得加以關注。
(一)中-短期的俄羅斯外交戰略
由于上文已經對世界秩序問題有較多分析,筆者將簡要闡述這一背景下的俄羅斯對外關系及國內政治經濟進程。先來看俄羅斯對外關系發展的前景與部署。
俄羅斯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研究員伊萬·季莫費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主編的《全球預測2019-2024》,可能是俄羅斯方面與“2024議程”這一話題關聯最為直接的一部作品。①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РСМД 2019-2024: Cборник.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РСМД). М.: НП РСМДб, 2019.該作品重點是研究世界秩序激變形勢下的中短期預測。季莫費耶夫認為,在黑天鵝頻出的如此動蕩的時期,中短期預測要比長期預測來得困難得多。季莫費耶夫就未來四五年世界秩序的動態變化提供了以下四種前景分析:
第一種前景,自由世界秩序的轉型:重回特朗普掌權之前的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方針是改變特朗普所主張的對盟友與伙伴關系中嚴格的實用主義、毀壞經濟上不利于美國的所有體制與機制、以民族利己主義來代替國際責任。內政是這類政策的觸發器,因為特朗普正在全力以赴旨在實現2020年總統連任。問題在于,這樣的政策非常可能在政治變動中被重新替代。一旦特朗普競選失敗,將會出現以下變化:(1)大西洋關系得到鞏固,與亞太盟友的防務合作會加強;(2)重啟美國與亞太和歐洲的自由貿易區項目;(3)謹慎處理對華關系,在對華暫時妥協的基礎上集中精力對付俄羅斯;(4)對俄羅斯施加集體的經濟與防務壓力;(5)在對伊朗施壓的前提下有選擇地參與中東事務;(6)增加對烏克蘭的經濟與防務支持;(7)保持單極經濟優勢。這樣的發展趨勢顯然對俄羅斯不利,孤立和潛能削弱會繼續,會迫使俄羅斯或是大幅增加軍事開支窮于應對,或是在沒有任何保障的前提下與西方妥協,實際上是使俄羅斯喪失平等對話的地位,淪落到投降的境地。“集體的西方”會覺得自己有能力迫使俄羅斯就范。
第二種前景,新多極世界:這一前景發生在美國轉向務實單邊主義路線難以被逆轉的情況之下。俄羅斯與中國相互獨立地發揮作用,印度偏于傳統的自治方針,歐盟對美國單邊政策的不滿導致其獨立傾向增長,企圖恢復前特朗普時期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失敗。于是新多極世界表現出以下態勢:(1)在歐盟自治趨勢抬升之下,北約仍得保持,對俄羅斯實行遏制;(2)由于腐敗和體制無能,烏克蘭前景灰暗;(3)以美國為中心的若干地區貿易體制舉步維艱,地區玩家自行其是;(4)中國的實力增長,謹慎處理與莫斯科的伙伴關系,不轉向軍事同盟,中美沖突受到控制;(5)伊朗適應美國制裁,在中東事務中俄羅斯發揮積極作用,中國也增加參與度。對俄羅斯來說,新多極世界的前景更容易被接受。俄羅斯有了與伙伴們周旋的更大空間,對孤立俄羅斯的企圖的抵制能力增強,會有更多運作俄海外外交資產的可能性。但處于這種新多極世界,一點也不比與“自由世界秩序”打交道來得省力,玩家們各顧自己,誰也不能犯錯,否則,在內政上引起的后果代價巨大。
第三種前景,兩極世界的恢復:這一前景發生在中美沖突激化的情況下,美國因中國科技進步和變成國際軍火市場的有力競爭者而加大對華壓力。中美矛盾不可逆轉:貿易戰變成了經濟制裁,亞洲武器競賽加速。中美兩大國的尖銳沖突刺激著原來盟友關系的鞏固,并新增盟友參與。其中:(1)美國聯合起亞洲盟友日本、韓國等,旨在加強安全領域的分擔責任;美國還旨在與印度和越南建立“軟盟友關系”;(2)俄羅斯與中國建立的針對美國的軍事-政治聯盟得以全面加強;(3)由于對美國的戰略依附關系,歐盟喪失獨立性;(4)中國在支持俄羅斯在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提出自己的相關發展模式。這一前景對俄羅斯的好處是,有保障地克服了被隔離孤立的狀態,由于伙伴關系運作而穩固了自己的安全性。但是這些好處也帶來缺點:喪失了回旋余地,成為中國小伙伴后,可能會對其出現過多的戰略依賴。
第四種前景,喪失穩定并且各關鍵力量中心之間發生沖突:這一沖突前景僅可能由于偶然或局部原因所導致,但一旦沖突擴大會導致嚴重后果。特別是大國間沖突由于動用盟友關系和資源規模,會進一步刺激政治經濟形勢的緊張。這一前景可能的觸發因素:(1)在敘利亞、黑海和波羅的海等美俄雙方都有參與的敏感地區,沖突易于升級;(2)針對軍事和重要基礎設施的計算機系統,與軍事沖突有關的數字領域;(3)中美在南海爆發摩擦與美俄間沖突相比,一般尚可控制,但不排除沖突的迅速升級;(4)對于有關行動和意愿的單方面解讀(比如,對于重大軍事演習),以及企圖先發制人的侵略行動。
雖然所有這些前景預測都會受到具體條件的局限,但在季莫費耶夫看來,新多極世界的發展模式盡管也需要付出代價,但對于俄羅斯最為有利。因為在這一前景下,多向度政策運用、自由回旋的余地、運用外交政策來解決國內發展的任務,依然是俄羅斯外交的最高使命。①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Парад плане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ценарии динамик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РСМД 2019-2024. С.6-11.
對于中-短期俄羅斯對外戰略來說,季莫費耶夫的評估不無道理。第一,在中-短期立足于新多極世界的立場,最大限度地基于主權國家立場,保持獨立自主的外交運作,發揮俄羅斯的大國優勢,服務于國內發展的需要,這是俄羅斯的基本立場。第二,前述俄羅斯學界對于“多極化”問題的含義及其延續時段的反思,可能會成為今后四到五年間俄羅斯外交戰略的一個特點:前一階段,對于推進俄羅斯武裝部隊裝備現代化已經做出了極大的努力,這為下階段俄羅斯爭取與美國在戰略武器領域的談判和博弈提供了基礎和回旋空間。而且俄羅斯對外戰略會盡可能顯示其彈性,在堅持強硬立場的同時,不放棄一切談判妥協以實現國家利益的機會。第三,俄羅斯外交在近年來實際上已經展示出一個與2014年烏克蘭危機時期很不相同的面貌:除了穩固俄羅斯在周邊地區以及傳統的伙伴關系以外,不僅圍繞烏克蘭問題本身的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談判出現了令人期待的前景,而且俄羅斯居然在受到西方嚴厲制裁、國內經濟發展受到打壓的形勢下,躍出外線發展,在中東、亞太、拉美、非洲都有所伸展。顯然這已經不能夠以蘇聯時期的“全球擴張”這樣一類簡單的判斷來描摹,而是一個盡管暫處弱勢,但是通過搞活外交,以提振信心為宗旨,通過首先在中東、然后拓展至在全球布局,以精心選擇的目標、有限的投入、以及靈活多樣的戰略戰術,廣泛建立伙伴關系但也不排除在成熟條件下與美國周旋,在世界各關鍵地區打下楔子,以備長遠之用。俄羅斯在敘利亞那樣異常復雜艱難的環境中,能夠一步步地站穩腳跟,以實力、智慧和信譽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這是俄羅斯新時期大國外交的一個縮影。第四,俄羅斯力爭通過這樣的全局安排,在今后四五年時間內排兵布陣,以維護自己的大國影響力。同時,為在一個較長時期的世界秩序轉型過程中,不僅是以“戰斗民族”,而且也以昔日運作大國外交的豐厚積累,來贏得自己的地位和份額。
(二)“全球轉型”下的“俄羅斯國際政治經濟學”
2020年初,普京總統通過及時改組政府、大力推動解決國內經濟民生問題,提出以2024年為完成期限的12項直接事關民生的國家規劃;同時提出憲法修正案,把改善當前社會經濟狀況與解決2024年面臨的領導人更替問題聯系起來,以期統籌解決俄羅斯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挑戰。在全球轉型的背景之下,要打造一個能夠維持長治久安的歐亞大國,使一個曾經千瘡百孔的經濟走向穩定發展,對俄羅斯來說并非易事。第一,從經濟上看,俄羅斯在過去30年里以十年為一個周期發生變化:1989-1999年,是蘇聯經濟崩塌和俄羅斯痛苦轉型的階段;1999-2009年,是俄羅斯經濟開始復蘇增長的“黃金十年”,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下,2009年是G20中滑坡最嚴重的國家;2009-2019年在烏克蘭危機和遭遇西方制裁之下,俄羅斯經濟被經常持尖銳批評態度的人稱作是“失去的十年”。俄羅斯學者伊諾澤姆采夫(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認為,與其說俄羅斯目前的經濟狀況是由能源為主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還不如說是由于過于倚重國家儲備基金,指望通過以國家為后盾的儲備基金來推動經濟所造成的。這最終導致了消費不振、私人部門萎縮。①弗·伊諾澤姆采夫:“俄羅斯:經濟停滯的帝國”,《財經》雜志2020年年刊:預測與戰略。現在的問題在于,俄羅斯能否在一個短時期內,依然在能源主導的經濟結構之下,通過削弱國家支持、發展私人部門,來贏得迅速發展呢?20世紀90年代“休克療法”式的經濟改革方案,就是旨在通過類似的路徑來解決問題,結果卻適得其反。對于這段歷史,人們是否還記憶猶新?俄羅斯作為一個超大體量的國家,在其獨特的自然人文條件之下,尤其在整整70年厲行政治經濟集權模式之后,如何來發展市場經濟,是否能夠在一個短時期內就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呢?看來,這一系列問題依然令俄羅斯精英百思而難得其解。
于是,猶如資深政治家蘇爾科夫所言,對于一個“長久國家”的需求出現了。這是從國家政治建構的角度,來看待俄羅斯當前走向的第二個問題。那么如何來強化國家建構呢?歐洲現代民主國家發端于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系和市民社會傳統。但俄羅斯并不是一個歐洲式的民族國家,也不存在歐洲式的市民階層基礎。俄羅斯是一個延續了千年生命的宏大帝國。俄羅斯學習西方四百多年,習得大量政治經濟與人文成果,但也并沒有使自己變成一個西歐式的民族國家。十月革命使俄羅斯走上了與西方決然對立的另一條道路,這使得俄蘇國家建構與歐美相去更遠。冷戰終結,蘇聯解體,似乎有機會使其變成一個類似于歐洲國家式的政治單位,但是轉型失敗、地緣政治抗爭加劇,使得這樣的期待又告落空。與此同時,一個前所未見的“全球轉型”開始了,先是新興國家(包括老牌帝國、但相對落后的俄羅斯)崛起,西方本身根基動搖,出現了數百年未見的,尤其是來自西方自身內部的挑戰,包括其國家建構。在這樣的大變動中,俄羅斯開始尋求既是按其歷史發展邏輯而來的“長久國家”,謀求符合自己國情的國家建構,來解決自己面臨的復雜而尖銳的內外挑戰,但也從未放棄將這樣的“長久國家”置于現代民主基礎之上的嘗試。事實上普京一直對于蘇爾科夫的“主權民主論”持謹慎態度,他認為,“主權主外,而民主主內,兩者是何關系,還值得深入研究。”①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третьего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9 сентября 2006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 s/president/transcripts/23789當下普京力主對2024年以后的憲政體制作重新安排。普京明確表示他將不再參加總統大選,但作為強人離開之后,必須對既有政治體制做好安排:俄羅斯議會將會在任命國家機構領導人的問題上擁有更大的權力,但俄羅斯仍然會是一個總統制國家。普京力主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來決定是否、以及如何推進憲政改革。普京明確說:這樣的實驗有可能失敗。但是無論如何,在“全球轉型”的背景下,無論就國家內部建構而言,還是對國家間關系來說,都應該采用更加為國際社會所認可的政治安排來推進憲政改革,這是“合法性與權力相平衡”的一次重要實驗。
最后的問題,“2024議程”所透露出來的不僅是挽救經濟的“經濟學問題”,也不僅是政治經濟一攬子推進的“政治經濟學問題”,而是順應世界秩序轉型的大勢,以國內政治經濟改革應對國際變局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問題。其一,迄今為止,歐美國家依然流行的觀念是:西方與中俄間不可逾越的障礙是價值觀念的對立。雖然,事實上無論東方與西方,民主、自由、安全、發展、獨立、互相尊重,所有這些觀念都是各國普遍追求的理念,但是東西方不同歷史背景之下的不同道路、不同時間和不同組合方式所引起的歧見依然隔閡深重。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2024議程”既明確強調維護主權,但又力圖關注公意,努力超越和克服國際歧見,這一點值得關注。其二,具體而言,俄羅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依然會堅定地推進多極化進程,但是在目標、實現方式和時間觀念方面已開始調整。俄羅斯已經超越“危機應對式”的外交戰略階段,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面向全球排兵布陣的格局,因此更加關注全方位的“權力與合法性的平衡”——既有政治與經濟的均衡,又有國內與國際的均衡,兼顧俄羅斯本身處境與國外反響之間的均衡,還矚目當下與長遠的平衡。今后這四五年,顯然是俄羅斯這一幕大戲登臺的一個重要階段,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