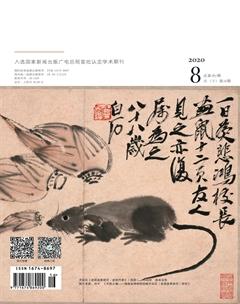嘉峪關西長城壕塹修建時間略考
張斌
摘 要:嘉峪關是明代萬里長城的西端起點,也是明王朝西北邊防的重要門戶。為鞏固西北邊防,明王朝在嘉峪關兩翼及周邊修筑了由關堡、墻體、壕塹、烽燧等要素構成的長城防御體系。文章通過對嘉峪關境內明代長城的營建史料進行整理研究,初步考證了西長城外側壕塹的修建時間。
關鍵詞:西長城;壕塹;防御體系;秦纮
嘉峪關以其獨特的歷史地理背景和復雜的邊防形式,造就了“諸夷入供之要路,河西保障之喉襟”的重要歷史地位和邊防作用。明初,宋國公馮勝率兵討伐北元殘余勢力平定河西地區,將敦煌以西區域摒棄,以嘉峪關為西北防備的界限,修筑嘉峪關。從明洪武五年(1372)至萬歷四十八年(1620)的200多年間,明王朝在嘉峪關兩翼及周邊修筑了由墻體、壕塹、關堡、烽燧等要素構成的長城防御體系。
近年來,為理清嘉峪關境內墻體、壕塹、關堡、墩臺等長城資源的修筑時間脈絡,我們通過對肅州衛和嘉峪關長城修建史料以及地方志書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整理研究,并結合甘肅省明長城資源調查資料和2014年嘉峪關長城進行維修時對西長城外側壕塹的考古發掘資料,理清了嘉峪關長城修筑的歷史脈絡,初步研究考證嘉峪關西長城外側壕塹的修筑時間。
1 明代前期西北邊防設置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定都應天后,派徐達、常遇春率兵討元,攻克大都,元朝滅亡。元順帝雖逃往漠北自守,但仍有很強的實力控制著北方,陜西、甘肅一帶有擴廓帖木兒(王保保)的十八萬人馬占據,河西走廊至哈密、吐魯番等地域都仍在北元的控制之下,對明朝的穩定構成了持久而巨大的威脅。為此,從洪武二年(1369)開始,明朝對北元殘余勢力發起了數次討伐。其中,洪武三年(1370),大將軍徐達率軍從潼關出西安擊潰了盤踞陜西、甘肅的擴廓帖木兒勢力。洪武五年(1372),宋國公馮勝出金蘭取甘州、肅州,進至瓜州和沙洲,平定河西。①明廷派宋國公馮勝將元朝的殘余勢力逐出河西走廊后,把地處河西走廊最狹窄之處的嘉峪關作為西北邊防的極邊要地,遂摒棄敦煌而以嘉峪關為界,在黑山和祁連山之間的嘉峪塬選址修建嘉峪關。《肅州新志》記載:“明初,宋國公馮勝略定河西,截敦煌以西悉棄之,以此關為限,遂為西北極邊,筑以土城,周圍二百二十丈,高二丈余,闊厚丈余。址依岡坡,不能鑿池。”②
經過數次討伐,北元殘余勢力雖得以削弱,但北元后裔韃靼和瓦剌先后崛起,時常侵擾邊境,危及西北邊防安全。因此,明朝將河西地區視為一個單獨的行政區域,特設陜西行都指揮使司主管河西軍政,在河西走廊設置軍政一體的莊浪衛、涼州衛、鎮番衛、永昌衛、山丹衛、甘州左衛、甘州中衛、甘州右衛、甘州前衛、甘州后衛、肅州衛、西寧衛、鎮夷守御千戶所、古浪守御千戶所、高臺守御千戶所等十二衛和三個守御千戶所。肅州地處極邊,自古是控制西域的重要門戶。洪武五年(1372),明王朝平定河西走廊后,放棄敦煌以嘉峪關為界,使肅州成了防守蒙元勢力的最西邊防,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朝政府將甘州左衛改為肅州衛指揮使司,重置甘州中中衛指揮使司。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將甘州中中衛改設為甘州左衛指揮使司,將甘州左衛從甘州遷出,調至肅州,設立肅州衛。
洪武、永樂年間,明廷充分考慮西北邊防形勢,為“屏藩河西”,在嘉峪關以西至哈密以東750多千米的區域先后設置了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金蒙古、哈密等七個衛所,史稱“關西七衛”,作為明朝西陲的“屏藩”。設立關西七衛的同時,明廷將西域民族部落首領封王于七衛,以羈縻政策管理七衛,和平發展與嘉峪關外各民族部落之間的關系,以維護西北邊境安寧。
從洪武至成化的百年間,由于洪武、永樂、宣德朝的強大,加之關西七衛的屏護,肅州衛、嘉峪關一帶相安無事。因此,明王朝也未在肅州衛修筑長城軍事防御設施來鞏固邊防。
2 明成化至萬歷初年嘉峪關長城修建情況
明成化至嘉靖初年,明朝西北邊境出現了嚴重危機。尤其成化年間,嘉峪關以西的吐魯番崛起,數犯哈密衛,關西七衛被迫東遷,嘉峪關日漸暴露于前沿,西北邊防形勢緊張。
弘治五年(1492)四月,關外吐魯番回鶻部落崛起,速檀(王)阿黑麻率眾侵占哈密衛,關外七衛盡被吐魯番攻破,流民內徙至肅州,嘉峪關警報頻傳。弘治六年(1493),吐魯番復據哈密,引起了明王朝的不滿,明孝宗在禮官耿裕等眾臣的進諫下,將在京的吐魯番使者全部遣返,并派大臣張海抵達甘肅,“遵朝議,卻其貢物,羈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于邊,閉嘉峪關,永絕貢道”①。明王朝第一次封閉嘉峪關實施封關絕貢,并以嘉峪關為肅州的重要門戶,嚴加設防,諭令肅州改修嘉峪關,于弘治八年(1495)完工。
第一次封閉嘉峪關后,肅州三面受敵,西面有東察合臺汗國建立的吐魯番進逼,北有來自河套的蒙古部落的侵襲,西南有游牧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的騷擾,邊患嚴重,因此,嘉峪關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弘治十六年(1503),甘肅鎮總兵官都督劉勝奏“備邊四事”,請議修筑甘肅鎮長城,尤其提議修筑肅州嘉峪關一帶長城。《明孝宗實錄》載:“甘肅一帶,孤懸河外,前鎮巡官議,自莊浪接寧夏岡子墩起,至肅州嘉峪關討來河止,修筑邊墻總二千六百七十八里,連增移墩臺,首末需三年告完,該用人夫九萬。今陜西行都司所屬衛所,除馬隊外,見在步隊并雜差旗軍止一萬六千余人。乞量于腹里起倩人夫三五萬,各委州縣佐貳官管領,布按二司委堂上官同本邊分守守備等官提督修筑。”②
正德元年(1506)八月,肅州兵備副使李端澄再次改修嘉峪關,按照先年修筑關樓的樣式、規格監修起了內城的光化、柔遠二樓,于次年二月落成。同時,在內城修建了官廳、夷廠、倉庫等附屬建筑物。正德九年(1514)吐魯番第三次占據哈密。正德十一年(1516)十一月,吐魯番大舉入嘉峪關攻肅州,《邊政考》載:“十一年六月,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仍據哈密,……十一月滿速兒牙木蘭領兵會合罕東左衛土巴部落幾萬余騎入嘉峪關。十六日,游擊芮寧領兵出南門御之敗績,官軍死者八百四十二人,參將蔣存禮出北門被圍,官軍死者一百三十九人。十九日,陳九疇……總兵官史鏞副總兵官鄭廉十一月二十日俱統兵迎戰于臨水西黃泥鋪,賊抵肅州凡入境月余方回。 ”③
嘉靖三年(1524),吐魯番首領再次親自領兵入侵肅州,進逼甘州。明廷雖派兵將其擊退,但已失去對嘉峪關外的控制,明廷決定封閉嘉峪關,劃關而治。第二次封閉嘉峪關后,明廷為加強嘉峪關防務,嘉靖十八年(1539),明廷命肅州衛修筑嘉峪關兩翼的西長城。《明世宗實錄》卷299載:“丙申,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鑾言,嘉峪關最臨邊境,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墻壕淤損,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損者,任于壕內填筑邊墻一道,每五里設墩臺一座,以為保障,上從其議。”④《肅鎮華夷志校注》又載:“嘉靖十八年七月,大學士翟鑾行邊時,肅州兵備李函既諸行邊執事,駐節嘉峪,閱視隘口,請議筑修邊墻以備西邊。翟公許可,越明春暮,遂議筑邊,南北與關相連。南自討來河,北盡石關兒,其延三十里。”⑤嘉靖二十八年(1549),甘肅巡撫楊博、兵備副使王儀展筑嘉峪關城垣,添筑敵樓、角樓、墩臺等,還夯筑了外城墻,在外城墻外開挖護城壕。
隆慶六年(1572)至萬歷二年(1574),《肅鎮華夷志》載:“嘉峪關起鎮夷千戶所止,邊墻、崖榨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丈,計七十五里二百六十步,都御史廖逢節議題,隆慶六年修完。自新城兒東長城西頭起,嘉峪關北邊墻、新腰墩止,邊墻一萬九百八十四丈,底闊八尺,頂闊二尺五寸,實臺高一丈,垛墻二尺,共高一丈二尺,隨墻大中墩二座,共用本色糧四百七十石二斗,折色銀二千三百八十二錢,萬歷元年修完。自下古城迤北東長城角墩起,靖虜墩東壕頭臨水河北崖止,又自嘉峪關起、鎮夷所止邊墻崖榨二千六百四十六丈,內邊墻底闊一丈,頂闊六尺,實臺高一丈二尺,垛墻三尺,共高一丈五尺,崖榨高三丈,闊二丈,共用折色銀二百八十一兩八錢七分,萬歷二年修完。下古城迤東自靖虜墩起,苦水界牌至,遍壕長五千八百二十丈,俱口闊三丈,深至見水為止,底闊一丈,兩岸筑土堰各一道。底闊四尺,頂闊一尺五寸,高五尺,共用鹽菜銀五百八十二兩。又于通賊隘口嘉峪關迤北水關兒適中金佛寺堡、白家灣、下古城堡,東北大口子添墩三座,共用鹽菜銀九兩,幫接嘉峪關迤北水關兒舊邊墻一節,長四十四丈,底闊一丈,頂闊六尺,實臺高一丈二尺,垛墻三尺,共高一丈五尺,俱不支銀錢。”至此,肅州衛長城防線及嘉峪關周邊的長城防御體系基本形成。
3 嘉峪關西長城壕塹修建時間考證
從現有的明代修筑嘉峪關長城史料看,嘉峪關西長城及肅州衛管轄的長城均有修建記載,但嘉峪關西長城外側的壕塹修筑于何時沒有明確記載。僅《明世宗實錄》卷299“嘉峪關最臨邊境,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墻壕淤損,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損者,任于壕內填筑邊墻一道”,其中有壕塹淤損的記載,說明西長城外側的壕塹在嘉靖十八年(1539)之前就已存在,并非嘉靖十八年(1539)肅州兵備李函修筑西長城是時修建的。而且2014年在配合嘉峪關長城保護工程時對嘉峪關西長城外側的壕塹局部的發掘資料顯示,壕塹有明顯二次修筑痕跡。壕塹深度4.5米,壕塹的邊沿外壟整體暴露于地表,壕塹內風成沙一層層堆積。壕塹剖面大致呈梯形,口大底小,壕塹下部未處理,為原生戈壁沙礫層,上部東西兩壟內側邊緣有人為碼砌的鵝卵石,排列有一定規律。這一考古發掘資料也印證了上述史料中修浚壕塹淤損的記載。
從明弘治五年(1492)至嘉靖初年的明王朝西北邊境危機來看,嘉峪關外吐魯番部落崛起后,吐魯番首領速檀(王)阿黑麻數次率眾侵占哈密,關外七衛盡被吐魯番攻破,流民內徙至肅州,嘉峪關警報頻傳,明廷兩次封閉嘉峪關,實施封關絕貢,并以嘉峪關為肅州重要門戶,嚴加設防,加固修葺嘉峪關。嘉峪關雖地處河西走廊狹窄之處,但明廷不可能以一座孤城抵御吐魯番的入侵。
馬順平的《“界在羌番,回虜之間”—明代甘肅鎮邊墻修建考》一文中,根據嘉靖《陜西通志》卷19《文獻七全陜名宦》中弘治年間陜西三邊總制秦纮命三邊鏟崖設險修筑延綏、寧夏、甘肅三鎮長城的記載,并與弘治十六年(1503)甘肅鎮總兵官都督劉勝奏請修筑甘肅鎮長城的“備邊四事”史料以及《皇明九邊考》中延綏、寧夏二鎮修筑記載的長城修筑的起始點和長度分析,認為弘治十六年(1503)甘肅鎮總兵官都督劉勝上奏請議修筑甘肅鎮長城,特別是肅州嘉峪關一帶長城后,三邊總制秦纮利用其山川形勢的特點,運用“鏟崖設險”的方式修筑了東起于寧夏岡子墩,西至嘉峪關南討來河的長城,是甘肅鎮長城的肇始階段。①
另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四年(1545)成圖的《甘肅鎮戰守圖略》中甘肅鎮轄區內山丘地帶均詳細地繪制有“鏟崖設險”的長城,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書的《邊政考·肅州圖卷》中嘉峪關兩翼西長城外側壕塹也繪制在圖。與此同時,近年來的甘肅省明長城資源調查中,河西走廊明代長城沿線也發現了這種利用自然地勢“鏟崖設險”修建壕塹或山險墻與長城墻體并行存在。查閱甘肅長城相關史料,均未找到其他的修建記載,相比之下,這些壕塹的修筑方式均與弘治十六年(1503)甘肅鎮總兵官都督劉勝上奏請議修筑甘肅鎮長城后,陜西三邊總制秦纮命三邊運用“鏟崖設險”方式修筑延綏、寧夏、甘肅三鎮長城的記載中的“鏟崖設險”的修筑工藝相符。
綜上所述,嘉峪關長城防御體系主要是在洪武、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歷幾個時期修建,而嘉峪關西長城外側的壕塹是弘治十六年(1503)三邊總制秦纮修筑東起寧夏鎮岡子墩、西至嘉峪關討賴河的甘肅鎮長城時修筑。嘉靖十八年(1539)兵部尚書翟鑾巡邊時,肅州兵備李函修筑嘉峪關兩翼西長城時修浚其淤損,并加以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