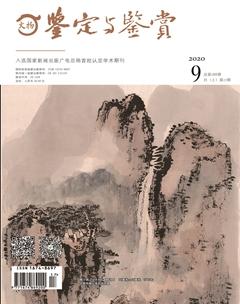米芾隸書風格淵源考析
孫思凡



摘 要:宋代的隸書向不為后世所重,因風格較為單一,藝術表現力不強,但著名書法家米芾筆下的隸書卻與時人不同,他突破當時程式化隸書的影響,將隸書演繹得自然率意。文章從書跡入手,將同時期書法家的隸書作品與米芾隸書相對比,歸納米芾隸書書風特點,并著重從其天性、經歷、取法三個方面探討影響其隸書書風形成的原因。
關鍵詞:米芾;隸書;率意書風;成因
1 米芾隸書創作的背景與時代風格
1.1 家學淵源與仕途境遇
米芾的父祖輩皆任武職,從五世祖米信開始,便是趙宋王朝的開國元戎,后因北宋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局面,米芾的父親這才決定讓米家后代棄武從儒。自此可知,出生在這種世代為武官的家庭,其骨子里的性格并非如一般讀書人那樣平靜隨和,而是保有習武之人的率意不拘。《宋史》言:“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有舊。”宋莊綽《雞肋編》卷上言:“或言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為殿侍。”可知米芾“蔭庇”入仕,曹寶麟教授曾道“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三大目標,何曾像老米那樣以書廢事呢?”他并沒有什么政治理想和政治野心,從側面來說這也有利于他保持天真恣意。
米芾的隸書創作風格多樣,這與好友李公麟對他的影響以及他在宣和內府接觸了眾多古器物是分不開的。北宋中期,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文人開金石學之先,大量收集商周秦漢時期的鐘鼎彝器、碑刻,并進行著錄和研究,其本意雖不是針對書法,但對時人篆隸書的學習有著較大的推動作用。米芾自然也不例外,在其任職太常博士期間,他觀賞了大量的古器物銘文,實物的接觸對他的篆隸書創作有著巨大的影響。他將風格各異的古器物銘文融入隸書創作中,其隸書風格也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有別于同時期其他學習魏晉風貌書家筆下的隸書。
1.2 隸書創作的時代風格
一般來講,宋代是有隸書繁盛的社會基礎及歷史基礎的,但或因尚意書風的引導,篆、隸、楷類書體的規范與嚴整性不如行草書利于情感的抒發,又或因宋代人過于重視蔡邕的《熹平石經》等官方程式化隸書等原因,導致宋代隸書的研習者雖然不少,其隸書創作的藝術水準卻普遍不高。元代陶宗儀的《書史會要》中收錄了不少宋代的善隸書家,仁宗時期是最初開始興起取法漢魏隸書的時期,以此時期存有的王洙隸書作品《范仲淹神道碑》(圖1)為例。
朱長文在《續書斷》中稱:“(王洙)晚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可見其隸書是具有一定的時代代表性的。王洙的隸書在用筆上略顯板滯,點畫、粗細變化不大,體勢上略呈長方形,《王氏談錄·筆法》載:“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方正,然后以奇古為工。”與漢魏隸書風格相似。
與米芾并稱為“宋四家”的蔡襄也有隸書傳世,如《劉蒙伯墓褐文》的碑額(圖2)。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隸書較漢魏風格的隸書更為規矩、整潔,除不似唐隸略呈扁狀外,其行筆嚴守法度、注意雕琢,近似唐隸,但缺少自然地流露。
北宋中后期司馬光、蔡京、黃伯思也以善隸為名,以司馬光《王尚恭墓志》為例(圖3),此墓志中隸書在體勢上與王洙《范仲淹碑》相似,方正且近縱勢,筆畫更加厚重,也有漢魏時期隸書的風貌。
2 米芾隸書風格的厘定
米芾的隸書在用筆、結體、布局、風格上則與上文提及的同時代其他書家的隸書作品有明顯不同。南宋時高宗趙構命以內府所藏米芾墨跡摹勒上石,刻成《紹興米帖》,其中現存米芾篆隸作品17件,隸書9件,暫將其劃分為四類風格。
第一類風格如圖4(左),是米芾隸書作品中相對平穩的一類,尤其是橫畫的處理,入筆方勁,中行遒緩,但已經出現行書筆意;第二類風格如圖4(中),點畫的起收轉折方中有圓,尤其是對波挑的處理,不僅橫畫一波三折,僅一個收筆處便極具裝飾意味,用筆豐富;第三類風格如圖4(右),其與第一類風格較相似,屬于第一類風格的放大版,相對第一類更加率真自然,行書筆意也更多,收筆處更尖銳。
第四類風格如圖5,是米芾隸書作品中最率意的一類。在點畫的表現上,行書連帶關系更為明顯,筆畫的起收筆處都沒有進行專門的處理。字與字之間、單個字中的筆畫之間輕重緩急較為夸張,波勢之筆多按筆鋪毫,且點畫粗細對比非常強烈,出鋒輕佻率意。從整體的章法上看,字距、行距隨機留空,上下錯落有致,與通常的隸書章法相去甚遠,反而帶有行草書章法的意味,可謂“不守規矩”。正如傅申在《海外書跡研究》中說:“他的隸書是用他習慣的行書筆畫寫出的,總的結構趨向垂直,字的間架較松散,筆法自然,不因襲時尚。”
綜上,米芾這四類隸書的創作迅疾跌宕、風格多樣,正如他自己明確提出的戲墨觀點—“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這是宋代尚意書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他癲逸性格在書法創作上最生動的體現。
米芾的這幾件隸書作品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值得注意,那便是其抄寫的內容與現刊行的原典籍內容有較大差異,常有缺衍、顛倒現象,并且還有不少異體字出現。以圖4為例,這是其抄寫的《般若波羅蜜心經》。但米芾在書寫時,直接在第一個“舍利子”后插入了第二個“舍利子”后面的內容,即“是諸法空相”;無獨有偶,在“空不異色”之后又脫文八字,接上了“空即是色”后面的內容。筆者對此推測有二:一是米芾因書寫時只注重用筆而忽視了文辭內容,故思想神游將文本寫錯;第二種推測是米芾對于文本有著自己的解讀,他認為有些文辭屬于重復,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與前文“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意思相近,故將其省略;又如原文中對舍利子的解釋出現過兩次,一次是“舍利子,色不異空……”第二次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米芾將“是諸法空相”插入第一次的解讀之中,構成“舍利子,是諸法空相,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總分結構,也更利于理解。這表明他對于書法也好、佛經也罷,從來不是盲目地認同、采取,而是補上了自己的思考。
劉鎮《尚意書風下的篆書日常書寫考察—以米芾為例》曾提出類似的問題并闡述其觀點,他認為我們不能妄加猜測是米芾當時書寫依據的文辭版本不好,或者刻帖人文化水平低劣等原因,“不如說其援引行草書創作意趣到篆書創作中進行極致地表達,已經超越對文辭本身的關注”,這樣的觀點更加符合實際,也更符合米芾的個性,其隸書創作亦如是。
3 隸法師宜官
《宣和書譜》中載:“文臣米芾……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晩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米芾在《自敘帖》中也自稱:“入晉魏平淡,棄鐘方而師師宜官,《劉寬碑》是也。”漢末書法家師宜官并無作品傳世,但南朝梁武帝在《古今書人優劣評》中對其作品有這樣一番點評:“師宜官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結合文章第一部分對米芾隸書作品風格的觀察,可以說這番點評用在米芾隸書上也是相當合適的。
師宜官在漢末以隸書著名,但其風格與漢魏隸書的整體風格不甚相同,在眾人以蔡邕《熹平石經》這一類端莊古樸的隸書作為學習的不二法門時,米芾卻“棄鐘方而師師宜官”,這或許是米芾雖取法漢魏隸書,但其作品中少有漢魏隸書的氣息,并不真正符合漢魏隸書美學特征的關鍵因素。
至于米芾為何要選擇取法師宜官的隸書,筆者有如下推測。首先縱觀米芾的學書歷程,可以發現他本身就對自然率意、不拘小節的書風有著特別的偏愛,一如他學顏楷而放到一幅紙大小,目的便在于得到寬博正大的體勢;他曾豪奪沈傳師的大字詩碑《道林寺詩》,此詩碑也是結構寬博;他學習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他還將書法比作金玉,意在推崇作書的隨機即興,一如師宜官當街題壁、醉書,妙境不由“預想”而得。
若具體分析兩人的淵源,一是在性格方面。西晉書法家衛恒《四體書勢》中最早有師宜官作書的記載:“……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他與米芾一般,都是一位在時人眼中“瘋癲”的書法家,流傳下許多“放浪形骸”的小故事,并且“甚矜其能”,有一身才華與傲骨。米芾會故意制造輿論,以求通過精勤與智慧來留得身后名,與師宜官在街上題壁書寫丈長大字“嘩眾取寵”異曲同工;米芾對“尚意”的追求,即舍去一切功利目的,師宜官作書也是如此,只為自己盡興。因此米芾選擇師宜官,追求的是心靈上的歸屬。
二是源于米芾對楚國書法藝術的崇拜與追求。楚國為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其屬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河南省南部、江蘇、浙江等地。米芾自詡其為楚國后裔,而師宜官是南陽人,南陽亦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境內。
三是其“不以書名大小而妄為耳鑒”。上文提到漢魏擅寫隸書的傳世名家主推蔡邕,梁鵠亦有卓越的成就,師宜官的名氣雖在,卻并不如他們。但米芾博采眾長,不以書名大小而妄為耳鑒,亦如他贊賞唐朝并無盛名的段季展,以及學習并不著名的羅讓等。
四是米芾的特殊執筆法,即五指包管。這樣的執筆方式最適合站立書寫,尤其是題寫墻壁,羊欣在《采古來能書人名》中有對師宜官的記載:“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從這一則記載可以看出師宜官的個性張揚,也證明其擅長題壁,而米芾的五指包管法使他在學習師宜官的題壁書時更為得心應手。當然,最關鍵的一點還是米芾對師宜官隸書風格的認可與喜愛,畢竟隸書這一規整的書體與他對率意的追求似乎并不合拍,他在臨寫程式化的隸書時可能常常會感到不自在,而從師宜官“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的演繹中他看到了希望,從而意識到隸書也可以作為抒發性情的載體。
4 余論
米芾將創作行草書時的意氣、用筆融入隸書當中,繼而將隸書也改造成了“尚意”的載體,形成了不同于時代的個人獨特的隸書風貌。關于其隸書風格的成因,據史書記載當與師宜官有著不可分的關系,但因缺少師宜官的書跡進行實物佐證,我們也只能通過文獻記載去勾連、推測。對于米芾隸書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地深入。
[1]上海書畫出版社.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2]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米芾卷[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5.
[3]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4]米芾.書史[M].趙宏,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5]陶宗儀.中國藝術文獻叢刊:書史會要[M].徐美潔,校.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6]方波.宋人隸書審美觀念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4.
[7]魏平柱.米芾書法家成因初探[J].襄樊學院學報,2008(3):79-82.
[8]劉鎮.意書風下的篆書日常書寫考察—以米芾為例[J].書法,2016(5):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