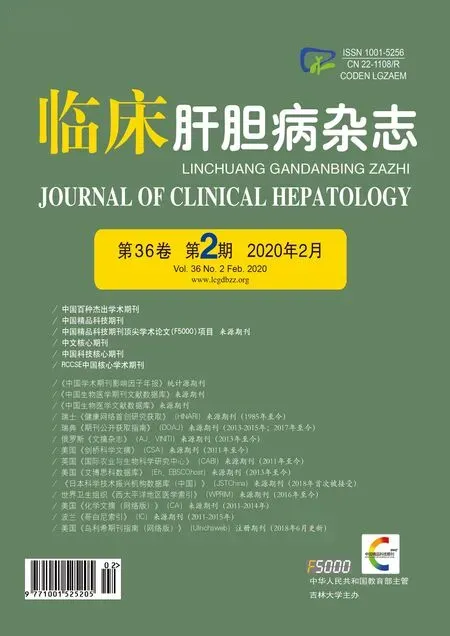肝細胞癌放療降期
——從姑息走向根治
曾昭沖, 孫建國, 郎錦義
1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放療科, 上海 200032; 2 陸軍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腫瘤科,重慶 400037; 3 電子科技大學附屬四川省腫瘤醫院 放療科, 成都 610041
惡性腫瘤分期的目的之一是指導按分期治療,惡性腫瘤某一期別的治療有其規范或指南,但治療方案不是一成不變。當治療到某一階段再評估療效和再分期,有可能下降到另一期別或分型,此時,必須對治療進行適時調整,以讓患者盡可能獲益,甚至達到根治。
隨著原發性肝癌治療手段增多,治療效果提高,降期治療得到重視,尤其是配合外科手術的降期治療,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可以從姑息走向根治。降期治療分為新輔助治療和轉化治療,新輔助治療是在初始能手術切除的基礎上,通過非手術手段,使腫瘤進一步縮小或降期或降型,獲得根治性手術切除的概率更大,根治更徹底。轉化治療是初始不能手術切除,經過積極治療后,有可能轉變為可手術切除。
本文從外放療的角度論述不同分期的原發性肝癌特別是肝細胞癌的降期治療。降期治療可使肝細胞癌的姑息治療走向根治,使不可治愈向可治愈轉化,甚至帶來治療結局的飛躍。
1 不能手術切除的Ⅱ期肝細胞癌降為Ⅰ期,或Ⅰb期降為Ⅰa期,部分轉化為根治性手術切除
局限在肝內但不能手術切除的肝細胞癌患者,給予經肝動脈化療栓塞(TACE)后結合外放療,雖然受限于全肝的放射耐受劑量,達不到完全控制腫瘤,但放療后腫瘤縮小,達到部分緩解,外科醫生認為可以手術時,應該盡可能給予手術切除。筆者[1]曾報道,外放療后,不能手術切除的肝癌患者轉化為二期手術,手術切除率23%(8/35),手術標本有殘存的癌細胞;接受手術的患者,較未能手術切除者的生存期長。同期臨床資料[2]顯示,單純TACE獲得二期手術切除率為12.8%(19/149),TACE結合外放療二期手術切除率為20.4%(11/54)。病例1是大肝癌轉化為小肝癌,獲得手術切除機會(圖1)。
注:a,介入后3周復查CT,腫瘤10.6 cm×5.8 cm,超過一半的腫瘤無碘油沉積;b、c,介入后1個月開始放療,50 Gy/25次;d,放療結束后7周復查CT,腫瘤縮小到5 cm,外科醫生考慮降期手術;e,手術切除標本,可見魚肉樣殘存癌組織;f, 術后50 d隨訪CT,切緣術后改變;g,術后1年隨訪MRI,未見腫瘤。迄今存活6年。
圖1不能切除的大肝癌降期后手術
2 Ⅲa期術前新輔助放療,或部分降為Ⅱ期或Ⅰ期,轉化為可手術切除或肝移植
2.1 新輔助放療 肝細胞癌伴門靜脈癌栓(Ⅲa期)患者,經過積極手術切除,只有小部分患者獲得長期生存,大部分患者在短期內出現肝內復發或轉移,導致死亡。對門靜脈癌栓進行單純放療,只是姑息手段。日本學者[3]報道,肝細胞癌合并癌栓的患者,接受術前新輔助放療,較單純手術的療效好,對門靜脈一級分支或主干癌栓先給予放療30~36 Gy/10~12次,放療結束后2周內手術取栓及肝內病灶切除,術后根據情況予介入、射頻、無水酒精注射等治療。結果顯示:手術結合外放療的患者中位生存期為19.6個月,不手術者為9.1個月,兩組生存期有顯著差異(P=0.036);手術標本病理顯示,83%的癌栓完全壞死(病理完全緩解)。因此,手術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原發灶的控制率和疏通門靜脈。對于合并癌栓的患者,術前放療結合外科手術切除取栓是綜合治療的有效模式。
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進行一項隨機前瞻多中心的臨床研究[4],比較肝細胞癌伴門靜脈癌栓患者的術前新輔助放療與不放療的生存情況,放療組82例,給予18 Gy/6次的新輔助外放療;對照組82例,未行新輔助放療。結果顯示:新輔助放療組的1、2年生存率分別為75.2%、27.4%,對照組分別為43.1%,9.4%,兩組生存率有統計學差異(P<0.001)。新輔助放療明顯提高肝細胞癌患者的術后生存期。病例2是門靜脈主干癌栓,經過新輔助放療,癌栓從程氏Ⅲ型降為Ⅱ型,最后獲得手術切除(圖2)。
注:a,放療前MRI檢查,發現門靜脈主干和右后支癌栓(箭頭所示);b,放療后3個月隨訪MRI,癌栓明顯縮小,血供減少(箭頭所示),患者獲得切除機會。
圖2新輔助放療后門靜脈癌栓程氏Ⅲ型降為程氏Ⅱ型
2.2 轉化治療 韓國Yonsei大學的Kim等[5]回顧性分析了同步放化療對肝細胞癌患者的療效,入選264例患者,因門靜脈癌栓或殘肝體積不足,不能行手術治療而接受三維適形放療,大部分患者接受單次劑量1.8 Gy,總劑量45 Gy的放射治療,同時在放療的第1周、第5周靜脈輸注5-氟尿嘧啶(5-FU)。放療結束1個月后,靜脈輸注5-FU和順鉑,每4周1次,共3~12個周期。其中18例患者轉化為可手術切除,術后病理顯示,4例(22.2%)腫瘤完全壞死,7例(38.9%)腫瘤70%~99%壞死。接受手術的18例患者,中位生存期和中位無疾病進展期分別為40和24個月,4例腫瘤完全壞死的患者中位無病生存期為54.6個月。因此,不能手術切除的肝細胞癌患者,接受適形放療后,部分患者轉化為可手術切除。
2.3 移植前窗口期觀察 對超出肝細胞癌移植標準的患者,接受外放療可以縮小病灶,特別是作為窗口期,篩選出生物學行為好的肝癌患者,即使超出標準的肝細胞癌患者,也可能納入肝移植標準,獲得肝移植機會。而生物學行為差的腫瘤,在治療過程中,向肝外轉移,從而失去肝移植機會。筆者已經運用介入治療結合外放療,使得10余例肝癌伴門靜脈癌栓患者獲得肝移植機會,最長1例已存活11年。病例3是癌栓患者接受放療后,肝內病灶縮小,長達5個月的窗口期觀察,無遠處轉移,從而給予原位肝移植(圖3)。類似研究在其他國家有所報道,但均是個例[6]。如,17例肝細胞癌伴門靜脈癌栓患者,接受介入治療結合放療,隨后接受肝移植,1、3年的生存率分別是87%和60%[7]。5例門靜脈癌栓接受介入和介入后放療,降期后再接受肝移植,其1、3年生存期為100%和80%,同一時期配對的10例(1∶2匹配)門靜脈癌栓患者,單純放療,1、3年生存期僅50%和30%[8]。由于供體來源短缺,國內外這類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摸索。
注:a、b,MRI見門靜脈主干、分支癌栓,肝內彌漫性病灶;c、d, CT掃描制定放療計劃,給予TOMO放療50 Gy/25次,包括右葉及其門靜脈主干;e,放療后3周隨訪CT,門靜脈癌栓明顯縮小,但是腹水增多。于2011年9月28日接受肝移植。術后病理:肝內腫塊14枚,最大位于肝右葉,5.5 cm×7.4 cm×3.5 cm,門靜脈癌栓;f、g,移植術后5個月和6年隨訪MRI,無肝內復發,迄今存活8年。
圖3門靜脈癌栓放療后原位肝移植
3 T1或T2肝癌肝移植前的橋接放療
對于符合肝移植適應證的肝細胞癌患者,原位肝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療手段。但是,由于肝臟供體數量有限,不少患者在較長的肝源等待中發生腫瘤進展,從而喪失最佳的肝移植治療機會。因此,在肝源等待期,延緩腫瘤進展的橋接治療非常重要。
立體定向放療(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SBRT)可以作為肝癌患者等待肝移植前的一種橋接治療,既不屬于新輔助放療,也不屬于轉化放療。由于SBRT屬于根治性治療,T1 或T2的患者,絕大部分可以降為T0。肝移植的目的是把失代償的肝臟更換為肝功能正常的肝臟。放療的目的是在特定的時期(缺乏供肝)控制腫瘤的進展。
美國Rochester大學醫學中心和密西根William Beaumont醫院報道了18例移植前接受SBRT的肝癌患者,中位放療劑量為50 Gy/10次,沒有嚴重的胃腸道不良反應和放射性肝炎發生[9]。放療后中位等待期為6.3個月,12例患者成功接受了肝移植術,10例患者病理顯示腫瘤完全壞死。術后中位隨訪期19.6個月,所有患者均存活[10]。因此,SBRT是肝癌患者等待肝移植前一種安全有效的銜接治療措施,能夠在移植前控制腫瘤,利于緩解肝源壓力,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
研究[11]報道,379例患者接受肝移植的移植前橋接治療,其中36例接受SBRT,99例接受介入栓塞化療,244例接受射頻消融。最終有312例患者獲得肝移植,SBRT組30例,介入栓塞化療79例,射頻消融203例,3組獲得肝移植的概率相似。1、3、5年生存率分別為:SBRT組83%、61%和61%,介入栓塞化療組86%、61%和56%,射頻消融組86%、72%和61%,3組間無明顯差異(P=0.4)。SBRT作為肝細胞癌移植前的橋接治療,和介入栓塞、射頻消融一樣安全有效。對伴有腹水、凝血酶原時間延長的肝細胞癌患者的移植前橋接治療,相比介入栓塞、射頻消融,SBRT更有優勢。病例4為肝功能為Child-Pugh C 級的小肝癌患者,在22個月的等待肝源期間,接受SBRT,最終獲得肝源,成功移植(圖4)。
還有研究[12]報道,符合米蘭或舊金山肝移植標準的肝細胞癌69例,隨機分為36例介入,33例接受質子放療,其中,介入組10例(10/36)獲得肝移植機會,質子組12例(12/33)獲得肝移植機會。術后病理檢查發現,介入組完全緩解率10%,質子組為25%。兩組患者移植后的生存率無顯著差異。因此,質子放療和介入治療一樣,可以使腫瘤降期,贏得等候時間,不影響肝移植成功率。
4 大肝癌(T2)經介入栓塞化療降期為小肝癌(T1),再予以SBRT,達到根治性放療
如果肝腫瘤較大,SBRT容易帶來肝損傷。經過介入栓塞化療后,肝腫瘤明顯縮小,直徑一般小于5 cm,特別是單發腫瘤,則給予SBRT,從而使不能根治的肝內腫瘤轉化為可根治。我國香港報道[13]顯示,49例患者接受介入治療后給予SBRT, 較98例(1∶2配對)接受單純介入治療的對照組,SBRT者腫瘤局控率和生存期都遠有優勢。病例5是局限肝內的大肝癌患者,腫瘤靠近肝門不能手術,介入后腫瘤降期,調整為SBRT,獲得完全緩解(圖5)。
注:a,放療前增強CT,右后葉病灶2 cm,箭頭所示,動脈期強化,中等量腹水;b,CT 和MRI融合確定靶區,制定SBRT計劃,腫瘤50 Gy/5次;c~e,分別為放療后2、5、9個月隨訪的MRI,腫瘤消失,放療區域(瘤床)充血,系放療后改變,少量腹水;f,放療后22個月等到肝源,接受肝移植,移植后1年隨訪CT。
圖4肝細胞癌肝移植前的橋接放療
5 總結
綜上所述,肝癌放療降期的目的是為進一步達到根治創造條件。手術、SBRT和射頻消融均是局部治療,均能達到根治性治療。這三者中,手術切除是最常用的手段。降期后的局部治療,可以讓患者從姑息走向根治。表1列出肝癌放療降期的分類管理。
降期是相對的概念,分期的標準也是相對的,根治才是目的。病例1所示,放療前腫瘤10.6 cm,單發,屬于Ⅰb期,經過放療后,腫瘤縮小到5.0 cm,此時屬于Ⅰa期,可以順理成章地認為降期。但是,如果此時的腫瘤5.1 cm,是否為降期?其實,此時5.0 cm和5.1 cm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放療的目的就是縮小腫瘤,達到根治性手術切除。病例2合并門靜脈癌栓,通過放療后,癌栓雖然縮小了,但仍然存在,再分期仍然屬于Ⅲa期,但是以程氏癌栓分型[14],已經從Ⅲ型降到Ⅱ型。病例3和4都是移植前的橋接放療,但是放療目的各不相同。病例3放療目的不是降期,而是作為窗口期,觀察是否出現遠處轉移,甄別惡性腫瘤的生物學行為;病例4則無需降期也可以手術,只是等待供肝,與時間賽跑。降期后即使不能外科治療才能根治,如果大肝癌轉化為小肝癌,SBRT或射頻消融,部分患者也可能達到根治。病例5就是降期后用SBRT獲得根治。
注:a,MRI顯示肝門部7.5 cm病灶,動脈期明顯增強,肝細胞癌的影像學表現;b,6次介入后PET-CT示腫瘤縮小,部分碘油沉積,瘤內糖代謝較高,SUV值4.7 g/ml;c,7次介入和7次FOLFOX4化療,SBRT前,MRI示下腔靜脈旁病灶1.8 cm,動脈期無強化;d,CT上勾畫的靶區制定放療計劃,SBRT腫瘤等劑量分布曲線,55.5 Gy/15次;e,SBRT后11個月,PET-CT顯示腫瘤無糖代謝;f,SBRT后16個月隨訪MRI,與放療前(c)比較,病灶縮小到0.9 cm,無血供;g,SBRT后4年隨訪MRI,病灶大小穩定,無血供;h,整個治療過程中的AFP變化。SBRT后,AFP降至最低點。
圖5不能手術切除大肝癌接受介入后轉化為小肝癌,接受SBRT
最引人爭議的問題是,能不能手術,均由肝膽外科醫師決定。一般是Ⅰ期肝細胞癌,只要沒有手術禁忌證,技術上可行,都可以手術;Ⅱ期則取決于外科醫生;有些外科醫生甚至Ⅲa(癌栓)都可以直接手術。現在缺乏手術切除適應證的統一標準,不同級別的肝膽外科掌握手術的原則不同,國內外肝癌手術適應證也存在很大差異,對降期后的手術治療存在爭議屬于正常的學術討論。雖然肝癌放療降期治療的病例數較少,但相關研究報道逐漸增多,循證級別逐漸提高。希望本文提供的臨床研究數據和臨床病例能拋磚引玉,對于肝細胞癌這一難治疾病,在臨床實踐中借鑒探索。

表1 肝癌放療降期的分類管理
注:1)不排斥使用射頻消融或無水酒精注射;IMRT,調強放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