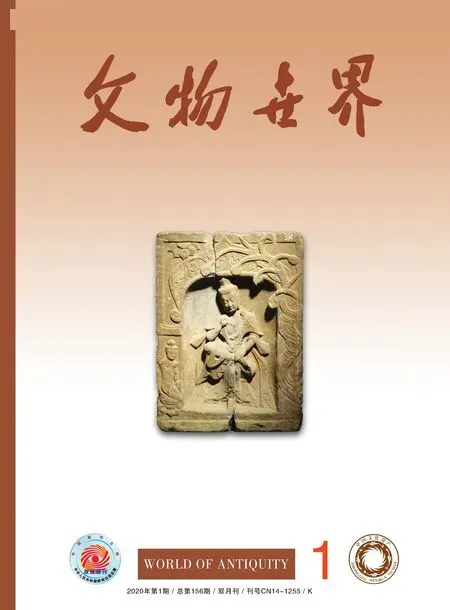大同市云波里華宇二期壁畫墓的年代[1]
□侯曉剛
2019年4月,大同市平城區云波路南側與源興街北側之間云波里華宇二期施工現場出土一座壁畫墓。在墓室四壁和甬道兩壁,華宇二期壁畫墓保留有七處用紅、黑、白三種顏料(也有少量的青色顏料)繪制出的古代珍稀壁畫。此墓葬壁畫因人物眾多、場面壯觀而顯得氣勢宏偉,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在搶救發掘過程中,沒有發現墓志之類表明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的文物。因此,要明確該壁畫墓的年代,須得由墓葬位置、墓葬形制、壁畫人物服飾及壁畫所見名物等方面綜合考量,并進行相關比較分析,方可得出大致的初步判斷。
一、墓葬位置
依華宇二期壁畫墓出土位置來看,其居于大同市平城區云波路南側與源興街北側之間,地處古如渾水(今御河)和古武周川(今十里河)交匯處,即御河以西、十里河以北的地帶。此地帶以及十里河南岸的廣闊地方,是北魏首都平城的南郊地區。在這塊土地上,以華宇二期壁畫墓出土處云波路為起點向周邊考察,可以發現,幾乎遍地都是北魏墓葬或墓葬群。
先從起點云波路考察,2009年4月在云波路中段道路建設工地上(即華宇二期壁畫墓北約數十米處)發掘了一座北魏平城時期壁畫墓[1];接著由云波路向南出發,沿魏都大道約800 米處,即大同市電焊器材廠,此處即是北魏南郊墓葬群。1987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大同市博物館聯合考古隊在大同市電焊器材廠擴建工地上發現了257個墓葬,發掘了167 座北魏墓葬[2]。其中,基于考古類型學的分析,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單位所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認為,此墓群中自道武帝天興元年(398年)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之間的北魏平城時期墓葬共有134 座[2];再由云波路至南郊墓葬群向東南方向看,依次排列著2001年5月發掘的七里村北魏墓群[3]、1997年 7 到 9月間出土的智家堡北魏墓群[4][5]和1998年12月發掘的田村北魏墓[6],其墓葬數分別為34座、2座和1座;更進一步跨過十里河向南走至大同南郊馬辛莊北之仝家灣,2008年5月發掘了富喬垃圾焚燒發電廠北魏墓群,鉆探墓葬數達58 座[7]。
二、墓葬形制
據北魏墓群的相關研究顯示,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的年代和形制大致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界定。1987年發掘大同南郊167 座北魏墓群的成果表明:根據綜合比對研究,依靠墓葬隨葬品中陶器的類型分析,這批墓群的年代確定為五個時段[2],分別為①遷都平城之前(398年以前)、②遷都平城初期(398-439年)、③太武帝統一黃河流域至太和初年左右時期(439 至477年左右)、④太和初年左右至遷都洛陽時期(477年左右至493年)、⑤遷都洛陽以后(493年以后)。
167 座北魏墓的形制分為五種,分別為豎穴土坑墓、豎井墓道土洞墓、豎井墓道橫穴墓、長斜坡墓道土洞墓和長斜坡墓道磚室墓。
根據對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已發掘的167 座墓葬之所屬時期、形制和數量關系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兩點認識:
1.大同南郊發掘的167 座北魏墓,豎穴土坑墓和豎井墓道土洞墓的數量為67 座,長斜坡墓道土洞墓為98 座。隨著從第一期到第五期的時間推移,67 座豎穴土坑墓和豎井墓道土洞墓分布在五個時期的數量分別為 1 座、22 座、20 座、10 座、2座,除開第一時期外(因為此時期平城人口比較少),這兩種類型的墓葬數量呈逐期減少的趨勢;98 座長斜坡墓道土洞墓分布在五個時期的數量分別為 2 座、11 座、39 座、31 座、6 座,這種類型的墓葬數量在逐期增加(第四期數量雖比第三期少,但總數依然可觀。第五期只有6 座,原因是首都南遷引起的人口減少)。
2.第二、三、四期時段內(398年-493年)的墓葬總數為134 座,明確為此階段的長斜坡墓道土洞墓和磚室墓共81 座,占此時期南郊北魏墓群數量的60%。更進一步來看,第三、四期時間段內(439-493年)的長斜坡墓道土洞墓總數為70 座,占第二、三、四期總數81 座的86%。這說明遷都平城后,隨著平城人口的增多,長斜坡墓道單室墓成為平城時代439年-493年五十五年間人們所采用的最主流的墓葬形制。
綜合上述分析,如果華宇二期壁畫墓確實為北魏墓葬的話,則它那種長斜坡墓道弧方形磚構單室墓的墓葬形制特點,就非常滿足平城時代主流墓葬形制——長斜坡墓道單室墓的形制要求,屬于平城時期北魏太延五年(439年)至太和十八年(493年)五十多年間的主流墓葬。進一步來說,由于長斜坡墓道磚構單室壁畫墓相對土洞墓來說,耗時更多,花費更大,更能體現墓主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那么華宇二期壁畫墓很可能是一座貴族墓。
三、壁畫人物服飾
華宇二期壁畫墓的年代歸屬問題,可以從其壁畫中人物服飾的時代特色來確定。從中國傳統的死亡觀念和喪葬禮儀來看,人們認為死亡后會去另一個世界,并為到達另一個世界準備了繁復的禮儀。漢代時,人們便在墓葬中創作大量圖像藝術作品,以表達墓主人到達的另一個世界的模樣。墓葬壁畫是眾多表現死后“理想家園”藝術作品中最直觀的圖像系統,既然它表現的是現實世界的模擬和美化,則壁畫中人物的服飾一定能透露墓主人生活的時代信息。
從華宇二期壁畫墓出土的壁畫內容來看,可以發現其人物服飾主要為典型的鮮卑人打扮。就人物服飾而言,鮮卑人的服飾特征主要由帽和服兩部分來體現。據呂一飛研究,河南國的“大頭長裙帽”、后周流行的“垂裙覆帶”式突騎帽都是鮮卑帽,其特點是帽的兩側及后背皆垂裙至肩,并以云岡石窟曇曜五窟中的第16 窟南壁門拱東側彌勒龕下供養人像所戴帽子為例,明確描述了鮮卑帽的具體樣貌(圖二)。將華宇二期壁畫墓中的人物帽飾(圖三)與之對比,可以發現這些男女人物頭上所戴帽子一模一樣,明若符契。作為華宇二期壁畫墓的中心人物,雖因壁畫漫漶不容易明察,但若仔細辨認,則墓主夫婦所戴胡帽與圖四中所示的男女帽飾完全一致。又據呂一飛援引王國維《胡服考》進行的考證,袴褶是受胡服影響而出現的“上衣下褲”服裝,其基本式樣是上裝為大袖或小袖的短身袍、衫,下身穿褲。這種式樣的服裝,尤在北魏官員和平民中受歡迎。考察華宇二期壁畫中的男性服裝,基本上都是這種“上衣下褲”式的袴褶裝扮。
4.1 保護資源的多樣性、完整性、真實性 對于自然資源及環境的保護,要以系統觀、整體觀的角度認知和實施。坎布拉園區的地質地貌、氣候、土壤、水文、生物等資源與環境要素構成了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對其保護首先是對其完整性進行保護。要保護構成整個園區自然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與自然過程,如自然豐富性、多樣性、動植物物種遺傳與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對于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資源在保存、修繕、利用的過程中,確定恰當的保護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護文化資源的真實性、完整性、可持續性。

圖二 云岡石窟第16 窟南壁門拱東側彌勒龕下供養人像

圖三 華宇二期壁畫墓之北壁人像
討論至此,可以明確知道:華宇二期墓葬壁畫中所見人物服飾屬于北魏鮮卑人打扮,它的墓葬形制屬于平城時期特定階段(439年-493)年的主流形制,其位置居于北魏平城時期傳統墓葬區。就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分布規律來看,486年建立明堂之后北魏南郊墓葬的北界進一步南移至今天明堂遺址以南的地方。華宇二期壁畫墓出土位置處于明堂遺址西南角,直線距離僅約1700 米,則華宇二期壁畫墓不太可能是486年后的產物,其墓主人可能是486年以前就埋葬于此,且也沒有遵守明堂、太廟禮儀性建筑對周邊不得葬墓或者遷移他處的約制。因此,可以初步得出關于此壁畫墓大致年代的結論:華宇二期壁畫墓很可能屬于北魏平城時期中太延五年(439年)至太和十年(486年)之間的產物。

圖四 華宇二期壁畫墓東壁中的飲酒器具

圖五 解興石堂后壁墓主人夫婦圖
四、壁畫所見名物
進一步來講,分析華宇二期壁畫墓中壁畫里所見名物,將它與大約同時期(439年至486年)大同出土的有紀年墓葬圖像中的名物進行比較,比較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可以最大程度地逼近華宇二期壁畫墓的實際年代。就華宇二期墓葬壁畫所見名物而言,其中有二種名物,最值得關注。
其一,為東壁中央所見柵狀曲足案幾上放置圓筒形酒樽的組合用具(圖四)。大同北朝藝術研究院收藏有一座名為“解興石堂”的石質文物,其石堂壁面上繪制有壁畫,石堂后壁為墓主人夫婦圖,石堂門楣上有“大□太安四年(458年)”的紀年(圖五)[8]。2008年5月,大同市南郊仝家灣發掘了10 座北魏墓葬,其中的M9 為唯一保存紀年文字和壁畫的墓葬[9],在墓葬甬道東壁靠近墓門處有朱色題記,題記中有“和平二年(461年)”紀年,其墓室北壁壁畫為墓主人夫婦。如圖五所示解興石堂后壁上,墓主夫婦面前各置一個柵狀曲足案幾,上放圓筒形酒樽,仆人正在拿杓舀酒。M9 墓室北壁墓主圖中,一個仆人也正在從類似組合用具中挹酒。除此之外,在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畫(圖六)、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槨壁畫(圖七)中也出現了同樣的飲酒器具。這種柵狀曲足案幾上放置圓筒形酒樽的組合用具,同華宇二期壁畫墓中的飲酒器具幾乎一模一樣,特別是智家堡棺板畫中的飲酒器具與華宇二期壁畫墓中的如出一轍。

圖六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畫中的飲酒器具
上述五種墓葬圖像資料中,基于解興石堂(458年)和 M9 壁畫墓(461年)屬于北魏文成帝時期太安和平年間(455-465年)遺物的實際情況,則其他三種圖像中所見的組合飲酒器具,一定是北魏文成帝時期廣泛流行于貴族間的日常用具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考慮到比較早期的沙嶺壁畫墓(435年)中沒有發現類似的用具圖像[10],較晚司馬金龍墓(484年)屏風漆畫中也沒有發現該類物品,則此類組合飲酒用具似乎是文成帝太安和平年間(455-465年)的流行用具,或者說這類飲酒用具是此時期十多年間流行在畫家創作圖畫作品過程中的一種風尚。

圖七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中的飲酒器具
大同北魏墓葬圖像系統中集中出現組合飲酒器具,反映了解興石堂、仝家灣北魏墓、華宇二期北魏壁畫墓、智家堡兩座北魏墓應該都屬于同一時代的墓葬文化,因為流行在眾多墓葬圖像系統中的飲酒器具作為一種時尚圖像,其創作者之間必定彼此熟悉甚至極可能是師門關系,他們必然是同時代的北魏工匠,即使彼此隔代,應該也不會太遙遠。
其二、為華宇二期壁畫墓中西壁邊框中所見的忍冬紋。這些忍冬紋以單葉形象出現,且彼此之間不連接。關于忍冬紋紋樣在北魏圖像系統所反映的時期早晚關系,《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認為,南郊墓群中M229 和M112 中單葉形象的忍冬紋在未連接而以并列形式出現時的情形,同云岡石窟第7、第8 窟前帶狀界紋紋飾、第19 窟、第18 窟脅侍佛背光紋飾一樣,都是單葉首尾相連或單葉并列而成的忍冬紋,在敦煌石窟北涼時期的紋樣中很常見,代表的時期應該是云岡石窟早期(460-465年)及中期(465-494年)初期。這種情況,在仝家灣北魏墓M9(461年)甬道東壁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其甬道東壁的忍冬紋單個排列,呈奔跑的小人樣,且彼此不相連接。將華宇二期壁畫墓西壁邊框中所見的忍冬紋樣與仝家灣中的進行比較,無論在排列方式、輪廓形狀,還是在繪圖風格上,兩者完全相似。如此看來,忍冬紋作為名物證據,又一次支撐了華宇二期壁畫墓和仝家灣北魏墓都是屬于文成帝太安和平年間(455-465年)的產物的觀點。
總而言之,綜合墓葬位置、墓葬形制和墓葬壁畫人物服飾的情況,可以推測華宇二期壁畫墓極大可能屬于北魏平城時期(398-493年)中太延五年至太和十年之間(439-486年年)的產物的遺跡。再進一步,綜合考慮壁畫中代表名物之飲酒器具與忍冬紋分布時期的情況,則華宇二期壁畫墓極有可能為北魏平城時期文成帝太安、和平年間(455-465年)的產物。
[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2期,13~25頁。
[2]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0期,25~49頁。
[4]王銀田、劉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文物》2001年第7期,40~51頁。
[5]劉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畫》,《文物》2004年第12期,35~47頁。
[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區田村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5期,4~18頁。
[7]張慶捷《大同南郊北魏墓考古新發現(A)》,《200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107頁。
[8]大同北朝藝術研究院編著《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圖錄—青銅器 陶瓷器 墓葬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灣北魏墓(M7、M9)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12期,4~22頁。
[10]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0期,4~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