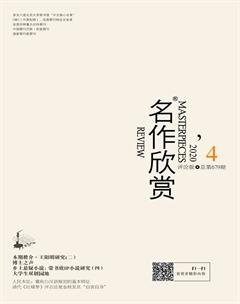試析扎米亞京在小說《洞穴》 中的隱喻
摘 要: 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作家扎米亞京作為冷靜獨立的“持不同政見者”,用看似荒誕的筆觸展現了俄羅斯 20世紀 20年代初知識分子艱難、矛盾的處境。本文以小說《洞穴》 中的隱喻作為切入點,揭開晦澀文字背后的深義,探討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異化與掙扎。
關鍵詞:扎米亞京 洞穴 隱喻 人性
一、序言:隱喻的特征與本質
俄羅斯作家扎米亞京的中短篇小說《洞穴》是一篇初讀覺得甚是隱晦的作品,原因在于這篇文章從標題到文中各處描寫都滲透了隱喻的表現手法,文字和形象在熟悉和陌生之間游離。
“隱喻最重要的語義特征包括:矛盾性、模糊性、不可窮盡性、系統性和方向性,等等”a。“矛盾性”只是隱喻的表象,從本質上說,“隱喻是以喻體和本體之間的相似性作為意義轉移的基礎的”b,所以隱喻的本質還是“相似性”。而語言中的隱喻必須放在語境的框架下才能理解,因此,我們必須結合“語境”尋找喻體、本體的“相似性”特征,才能揭開隱喻“矛盾性”“模糊性”的外衣,體會作者表達的原始訴求。
二、標題的隱喻:矛盾的匯聚點
《洞穴》講述了一對住在洞穴里的知識分子夫婦馬爾金和瑪莎在柴火告罄時忍受嚴寒的故事。丈夫馬爾金為了能在妻子命名日那天有柴燒,在激烈的內心斗爭后,昧著良心偷了鄰居奧別爾德紹夫家的幾塊木柴。鄰居發現后告發了馬爾金,居委會主席謝利霍夫上門催其還柴。馬爾金在良心和恐懼的折磨下,準備服毒自殺;更可悲的是,妻子竟然向丈夫乞求這唯一的毒藥,仿佛死亡是解脫的天堂。
這篇小說寫于1920年(發表于1921年),十月革命后的俄羅斯正經歷“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下的物資匱乏。很顯然,作者借“石器時代”的荒涼影射當時彼得堡人民困窘的生活。為何使用隱喻?原因有二:一是語言上的創新,將熟悉的話題陌生化,更好地傳達所談事物的特征。“石器時代”與現代文明形成強烈的對比,暗指人民過著近乎原始的貧困生活。使用“隱喻”的第二個原因是當時俄羅斯嚴格的書刊檢查制度,迫使作者只能借古諷今,虛實相間。
談到創作背景,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作家葉甫蓋尼·伊萬諾維奇·扎米亞京(1884—1937)。他的一生充滿悲劇色彩, 始終是“持不同政見者”。在俄羅斯帝國時期,他參加學生革命活動,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多次被逮捕、流放,其作品被禁。而在十月革命之后, 他對布爾什維克當局的政策毫不留情地指責,并退出布爾什維克黨。1921年(一說是1920年),他創作了20世紀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我們》。1927年該小說在布拉格出版之后,蘇聯當局剝奪了扎米亞京寫作和出版的權利。1932年他流亡法國,1937年客死巴黎。扎米亞京是白銀時代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以諷刺、荒誕聞名,作品多針砭時弊,充滿了對人、對革命、對俄羅斯的深深憂慮。他提倡走“阻力最大的路”c,堅持自由獨立的思考。
小說的時間、空間背景很模糊。通過“幾個世紀以前彼得堡曾在這里”d,可推出故事發生在彼得堡,通過“電燈”“熨斗”“鋼琴”,得知是在現代社會。但標題的“洞穴”,開頭的“冰川,猛瑪,荒原”,還有“渾身纏滿獸皮、大衣、被單和破衣爛衫的穴居人”,這些描述給人一種強烈的時空錯位感,把讀者拉回到遙遠的“石器時代”,拉到荒涼的洞穴中。
我們來看看“洞穴”這個標題的隱喻形成機制。萊考夫認為,“隱喻意義是源域事物的部分特征向目的域映射的結果”e“在理解過程中,源領域事物的特征向目標領域轉移”。f那么,“洞穴”這個源領域的概念有哪些特征?
在基本含義上,“洞穴”直接指向“石器時代”的時間背景,這一點前面創作背景已經分析過了,是對當時社會貧困生活的影射。
在外在特征上,文中對“洞穴”的描述有:“黑暗的洞穴”“洞穴的黑乎乎的拱頂顫動著”“昏暗的結著薄冰的窄道”“呈拱形的天花板漸漸下沉,壓扁了椅子,寫字臺……”“書房的地板是一塊冰”“……巨大的、死寂的洞穴”“冰冷的穿堂風”,通過這些描述可以總結出“洞穴”的特征:狹窄,封閉,黑暗,寒冷,令人壓抑,給人帶來一種恐懼和絕望的情緒。
在文化內涵上,小說中把“洞穴”比作“諾亞方舟”,賦予其深刻的文化意義。“在洞穴的彼得堡的臥室里,就好像不久前在諾亞方舟上一樣:各種潔物和不潔物被洪水的激流沖得七零八落”。在《圣經》故事中,大洪水是人類面臨的滅頂災難,而諾亞方舟是人類唯一的避難所。在這篇小說中,穴居人也只能“從一個洞穴退往另一個洞穴。……再也無處可退了”。這里的“洪水”可以理解為當時俄羅斯混亂的內戰局面,也可以理解為十月革命帶來的動蕩。“洞穴”是人們最后的希望和避難所。
這就形成了“洞穴”隱喻含義的第一重矛盾:漆黑、壓抑、寒冷的洞穴讓人感到恐懼和絕望;而“諾亞方舟” 的洞穴又是人們最后的避難所。這是作者對于動蕩時代的復雜情緒,既恐懼,又懷有一絲希望;這也是作者對于十月革命辯證的態度,曾為革命進過監獄,卻在革命成功后抱以懷疑和指責,從不盲從,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另外,“洞穴”的符號學含義也很豐富。一本《符號詞典》 中寫道:“洞穴是宇宙的象征,它是世界的中心,是神與人相遇的地方,因為所有死去的神和救世主都在洞穴里復活。……洞穴既是安葬逝者的地方,也是隱藏秘密的地方,既是人類起源的地方,也是人死后埋葬的地方。”g
另一本《符號詞典》中也有相似的闡述:“洞穴是避難所,象征娘胎,象征生命的誕生與重生。但它也有消極的象征意義——陰間,通往地獄的入口;心理學認為它象征被壓抑的潛意識。……基督教認為洞穴是精神之源,因圣人耶穌就誕生于洞穴內的牲口槽里。……在民間神話中,洞穴經常象征不太高尚的事物,比如阿拉丁正是在洞穴里發現了寶藏,而寶藏被惡龍和狡詐的妖魔守護。”h
這是“洞穴”隱喻含義的第二重矛盾:“洞穴”既象征新生,也象征死亡;既指向美好,也通往陰暗——它是善與惡的交匯點,是矛盾的爆發點。標題含義里的雙重矛盾與后文主人公馬爾金的人格分裂(人性與獸性的斗爭)形成呼應,這種矛盾對立的氛圍也貫穿了整篇小說。
三、洞穴中事物的隱喻:對立的意象群
整篇小說都籠罩在龐大的隱喻敘事手法之下。而且,文中許多意象都體現了標題中隱含的矛盾對立。
(一)洞穴中最核心的意象——鐵爐
文中第一次這樣描述它:“占據這個宇宙中心的是上帝——矮腳、銹紅色、敦實、貪婪的洞穴之神:鐵爐。”在這次提及“鐵爐”一詞后,后面再未出現該詞,而是將其神化,稱它為“上帝”“鐵的上帝”“洞穴之神”。的確,鐵爐從外形上讓人聯想到俄羅斯多神教的神;另外,“火”在東斯拉夫民族的傳統信仰中是崇拜自然力量的象征。在俄羅斯多神教中,“灶神”是家庭最重要的守護神,它維護房子的溫暖和家庭的平安。可見,鐵爐對于穴居人的生活十分重要。
小說中的鐵爐有兩副面孔:燃燒和熄滅,分別展現為“慈悲”的和“漠然”兩種形態。而它的燃燒狀況與主人公的情緒、與故事情節的發展密切相關,可以說是情節發展的暗線(明線是時間的推移)。
第一次燃燒:當故事開頭剛燒起爐子時,“上帝呼哧呼哧作響”,這時,馬爾金和瑪莎“虔敬地、肅默地、充滿感激地把手伸向它。有那么一刻,洞穴里仿佛是春天,這一刻仿佛可以脫下獸皮,去掉鐵爪、獠牙,甚至纖弱的思想的綠莖也突破凍僵的大腦的硬殼鉆了出來”。這里“纖弱的思想的綠莖”指二人在爐火的溫暖下,變成重新能思考會說話的人,而不是之前凍僵的沉默不語的、披著“獸皮”、長著“鐵爪,獠牙”的恐怖面目。精神的重生依賴爐火的溫暖,令人深思。
第一次熄滅:“洞穴之神漸漸安靜、縮攏起來,無聲無息了,只是偶爾發出一點點輕微的噼啪聲”,此時馬爾金聽到樓下的鄰居奧別爾德紹夫家劈木柴,他出現了第一次人格分裂,憂心木柴的事。于是他借口去樓下接水,找鄰居借木柴。第一次的爐火熄滅暗示了悲劇的開端。沒有爐火,沒有溫暖,就沒有出路。
第二次燃燒:由于馬爾金偷來了劈柴,29日白天再次燃起爐火。“洞穴之神的肚子一大早就塞得滿滿的,大發慈悲地呼呼作響”,馬爾金和瑪莎終于可以輕松、愉悅地回憶往昔美好的時光。爐火重新點燃了夫妻倆的幸福感。
第二次熄滅:29日傍晚,居委會主席謝利霍夫突然造訪,詢問劈柴的事。馬爾金知道事情敗露,受到良心和恐懼的折磨,在迷茫中“把最后幾根劈柴扔進火爐”“毫無道理地碰到了茶壺、小鍋”,水潑到爐子里,“洞穴之神發出毒蛇般的咝咝聲”。這次熄滅,是悲劇的徹底降臨,短暫的幸福泡沫已破滅,主人公不得不面對慘白的現實。
第三次燃燒:馬爾金“重新生起了火”,但燒的不再是劈柴,而是他們以前的信札,燒的是以前美好生活的回憶。“鐵神慈善地呼哧著,貪婪地吞食著……信箋”“鐵爐漠然吞噬著……話語”。這次燃燒如同回光返照一般慘烈。馬爾金向妻子坦白了偷柴的事實,大呼:“我全燒了——全部!我不是說劈柴!”他想說的或許是,他燒掉的還有知識分子的良知,燒掉的是對生活的信念和希望。但鐵爐始終都只保持漠然,毫無憐憫之心,“鐵神冷漠地打著鼾”。
結合鐵爐的符號學文化內涵,以及它作為第二線索的結構功能,我們可以認為:鐵爐象征人類最基本的物質需求,當它得到滿足時,人們感到溫暖和幸福,其精神世界獲得重生;而當它得不到滿足時,人們陷入恐慌和絕望,甚至丟棄精神上的寄托(信札),甚至放棄生命(藍瓶子的毒藥)。
(二)一組對立的意象群:物質與精神
除了上文提到的鐵爐,文中還有一系列象征物質生活的意象:石斧、獸皮、木柴、陶片一般的小餅、五個雪白的土豆、真正的茶葉;這些物品與穴居人的起居生活密切相關,都屬于實用的、與物質生活相關的事物。
文中與之相對立的象征精神生活的意象有:書籍、斯克里亞賓的74號作品、信箋,還有瑪莎回憶中的鋼琴、木馬形狀的煙灰缸、睿智的月亮、神奇的流浪琴師,這些代表了這對知識分子夫婦曾經擁有的幸福生活,都屬于浪漫主義的,與精神生活相關的事物。
這些代表物質生活的事物是主人公夫婦生活的基本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木柴”,故事的發展脈絡和木柴息息相關:缺少木柴時,夫婦二人凍得蜷縮成一團;偷到木柴后,夫婦二人才得以回憶過去與精神生活相關的浪漫情景。
除了這兩組具體事物的隱喻,還有一組“上—下”的方位也分別象征了精神和物質。小說中把馬爾金和奧別爾德紹夫安排成樓上、樓下的鄰居,而不是同一樓層的鄰居,這是為什么呢?這種別有用心的安排是因為“上”象征著上層的精神生活,馬爾金一家是上層知識分子,更加注重精神層面的生活;“下”象征著下層的物質生活,奧別爾德紹夫一家粗魯自私,注重追求物質生活。而物質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礎,當物質生活得不到保障,精神世界也將崩塌,整個生活都將陷入絕境。所以,小說的末尾,馬爾金坦白了偷木柴的罪行——踐踏了良心準則;燒掉了信箋——拋棄了詩情畫意;甚至拿出了藍色的毒藥瓶——徹底放棄生命。
這種“上—下”的象征意義在文中其他地方也有體現。比如,“在這種日子里你只要仰頭向上看,只要不看見腳下的土地——你甚至可以相信,還是快樂的日子,還是夏天”“如果仰起頭聽那聲音——那太像從前的聲音”。在這些文字中,“仰頭向上”指回想過去的美好記憶,用精神的力量支撐自己;“腳下的土地”指困窘的物質生活現狀。
四、穴居人形象的隱喻:扭曲的人性
(一)知識分子馬爾金和瑪莎
小說主人公馬爾金和他的妻子瑪莎都是知識分子,這從他們房間里的書籍、斯克里亞賓74號作品、鋼琴、信札等物件可以看出來。而且,他的鄰居對其稱呼名字加父稱,這是很尊敬的稱呼方式;居委會主席稱他為“先生”,稱瑪莎為“夫人”,可見二人社會地位較高。但是他們在物質生活上極為貧困,連妻子過命名日都沒有柴燒,他們只能懷念過去無憂無慮的生活。
主人公馬爾金的肖像描寫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隱喻是“黏土”,比如,當他騙瑪莎家里還有很多柴時,“他的臉皺皺巴巴,呈黏土色”;當他聽見鄰居在樓下劈柴時,他分裂成兩片,“其中的一片正黏乎乎地向瑪莎微笑”;當他在通過鄰居家堆滿柴垛的窄道間穿過時,“黏土的馬爾金·馬爾金內奇的一側身子撞在了木柴上,碰得生疼——泥身上癟進一個深深的凹痕”;在居委會主席謝利霍夫離開之前,“馬爾金·馬爾金內奇黏土臉微笑著”;在謝利霍夫離開之后,“渾身土色,冰冷,盲人一般,馬爾金·馬爾金內奇不時麻木地撞到洞穴里被洪水沖得七零八落的東西上”;當瑪莎斥責他笨手笨腳弄潑茶壺,澆熄爐火時,“只是黏土上由于某些話,由于衣柜、椅子、寫字臺的硬角不斷磕出的凹痕,在隱隱作痛”。
“黏土”有哪些特征?枯黃,柔軟,可塑性強。用這個詞來形容人,仿佛看到一個臉色蒼白、表情呆滯、毫無生氣的人;這團“黏土”還很容易碰撞到硬物上,表明馬爾金很容易受到心靈的傷害,每次受到打擊后,內心都會留下深深的傷痕。
有意思的是,當馬爾金撞在硬物上時,兩次出現了一只到處亂撞的小鳥。這只小鳥并不是真實出現的鳥,而是慌亂茫然的馬爾金的化身。比如,當瑪莎請求明天生火,他聽到樓下劈柴的聲音時,他分裂成兩片,一片化作“黏土”,“而他的另一片,卻好像從自由自在的天地中飛進房間的一只小鳥,糊里糊涂,到處亂撞,碰到天花板、玻璃窗、墻壁:‘上哪兒去找劈柴——上哪兒去找劈柴”。這只茫然無助的小鳥就是馬爾金自己,他知道家中已無劈柴,而他就是撞破天花板也找不到明天的出路。第二次小鳥出現,是當馬爾金準備向鄰居借柴時,“一只飛進來的小鳥簌簌地撲扇起翅膀,時而向右,時而向左——突然,它絕望了,用盡全力向墻上撞去”。這其實是暗指馬爾金內心的走投無路,小鳥的絕望象征了他的絕望。
馬爾金在文中出現了三次人格分裂,與前文分析的標題“洞穴”的矛盾含義形成呼應。
第一次人格分裂上文已分析,是在他第一次聽到樓下劈柴的聲音時,他裂成兩片,一片變成“黏土”,對著妻子微笑,隱瞞木柴告罄的事實;另一片變成到處亂撞的“小鳥”,尋找木柴。“黏土”和“小鳥”都是馬爾金茫然無助的內心寫照。面對瑪莎的請求和生活的困境,他一面用善意的謊言欺騙妻子,一面絕望地尋找出路。這是謊言與真實的斗爭。
第二次人格分裂。當馬爾金在鄰居家的窄道門外時,他猶豫是否要偷木柴,“兩個馬爾金·馬爾金內奇進行著殊死的搏斗:那個從前的,懂得斯克里亞賓斯克的馬爾金·馬爾金內奇知道不能這樣,而另一個新的,穴居的馬爾金·馬爾金內奇知道必須這樣。穴居的那個把牙齒咬得咯吱吱響,把對手壓在身下,掐死了……像頭野獸一躥一跳地大步往樓上跑”。這里分裂的兩半,一半是善良的、知羞恥的知識分子,拒絕偷柴;另一半是穴居人馬爾金,被困窘的生活異化成了“野獸”,為了滿足保暖的基本需求,不顧廉恥地偷柴并逃跑。這是生活壓迫之下的人性扭曲,也是小說悲劇的根源。這是人性與獸性的斗爭。
第三次人格分裂。當鄰居發現丟了劈柴,回來奔跑大喊時,“被劈成兩半的馬爾金·馬爾金內奇一半兒身子看見了永恒的流浪琴師,永恒的木馬,永恒的冰塊,而另一半,——時斷時續地呼吸——和奧別爾德紹夫一起數著劈柴”。一半的馬爾金留在和妻子過去的美好回憶中;另一半的他跟鄰居一起清點劈柴,面對現實的絕境。這時鄰居還沒有上門問罪,但馬爾金已經備受良心的折磨,知道這是遲早都要面臨的現實審判。這是過去與現在的斗爭。
每一次人格分裂都是馬爾金激烈心理斗爭的產物,他的內心分裂成兩個人:一個是生活在過去的文明人,一個是生活在現在的野蠻人。在第二次人格分裂中,表面上是野蠻人打敗了文明人,但在他內心深處,仍然深受良心的折磨,最終他的選擇了人性,選擇用死亡來結束這卑鄙、卑微的穴居生活。
同樣作為知識分子,女主人公瑪莎在文中的肖像描寫有:“看起來像掛在光禿禿的樹上搖搖晃晃的最后一片枯葉”“還有床上的瑪莎——她躺在床上,好像平平地鋪著的一張紙”“被壓扁了的、紙一般的瑪莎在床上笑著”。枯葉和扁平的紙人不僅指瑪莎在外形上消瘦虛弱,也暗指她的內心對生活失去了希望,跟馬爾金一樣,被貧困壓迫得沒有一絲生機。
(二)暴發戶奧別爾德紹夫
奧別爾德紹夫(Обертышев)i這個姓氏可以拆成“貪財敲詐者”(берун)和“騙子”(обирала)這兩個詞。姓氏中的隱喻暗指他是一個狡猾、貪婪、吝嗇的人,由此可推測,他的劈柴(財富)來路也未必干凈。再結合他粗魯的外貌(“很久沒有刮過胡子”)和粗鄙的言辭(比如,勸馬爾金“書很好燒”),我們可以推斷出,他代表著那個年代的暴發戶:沒有什么文化,但物質生活過得不錯。
除了姓氏的隱喻,他的肖像描寫也有很多隱喻,比如,“呲著他的石頭牙,微笑著”“從雜草中鉆出一堆黃色的、石頭般的牙齒;而石縫中擠出一條一閃即逝的蜥蜴尾巴——微笑”。不難發現,馬爾金的肖像描寫的核心隱喻是“黏土”,而奧別爾德紹夫的核心隱喻是“石頭”,這也是一組鮮明的對比。
石頭有什么特點?堅硬,冷冰冰,武器。所以,他的性格特點與馬爾金截然相反。他強壯,冷漠,時刻用武器一般的“石牙”保護自己,拒絕別人。比如,當馬爾金委婉地向他借柴時,“雜草叢中露出了黃色的石牙。黃牙從眼睛里伸出,奧別爾德紹夫全身長出了黃牙,越長越長”。如此猙獰的描寫讓人毛骨悚然,給人一種野獸般兇猛殘忍的感覺。在他拒絕借柴給馬爾金之后,他“伸出他那蜥蜴般靈巧的手急速一握”,可見他的狡黠與冷漠。
有意思的是, 當作者描述到奧別爾德紹夫的妻子時,用了“母的”(самка)這個用來形容雌性動物的詞,暗指他們一家人都接近于獸類,具有相當高的獸性,對他人存有極強的防備心,并漠視他人的苦難。
(三)革命政府代表謝利霍夫
居委會主席謝利霍夫(Селихов)這個姓氏的詞根意為“村落遺址”(селище)、“村落”(село),他在文中可以理解為革命政府的官方代表。俄國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無產階級形成歷史較短,成分較復雜,其中有不少人來自于農村,這個姓氏暗示了革命政府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農民出身。
對謝利霍夫的肖像描寫有:“早年他曾有六普特重,如今只剩下一半了,在夾克外套里晃晃蕩蕩,好像嵌在響鈴里的核桃”“謝利霍夫穿好套靴、裘皮大衣,活像一頭猛犸”。一方面,謝利霍夫和馬爾金一家人相像,都瘦弱單薄,喜歡喝酒卻只能用霍夫曼滴劑做酒精,可見他的物質條件也不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和奧別爾德紹夫有相似之處,因為“猛犸”是獸性的體現(文章結尾描寫奧別爾德紹夫來討柴時,“響起了一個最強悍的猛犸的沉重、均勻的腳步聲”)。他前來問責讓馬爾金感到極度的恐懼,因此,他也是導致悲劇的劊子手之一。
謝利霍夫尊敬地稱馬爾金為“我的先生”,稱瑪莎為“夫人”,稱奧別爾德紹夫為“卑鄙的虱子”(憑此可推測,奧別爾德紹夫確非正派之人),可見這位官方代表仍保持對知識分子夫妻的尊重,對卑鄙、粗鄙的奧別爾德紹夫的不屑;但落到具體事務上,他“還是得去刑事科”,并建議馬爾金“用那些劈柴堵上他的嘴”。他只能按章辦事,于馬爾金的困境毫無益處,從根本上說仍然是冷漠的、無情的穴居野獸之一。
五、隱喻的背后:人性與獸性的斗爭
我們首先分析了“洞穴”的標題隱喻,然后研究了文中的事物隱喻和人物隱喻,最后來探討一下作者的創作意圖。
作者扎米亞京曾在《在后臺》一文中回憶起自己創作《洞穴》的起因:“1919年,冬天,夜班,在室外。跟我一同值班的同事,一位凍餓交加的教授,抱怨自己的身體狀況:‘哪怕只是偷點劈柴呢!可最痛苦的是我辦不到,即使去死,我也不會去偷。第二天,我坐下來寫小說《洞穴》。”j
這個生活片段是作者動筆的直接導火索,但他并沒有將其平鋪直敘地寫出來,而是將同事心中剎那的“惡念”落到現實中,放到石器時代的隱喻背景之中,以穴居人來隱喻生活在彼得堡的幾類人,讓“獸性”與“人性”進行激烈的斗爭。“獸性”在每個穴居人身上都有所體現,這是他們在寒冷的洞穴里的自我保衛機制。區別只在于,有些人任何時候都體現出獸性(奧別爾德紹夫),有些人偶爾體現出獸性(馬爾金、謝利霍夫),第二種人在良心上就會受到折磨(馬爾金因偷柴而恐懼、自責),并被迫走入絕境(馬爾金拿出毒藥準備自殺)。
偷柴雖犯法,但罪不至死。馬爾金和瑪莎想自殺不僅僅因為偷了幾塊柴;馬爾金說:“我全燒了!”他把自己的良心、對過去的回憶、對生活的希望全燒了,他對這樣貧困、冷酷的生活毫不留戀了。瑪莎也是如此,所以她向丈夫乞求毒藥:“你可憐我……要是你還愛我……”在那樣殘酷的時代,仿佛死去才是保持體面和尊嚴的唯一途徑。
《洞穴》不僅是對十月革命后知識分子們過的挨凍絕望生活的諷喻,更表達了作家對社會大轉折時期個人選擇的深刻思考——人性與獸性的斗爭。扎米亞京以荒誕的風格、隱喻的手法,控訴了一個讓人性扭曲的復雜時代,彰顯了獨立知識分子高傲的靈魂。
需要指出的是,扎米亞京之前是極為向往革命的,但是他后來對十月革命后俄國的現狀很不滿,也不是完全否認革命,只是對其持一種懷疑的態度。因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事實上并沒有給當時的人民帶來幸福的生活(這與俄羅斯當時的國內戰爭也有關系)。相反,十月革命后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一定程度上奪去了知識分子們曾經富足體面的生活,而給了某些卑鄙小人投機發財的機會,社會公平在某種程度上并未得到完全的體現。總之,作者寫下小說《洞穴》,表達了對于人性在革命轉折時期遇到的嚴峻考驗的深刻思考。
ab束定芳:《論隱喻的本質及語義特征》,《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第10頁,第14頁。
c 李雪梅:《扎米亞京〈縣城三部曲〉的時空體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2007》。
d〔俄〕 扎米亞京:《洞穴》,黃玫譯,周啟超主編:《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文出處同此,不再注明。
ef束定芳:《隱喻學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第133頁。
g Керлот Хуан Эдуардо. Словарь символов /Переводчик: Данько Ю. А., Богун Н. А., Козунина С. Г.,Курганский В. А. – М. : Рефл-бук, 1994. – 608с.
h Джек Тресиддер. Словарь символов – М. : Фаир-Пресс, 1999.
i Замятин Е. И. , Пещера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Т.1 Уездное – М.: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03.
j〔俄〕 符·阿格諾索夫:《20世紀俄羅斯文學》,凌建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頁。
作 者: 陳汝嵐,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專業2010級學士,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語言學2014級碩士(公費獎學金),曾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擔任過一年半的俄語教師,目前為自由譯員。
編 輯: 張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