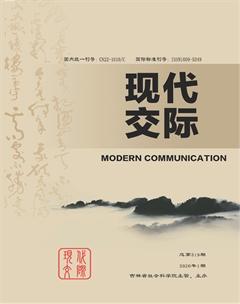理性選擇視角的農村養老保險參保意愿研究
鄭愛云
摘要:以理性選擇理論為視角,對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參保意愿進行分析研究,同時提出相關的建議措施。“理性經濟人”假設是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首先提出如今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存在的問題,后又基于這一“理性經濟人”假設,分析了農民在選擇投保與選擇何種投保檔次中的策略選擇,并進行了深層次的原因分析,最后又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角度提出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路徑。
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理性選擇 理論參保 選擇路徑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1-0063-03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針對農村情況特別的老人一直有救濟的政策,比如“五保戶”政策,但1986年之前一直都沒有針對全體農民的養老保障政策。1986年,開始以縣為單位進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由于問題太多,工作被迫終止;2002年,開始實行“新農保”政策,區別于城鎮的“城居保”,農村與城鎮依然實行雙軌制;2014年,為了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便將“新農保”與“城居保”兩個系統合并為“城鄉居民保”一個系統,該制度的實行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如何吸引農民提高參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投保檔次,以及如何完善這一制度依然是學者們討論的問題。
一、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和問題
自1986年的“老農保”出現一系列問題后,一直到2002年都沒有開展新的農保工作,直到2002年“新農保”出臺,國家又開始將農村的養老保險工作提上日程。2011年開啟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2012年全面覆蓋,參保對象針對城鎮中年滿16—60周歲的非從業居民,主要是為了解決城鎮中非從業人員的養老問題。“城居保制度”與“新農保制度”非常相似,有的學者提出設置兩個機構管理容易造成人力物力財力上的浪費。2014年為了建設城鄉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務院提出將“新農保制度”與“城居保制度”并軌實施,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簡稱“城鄉民居保”。
“城鄉居民保”與之前的“新農保制度”相比有進步之處,但也面臨著與“新農保”同樣的問題,比如制度合法性較弱、制度規則設置不完善和農民參保檔次低等,其中農民的參保檔次是較為突出的問題。因為在這背后存在著很多復雜的原因。不管是“老農保”“新農保”還是“城鄉居民保”,都設置了不同的繳費檔次,多繳多補貼,長繳獲益高,但是農民的反應并不強烈,選擇最低檔次的居多。據云南省有關統計,云南省農民參與“城鄉居民保”最低繳費檔次100元的居民占到總參保人數的90%;參與200—500元繳費檔次的也不過9%;參與600—1000元繳費檔次的人僅僅占到參保總人數的0.6%;參與1500—2000元繳費檔次的幾乎沒有,僅僅占參保總人數的0.05%。總體來看,參保人數看起來雖多,但是繳費水平太低。由此可見,政府建立的繳費激勵機制形同虛設,一定程度上激勵了參保行為,但并沒有起到激勵農民多繳、長繳的目的,農民的觀念依然需要轉變,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仍然較低。
二、理性選擇理論對農民參保意愿問題分析
(一)農民選擇投保行為的“理性”分析
農民選擇是否投保受到其參保成本與參保收益的影響。各種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都假設個體是政治過程的主角,個體都是理性的,都為了個人效用行動。農民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受益人,不管制度如何演變,農民都是這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存在。農民是這項制度存在的意義所在,是這項制度的主要受惠者與參與者,因此農民作為“理性人”在選擇是否參保的行為過程中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
從已有的研究結果和對文獻資料分析可知,在“老農保”時期,農民參保積極性不高,主要是因為當時農民老考慮到養老金的給付水平無法滿足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1992年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剛剛試行時,大部分農民選擇每月2元的最低投保檔次,按照當時民政部的計算方法和標準,15年后僅僅能領取9.9元/月的養老金,根本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時農民對這一制度了解的信息并不全面,又受以家庭養老為主的傳統養老觀念影響,農民參保時只會在他可預見的范圍內計算收益,而不會考慮長遠收益。同時,由于大多數農民的投資消費意愿不強烈,也沒有應對風險的能力,往往會選擇以現金的形式持有財富,以投資獲益的方式并沒有深入到廣大農民中,所以農民的參保意愿也不強。
(二)“理性”農民對投保檔次的選擇策略
農民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參與者。根據理性選擇理論,農民會根據自己的利益權衡選擇參保檔次。農民選擇參保檔次的考慮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資金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權衡,比如各個繳費檔次的補貼率、個人賬戶積累額中個人繳費和繳費補貼貢獻比率、個人繳費投入的收回時間點等,都是農民權衡的因素;二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化解風險的能力與其他方式(如商業養老、家庭養老)的比較。由此能夠看出,農民會用自己有限的知識和認知作出最優決策,同時也會影響政府未來的決策選擇。農民對于投保檔次的選擇有兩個:提高與不提高。同時農民關注微觀上實惠的目標,農民選擇較低繳費檔次并不完全是因為農民繳費能力弱,而是因為農民產生了依賴政府財政補貼的養老思想。
三、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路徑
(一)加強制度的法律保障并完善有關制度
1.中央立法先行
立法的功能是建章立制。“無規矩不成方圓”,國家立法就在于為國家和社會訂立一套章程和規矩,讓國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這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和途徑相符合,法制化是社會保障的必經之路。國家應當加強針對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立法工作,從而推動城鄉統一社會保障工作的進行。盡管地方政府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這種責任也是在國家的統一規制和目標下進行的。地方能根據國家的統一目標依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設置相應的行政法規,但也會導致各地模式不盡相同,很難使社會保障走向成熟。因此,國家應該堅持中央主導,立法先行,使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律依靠,加強其政治合法性。
2.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激勵機制
(1)適當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
基礎養老金標準的提高可以增強制度對農民的吸引力,同時可以將基礎養老金的調整機制與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掛鉤,這樣也可以使農民從主觀上提升對制度的滿意度,從而增加政治信任。
(2)適當提高最低繳費檔次
現行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最低繳費檔次為100元,如果繳夠15年,個人賬戶積累2490.39元。如果提高最低繳費檔次至200元,繳夠15年,個人賬戶積累將翻倍。同時,最低繳費檔次標準的調整可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同步,不宜每年調整。另外,可以建立強制參保機制,這也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重要區別。強制參保可以讓一部分有繳費能力但是不愿意參保的人選擇最低繳費檔次,體現社會保險制度強制性的同時也能起到擴大社會福利的作用。
(3)調整補貼方式,逐步建立按相同補貼率給予補貼的機制
目前大多數省份為了鼓勵農民“多繳”采取分檔遞進補貼,但是每進一檔每人每年遞增五元或十元的幅度確實沒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也有失公平。應該采取按照補貼率分檔進補或者逐步按照相同的補貼率對個人繳費進行補貼。考慮到財政補貼的壓力,可以將最低繳費檔次的補貼適當降低,在最低繳費補貼率降低的基礎上實行按補貼率進行分檔進補,或者實行相同的補貼率,更加體現養老保險的普惠性與公平性。
(二)強化農民與基層組織的依賴關系——服從與信任
1.強化農民對基層組織的依賴關系
由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對象是農村居民和未從業的城鎮居民,并且農村居民占的份額較大,因此,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推行關鍵在農村,在農村推行城鄉居民保制度關鍵在于農民對基層組織領導人的服從和信任程度。如今的村集體活動大大減少,也只有村委會選舉時村民才會集體活動,并且很多在外務工或上學的年輕人都不會參與。村莊公共集體活動減少,就意味著村莊公共空間減少,農民對村莊公共服務事業也比較冷漠。對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重視程度也隨之減弱,對村莊領導人宣傳的各種政策也毫不關心。因此,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與基層組織的互動關系。首先,基層組織的領導人要深入農民群眾。很多村組織領導人往往也都是農民,官本位的傳統思想仍然很重,都要擺一擺官架子,服務人民意識差,農民對村組織的信任和依賴也相應減少。其次,農民要增強自己的權利意識。農民應該增強權利意識,加強對村組織的監督,促使村組織增強服務意識和能力。
2.發展村莊集體經濟并增強自主治理能力
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之所以在農村的施行一直不理想,也與村莊集體經濟的沒落有關,“集體補助”一直都是空話。因此,鄉村要抓住鄉村振興的機遇,大力發展鄉村集體經濟。首先,完善村級民主自治機制,界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其次,規范整合公共政策資源,提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效能;最后,重視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領導,基層鄉鎮政府應該與村干部集體針對村內的優勢和劣勢,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出路,真正讓農村集體經濟“活”起來,而不再是一個空殼。
總之,雖然隨著城市化的推進,鄉村社會的結構與過去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是仍然還是一個俗人社會,他們仍然為生計而奔波,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經濟問題。要想讓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真正得到農民的認可和信任,讓農民自愿參保并自愿提高參保檔次,就要讓農民看到這項制度能夠為他們帶來多大的利益。當然,在農村要想保證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行,強制農民參保、強制農民服從,也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要以自愿參保為主、強制參保為輔。
四、結語
從理性選擇的角度對農民參保問題進行研究為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將行為主體視為“理性經濟人”。農民作為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受益者和參與者,理所當然會對自己的投保行為進行理性行為分析,農民的參保意愿和選擇策略必然會受其影響。農民的參保率和投保檔次的高低不僅與農民的“理性行為”有關,還與政府的相關政策及其態度有關,政府完善相關制度與法律將會提高農民對政策的信任度。農村養老保險工作的推行關鍵在于基層領導干部尤其是村干部的工作態度與方法,盡管鄉村社會隨著城市化的推進結構發生了改變,但是農村的老人依然還留在那里,鄉村社會還算半個“熟人社會”,政策的推行有時還是需要以人際關系為主的社會資本的推動。
參考文獻:
[1] B.蓋伊·彼得斯.政治科學中的制度理論新制度主義[M].3版.王向民,段紅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于建華,薛興利,畢紅霞,等.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進化博弈分析:基于政府與農民的視角[J].農村經濟,2014(2).
[3]王立國.基于社會公正視角的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2).
[4]董磊明.村莊公共空間的萎縮與拓展[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5).
[5]張敬一,趙新亞.農村養老保障政策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6]張娜.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城鄉居保農村居民的籌資能力分析:以廣西兩縣為例[J].經濟與社會發展,2018(4).
[7]曹愛軍.現代化進程中民生發展的政治邏輯[J].社會科學戰線,2018(1).
責任編輯:張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