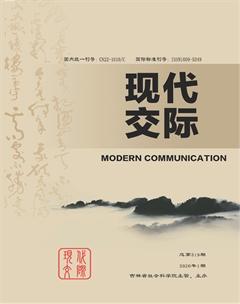《同名人》中黑人女性角色的“他者”地位
王立杰
摘要:裘帕·拉希莉是美國當代著名的印度裔女作家。憑借首部作品《疾病解說者》于2000年獲得普利策文學獎。她的首部長篇小說《同名人》成功地描述了二代移民家庭在異國他鄉居無定所的飄零感,以及無法找尋身份認同的疼痛感。其中三位女性主人公在面臨婚姻等人生重大抉擇時,更加顯露出黑人女性的雙重“他者”地位。運用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來解讀《同名人》中的男女關系和兩性地位,并探究黑人女性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根源。
關鍵詞:《同名人》 女性角色 后殖民女性主義 他者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1-0117-02
《同名人》是裘帕·拉希莉歷時三年精心打造的首部長篇小說,小說中所表達的移民群體在異國他鄉所要承受的飄零感及疼痛感,真實深刻地反映出移民家庭的生活狀況,引起人們共鳴。《同名人》不但引起了美國主流文化對印裔文學的興趣和關注,在美國文學屆獲得了一致好評,而且使印裔文學家引起美國主流社會的關注,開啟了第三世界的印度裔移民尤其是處于“他者”地位的女性群體對白人主流文化的反擊。
一、《同名人》及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介紹
生活在印裔移民家庭中,從小接受印美文化雙重教育的切身經歷,為拉希莉的寫作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小說《同名人》講述的是成功實現“美國夢”的印度移民艾修克與新婚妻子阿西瑪遠離故土來到美國開啟新的人生旅程的故事。小說中阿西瑪嫁給了與她僅有一面之緣的艾修克,并隨他來到美國。文章圍繞著他們的兒子果戈里的人生經歷展開敘述。不僅描述了二代移民家庭遠離故土、漂泊無依的生活,同時也刻畫了黑人女性群體在獲得身份認同的過程中,通過男女關系和婚戀途徑進行自身身份探索的過程。
后殖民女性主義不僅要求政治、地位方面的平等、自由,在語言方面也要求建立自己的一方領土:女性話語,這充分顯示出女性意識的覺醒。后殖民女性主義“關注第三世界婦女在男權中心文化和白人中心文化話語中面臨的關于性別、種族的雙重壓迫,致力于反抗文化上的霸權統治,改變自己作為‘他者的文化身份,發出屬于自己真正的聲音”[1]。小說中的艾修克和阿西瑪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是典型的實現美國夢的第一代移民群體,然而,黑色的皮膚依然使他們難逃“他者”的命運。文中阿西瑪、毛舒米和索尼婭在面臨文化沖突和身份認同時,通過兩性關系這種途徑,重新定位自身身份,尋求自身的文化歸屬感。
二、“他者”地位的根源
在西方世界,女性本就處于弱勢群體,而來自第三世界的阿西瑪,則更是難逃“他者”的命運。小說中阿西瑪是一位孟加拉人,即使身處美國多年,她依然固守著自己本族文化的根,她堅持穿莎麗,眉間點吉祥痣,為孩子們做印度飯,讓他們學習孟加拉語。她從不直呼丈夫的名字,即使是即將生產之時,也只是用“你在聽嗎?”這樣的話語來代替,并將這一習慣一直延續。只有在每隔一兩年,一家人回到印度生活一段時間時,阿西瑪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長久漂泊在異國他鄉只能成為西方文化霸權中的“他者”。
毛舒米出生于英國,生長于美國,后來又求學于巴黎。在她年幼之時,便“在紙上寫下誓詞,發誓永遠不找孟加拉男子”[2]。在她的身上更能體現出多國文化的雜糅性。毛舒米在與果戈里結合之前曾向一位美國男子求婚,并將其帶回印度。但是在婚前幾個星期,她聽到未婚夫對印度之行不滿的言詞,便拒絕了這場婚禮。她的這一舉動,既是維護自身身份、地位,也是維護印度故鄉的尊嚴,同時也體現出她在家國文化與異國文化之間協調的失敗和對西方文化的妥協。小說中裘帕·拉希莉對索妮婭的描述并不多,但從她非常“美國化”的穿著、喜好來看,同果戈里一樣,她也一直處于自身身份的探索中。在父親去世之后,她搬回家去和母親同住并主動擔負起為家人做印式早餐的責任。每隔一兩年就回孟加拉省親的方式,使印度文化的根深深埋在她的內心。處于第三世界女性弱勢群體的索妮婭,在西方文化霸權的壓迫下,還是選擇回歸家庭,顯示出黑人女性在異國他鄉被邊緣化的處境和“他者”地位。
三、“他者”地位的逃離
《同名人》中阿西瑪作為第一代印度移民的代表,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以后,她們開始在感恩節的時候為家人烤火雞,盡管抹的是蒜、茴香和辣椒粉。圣誕節的時候堆雪人,裝飾房間,大張旗鼓地慶祝。盡管看似與美國人的習俗相差無幾,但在做賀卡的時候,她會留意不選擇“圣誕快樂”字樣的,而只挑選帶有“新春快樂”這樣的字符,用以體現自己的“他者”身份,而非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在丈夫艾修克離世之后,她毅然決然地賣掉在美國的房子回到印度。阿西瑪的逃離就是她勇于與白人中心文化抗衡的體現,是從邊緣社會向主流社會發出反抗的最好證明。
毛舒米在和果戈里結婚之后,一次偶然的機會和自己少女時代暗戀的美國人德米特利重新取得聯系,他的再次出現加速了果戈里和毛舒米婚姻的破裂。毛舒米最終選擇了第三方文化,逃離美國和印度,在法蘭西找到屬于自己的樂土。“她沉湎在第三國語言、第三種文化里,那兒成了她的避難所;她接近了法蘭西,一種與美國和印度不同的文化”[3]。毛舒米的逃離是“對自己妥協歸屬印度文化空間的不滿,更是對印度傳統文化的背叛”[4]。同時也是對西方第一世界和對黑人女性“他者”地位的挑戰。
索妮婭在面臨兩性關系時,選擇本杰明這位有著一半猶太血統和一半華裔血統的美國人。“從流散文學來看,流散者反對固化身份,提倡混合身份。”[5]作為二代移民的索妮婭,在接受西方文化侵襲及家庭印度文化的熏陶之后,和毛舒米一樣選擇逃離西方文化及印度故鄉的文化。而與毛舒米不同的是,她通過婚姻,與一位和她一樣有著自我身份焦慮的年輕人結合。索妮婭的選擇使自己的身份又多了一種可能,同時也產生了猶太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碰撞。以后她將面臨的關于身份認同的道路還很艱辛和漫長,但她已經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走向自己更加廣闊多彩的人生。
四、結語
“女性書寫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沖破男性語言牢籠的束約。女性身體帶著一千零一個通向激情的門檻,一旦她粉碎枷鎖、擺脫監視,它就會表達出四通八達貫穿全身的豐富意義和內涵”[6]。女性群體更應該通過自己的身體、自己的行動創造屬于自己的無堅不摧的語言,沖破主流文化對邊緣群體“他者”化的行為。《同名人》揭露了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群體,在面臨種族和性別上的“他者”身份時,勇敢作出選擇,在自我身份認同的道路上重塑自我、重構黑人女性文化和價值觀。只有自己主動打破沉默,才能找到自己應有的文化身份和位置。
參考文獻:
[1]汪佳,王美萍.雙重“他者”的逃離:后殖民女性主義視角下的《關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記》[J].廣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16,12(6):92.
[2]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M].盛寧,韓敏中,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22.
[3]裘帕·拉希莉.同名人[M].吳冰青,盧肖慧,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4]張瑋.異族婚戀:文化交流和身份認同的方式[J].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5(5):52.
[5]陳春霞.名字的背后是什么:評裘帕·拉希莉的小說《同名人》[J].西北大學學報,2008(1):159.
[6]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