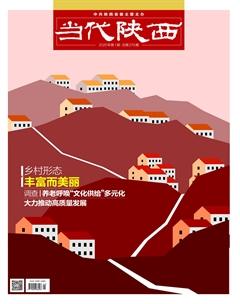當一名扶貧干部是什么感受
郝文錦


“請把分紅的佐證資料、銀行票據、貧困戶領取分紅的名單取來。”
2019年5月16日。檢查組來到某科技公司,公司工作人員把各種財務表冊攤了一桌子。公司領導剛剛坐下,正要給檢查組說明情況,正在查看資料的謝友榮頭也不抬地說。
“……”工作人員一怔,似乎沒有反應過來,扭頭看向公司領導。
“2015年10月,某集團公司以入股形式向你公司注入股本金1807.07萬元。按該集團與你公司簽訂的《陜西省現代農業產業精準扶貧投資協議書》。你公司需每年按集團公司注資金額5%的標準給貧困戶分紅。據上報資料:2018年6月。你公司為505戶貧困戶補發了2016年度分紅56.62萬元;為542戶貧困戶發放2017年度分紅90.385萬元。我們現在核實情況,需要看分紅的佐證資料、銀行票據、貧困戶領取分紅的名單。明白了嗎?”謝友榮翻看著手中的資料,不急不慢地說。
我不懂財務,很是驚訝于她對財務工作的熟悉,只兩分鐘就在那么多賬表、賬冊里發現所缺資料,看著她一臉的認真,聽上去不容置疑的語氣,感受著她對工作的嚴謹。
我和謝友榮以前不認識,出發前一天的扶貧整改檢查組分組會上也沒有注意過,只是看了看組員名單,可就這么短的時間、這么一些話讓我對她刮目相看,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我不是學財務的。正經的西安外國語大學日語翻譯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啊?日語翻譯還是研究生?這么好的專業,這么高的學歷,怎么會坐辦公室搞財務工作呢?
“畢業時,本可以回老家工作的,那里日資企業很多,既可以從事喜愛的專業、享受優厚的薪資待遇,又可以在父母跟前無憂無慮地生活。可是,他要去馬蘭,沒辦法,我只好在馬蘭基地西安研究院安家落戶了。”她摘下眼鏡擦了擦,又重新戴好,看著我們聽得認真,滿是幸福地笑笑。
2016年。她放棄了13年來付出無數心血的日語翻譯專業,以筆試、面試雙第一的好成績考入藍田縣扶貧辦,成為一名基層扶貧干部,投身到脫貧攻堅最前線。
從此,她的心里只有扶貧兩個字。
“學了13年呢,都拿到了碩士,搞日本文學研究、做翻譯、當老師不好嗎?為啥要當一名事業干部呢?”我真想不通,不假思索地問。“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她朗朗地說,然后向我笑笑。這可是出自明代詩人于謙的《詠煤炭》里的名句,經她隨口一說,卻真是震撼到我了。
藍田縣是革命老區縣。基礎薄弱,2015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近10萬人,是西安市脫貧攻堅戰主戰場之一,脫貧任務異常繁重。
從小在平原長大沒見過大山,她對大山深處的貧困沒什么概念。但當她第一次走進大山入戶走訪時,才發現還有這么多群眾生活得如此窮困。她說:“當時我真的落下了淚,真沒想到現在還有這么窮的。我不是唱高調,當時就覺得,幫助他們走出貧困是我的使命。”
藍田縣以山嶺為主。山區群眾居住分散。入戶走訪常常只能步行。2016年冬天的一次入戶走訪,積雪覆蓋著蜿蜒的山路,似哨聲一樣的風穿透衣服,好不容易走到群眾家里,已被凍僵的手指怎么都不聽使喚,本就身體單薄的她差點被凍成了“冰塊”。“還有一次進村。剛巧趕上修路,我們像走鋼絲一樣,從側面僅有一腳寬、旁邊就是數十米深溝的路沿上通過。后來想想,還真是可怕,也不知道當時怎么走過去的。”
她眉飛色舞地講著,兩只手還不停地配合著語氣,卻始終帶著笑意。“后來,我到省上掛職,好多次到貧困村調研,我曾拿著手電筒夜行山路1個多小時,相信不?”她問的很認真,似乎我們不曾去過山村,不曾經歷過似的。
“當然相信,你說的再艱難我們都相信,因為,我們遇到的情況或許比你的經歷更嚴重。”一旁的同事薛振華說。
我說:“這兩年脫貧攻堅任務繁重,對女同志可是不小的考驗呢。”
扶貧辦的工作本就很辛苦,她還總是申請到最艱苦的崗位。2017年5月,主動申請前去脫貧攻堅指揮部工作;2017年11月到2019年6月,被市上推薦到省脫貧攻堅指揮部掛職學習。三年多時間,換了8個辦公位置。
初到扶貧辦時,科室只有2人,工作異常繁忙,她主動承擔起文稿寫作工作,從此沒有了節假日,通宵處理文件是常事,甚至生病了也不放下工作。縣上剛成立脫貧攻堅指揮部時,她一人承擔起辦公室所有業務,成天離不開辦公室,每天都走2萬多步,一個月瘦了10斤。她愛人知道后,心疼得不得了,但她笑著說:“瘦了不是更好看了嗎?”
在省上掛職期間,負責指導全省脫貧攻堅項目庫建設。千陽縣“項目超市”和鎮安縣“戶分三類”作為全國典型經驗,受到國務院扶貧辦的充分肯定;較好的理論、文字功底和基層工作實踐,讓她在綜合文稿寫作、各類材料撰寫方面有著獨到見解,多次起草向國務院扶貧辦的匯報材料,在媒體發表的《陜西多措并舉強化扶貧資金監管》在國務院扶貧辦官網刊登。
“今年我被評為2018年度的優秀。還被選舉為扶貧辦支部委員呢。”說著,又咯咯咯笑了起來。
“腳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這話不知最早是誰說的,我覺得這話說的真好。”她突然發了感慨,在我們每個人臉上看一遍。開心地說:“我還是幾個孩子的知心姐姐呢。”
藍田縣扶貧辦給每一位干部都確定一個貧困戶作為扶貧對象,謝友榮的扶貧對象在大山深處的岱峪村,很遠,來回得跑4個多小時。三個孩子的父母離異了,奶奶癱瘓在床,靠他們的父親掙錢養家。這三個孩子分別上小學、初中和高中,雖然家境很差,但他們學習成績都很好,墻壁上貼滿的獎狀是他們家最好的裝飾。
“我長大了想當一名幼兒園老師!”
“我想當作家!”
“我想當軍人!”
當她和孩子們聊天的時候,三個孩子各有各的理想。身處寒門,卻能保有一個積極向上、遠大的夢,相當難得。她為他們的理想大受感動。從此,她的心里多了一份牽掛。盡管單位里的工作多到經常加班加點,有時甚至回不了家,但她只要有一點時間,就跑去看看孩子們。
就是在省、市扶貧辦掛職期間也沒有以任何理由放下這份牽掛。每次去都給孩子們帶一些學習和生活用品,都要聽聽孩子們的學習情況,鼓勵他們好好學習。她的付出得到了姐弟們的認可,時間久了,她成了這三個孩子的“知心姐姐”,孩子們遇到任何事情都會告訴她。
“媽媽離家時弟弟只有2歲。從那以后再也沒見過媽媽。”孩子黯然地說。她看著孩子們低垂著頭,聽著他們哽咽的聲音。伸開雙臂把他們摟在懷里。她想,不僅要做他們的“知心姐姐”,還得做好“媽媽”的角色:“你們只管好好學習,剩下的事不用考慮。”
兩年多來,她幫助這三個孩子申請了教育資助,給他們家申請“美居”房屋,還申請了2萬元產業扶持資金,幫助孩子們的父親發展白皮松種植、中蜂養殖,聯系銷售蜂蜜……
2018年夏天,姐姐考上了理想的大學,妹妹考入縣城重點高中。
“工作上盡心盡力。對那三個孩子也力所能及地幫扶了,可是,對父母家人,我真覺得虧欠太多,在兩個兒子面前我真不是個好媽媽。”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馬蘭基地的前輩們遠離父母、拋下兒女。她的愛人和其他馬蘭人一樣,也是經常不在家,哪怕在她剛生完孩子最需要照顧的時候,他也不在她身邊,但她從來沒有怨言。她說:“我和‘馬蘭人一樣,無暇好好孝老教子。”
孩子的成長需要父母的陪伴,但她是“缺席母親”,基本沒接送過兩個兒子上下學,孩子們過兒童節都沒有時間陪伴,甚至沒法好好照顧生病的孩子。2017年因為經常加班不在家,有段時間甚至被孩子們遺忘。
周末偶爾在家。兒子會不習慣地問:“媽媽,你今天怎么在家呢?”在她腦海里至今還記得。晚上加班回家看到孩子發著高燒躺在沙發上的情景,也記得冰天雪地里只有他們在“玩雪”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