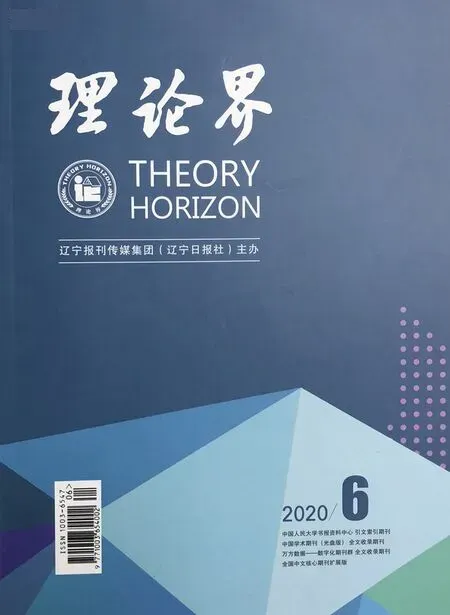論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的“社會時間觀”
趙 莉 王 聚
一、引言
討論歷史維度的“時間”意在區分“社會時間”與物理性的“絕對時間”之間的不同,但這種區分并非易事。因為它不是在說明一個物體的屬性,對社會時間的表達不可以采用累計疊加的方式。要想真正理解時間的本真內涵,就需要一度深入到歷史當中去。因此,要清楚地作出區分工作,就需要解決好三個問題:歷史何以成為時間的第一要義?歷史和時間的契合點在哪里?時間如何成為歷史本身?而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可以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找到。
二、時間是歷史的非邏輯化
對歷史本身的探究歷來倍受哲學家的青睞,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歷史有著誘人的寶貴財富,了解歷史是當下人必做的功課;二是因為如果要想取得寶貴的歷史財富,則需解決歷史留下的“難題”,即“如何深入到歷史當中去”這個問題不可以簡單等同于“如何回到過去”,因為后者的提問方式將歷史鎖定在了已然逝去的物理性時間之中。當面對這種問題時,任何答案都顯得軟弱無力。因為物理性的時間已經表明了自身的不可逆性,當前的人類科技發展還實現不了穿越到過去,而對這種技術的期望倒不如去史籍中查閱資料來得更加有效。當然,史籍中的資料也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在這里對史籍的質疑不是質疑其所能提供的資料的數量和真實可信度,問題的關鍵在于:史籍成為史籍的條件何在?舉例來說,史籍記載的都是“歷史事件”,若從經驗事件的角度來講,這些“歷史事件”并不能代表整個歷史。因為文本的有限性首先規定了這點,不過這并不影響史籍自身的意義與價值,更為值得關注的是歷史事件怎樣走進史籍。對于這個問題,黑格爾給出非常準確的答案——理性自身。“哲學作為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會出現。概念所教導的也必然就是歷史所呈現的。”可見,更確切地說,是思維依托概念、邏輯和判斷輪廓出了一套屬于史籍的體系,而史學家則站在這套體系的“肩膀”上來選擇載入史冊的那些“歷史事件”。至此,就史籍(或者是整個史學)本身的可能性而言,它總要面對這樣的困惑,即被用來證明思想疑惑的史學資料本身總是由思維來奠定其基礎的。可以說,歷史仿佛走進了“絕對精神的怪圈”,由思辨理性出發,經過邏輯的梳理,走向經驗事實的懷抱。在這樣的歷史面前,只有一個結果可言,那便是“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對灰色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態變得年青,而只能作為認識的對象。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
馬克思對此作出了這樣的評述,“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這樣:好像后期歷史是前期歷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于是歷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為某個與‘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識’‘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實,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后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歷史對后期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在馬克思看來,由理性邏輯所構造的歷史是一堆抽象物的集合體。史學家們憑借自己的敏銳“眼光”,也能看到一些在邏輯體系之外“漂游著”的現實性。但這并不能改變什么,他們除了對史籍進行一些補充之外,剩下的無非就是要靠著無休止的爭論來樹立一套全新的邏輯體系以便能更精確地篩選進入史籍的“歷史事件”。于是史學總是擺脫不了理性邏輯的“陰霾王國”,歷史哲學應運而生。
在歷史哲學面前,時間失去了本體論意義而成了純粹的外在性規定,并且在歷史哲學這,時間通常的表現形式是經驗事件的延續性,因為事件與事件之間前后相續是有章可循的,而時間的使命就是讓這種在歷史事件之外的排序方法變得有序和通暢,但是它忘了時間最為重要的使命,即使歷史事件成為其自身。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雖然歷史哲學使時間失去了本身的內涵,但是歷史哲學的生命是由史學“困境”所賦予的,歷史哲學閹割掉了時間的真相,同時也為尋找這種真相提供了一條路徑,即歷史哲學對主觀思想的揚棄,這樣就能消除歷史的現實性和理性的先驗原則之間的對立。換而言之,如何深入到歷史當中去不是邏輯的先驗原則所能解決的,內在的自由之境所能提供的最高成果就是康德的物自體之不可知,唯有剝落掉主觀思想的純粹性外衣,才能探究到真實的社會現實,而這也是“社會時間”的真正本體論內涵之所在。當然對本體論內涵的揭示需要來自這個領域的相關革命作為支撐,而對主觀思想的揚棄就是一場這樣性質的運動。歷史哲學妄圖徹底揚棄主觀思想,但它對理性的“溺愛”導致它最終以失敗告終。而歷史唯物主義是繼歷史哲學之后的真正的“革命者”,它以感性活動、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去改造主觀思想給“社會時間”帶來的“理性牢籠”。
三、感性活動是對社會時間的澄明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能動的生活過程”,或者直接稱它為這種“感性活動”,它自身就意味著一種終結,終結的對象就是一直沉浸在認識論領域,不斷地進行著意識形態戰爭的經驗論和唯理論。他們對歷史的認識就是對歷史的“解釋”,不管是“事實的匯集”,亦或純粹的“想象活動”,它都不可能逃離“意識的內在性”。因為認識論中的主客體唯有分離開來,才能有真理可言。然而,這種真理的獲得是“可悲的”,對主體的無限復歸是認識論的最高理想。在這種復歸中,社會時間與物理性的“絕對時間”之間,開始逐漸劃上了等號。均勻性和不可逆性的物理性內涵開始逐漸地進入社會時間的領域,最后甚至將時間演化為數字的表達。這樣做無非是方便于“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以及邏輯體系的標識。一句話,工具理性就是“社會時間”的歸宿。
然而,感性活動是對社會時間的一次“洗禮”,因為它可以除去社會時間身上的“魅影”,還其以原貌。感性活動之所以可以達到如此效果,是因為此時的“感性”已非認識論范疇中的感性概念。從認識論的角度剖析,感性總是被看作是有待理性“加工”的潛在“原料”,這使得感性被當作一種媒介,它的存在形式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現象,最終要經過人類的加工轉化為理性,這樣的看法使理性成了一切的歸宿,堪比神性。但是在歷史唯物主義那里,感性在本體論中的首要地位才是不可撼動的。同時在馬克思那里,感性的對象性特質是最為關鍵的。
對象性不是實體和實體之間的物質性關聯,相比物質性的關聯,對象性更是一種生命的表達方式。“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于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當然,這種生命的表達不是生物學意義的,因為它所要展示的是人,而不是動物般的自在自發狀態,更不是認識論所要闡述的作為客體與主體處于分離的那種狀態。在這種生命的表達方式中,人直接地就是自然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對象性的存在物進行對象性活動,如果它的本質規定中不包含對象性的東西,它就不進行對象性活動。它所以只創作或設定對象,因為它是被對象設定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設定這一行動中從自己的‘純粹的活動’轉而創造對象,而是它的對象性的產物僅僅證實了它的對象性活動,證實了它的活動是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動。”這樣說來,對象性所孕育的生命表達方式意在凸顯對象性的存在物處在一種現實的活動之中。這種現實性不需要理性邏輯的預設,它來自生活于其中的對象對它自身的真切“體悟”。之所以是一種體悟,是因為體悟之感必來自對先前一切的前提的揚棄方可實現。也唯有這樣的做法,才可能真正地實現社會時間的去“工具理性”化。
以對象性來詮釋社會時間,人們會發現社會時間是一個面向當下生活敞開的“場”,而不是某種度量工具或者數字表達。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我們須得源源始始地解說時間性之為領會著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從這一時間性出發解說時間之為存在之領會的視野”。“時間性”要領會“此在的存在”,也就是說社會時間想要揚棄自身的工具理性的依托,則它必須成為一種敞開的“場”。因為“如果設想有一個磁場,它的中心沒有磁石這樣一種堅實物體,人的存在就是這樣一種場,不過,在它的中心也沒有任何精神實體或自我實體向外輻射。……我的存在中的‘我的’并不在于我的場的中心有一個‘我——實體’這個事實,而毋寧在于這‘我的’彌漫于我的存在的整個場里”。當然,以類似物理學用語的“場”來闡述社會時間確有不當,但這種說法非常形象地表達出了理性的實體性在社會時間中的消解。伴隨理性的淡化,社會時間開始成為“一本打開了的關于現實生活的本質力量的書”。這種本質力量就是為了說明社會時間是現實生活的“外化”,或者說社會時間對現實生活來說,是它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可見,時間也是一種生命的表達方式。它存在的本體論內涵是,生命的自我展示需要時間來慰藉。中國有一句話叫“歲月如梭”,用它可以很好地來說明時間。“歲月”如果用物理時間來計算,則其與“如梭”二字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歲月”一旦換算成數字便是呈以百計千計甚至萬計之貌,“如梭”二字確實難以形容它。由此可見,“歲月如梭”中所含有的時間因子并非物理性的“絕對時間”,它是一種社會時間的表達,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只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是當下賦予了它生命。“歲月如梭”的感慨意義在于生命自我展現的曲折,然而這種曲折使生命自身釋放了魅力和光芒。不論光的程度到底如何,但是它使生命在當下的生活中得到了回憶的安慰,為直面人生的終結——死亡,平添了一份勇氣。此時的社會時間開始融入到了社會現實當中,成為了歷史自身。
四、社會現實是社會時間的歷史實現
社會現實的發現得益于對主觀思想或者主觀意識的存在的批判,主觀思想,或者主觀意識的存在是對社會現實的最大的遮蔽。在主觀意識占統治的年代里,社會現實總是顯得晦澀不明。社會現實與主觀思想的決裂想要表明的就是,社會現實不是經驗事件的羅列和組合。在這里,要進入社會現實的首要路徑就是“現實的前提”,而不是“經驗的前提”“理論的前提”。“現實的前提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資料,包括他們已有的和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賦予“現實的”的一詞以三層意思,即“活動”“物質生活資料”以及“活動創造出來”,但這三層意思不是簡單的累積疊加。“活動”直指理性自身,“物質生活資料”更多代表的是感性的社會存在。在它們之間,馬克思以“和”字相連,因為“活動”和“物質生活資料”都是由“活動創造出來的”,但兩個“活動”含義不同,后者是指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在對象性活動中,純粹的理性活動失去其自身的獨斷論性質。
在這里,感性的社會存在成為純粹理性活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對象性存在物,此時的感性社會存在也不是理性的潛在式的質料。相比而言,感性的社會存在已然成為了一份“催化劑”,這種催化效果更多的是讓理性活動離開自身內在的束縛,滲透到真實的“物質生活資料”當中去。現實性一旦實現理性活動的這一轉變,社會現實就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可見社會現實就是在這樣一種整體性得到充分擴充的時刻誕生的,而社會時間則是對這種時刻最好的描述和表達方式。用描述和表達來形容社會時間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聯,不是要將社會時間當作記載手段或者測量工具,因為社會現實不是經驗事件,它不需要來自外部的邏輯預設,對社會現實的表達和描述的唯一可靠路徑只有從其自身內部出發找尋才有可能,即社會時間對社會現實所作出的描述和表達,源自于社會時間與社會現實之間內在的一致性,此時的社會時間成為了歷史本身,歷史的全部本真內涵都在這種帶有總體性的社會時間中得以展示。
社會現實是純粹理性和“物質生活資料”的內在統一,這個統一通過感性的對象性的活動得以實現,并且社會現實以整體性的實現方式來表達自身,并將這種整體性賦予社會時間。如果說感性活動還原了社會時間的本真狀態,使社會時間與歷史成為了彼此依靠的對象性存在物,那么社會現實則以整體性的展現形式使社會時間成為歷史本身。歷史的本真狀態是“構成其最極端的存在可能性的東西”。可見,歷史不是片段的簡單羅列和組合,真實的歷史更多地是趨向在某種可能性當中,這種可能性不是純粹理性的預設,想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它,就需要一種整體性的原則,因為只有在整體性的視域中,歷史的可能性才能得以本真地展示。這時歷史在面對過去,甚至將來,已不再是局限于過去的或者是將來的那個片段。
也唯有如此,即當社會時間成為歷史時,歷史規律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揭示。所謂揭示不是指理性邏輯的推演,而是現實的描述。這也是馬克思所探索的歷史科學的任務所在。與此同時,作為處在社會時間中的現實個人,才真正成為創造歷史的主體,現實個人的感性活動、未來追求等才真實地創造著、引領著歷史及其發展方向。也就是說,現實的個人在歷史舞臺上才真正出場,否則只不過是理性形而上學下的抽象個人,并未進入歷史本身。
五、結語
歷史的立足點已經是一個整體,“過去、現在、將來”無一能代表歷史本身,唯有作為整體出現才有這種可能,而社會時間就是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也就是說社會時間作為歷史的對象性的存在物,以一種整體性的方式,將歷史展現出來。這樣,社會時間的全部內涵和使命得到了最終的體現,社會時間成為歷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