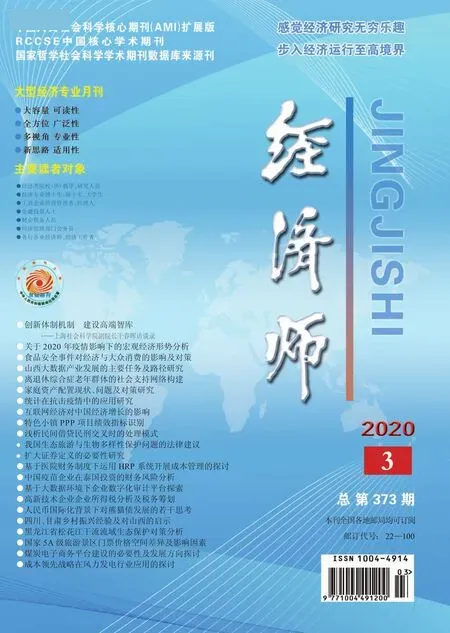以案分析盜竊罪與侵占罪的界限
●梁瀟逸
一、李儼遒盜竊案及由其引發的爭議
(一)案情簡介
被告人李儼遒于2000年7 月18 日乘坐青島至深圳的航班,行程目的地為深圳。中途經停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中轉下飛機。飛機乘務人員通知飛往上海的旅客先下飛機,飛往深圳的旅客后下飛機。其中,飛機前艙118 排坐的是到上海的旅客,18 排之后是到深圳的旅客。被告人李儼遒待飛往上海的旅客陸續走空后準備下飛機時,發現16 排通道左側豎放著一個白色紙袋以及黑色真皮皮包,見四處無人,隨即將白色紙袋與黑色真皮皮包占為己有,并攜帶包內財物8600 元人民幣及一個諾基亞手機飛回深圳。2000年8 月上旬,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公安分局將其抓獲。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最終以盜竊罪判處李儼遒拘役6 個月,罰金人民幣1000 元。①
(二)案件爭議焦點
李儼遒盜竊案判決一出,隨即引起學界激烈的爭議,爭議焦點主要圍繞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成立盜竊罪還是侵占罪展開。認為成立侵占罪的學者認為:白色紙袋與黑色真皮皮包系飛往上海旅客的遺忘物,財物已經脫離了物主的實際控制,被告人拿走財物的行為沒有侵犯他人合法占有的權利,此行為系拾得他人遺忘物。認為成立盜竊罪的學者則認為:飛機乘務人員對旅客遺失物有管理的義務,白色紙袋與黑色真皮皮包雖然脫離了物主的實際控制,但仍然在乘務人員的控制之下,被告人拿走財物的行為破壞了乘務人員對旅客遺失物的合法占有,應定為盜竊罪。
二、占有歸屬的判斷
“占有”一詞在刑法學和民法學有著不同的定義與闡釋,民法學中“占有”一詞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要求行為人對財物實現了支配、管領的能力;二是行為人主觀上對財物具有占有的意思。而刑法學則強調占有是一種客觀的事實和狀態。②在侵占罪中,行為人的行為在構成犯罪之前已經合法占有財物,實施侵占的過程主要是指將合法占有變為所有,即剝奪了財物所有人的所有權。而盜竊罪則是以秘密的手段破壞原占有的犯罪行為。由此可以得出,區分盜竊罪與侵占罪,關鍵在于犯罪行為是否破壞了他人的占有狀態。那么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財物的占有歸屬屬于何種狀態,就成了需要探究的重要課題。
結合本案案情可知,飛機抵達浦東國際機場時通知上海的旅客先走,在上海旅客陸續走空后,被告人準備下飛機時才發現先前乘客遺忘在通道左側的財物。說明此時物主已經下飛機,失去了對財物的占有和支配,物主對物不再具有有效控制力。而針對類似飛機機艙、賓館、飯店等特殊的空間,一般都存在著管理者對空間的控制,以至于影響到財物占有歸屬狀態。所以,本案財物脫離原占有后的占有歸屬狀態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有管理者的場合,拾得遺忘物的行為屬于盜竊罪還是侵占罪,在司法實踐中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爭議。類似案件如許霆案、梁麗案也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刑法學界中的“二重控制理論”在司法實踐中得到了普遍的運用,“二重控制理論”主要是指:在有管理者的公共場合,如電影院、餐廳,財物不僅被財物所有人所占有和支配,公共場合的管理者也對客人財物有妥善保管的責任與義務。遺忘物或者遺失物在上訴特定場所脫離了所有人的合法占有,該遺忘物或者遺失物應視為繼而被管理者合法占有。如果此時有第三人破壞了管理者基于責任形成的第二重占有狀態,則該行為有可能構成盜竊行為;如果財物脫離了占有人的支配與占有,同時也沒有形成“二重控制”,則第三人將其拾走的行為可能構成侵占罪或者定性為民法上的拾得遺失物。
三、空間屬性對占有歸屬的影響
有學者指出:“侵占罪和盜竊罪在遺忘物這個對象上,形成了一個微妙的交叉點,遺忘物所在的空間屬性關系到第二重控制的形成與否,進而關系到行為定性。”③不同的空間有著不同的屬性,管理者對財物的控制力度也會相應地受到影響。結合司法實踐與社會經驗,可以從穩定性出發將空間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人員流動性較強的空間,例如火車站、地鐵、機場。在此類場合中,合法占有人或所有人在對財務進行監管時,應盡到更高的注意義務。由于空間穩定性較低,客流量較大,導致管理者對遺忘物的控制力度受到削弱,管理者很難對遺忘物實現二重控制的支配與占有,此種情形中有第三人拾走遺忘物的行為就應當定性為侵占。二是人員流動性較弱的空間,大多具有一定的封閉性或者比較私人的場所,例如,電影院、酒店客房、飯店包間等。在此類場合中,空間穩定性較強,管理者對遺忘物可以實現較強的支配力度,并應盡到與合法占有人或所有人同等程度的注意義務。譬如酒店退房的客人將財物遺忘在房間隨即離開,酒店管理者或者保潔工作人員很容易在第一時間發現,繼而對遺忘物實現合法占有,并負有妥善保管的責任。此種情況下第三人將遺忘物非法占有的行為,破壞了管理者的占有狀態,應當定性為盜竊罪。
結合本案分析,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場所系機艙。飛機機艙的乘客人數有限,在特定的時間段內不會產生較強的人員流動,屬于較為封閉、固定的空間。乘務人員對旅客遺忘物的支配力度沒有受到空間屬性的影響。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因發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過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隨身攜帶物品毀滅、遺失或者損壞的,承運人應當承擔責任。機組乘務人員應依法對旅客遺失物盡到妥善保管的義務,即乘務人員對旅客遺忘物實現了“二重控制”。綜上所述,本案中物主將財物遺忘在飛機機艙通道后,該財物雖然脫離了原占有人,但是由于機艙這種特定環境的性質,決定了乘務人員對遺忘物形成了新的占有。所以該遺忘物并不在李儼遒有權控制的范圍之內,其對于李儼遒來說應是他人占有的財物。李儼遒的行為符合盜竊罪的犯罪特征。
四、犯罪目的產生的時間節點
盜竊罪與侵占罪主觀上都存在不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但目的產生的時間不同。對此,陳興良教授認為。侵占罪在實踐中多產生于行為人與物主合法的委托關系,譬如保管、加工、運輸合同等,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多產生于合法的法律關系形成之后。而在盜竊罪中,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則發生在秘密竊取他人財物之前。④結合本案案情分析,被告人李儼遒在發現遺忘在座位的財物后,見四處無人并將其占為己有,帶回深圳。通過被告人一系列的行為可以看出,其發現遺忘物之時便已經產生不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并且在此之前李儼遒與失主之間并不存在合法的委托關系。綜上所述,被告人李儼遒犯罪目的產生時間節點層面,符合盜竊罪的特征,與侵占罪犯罪目的的產生時間具有明顯的差別。
五、犯罪客體
從廣義上說,盜竊罪與侵占罪都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益。而在狹義上,兩罪所侵害的客體又是有一定區別的。侵占罪與盜竊罪在犯罪客體層面存在著的重疊的現象。有學者認為,盜竊罪與侵占罪客體的區別體現為占有和所有權之間的區別。如果行為人侵害的對象包括占有和所有權,那么構成盜竊罪;而在侵占罪中,如前文所述,侵占行為大多以行為人和原所有人存在委托關系為基礎。而行為人對物已經實現了合法的占有,其侵害的則僅是財物原所有人的所有權。換言之,盜竊罪的犯罪客體包括他人的占有與所有權;而侵占罪的犯罪客體則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結合案情,依前文所述,旅客遺忘在機艙內的財物仍然處于乘務人員的占有之下,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取走遺忘物的行為不僅侵犯了遺忘物所有人的所有權,更侵犯了乘務人員對遺忘物合法占有的權利。本案侵害的客體與司法實踐中侵占罪侵犯的客體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區別。
結語
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在司法實踐中,盜竊罪與侵占罪的區分一直是頗受爭議的話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新的犯罪手段與場合也不斷涌現,對此我們更應當重視對犯罪行為的定性研究,依據司法實踐不斷更新、豐富理論基礎,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保障人民財產安全,從而把全面依法治國推向前進。
注釋:
①陳興良.刑事疑案評析[M].北京:中國檢察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 頁
②黎宏.論財產犯中的占有[J].中國法學,2009(1)115
③葉希善.侵占遺忘物和盜竊遺忘物的區別新意——修正的二重控制論[J].法學,2005(8)51
④陳興良.刑事疑案評析[M].北京:中國檢察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