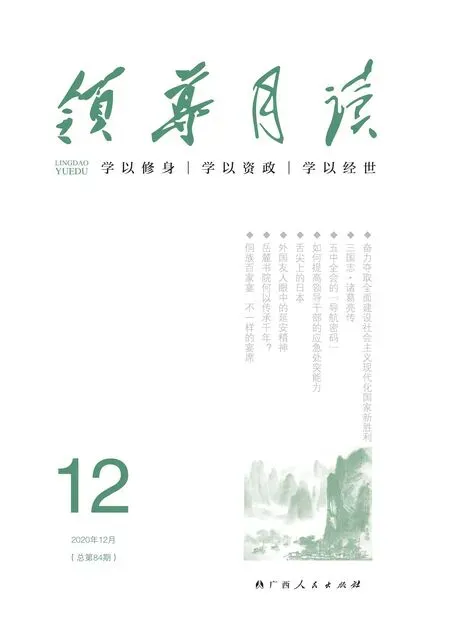荀子·儒效
[戰國]荀 子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①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②,舉其上客,億然③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茍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④,張法而度之,則晻⑤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⑥。
(原文據中華書局2015年版《荀子》)
【注釋】
①解果:又作“蟹蜾”,中間高兩旁低的帽子。
②便辟:諂媚逢迎,這里指受寵愛的小臣。
③億然:心安理得的樣子。
④儗?:因疑惑不解而羞愧。?,通“怍”,慚愧。
⑤晻:通“奄”,重疊,合拍。
⑥伯:通“白”,名聲顯著。
【譯文】
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者,有雅正的儒者,有偉大的儒者。不學習請教,不講求正義,把求取財富實利當作自己最高的目標的人是庸俗的人。穿著寬大的衣服,束著寬闊的腰帶,戴著中間高高聳立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只夠用來擾亂當代的政治措施,荒謬地學一些東西,雜亂地做一些事,不懂得效法圣明的帝王之法,統一制度,不懂得把禮義置于最高地位而把《詩》《書》置于次要地位;他的穿戴、行為已經與社會上的流俗一樣了,但還不知道厭惡這一套;他的言談議論已經和墨子沒有什么兩樣了,但是他的智慧卻不能分辨;他稱道古代圣王來欺騙愚昧的人而向他們求取衣食,得到別人的一點積蓄夠用來糊口,就得意揚揚了;跟隨君主的太子,侍奉君主的寵信小臣,吹捧君主的貴客,提心吊膽好像是終身沒入官府的奴隸而不敢有其他的志愿,這是庸俗的儒者。效法圣明的帝王之法,統一制度,推崇禮義而把《詩》《書》降到次要地位,他的言論和行為已經符合基本的法規了,但是他的智慧卻不能補足法制教令沒有涉及的地方和自己沒有聽見看見的地方,就是他的智慧還不能觸類旁通;懂就說懂,不懂就說不懂,對內不自欺,對外不欺人,根據這種觀念而尊重賢人、畏懼法令、不敢懈怠傲慢,這是雅正的儒者。效法古代的圣明帝王,以禮義為綱領,統一制度,根據不多的見聞把握很多的知識,根據古代的情況把握現在的情況,根據一件事物把握上萬件事物,如果是合乎仁義的事情,即使存在于鳥獸之中,也能像辨別黑白一樣把它辨認出來;奇特的事物、怪異的變化,雖然從來沒有聽見過,從來沒有看到過,突然在某一地方發生,也能應之以道而無所遲疑和不安,衡之以法而如同符節之相合,這是偉大的儒者。所以,君主如果任用庸俗的人,那么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也會滅亡,如果任用了庸俗的儒者,那么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僅能保存,如果任用了雅正的儒者,那么就是擁有千輛兵車的小國也能安定,如果任用了偉大的儒者,那么即使只有百里見方的國土也能長久,三年之后,天下就能夠統一,諸侯就會成為臣屬,如果是治理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那么一采取措施就能平定天下,一個早晨就能名揚天下。
【簡析】
《荀子·儒效》主要論述儒者的社會功效,一開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而安天下的大儒之效,接著提出“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儒家著名命題,并詳細展開論述,然后即從俗儒、俗人的角度將其與大儒做出鮮明對比。本選段就是這一部分的起始,荀子首先批評了俗人的社會危害,然后通過“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層層上比的邏輯,充分肯定雅儒“法后王、一制度、隆禮義”和大儒“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的政治主張和他們在統一天下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
長期以來,學界都認為和孟子極其強調居仁由義的“法先王”相比,《荀子》一書整體上更加強調的是隆禮重法的“法后王”,但實際上這種看法也有失偏頗,比如從這篇來看,荀子最為強調的就是積德遵道的君子修養,并且明確指出儒者都要向仲尼、子弓這樣的大儒學習,認為他們通達時就協調天下,窮困時就獨自樹立高貴的名聲,天也不能使他死亡,地也不能將他埋葬,這種尊道貴德的觀點和精神與孟子如出一轍,只是相比來說,身處戰國后期的荀子比身處戰國中期的孟子面對的政治形勢更加殘酷因而在精神上也更加焦慮,在思想主張上自然也更加務實,所以他先在本選段之前總體上論述大儒應該“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接著詳細對比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在治國功效上的不同,顯然是一種謀劃老成的游說策略,他對俗儒、雅儒的揚棄,甚至對許多孔門弟子以及子思、孟子的激烈批評,一方面可以視為儒者群體面對殘酷政治現實所做的類似“舍車保帥”的奮進救世行為,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對思想家提出的時代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孟、荀的儒家精神、焦慮心態、應變行為與救世思想顯然是前后一脈相承的,只是相比之下荀子比孟子更加務實、更能變通因而更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