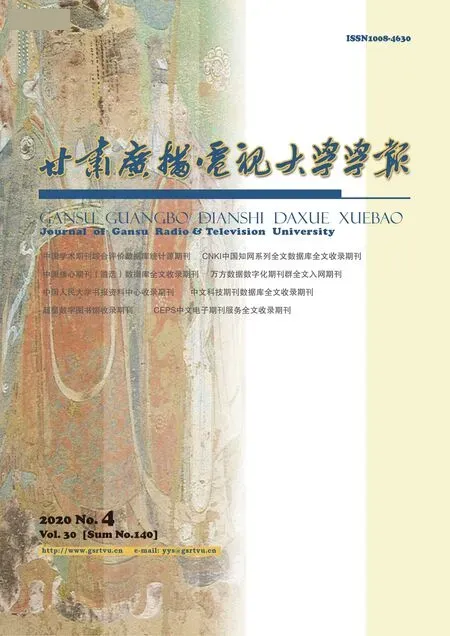情理之間:《文心雕龍》“修辭立誠”觀芻議
程龍浩
(曲阜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修辭立誠”之說取自《周易·乾·文言》:“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1]15孔子將君子的德行修養與修辭緊密結合在一起,“修辭”是君子內在德行修養的外在實踐,“誠”是指言辭的表達要真誠地發自內心。“修辭立其誠”作為中國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德性優先、誠意為文,這與儒學德行事業的內外之道結合起來,成為后世道德文章乃至修辭學的重要內容”[2],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承續了這種道德、文章的解釋路徑,一是指“祝盟”之作要“務實”“知信”,強調作者對神靈的虔誠;二是指一般文章要“情動而辭發”,遵循儒家倫理道德之真,傳達出作者的真情實感。
一、立誠在肅,修辭必甘
劉勰在《文心雕龍·祝盟》篇中,將各種祭祀用的文辭統稱為“祝”。他考察了祝文的發展流變,并制定了“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于無愧”的寫作規范。盟文是盟誓時向神明禱告的言辭,寫作盟文的大體要領是用貼切的語言表達出內心的忠誠。
“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極興焉。”[3]355祭祀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事關兆民的生存。伊耆在歲末祭祀與農業有關的“八神”,祈求風調雨順,禹舜在春天祭祀土地,希冀四海之內都能獲得大豐收,商履使用精誠的祝辭使“萬方罪己”,“犧盛惟馨,本于明德”[3]355,他們都為兆民的生養而虔誠地向神明發愿,他們的祝辭質樸無華但“利民之志,頗形于言矣”[3]358。春秋以來,禮崩樂壞,人們對于神明的觀念發生了改變,褻慢神靈濫用祭祀,祭祀失去了嚴肅性,祝辭也發生了改變,但晉國大夫張老所致“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4]的祝辭以及衛國太子征戰時所作“無絕筋、無斷骨、無面傷”[5]的禱告之辭,內容上都表現了作者內心的真實,得到了劉勰的肯定。劉勰“看重的正是與那些隨意夸大其辭做法迥異的‘雖造次顛沛必于祝’的虔誠。這種大實話中的真實、毫無修飾的言辭里的真誠,正是祝禱文體最重要的內在規定”[6]。漢代雖然整頓、嚴肅了各種祭祀的禮節,但摻雜了方士們的方術以致“秘祝移過,異于成湯之心”[3]368,因此劉勰感嘆祝辭逐漸失去其本來的意義和作用。劉勰提出了“凡群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于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3]375-376的寫作原則,認為班固的《祀濛山》、潘岳的《祭庾婦》是祝文體的典范之作,它們分別表現了祈禱時的誠懇肅靜和祭奠時的恭敬與哀痛。
盟是指古代諸侯國宣誓結盟時在神明面前祝告的話語。“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7]諸侯之間相互猜忌彼此不信任,便“殺牲歃血”向神明禱告,請求神的監督。諸侯禱告的文辭就是盟辭。盟誓在夏代就已經存在,夏禹、商湯、周武王都具有光明的道德,為天下百姓謀利的志愿誠摯無比,為人民所尊敬所信任,因此不用立下盟誓。東周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紛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演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崩樂壞誠信精神缺失,訂立盟約的事就經常發生,但劉勰并不認為在神靈的監督下盟誓就能成功。東周時代背盟、棄盟之事屢屢發生,盟約失去了其意義和作用,“由神靈信仰約束人類行為的盟誓功能己經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8]。“盟約最終要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有堅持道義,盟約才能堅持到底,道義就是忠誠信用,堅持這種道義就不用依賴于神。因此,盟文的寫作講求“講忠孝”“感激以立誠”“切致以敷辭”的原則。劉勰將祝、盟兩種文體放在一起論述,正是看到了兩者之間的相同之處。紀昀評價《祝盟》:“此篇獨崇實而不論文,是其識高于文士處,非不論文,論文之本也。”[3]354所謂“崇實”“論文之本”大概是指兩種文體的寫作都要表現作者內心的真誠、忠信之意。
二、綴文者情動而辭發
“修辭立誠”是《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體現在文體論中,而且也是創作論的重要命題,在全書多處涉及。“萬趣會文,不離辭情。”[3]1206劉勰認為文章的寫作離不開言辭和思想情感,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正是其創作論的主要內容。言與情的問題,在早期儒家典籍中就已經提到,《尚書·舜典》篇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9]50“詩”是用來表達人內在情志的,情感的宣泄又要“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9]50,真誠充實又保持“時中”不偏不倚。《詩大序》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9]50人心受到外在事物的感觸產生感情并且借助言辭表達出來,言辭的表達符合內心的情志就是“誠”,反之就是“不誠”。劉勰在《情采》中云:“繁采寡情,味之必厭。”[3]1175文章圖有華麗的形式而無情志充實的內容,只會惹人生厭,且“五情發而為辭章”,美好的辭章本于人的性情,“情”指的是人內心的情感。在劉勰看來文學創作就是以辭寫情,《文心雕龍》所謂“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3]1011,所謂“辭為肌膚,志實骨髓”[3]1038,所謂“綴文者情動而辭發”[3]1855皆是強調文學創作要以情志和言辭的關系作為基點。《明詩》篇說:“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173人的各種情感,受到四季變化、人事變遷的刺激而萌發,流瀉于詩文的字里行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4文章情理的流露要自然而然、純誠真實,不虛妄不矯飾。“情理位設,文采行乎其中”[3]1177,情感誠摯無比,文采也會隨即而來。因此寫作文章要盡力表現情志,如同繪畫講求色彩的糅合調配一樣,文章寫作“情交而雅俗異勢”[3]1119。顯然以辭寫情也要善于處理通與變,新與舊的關系,要通曉文情的變化,明了文章的各種風格,情感有了交錯融合,文章才會有雅俗體勢的不同。對于文學藝術來說情志(質)和言辭(文)必須緊密結合,“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義,密則無際,疏則千里。”[3]987思想情感要與言辭緊密結合,文章才能嚴謹不出差錯。情感的抒發是一個由積蓄到宣泄的過程,《詩經》中的《大雅》《小雅》之所以能使讀者感動,就在于真正抒發了作家積蓄良久的情感。劉勰批評漢代辭賦家過分追求華麗的文采,忽視了作家情志的真誠流露。漢代以后的文人作者學習漢代辭賦家,過分追求形式,“為文而造情”,進而導致了與《風》《雅》一類的“真美”“純誠”之文日離。但劉勰也在《情采》篇中列舉了莊周和韓非子講求文采和修飾的話,認為仔細研味《孝經》《道德經》《莊子》《韓非子》這些經典就可以發現它們所主張的是文章的華麗或樸實依附于人的真實情感,反對的是過度的文飾,寫作文章的根本法則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3]37,以辭寫情做到“銜華佩實”,即是劉勰所述“為情而造文”。
三、文以行立,行以文傳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1]272文學創作既要本于人的真實情感,又要“止乎禮義”。“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辨異”,以“禮”框“情”,既可使文章符合儒家倫理道德又保持雅正的文風。依經立義是劉勰文論體系的話語模式。“光彩元圣,炳耀仁孝”[3]30、“情感七始,化動八風”[3]229、“君子宜正其文”[3]251,所謂“仁孝”“化動八風”“正”都是指儒家的倫理道德之真,“文以行立,行以文傳”[3]85強調文章和德行相濟相成,德性優先,誠意為文。因而“修辭立誠”之“誠”在情感之真之外還應包括儒家的倫理道德之真,使文章內容符合儒家倫理道德。
六朝以來,形式主義文風越來越嚴重,文人作者越來越忽視文章的內容,離文章之根本越來越遠。深受儒學影響的劉勰想要返歸三代雅正文風,他“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3]1922,闡述為文之道,在師法上效仿圣人,在體制上宗法于經典著作。劉勰認為《五經》是一切文章、言論的始祖,承載著天地人三才的常道。同時《五經》文章具有華美的文采,《五經》之文為后世文章建立起了最高標準,“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3]83-84“不詭”“不雜”“不誕”“不回”“不蕪”“不淫”一字以蔽之就是“誠”,“誠”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情感的真誠、充實,還“必須充分注意其對真情實感和儒家道德的充滿張力的雙重指涉”[10]。劉勰顯然是繼承了儒家“有德者必有言”,德性優先、誠意為文的為文之道。孔子將德行與文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文辭、德行、忠誠、信義四項內容來教導學生。在《論語·八佾》篇中,孔子與子夏在討論《詩經》中的詩句時,孔子云:“繪事后素”,即繪事后于素,先有潔白的底子才能繪畫。朱熹作注云:“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11]。《論語》中有“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12]禮樂制度的核心是人內在的仁德。孔子所期望的理想人格,須先具有美好光明的德行,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施行禮儀規范加以文飾,是由質到文的演進。劉勰認為情理是文章的經線,言語文辭是文章的緯線,情理端正了文辭才會暢達,“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3]1157。劉勰還注意到了文章創作過程中“奇”與“正”的關系問題。“奇正”一詞是《文心雕龍》中一組重要的美學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寇效信在《釋“奇正”》一文中認為劉勰所論“正”即是指:“文章思想內容的典雅純正。”[13]劉勰在《正緯》篇中云:“經正緯奇。”經指的是儒家的經典,這些經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3]56。文章的寫作要依經立義,在偏邪和正確之間按住馬轡確定前進道路的方向。作家在創作時要“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3]1171,確定好文章的價值標準,內容符合儒家經義,文章的文采才能夠顯現。劉勰并不排斥“奇”,在《辨騷》篇中認為屈原的楚辭“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3]163-164。“奇”是指文章的內容奇譎煒曄,作家只有做到“執正馭奇”方能“文不滅志,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于紅紫”[3]1171,既把文章內容寫得既誠摯無比,又使文采華麗漂亮。劉勰注重文人的品行修養,認為文章事理意義的淺薄和深刻,不應與作者的才能、氣質、學識、習染相違背,文學創作的主體“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作品受作家思想感情和個人性格支配。劉勰列舉了歷代十二位作家,他們的個性與作品風格相一致,如賈誼才氣英俊、意氣風發,他的文章就文思高潔而風格清麗;陸機為人矜持莊重,他的文章就思想感情繁復而辭意隱晦曲折。劉勰認為君子要努力學習知識,“進德修業”,成為有文有質,內心充實飽滿,文采彪炳照耀的“梓材之士”。
《文心雕龍》“修辭立誠”觀理論淵源于先秦。劉勰依經立義,將“修辭立誠”觀貫穿全文,不僅從文體論的角度論述《祝盟》之作要“務實”“知信”表達出對神明的虔誠,還從創作論的角度談論一般文學作品的創作既要真誠地表達出情志,又要符合儒家的倫理道德,“修辭立誠”觀對當下的文藝創作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價值,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