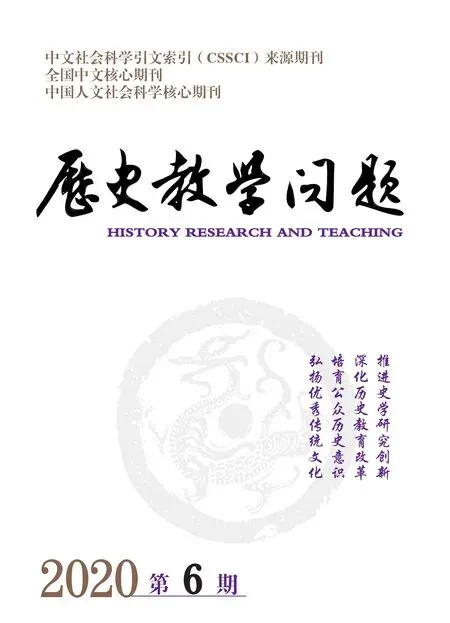《毛澤東選集》在中國的大眾閱讀(1949—1966)
楊 林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然而在建政伊始,如何穩定新政權,成為擺在新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大難題。新中國政府明白,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思想上都接受其領導,必須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新中國早期(1949—1966 年),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毛澤東選集》在全國統一出版、大力發行,不斷掀起閱讀熱潮。這是新中國早期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范圍內普及毛澤東思想的開端。迄今為止,有關這一問題的相關研究已不少,但其重心主要在新中國早期《毛澤東選集》的編輯、版本以及學習運動上,①研究成果主要有劉金田、吳曉梅:《〈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1944.7—1991.7)》,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許新年:《20 世紀50—70 年代我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熱潮述評》,《河南社會科學》2005 年第1 期;楊鑫潔、祝彥:《1960 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與毛澤東思想學習高潮的掀起》,《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 年第1 期;李翠翠:《建國初期〈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的歷史價值及現實啟示》,西南大學2015 年碩士學位論文;李雪梅:《1960 年初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6 期。而關于新中國早期廣大人民群眾對《毛澤東選集》的閱讀問題,則關注甚少。近年來,閱讀史研究在國內外史學界興起。相比于書籍的傳統研究,閱讀史主要是以讀者為中心來考察書籍,側重探究書籍怎樣到達讀者手中,讀者如何使用書籍,以及讀者閱讀書籍后產生的文化意義等。②韋胤宗:《閱讀史:材料與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18 年第3 期。本文擬以閱讀史的理論方法,再現新中國早期《毛澤東選集》大眾閱讀的復雜圖景。
一、大眾閱讀的準備
早在1940 年代后半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發動廣大人民群眾閱讀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作為“思想領域的解放戰爭”。③聶莉莉:《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新中國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及其周圍》,聶曉華譯,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37 頁。在當時的解放區,曾經有多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出版和發行,以供讀者閱讀。
新中國成立后,軍事領域的解放戰爭漸漸結束,但思想領域的解放戰爭實際上還在強力推進。在此背景之下,中共中央決定開展面向全國人民的《毛澤東選集》大眾閱讀運動。作為大眾閱讀的準備,中共中央決定統一《毛澤東選集》的版本、出版與發行。1950 年5 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負責《毛澤東選集》出版的編選等工作。實際上,毛澤東親自選定篇目,進行校閱,補充文稿,整理文字,加寫和修改題解和注釋。同年,中共中央決定將新華書店作為統一的國家發行機構,重點發行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1951 年4 月,《毛澤東選集》開始陸續發稿,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①陳矩弘:《新中國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108—123 頁。
與此同時,作為《毛澤東選集》大眾閱讀的準備,各級機構在新中國早期還通過各種措施向廣大人民群眾推銷該書。其一,實行“預訂制”。1952 年,《毛澤東選集》的出售開始實行預訂制。到1960 年,文化部下令,對于執有《毛澤東選集》各種預訂憑證的讀者,新華書店“必須保證供應”。②《關于〈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發行工作的通知》(1960 年5 月28 日),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編印:《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58—1961)》,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1982 年,第224 頁。其二,落實“雙軌制”。1953 年,新華書店開始通過采取“雙軌制”系統繞過其銷售網點來向農村擴展銷售渠道,即“雙軌制”要求商場、地方零售點和供銷合作社按照8%的提成比例銷售書籍。這些“經銷商”依賴于全新的供貨渠道,極大地擴大了客源。③丹尼爾·里斯:《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秦禾聲、高康、楊雯琦譯,唐少杰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103 頁。其三,提供補貼。1951年,新華書店規定,對于一部分無力購買《毛澤東選集》的機關干部,“由國家出版機關酌量予以書價補貼”。④《一九五一年出版工作計劃大綱(節要)》,《人民日報》1951 年2 月25 日,第6 版。其四,刊登廣告。早在1951 年全國各報紙、期刊上就開始刊登《毛澤東選集》的廣告。到1960 年代初,文化部規定各地新華書店在當地黨委宣傳部和文化(出版)局直接領導下,成立《毛澤東選集》發行宣傳小組,負責刊登廣告等宣傳工作。⑤《關于〈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發行宣傳工作的通知》(1960 年9 月16 日),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編印:《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58—1961)》,第227 頁。其五,推廣輔助性讀物。新中國早期,全國各地還出版發行了大量輔助讀者閱讀《毛澤東選集》的資料,如《〈毛澤東選集〉名詞解釋》《學習〈毛澤東選集〉第4 卷的輔導材料》《〈毛澤東選集〉中的成語故事》等。⑥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編:《〈毛澤東選集〉名詞解釋》,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 年;山西日報政教理論部編寫:《學習〈毛澤東選集〉第4 卷的輔導材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 年;甘肅師范大學政教系編:《〈毛澤東選集〉中的成語故事》,甘肅師范大學政教系,1964 年。
抑有進者,對《毛澤東選集》大眾閱讀準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新中國早期各有關部門也及時予以糾正。新華書店曾在1952 年大量增印《毛澤東選集》,但是全國各地尤其是農村卻出現《毛澤東選集》存貨太多的情況,新華書店很快就檢討自己在發行工作上“仍有很大的盲目性”,并及時調整發行數量。⑦《出版總署關于〈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積存問題向胡喬木等的匯報》(1952 年12 月27 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2 年)》,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年,第378 頁。又如1960 年,當文化部了解到一部分發行人員在發行《毛澤東選集》時存在著“接待讀者不熱情、不耐心”的現象時,立即給新華書店提出意見:“對目前暫時不能供應的讀者,要熱情地接待,耐心地解釋,說明由于印刷的數量很大,只能分批出版,分批供應;由于需要的人很多,只能逐步滿足。”⑧《關于發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服務態度的通知》(1960 年5 月28 日),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編印:《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58—1961)》,第229 頁。
在各方努力下,新中國早期《毛澤東選集》大眾閱讀的準備工作取得顯著成績。首先,在發行的版本上。《毛澤東選集》分平裝本、精裝本、袖珍本、普及本、單行本、合訂本以及供盲人使用的盲文版等多種形式印制發行。此外《毛澤東選集》還發行了蒙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藏文和朝鮮文等5 種少數民族文版。⑨詳見楊林:《〈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1950—1965)》,《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 年第5 期;楊林、張繼焦:《新中國70 年以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著作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 年第5 期。其次,在發行的數量上。根據1966 年的官方統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累計印數,約計一千萬部;六十五種單行本,共印六億一千余萬冊”。⑩《中共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于〈毛澤東選集〉印制發行工作的報告》(1966 年2 月21 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第50 冊,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44 頁。
二、大眾閱讀的行為
大眾閱讀的準備只是實現閱讀過程的基本前提,而具體的大眾閱讀行為才是閱讀過程的正式環節。在考察大眾閱讀的行為前,值得關注的是讀者閱讀的積極性。廣州的新華書店曾見證了讀者踴躍購買《毛澤東選集》的場景:1951 年10 月12 日,該店始售《毛澤東選集》,當天上午九時,該店“鐵閘邊已擠著一大群讀者”,“百數十雙眼睛注視著書店內的忙碌情景,有些人焦急地不時看手表。讀者愈來愈多,讀者們怕擁擠,自然地主動地列起隊來。一個工人說:‘你店的鐘慢了兩分鐘。’十時正,鐵閘一拉,讀者跑步進門,一面鼓掌歡呼。一個讀者情不自禁地握著工作同志的手說:‘同志你好啊!’讀者與同志們的心情融和在一片歡笑中”。①《作〈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發行工作總結》(1951 年10 月),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04-3-113-007-010。又據1960 年《人民日報》報道,江西省南昌市圖書館存有10 冊《毛澤東選集》,“這十冊書幾乎輪流不息地被讀者借閱著”。②《江西省圖書館的做法好》,《人民日報》1960 年11 月17 日,第8 版。由此可見,新中國早期廣大人民群眾閱讀《毛澤東選集》的積極性非常高。
讀者獲得《毛澤東選集》后,就轉入了正式閱讀的環節。就《毛澤東選集》的閱讀形式來看,首先可分為集體閱讀和個人閱讀。集體閱讀的形式,主要表現為學習班、學習小組和講用會等。如1951 年6月,西南局開辦《毛澤東選集》學習班,學習班上的干部必須閱讀《毛澤東選集》,并撰寫讀書報告。③《中共中央批轉西南局關于在職干部學習實施辦法的規定》(1951年8月17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冊,第440—441頁。又如1950 年代后期,吉林省延安縣東盛人民公社的婦女們組織了59 個《毛澤東選集》學習小組,共413 名婦女參加。④《婦女學習毛主席著作情況》(1960 年3 月30 日),吉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0016-1960-0013-0001。除此之外,至遲到1950 年代后期,全國各地的一些工人和農民還組織了《毛澤東選集》講用會。讀者先閱讀《毛澤東選集》,然后在講用會上給大家分享如何用毛澤東思想來解決自身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問題。⑤《廣東省工交系統毛主席著作學習動態(2)》(1965 年11 月26 日),廣東省檔案館藏,221-2-163-008-012;《〈毛主席視察過的杜湖村〉——舉行田頭“講用會”暢談學習毛主席著作體會》(1959 年12 月31 日),哈爾濱市檔案館藏,檔案號XD102-001-0041-002。需要注意的是,官方組織的《毛澤東選集》的集體閱讀一般都有閱讀時間的規定。1960 年,海南區黨委宣傳部就規定,海南直屬機關部長以上干部每月必須有3—4 天的專門時間集體閱讀《毛澤東選集》,市、縣委、廠礦、企業、事業黨委干部則每月不少于3 天。⑥《區黨委批轉區黨委宣傳部關于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意見》(1960 年11 月18 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14-1-250-018-019。1964 年河北省對干部集體閱讀《毛澤東選集》的一份規定還表明,閱讀進展落后者要受到組織的督促。⑦《南宮縣委中心學習小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情況(初稿)》(1964 年4 月3 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864-1-335。不過,民眾自己組織的《毛澤東選集》的集體閱讀,時間安排上就相對自由。一位叫侯永祿的農民在1965 年的日記中就記載了他們一群農民經常抽空一起集體閱讀《毛澤東選集》。⑧侯永祿:《農民日記——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 年,第143 頁。與集體閱讀相對的是個人閱讀。實際上,新中國早期廣大人民群眾以個人閱讀形式自學《毛澤東選集》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雷鋒對《毛澤東選集》的閱讀,在此不贅述。
《毛澤東選集》的閱讀形式,又可分為通讀和選讀。通讀是一種對讀者要求較高的閱讀形式,要求讀者讀完《毛澤東選集》全書。1963 年中央高級黨校曾設立面向黨員干部的普通班和高級研修班,要求學員“通讀”《毛澤東選集》。⑨《中央批轉林楓關于中央高級黨校工作問題的報告》(1963 年5 月21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57—1992)》,學習出版社,1996 年,第290 頁。根據宣傳部門的解釋,之所以對一些干部人員提出通讀《毛澤東選集》的要求,是為了讓他們“比較全面、深刻地學習毛澤東思想”。⑩《關于通讀〈毛澤東選集〉的學習提要(初稿)》(1964 年3 月),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5-4-285-099-104。《毛澤東選集》四卷部頭很大,通讀完需要相當精力,但民眾自愿通讀完《毛澤東選集》的積極性頗高。1960 年代初,湖北畜牧獸醫學校評選“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該校教師蔣賢文就因將《毛澤東選集》通讀多遍,同時又頗有心得見解而被評選上“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毛選學習積極分子材料》(1965 年10 月18 日),湖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SZ107-02-0269-003。選讀是相對于通讀的一種閱讀形式。新中國早期,中共杭州市婦聯支部委員會就曾制定一份面向組織內部的《關于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初步計劃》,要求組織成員都選讀《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哲學文章,而對通讀《毛澤東選集》全書則不作硬性要求。①《關于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初步計劃》(1960 年3 月23 日),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J127-001-074-017。其實,讀者讀懂《實踐論》和《矛盾論》等哲學文章需要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因此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一些群眾則青睞于選讀《毛澤東選集》中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通俗易懂的三篇文章,其又被稱為“老三篇”。需要注意的是,通讀和選讀也會出現于同一次的《毛澤東選集》的閱讀活動中。1960年,共青團廣東省委在給下級各部門下達關于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指示中,提出讀者在閱讀《毛澤東選集》時應分不同對象有不同要求,一些職務較高的干部需要通讀全書,其他干部和工農青年中的學習積極分子則有重點地選讀即可。②《關于組織青年學習和宣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指示》(1960 年10 月4 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32-1-46-111-112。
《毛澤東選集》的閱讀形式,還可分為精讀和粗讀。精讀對讀者的閱讀要求也較高。1964 年,中央規定從縣(團)委一級以上的干部,都應該精讀《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哲學篇章。③《中央關于縣以上干部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的決定》(1964 年8 月14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57—1992)》,第367 頁。既然有精讀,相對來說就有粗讀。1952 年,一位讀者在給《人民日報》的來信中說,他決定要學習《毛澤東選集》,計劃將書“先粗讀一遍,然后精讀。粗讀時在書端上寫眉批,精讀后寫學習總結”。④《讀者來信》,《人民日報》1952 年8 月13 日,第2 版。
除此之外,《毛澤東選集》還有朗讀和聽讀等閱讀形式。新中國建立前,我國教育幾乎為社會上層子女所壟斷。⑤參見梁晨、李中清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又根據官方的統計,新中國建立的1949 年,我國成人文盲率高達80%,而到1960 年代中期則下降到了57.3%。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組編:《共和國教育50 年(1949~1999)》,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290 頁。對文盲比例的大幅下降,《毛澤東選集》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配合掃盲運動的開展,新中國成立后在廣大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群眾中產生了聽讀《毛澤東選集》的形式。一般是負責宣傳教育工作的基層干部、學校教師或者聽讀者的親朋好友給他們朗讀《毛澤東選集》,聽讀者結合識字,在不斷解決《毛澤東選集》的生字和難句中理解毛澤東思想。⑦積極組織農村青年學習毛澤東著作》,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32-2-217-83-85。
綜上所述,新中國早期《毛澤東選集》大眾閱讀的讀者涵蓋了廣大干部、黨員、軍人、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群眾,其中工農群眾是閱讀的主要群體;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們創造了集體閱讀、個人閱讀、通讀、選讀、精讀、粗讀、朗讀和聽讀等多種閱讀形式。
三、大眾閱讀的衍生意義
新中國早期廣大人民群眾閱讀《毛澤東選集》,又衍生了怎樣的意義呢?閱讀史研究者往往認為,文本的意義是在閱讀中決定的,而不是由文本本身決定的。⑧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107 頁。澳大利亞的毛澤東研究專家尼克·奈特也提醒研究者在考察毛澤東著作的文本時,要注意到“讀者從來就不會是文本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讀者是從文本中提取意義的能動中介”。⑨尼克·奈特:《再思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探索》,閆方潔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18 頁。總的來看,讀者閱讀《毛澤東選集》衍生的意義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確立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新中國早期,在《毛澤東選集》大規模出版傳播的態勢下,廣大人民群眾接受毛澤東思想確實有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但是,廣大人民群眾確立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絕大多數卻是真心實意的。作為著名歷史學家的陳垣,他在民國時期就有一套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但在新中國建立后卻很快就表示服膺毛澤東思想。1954 年,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說,“解放以后,得讀《毛澤東選集》,思想為之大變,恍然前者皆非,今后當從頭學起”,并勸友人“當法韶山”。⑩《陳垣致佚名函》(1954 年),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796 頁。這正應了研究者所說,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代表人物們“便將自己的社會思想和歷史觀貼上了‘舊思想’的標簽封存起來,取而代之的,是名為‘新思想’的共產黨的思想方法”。①聶莉莉:《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新中國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及其周圍》,第14 頁。相較于陳垣這些長期任教于民國大學的知識分子,在中共幫助下實現當家作主的廣大工農民眾則更易于接受毛澤東思想。1960 年,哈爾濱制糖廠的一位叫王賢貴的工人給組織提交了他用十年的時間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體會:“十年來我在黨的培養教育下,認真學習了毛主席著作,逐步提高了階級覺悟……特別是在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給我很大的啟示,更感到毛澤東思想的空前偉大。”因此,“毛澤東思想是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1960 年),哈爾濱市檔案館藏,檔案號XD012-001-0463-018。
第二,將毛澤東思想作為行動指南。確立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后,將毛澤東思想作為行動指南是對讀者的更高要求。其實,隨著一波又一波《毛澤東選集》閱讀熱潮的掀起,黨政軍民學等各方面的廣大人民群眾都已經積極將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據《人民日報》報道,1951 年“三反運動”在全國發動后,各級干部“訂立了個人的學習計劃,開始研究《毛澤東選集》一、二卷有關‘三反’運動方面的文獻”。③《認真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人民日報》1952 年7 月20 日,第3 版。可見各級干部是在閱讀《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去推動“三反運動”的。又如,1960 年代初,民建廣東省工委等機構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提到,在開平縣政府動員人民群眾支援農業水利事業時,不少群眾存在畏難情緒,但是當他們閱讀了《毛澤東選集》中的“老三篇”后,決定服從分配和完成任務。④《開平縣家屬學習毛選情況調查報告》(1960 年11 月7 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48-1-73-173-182。在當時廣泛傳播的閱讀心得中,廣大人民群眾總是強調要以“老三篇”中張思德和白求恩無私奉獻和愚公不畏艱難的精神來指導自身工作上的問題。
第三,堅定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認同。新中國建立之際,部分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還不了解,可能對中國共產黨持觀望甚至是懷疑態度,但是在閱讀《毛澤東選集》后,他們堅定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認同。據《人民日報》報道,1952 年《毛澤東選集》哈薩克文單行本翻譯出版后,天山草原的哈薩克牧民們說:“讀了《毛澤東選集》以后,心里就亮了,懂得了我們為什么會得到這種幸福的生活。”⑤《毛主席的著作在天山草原》,《人民日報》1952 年7 月7 日,第3 版。他們在閱讀《毛澤東選集》后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到19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后,湖北的一個公社在“工作計劃”中寫道將開展“貧下中農討論”,討論主題是貧下中農“如何學習好毛選,團結一心,搞社會主義”。⑥《細峪公社“四清”運動代表會記錄:生產科長的“四清”材料》,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民間史料集刊》第8 卷,東方出版中心,2012 年,第77 頁。這就是在閱讀《毛澤東選集》中去努力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了。
顯然,廣大人民群眾閱讀《毛澤東選集》所衍生的上述意義都是積極的。“因為不滿舊中國的屈辱與舊政權的無能”,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人“張開雙臂擁抱了作為民族、國家的解放者降臨的共產黨和它所帶來的一切新思想、新觀念”。⑦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 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年,“前言”第25 頁。不過,新中國早期《毛澤東選集》大眾閱讀所衍生的意義,雖然積極的方面是主要的,但也存在著隱憂。從1950 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選集》的一些閱讀心得開始呈現出簡單化、庸俗化和“左”的不良傾向,或是“把某些科學、技術方面的創造、發明或發現,簡單、生硬地和毛澤東思想直接聯系起來”,⑧《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宣傳部關于毛澤東思想和領袖革命事跡宣傳中一些問題的檢查報告》(1961 年3 月15 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第36 冊,第354 頁。或是開始響應林彪所謂的“思想革命化”。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促進婦女思想革命化——覃巴公社吉兆大隊婦代會學毛著經驗》(1965 年11 月25 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33-2-332-71-75。《毛澤東選集》閱讀心得的這些不良傾向,使得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和嚴肅性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實際上也為后來毛澤東思想在“文革”期間逐步陷入困局乃至遭受重大挫折埋下了理論禍根。
結 論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中共一直比較注重發動廣大人民群眾閱讀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而新中國早期又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新中國早期,在中共統一全國的背景下,《毛澤東選集》在全國統一了版本、出版和發行。廣大干部、黨員、軍人、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群眾獲得《毛澤東選集》后,創造了集體閱讀、個人閱讀、通讀、選讀、精讀、粗讀、朗讀和聽讀等豐富多樣的閱讀形式。本文的研究表明,新中國早期《毛澤東選集》的這場大眾閱讀運動極具價值和意義。一方面,學界已指出19 世紀是西方全面興起大眾閱讀的時代,書籍不再為精英群體所獨享,普通大眾開始成為書籍閱讀的主要群體。①趙大川、施時英:《良渚文化發現人施昕更》,杭州出版社,2012 年,第195、197 頁。詳見2019 年4 月22 日《光明日報》刊發的一組關于大眾閱讀的文章,分別是景德祥著《19 世紀德國的“閱讀革命”》、宮艷麗著《英國大眾科學閱讀的興起》和顧杭著《十九世紀法國的大眾閱讀場所》。而中國完成這一閱讀革命則是在20 世紀中后期,其中《毛澤東選集》一書是推動這一閱讀革命的關鍵書籍。另一方面,正如高崢在研究新中國成立史時所言,“如果不去近距離地觀察中共重塑國人世界觀的過程,我們就不能夠理解在中共推動下大多數中國人是怎樣順利認同新政權及其革命目標”。②梁志成、黃宣佩執筆:《上海市金山縣戚家墩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3 年第1 期,第24、29 頁。高崢:《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干部蟬變(1949—1954)》,李國芳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年,“序言”第2 頁。實際上,通過考察新中國早期中共推動廣大人民群眾閱讀《毛澤東選集》的過程,可知這一過程對于民眾確立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并將之作為行動指南,以及社會主義國家認同的建構都有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