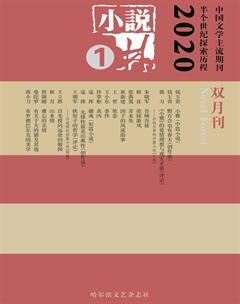難忘的親情
奶奶
我不知道奶奶年輕時候的樣子。上個世紀30年代初闖關東來到東北的山東掖縣農民的媳婦,也不可能會有一張年輕時候的照片。所以在我的記憶里,奶奶就是一個滿頭銀發,慈祥中又帶有一絲威嚴的老太太。
至今,奶奶雖然離開我們已經三十五年了,但她的樣子在我的記憶里仍十分清晰。奶奶個子不高,長著挺白凈的一張瓜子臉,兩只眼睛亮亮的挺有神,一頭白發從來都是一絲不茍。無論是縫了多少次補了多少次的舊衣服,在她身上總是利利索索。由于從小就裹了腳,穿著一雙只有十幾厘米長的尖頭小鞋,走起路來一顛一顛的。憑這一雙小腳,從遙遠的山東家來到東北,定是歷盡艱辛,也坐下了毛病,所以不到六十歲就拄上了拐棍。
算起來,奶奶應該是清朝光緒二十年生人,也就是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正好大我一個甲子,所以和我同屬馬。奶奶家姓丁,但一輩子沒有自己的名字。聽老一輩人講,奶奶姐妹兩個嫁給了我爺爺他們哥倆兒,所以姐兒倆都叫程丁氏。這也是在新中國戶籍上留下的舊時代的最后一批印記。
由于我的親爺爺去世比較早,奶奶領著大姑二姑和爸爸艱辛度日,吃盡了辛苦,也確立了她一家之主的地位,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她決斷。 聽爸爸說,奶奶沒有文化,認不了多少字,但全家人沒有一個人不佩服她的超人腦力。不要說全家人和所有親戚的生日記得清清楚楚,每個農歷的節令應該怎么過記得明明白白,就是后來家里面做加工糕點的生意,一本賬也全在她的腦子里面。該付誰家多少原料錢,糕點店還欠著家里多少貨款,一批貨做完了能掙多少錢,都算得一清二楚。這可能也是爸爸和我智商水平的基因來源吧。
我的記憶,就是奶奶在老房子里的一些事了。每天早上,她總是把一頭銀發打開,梳得絲滑柳順,在后腦勺處盤起一個發髻,再扣上一個黑色的塑料發卡。一雙小腳仔仔細細地纏上白色的裹腳布,褲角還要用黑色的布帶扎起,再套上她那雙任何人都無法企及的小鞋。我小時候最好奇的一件事就是看奶奶裹腳,我實在不明白,為什么奶奶除了大腳趾之外的四個腳趾都要纏到腳底下,直到懂事以后才知道那是舊社會對婦女殘害的結果。
一家人吃飯的時候,奶奶總是坐在正北面南的炕沿上,給我和妹妹拿吃的,給全家人夾菜,活脫脫一副母系社會的族長形象。我老爸直到現在還沒改過來的這個習慣,肯定是從奶奶那里繼承過來的。
奶奶喜歡養花,每當春天到來時,她總要在我家唯一一個朝南的窗前煤箱子上擺上一些花盆,種上鳳仙花、地瓜花、蜘蛛花、玻璃翠、爬山虎等各種草本花卉。花開季節,她就會護花使者一樣,一天不知巡視多少次。每當看到我蹲在煤箱子上擺弄她心愛的花草,她就會大呼小叫地顛到屋里窗前,做著要打我的手式,直到我跳下煤箱子逃走。
由于從我爸爸到我這輩兒,我們家都是一個男孩,奶奶對我從小就不錯眼珠地看著。記得媽媽和我說,我小時候有一次把奶奶嚇壞了——到了吃飯的時候屋里院里都找不到我,奶奶拄著拐棍都跑到大街上去了,全家人也都出去四處找我。可回來一看,我正蹲在廚房的鍋臺上一聲不響地研究灶王爺吶,嚇得奶奶連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剛上學的時候,奶奶每天都是看著我吃好飯,幫我穿好衣服,一直送到大門口,看著我上學。每天下午,我快放學了,奶奶都會拄著拐棍到大門口等我回來。院里的鄰居一看到我奶奶站在大門口,就會打趣地說,又等大孫子回來吶?
我永遠忘不掉的,是奶奶的兩件事。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我已經上小學了。由于口糧不夠吃,全家每月的糧食都要算計著用,經常要吃摻了甜菜渣滓、榆樹葉子或菜葉子拿不成個兒的玉米面窩窩頭。等到放寒假的時候,家里連往玉米面里摻的東西都沒有了。一天吃早飯的時候,奶奶端上來幾個藥針盒大小的玉米面餑餑,告訴我和妹妹,家里這個月的糧食不多了,得省著點兒吃。每人分一個小玉米面餑餑,今天早晨和中午要分兩頓吃。只知道貪玩的我和妹妹哪管那些,我們兩個一商量,早晨都吃了,咱中午就不吃了唄,三口五口就把那個小餑餑吃了。等到中午吃飯的時候,出外瘋玩了一上午的我面對著那一碗稀溜溜的苞米面粥才有點兒傻眼。這時,奶奶又從干糧筐里拿出了一個小玉米餑餑,從中間掰開,給了我和妹妹一人一半兒。等我們大口小口地吃完,才想起來問奶奶,你怎么不吃吶?奶奶說,我不餓。我這才明白,我和妹妹吃的是奶奶早晨和中午的口糧!雖然那時我只有七歲,心里也感到了一陣莫名的顫動。
令我永遠也忘不了的是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我為了考上大學沒日沒夜地復習,幾乎拼盡了全力。已經病重臥床的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經常叮囑我千萬注意要“勞逸結合”,別累壞了。兩輪考試結束,全家人都在緊張地等待考試結果,奶奶也進入了生命的最后階段。到1978年初的農歷臘月,奶奶病勢愈加沉重,隨時好像就要離我們而去,可支撐她堅持下去的唯一動力,就是和全家人一塊兒等我的大學錄取通知。她一天不知要問爸爸媽媽幾次,孫子考上沒有啊?大學的通知來了沒有啊?這不僅對她是一種煎熬,對我是更大的煎熬。就這樣,從臘月,到第二年正月,她每天都是在這樣地問著,一直問到一陣明白一陣糊涂了。爸爸媽媽最后和我商量,奶奶恐怕真的等不到你的考試結果出來了,就告訴她考上了吧。沒有辦法,我只好懷著忐忑的心情,假裝欣喜地告訴奶奶,奶奶,我考上大學了!奶奶聽罷,攥住我的手突然間號啕大哭起來:我的孫子終于考上大學了!我們家也有大學生了!我的孫子沒白挨累呀!我不禁也和她一起聲淚俱下了。
從知道這個“消息”以后,奶奶好像松了一口氣,人也進入了彌留狀態。兩天之后的凌晨,終于永遠閉上了眼睛,離我們而去了。而那一天正好是農歷正月二十,我二十四周歲的生日!
我并不迷信,但我永遠搞不懂,是不是奶奶自己選了這樣一個日子離開我,好讓我記住她這個最疼最愛我的人!
爺爺
從稍稍懂事開始,就有一件事令我非常迷惑。那就是為什么爸爸、媽媽管我和妹妹的奶奶叫媽,卻管爺爺叫叔叔。等長大一些才明白,原來奶奶是我們的親奶奶,爺爺卻不是我們的親爺爺。(這快趕上《紅燈記》戲文了)我的親爺爺很早就故去了,現在的爺爺是和奶奶后走到一起的。
爺爺叫張紫臣,很文氣的一個名字,但人卻不很文氣。中等身材,白凈臉膛,少言寡語,臉上總是帶著和善的微笑。由于從小就在河北老家學徒做點心,很早就駝了背。聽奶奶說,解放前,我們家就是一個糕點作坊,爺爺做出來的點心,都是挑挑兒送到“老鼎豐”去賣。由于做生意實誠,各種真材實料從不打折扣,無論是各種京八件兒點心還是川酥、棗泥各種月餅都做得遠近聞名,成了“老鼎豐”長年的供貨點。解放以后,公私合營,爺爺成了老鼎豐糕點廠第一代的點心師傅。
爺爺對我這個長孫可以說比奶奶還偏愛。在最初的記憶里,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爺爺下班。因為他常常會從那油漬麻花的黑棉襖兜里掏出一塊油紙包著的小點心,偷偷塞給我,然后低聲告訴我,快點兒吃,別讓小惠兒(我妹妹的小名)看見。可惜好景不長,爺爺很快就退休了,我再也沒吃到過他親手做的點心。可他還是經常悄悄地買回一點兒爐果、餅干等小點心,放在炕上最高處的一個小紙盒里,晚上拉上幔帳睡覺前偷偷遞給我一小塊兒。(估計我齲齒的病根兒也是這么做下的)這好景,也就維持到三年自然災害之前。
由于我和妹妹就差不到兩歲,所以爸爸、媽媽管妹妹,我從小就和爺爺、奶奶睡覺。爺爺雖然沒什么文化,但老一輩人口口相傳的故事還是知道不少。每天晚上睡覺前,我都會鬧著讓爺爺給我講故事。從孔子門徒會鳥語的公冶長,到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大鬧天宮的孫猴子,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我講一段,直到我乖乖地睡去。
退了休的爺爺承擔起了給全家人做飯的任務。無冬歷夏,每天早晨不到五點鐘,他第一個起來,點爐子做飯,趕在爸爸、媽媽上班之前做好早飯,再招呼我起床,全家人一起吃早飯。記得1961年之前,市場供應還充裕一些,魚呀、肉呀、菜呀、副食品呀還不缺,家里的伙食也還不錯。等到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啥都憑證、憑票了,家里的伙食自然也“水落船低”。吃飯的時候,爺爺總是很少吃菜,老是沖著咸菜、醬豆、豆瓣醬使勁。奶奶、爸爸、媽媽勸他多吃點兒菜,可他總是笑瞇瞇地說,我口重,吃咸的有味。
爺爺最大的愛好,就是偶爾到街口的水果商店買一杯“比瓦”(俄語啤酒),買一小塊兒粉腸,給自己改善一下生活。記得我也就是六七歲的時候,爺爺遞給我一個白色的大搪瓷缸子和一點兒零錢,讓我到街口的水果商店給他打杯“比瓦”。我買回來后,看著爺爺無比舒服地喝著不禁好奇起來,問他“比瓦”好喝嗎?爺爺說好喝,你嘗一口。我捧起搪瓷缸子不管好歹就喝了好幾大口,那又苦又澀又殺舌頭的味兒嗆得我直咳嗽,又打了個大嗝,把爺爺逗得哈哈大笑。不大一會兒工夫,我的臉就紅了,暈暈乎乎地跑到屋里炕上就躺下了。奶奶過來看到我滿臉通紅,嚇了一大跳,還以為我感冒發燒了,一問才知道爺爺給我喝了“比瓦”,氣得奶奶把爺爺好一頓數落,怎么讓這么點兒的孩子喝酒呢?慣孩子也沒有這么慣的!(由此得知,我先天酒量極差,后來能喝點也是生練出來的)打這以后,我再也沒碰過“比瓦”,等再喝啤酒,已是工作以后的事了。
爺爺不愧是做糕點的師傅出身,在家里做飯絕對是一把好手。無論是蒸饅頭、蒸窩窩頭,還是烙餅、搟面條、搟面片,都做得十分可口。我最喜歡看他貼大餅子。家里還有大鐵鍋的時候,鍋里燉上湯菜后,爺爺把和好的玉米面團成扁圓形,朝鍋邊一個挨一個地甩著手貼上去,等燉菜好了,大餅子也好了,用鏟子把大餅子鏟下來,那金紅色的渣兒別提有多香了。
就這樣,爺爺承包全家的做飯任務一直持續到1969年的冬天。那年的冬天,特別的冷,爺爺有一天早晨沒有起來做飯,他突然發起了高燒。到醫院看病后,醫生說他得了肺炎,開了一堆連打帶吃的藥。但從那天以后,他昏昏沉沉地臥床不起了。大家都以為他這次可能逃不過這一劫了。可一個多月后,他突然自己在炕上站了起來,麻利地穿好衣服,說要出去到同記商場取訂做的帽子。全家人都傻眼了,不知道這是出了什么狀況。沒辦法,奶奶只好讓我跟著他去了同記商場。到了商場柜臺前,他就向營業員要他訂的帽子,弄得營業員一頭霧水,反復向他解釋商場沒有訂帽子這個業務。
我好說歹說才把爺爺勸回了家,大家這才明白,原來爺爺“糊涂了”。我不知道這種高燒后的“糊涂”是不是現在說的老年癡呆癥,反正從那以后爺爺就管奶奶叫媽、管我叫二哥了。 糊涂后的爺爺除了再也不認識所有的人,身體其他方面反倒恢復了正常,只是性格一反從前,一向和善的他在院里經常提著拐棍嚇唬小孩,弄得院里的孩子見著他就跑。在家里除了對我和奶奶從不發脾氣,聽我倆的話,對其他人都沒有好氣兒。一次,媽媽在屋里調豆腐粉做的豆漿準備做豆腐腦,他從外邊回來看到盆里被攪得冒泡的豆漿,掄起棍子照媽媽頭上就是一棍子,嘴里還惡狠狠地罵著,想要藥死我們哪?
那時我已經參加工作了,也從爺爺、奶奶住的炕上搬了出來,自己住一張木床。干了一天的活兒本來很累了,可爺爺天天凌晨兩三點鐘就在炕上喊,關老爺來了!日頭爺快出來吧!弄得全家天天睡不成囫圇覺,他自己的身體也一點點地衰弱了。
這樣的日子,我們家過了好幾年,直到又到了一個寒冷的冬天,他早上又一次沒起來。這次,也是他永遠起不來了。
父親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時候開始記事的,但在我記憶的深處,總有那樣一個“畫面”揮之不去,像壓在心頭的一片陰影。
那是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晚上。平時熱鬧的家里寂然無聲,爺爺奶奶一句話也沒有,媽媽悶坐在床上,妹妹乖乖地偎在她身旁。家里所有的燈都沒有開,只有里屋門口對面的那張桌子上的臺燈開著,爸爸一聲不響地坐在那里。臺燈只照到了他臉的下半部。從后面看去,他的身子像就是一個巨大的陰影。
后來才知道,那一天是1958年的4月28日。一個決定了爸爸的一生和我們家幾十年生活軌跡的日子。這一天,我爸爸正式被學校宣布為“右派分子”。
稍稍懂事以后,我才知道“右派分子”是什么。
爸爸從第四中學的團支部書記、第一入黨積極分子,一夜之間被劃到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陣營里。中學三級教師被拿下,取消了他深愛的歷史教學資格,下放到校辦工廠。工資也從一百零一元降到了七十元。
媽媽由于爸爸的事也受到了牽連。入黨積極分子的資格被取消;政治工作隊成員被拿下;已經是全市小學著名教學骨干的她,消失在了公開教學的課堂上。性格溫柔、情感脆弱的媽媽從此得上了一種怪病,只要稍受刺激就會嗚嗚大哭,繼而抽搐昏厥。醫院后來診斷為較嚴重的精神官能癥。這是為什么?爸爸究竟犯了什么樣的錯誤?爸爸對外人是諱莫如深的,但只要家里來了真正的親戚和朋友,他卻像祥林嫂一樣,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痛說他的冤屈歷史。所以我對他說的這些“冤屈”也耳熟能詳了。
那是反右斗爭的末期,各單位都在按照上級下達的指標落實右派分子的名單。可大多數地方的指標還沒有完成,只好再次發動“大鳴大放”,加大力度“給黨提意見”。當時第四中學的領導找到了時任團支部書記的我爸,讓他再次組織廣大團員給黨提意見。我爸當即召開了一個團員骨干會議,號召大家敞開思想給黨提意見。我爸現場做記錄,連自己提出的意見和團員提出來的有價值的意見整理成一篇稿件,回家后用毛筆寫成大字報,第二天就在學校張貼出去了。
用我爸的話來說,這張大字報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一些呼聲。意見引經據典地提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從19世紀開始,沙皇俄國就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璦琿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侵占了中國16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寧同志在其著作中也對沙俄的這種野蠻行徑進行過譴責。現在中俄兩國交好,并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我黨應該向蘇聯領導人申請領土權利,要求蘇聯歸還沙俄侵占的中國領土。為了“顯示”他的專業素質,老爸還特意手繪了一幅中國地圖及三個不平等條約侵占的部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內容被扣上了“破壞中蘇友好”的罪名,和爸爸一起提意見的兩個歷史組的老師也被打成了“右派言論”。
十年之后,我爸祥林嫂似的傾訴又碰到了一個爆發點。1968年中蘇邊境發生爭端。珍寶島自衛反擊戰開始以后,我中央媒體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我爸1958年給黨提意見大字報的內容。文章義正詞嚴地譴責當年沙皇俄國利用不平等條約侵占中國領土的罪惡行徑,連配發的地圖都和老爸當年所畫地圖毫無分別。我老爸拿著登有這篇文章和地圖的報紙,腦袋晃得像撥浪鼓一樣:怎么我當年說這些事就是右派,現在報紙上登這些又是正確的了呢?
雖然爸爸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無形的“帽子”卻讓他和我們全家又戴了二十年。包括我和妹妹,從此也被貼上了“右派子女”的標簽。
“文革”期間,我們家最擔心的就是“舊賬重算”。雖然學校里大字報的批判沒落過兒,大院里的木門上也被寫上了“打倒大右派”的粉筆字口號。但大院里的鄰居們沒有挑事的,學校里的學生領袖喜歡爸爸的教學,尊重他的學識,硬是把他從批斗名單中拿掉了。當時學校一個紅衛兵領袖還曾找到我爸,跟他說,你歷史問題的檔案我們都找來看了,你當年提的意見沒有錯,不應該是右派。老爸作為一個有歷史問題的歷史老師在學校沒挨過批斗,我們家也沒被抄過家,這在當時簡直就是一個奇跡。
從我上學、參加工作填寫的第一張登記表開始,在“有無家庭歷史問題”一欄里,我都要老老實實地填上,父親在1958年被打成過右派。就是因為這一“家庭歷史問題”,不僅我爸爸自此與加入中國共產黨無緣,我媽媽虛掛了十八年的入黨積極分子,連我也是黨組織甚至是團組織慎重考慮的對象。
我從參加工作開始就“上進心比較強”,這可能是“胎里帶”的毛病。可我爸的歷史問題,卻讓我一步一個坎兒。到第一工具廠當工人以后,我三個月就離開師傅,一個人獨立操作把床子干活了,而且成品率在班組里名列前茅,可新徒工入團的名單里總排不上我。等到好不容易入了團,也當上了車間團支部副書記,入黨積極分子的名單里還是排不上我。直到我大學畢業到哈爾濱日報工作后,1985年8月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我已經三十周歲了。
最讓我屢受打擊的就是廠里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我很早就是我們車間的青年技術骨干,車間領導和師傅們都非常喜歡我的聰明和好學,認為我是技術上的好苗子,所以一有機會就推薦我上大學深造。可年復一年,名單報上去很快就被刷了下來,原因就是我有“家庭歷史問題”。我們車間主管技術的副主任曾到廠長辦公會上據理力爭,還是沒有辦法。和我一起入廠的徒工,當上工農兵學員都大學畢業返廠了,比我知識水平差而政治條件比我好的師兄弟也上了大學,我還是在工廠的機床上“搖搖把兒”。這種壓抑,這種氣悶,豈是用語言能表達清楚的?
鄧小平“撥亂反正”,徹底為右派平反之后,我們家才真正從“家庭歷史問題的”陰影中擺脫出來。時隔二十年之后,爸爸、媽媽用他們半生的努力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爸爸已五十三歲,媽媽四十七歲。打那以后,我們家的日子才算是“咸魚翻身”了。那時,我已經考上了大學。爸爸入黨當年就被推選為“優秀共產黨員”,并很快被評為“全國優秀班主任”;媽媽也當選“市勞動模范”,并首批被評為哈爾濱市的“特級教師”。院里的鄰居們都說,你們老程家這兩年真是喜事一個連著一個呀! 可我們全家都知道,我們家的好事是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分不開、是和改革開放分不開、是和小平同志分不開的。
表妹
我一直在猶豫是不是寫這樣一篇東西。因為寫了,等于在表妹的傷口上撒鹽,她看了肯定要難受。可不寫,她是最后一批離開大院的住戶,也是大院里身世和經歷最離奇最坎坷的人。好在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表妹雖然說不上現在已心靜如水,但她鋼絲一般的神經在經受了這些磨難之后,已變得更加堅韌,現在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已經像在講別人的故事了。
表妹1954年生人,和我同齡,是二姑和二姑父的女兒。但她是在六歲時才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記得她剛來到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時候,穿著一件毛衣外套,戴著一頂毛線織的圓形小帽,進屋不久就喊著要“灑水”,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來才知道南京話“灑水”的意思就是要尿尿。好幾天,我和妹妹見了她就頑皮地喊:我要灑水!
我突然多了個表妹,妹妹突然多了個表姐,我們兩個當然都很興奮。爸爸媽媽跟我倆說,二姑和姑父一直沒有小孩兒,二姑父在南京的三弟家孩子多,就把他最小的女兒過繼給二姑、二姑父做女兒。在山東人的老習慣里,兄弟之間過繼孩子是很正常的事。對表妹來說,大大成了爸爸,爸爸成了三叔,也只不過親人的位置換了一下。
表妹從小長得就不算漂亮,一看就是一個南方小女孩兒,但性格卻像個男孩子。到了我家,很快就和我和妹妹“打成一片了”。在院里玩兒的時候,她和女孩子在一起玩兒的時候少,卻和男孩子一起瘋淘的時候多,什么跑樓梯,抓人兒,跑起來一般的男孩子也追不上。她到我家以后很快就到附近的育民小學上學了,可這個女孩子上學還真是不太讓人省心,到了學校里和人打起架來,男生女生都不在乎,隔幾天就讓老師把家長找到學校一回。她叫盛蘭軍,院里的孩子后來給她起了個外號叫“齊天大圣”。一個女孩子能得到這樣一個“封號”,能淘成什么樣就可想而知了。
但表妹在家里和我和妹妹相處得卻非常和睦。表妹來之前,我和妹妹就是對立面兒,表妹來了之后,就是“會兒”,今兒個跟我一伙,明兒個跟我妹一伙,三個人打打鬧鬧地更熱鬧了。冬天出不去屋的時候,我們三個就是玩伴兒,寫完了作業,有時在二姑的家里一玩兒就是半天。二姑和二姑父老來得女,對表妹這個女兒格外寵愛,院兒里的孩子們也都知道,這個大院里唯一的獨生女是老盛家抱養的孩子,誰也不欺負她。那時候,表妹應該是大院孩子們中最享福的了。不用說別的,一直到都工作了,表妹不管啥時候回來,都能喝上二姑和二姑父晾好的放了白糖的涼白開。
時間過得飛快,我們三個在大院里長大了。妹妹和表妹都長成了身高一米六八的大姑娘。我到第一工具廠工作以后,妹妹到道外鉆石工具廠工作,表妹也到了道外金屬表帶廠工作,哥兒仨全成了“工人階級”。 那時候的金屬表帶廠雖然只是三輕局的一個廠子,規模不大,但經營得也還算衣食無憂。表妹性格直爽、干活潑辣,很快成了工廠里的骨干工人。由于她生性好動,身體素質好,很快成了工廠女籃隊員,經常出去打比賽。就這樣,很快和廠里男子籃球隊的一個小伙子好上了,這就是我現在的表妹夫劉克靜。
表妹是我們哥兒仨中第一個談婚論嫁的,妹夫家也是老道外一個工人家庭的孩子。妹夫家人口多房子小,沒地方給他們結婚。二姑父和親家商量后,把一室半的舊房子硬是間壁出兩間小屋,表妹和妹夫就在我們大雜院兒的老房子里成親了。表妹是1979年結婚的,第二年就給我們家添了個大胖小子。緊接著,妹妹1980年也結婚了,第二年我親外甥也出生了。我是1981年在老房子里結婚的,兒子也是第二年出生。就這樣,我們哥兒仨挨肩兒給大雜院添了三個第三代的男丁,只不過我這個當大哥的,兒子卻成了小表弟,表妹和妹妹的兒子成了大表哥、二表哥。這三個小子從一個門兒里晃晃悠悠地跑出去的時候,大院里的鄰居都羨慕不已:你看看人家,這孩子咋都這么會養呢?
1985年,二姑父去世不久我們就搬出了大院。表妹和妹夫伺候著逐漸衰老的二姑仍然生活在大院里。那時候二姑已經一時明白一時糊涂,有時竟神經兮兮地說家里土暖氣的管子里藏了什么東西。但我和媳婦每次去去看她的時候,她看上去十分清醒,拉著我的手家長里短地問個不停,還直張羅著給兒子拿吃的。
以后,表妹和表妹夫工作的金屬表帶廠經營越來越差,最后關門兒倒閉了,我表妹和表妹夫雙雙成了下崗工人。他們兩個又分別找了臨時工作,供著上學的外甥,伺候著年老多病失去了自理能力的二姑,生活越來越艱難了。
就在表妹和妹夫和命運抗爭的過程中,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1996年,她在南京的爸爸去世了。可當表妹悲痛地趕到南京為她的爸爸送葬后,卻又知道了一件更為不幸的事情。大姐吞吞吐吐地向她說,有一件事現在必須告訴你了,其實我們的爸爸也不是你的親爸爸,你是曾經做幼兒園長的媽媽在幼兒園門口撿回來收養的一個棄嬰。我實在不敢揣測表妹聽到這件事情是什么心情?她一直以為是親生父母的人,居然也是她的養父母!
2001年,我已經搬到井街胡同報社新蓋的一棟小樓里住了。那是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回到家,見客廳里還沒有開燈。表妹和我媳婦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不知在說什么。見到我回來了,表妹流著眼淚哽咽著跟我說,哥,我今天在道外四院檢查出胃癌了,我還沒有告訴克靜和興華,這可怎么辦吶?我一聽也急了,這怎么搞的,怎么突然就得這個病了呢?她說,這半年多就總是胃疼,可干臨時工作的地方活兒又忙,沒時間去看。最近疼得厲害了,到四院去檢查,今天出來結果大夫就問我,你家屬呢?我一聽就不是好事兒,就跟他說,我沒家屬,什么事兒你就跟我說吧。大夫這才直接告訴了我檢查結果。我跟表妹說,你先別急,道外四院檢查的結果也不一定準,咱們再找個地方好好查一查,然后再決定怎么辦。
第二天我就找了省醫院最權威的胃鏡檢查專家給她再次做了檢查,結果出來之后,和四院的檢查結果一樣,“低分化腺癌”。再也沒有什么說的了,只能盡快手術。我讓同事幫著找到了當時腫瘤醫院的院長張啟凡,也是全國胃癌手術的專家,向他說了表妹的家境,請他盡量幫忙,親自給她做手術。可一個胃癌手術至少要幾萬元的醫藥費,表妹家兩個下崗職工如何承受得起?我主持了我們家的家庭會議,我妹、我媽、我堂妹、堂弟都伸出援助之手,各出五千元錢,我岳母和內弟聽說也拿出了一筆錢,我和我媳婦拿出兩萬元錢,給表妹湊齊了住院費用。手術的時候,張啟凡院長和龐達副院長兩個頂級專家為這個下崗女工一起上了手術臺,手術相當成功,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掃蕩了已經有些轉移的淋巴腺。
要不說“屋漏偏逢連陰雨”。表妹住院手術事情我們沒敢告訴二姑,大家在醫院忙活表妹的時候家里沒人了,表妹夫的媽媽都到家里幫忙照顧二姑了。可誰曾想就在表妹要出院的前夕,二姑在家里吃早飯的時候,一口氣沒上來就過去了。沒辦法,我只好做主不告訴表妹,求醫院推遲表妹的出院時間,我在家主事把二姑“發送”了。等過了些日子,才告訴表妹,二姑走了。她捂著還沒長好的肚子堅持去了東華苑寄存骨灰的安息堂祭拜了二姑,哭得淚人兒一樣。我媳婦直勸她,你得想開,這是二姑最后心疼姑娘一把,怕你得病以后還得費力照顧她,就自己先走了。
表妹手術之后,按正常治療程序要做化療。可她執意不肯。她說,做這個手術已經牽累了這么多的人,親人們已經救了我一次,下面就是聽天由命,再也不能牽累大家了。張啟凡院長看到表妹態度如此堅決,也尊重了她的意見,但向她推薦了另外一種治療方案。那時,國外的一個醫療單位正和腫瘤醫院搞一項合作,就是手術后不做化療,也不吃任何藥物,只吃這家醫療機構免費提供的一種菌類提煉的藥物。表妹一聽,當時就簽了協議書,接連幾年時間,沒有吃任何抗腫瘤藥物,只吃這一種藥。說起來,表妹真是命運多舛,做過胃癌手術之后,由于體質弱緊接著又得了肺結核,但這些她都扛過來了。性格開朗、樂觀的她還參加了腫瘤醫院的抗癌俱樂部,向腫瘤患者現身說法,講自己抗癌的經歷,鼓勵他們調整心態,戰勝癌癥。
然而,不幸的事情還沒有結束。2004年冬天的一天,表妹又一臉憂傷地來到了我的家里。我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又出事了。果不其然,本來在一個私企打工的表妹夫,好好的又得了結腸癌。我不知道是不是道外的老房子里終年不見陽光濕氣太重,還是夫妻雙雙下崗壓力太大,一家里的兩個下崗職工居然都得了癌癥!我又找到了當時的腫瘤醫院院長徐秀玉大姐幫忙,讓她找最好的大夫、花最少的費用給表妹夫做手術。大夫的意見是,這個腫瘤位置太低,為了防止復發,最好的辦法是切掉結腸腫瘤后,直接改道造瘺。雖然患者要終身掛一個排便袋,生活受一些影響,但術后效果要好得多。
也許是上蒼也覺得命運對表妹表妹夫太不公平,在對他們做一些補償,表妹手術后至今已經十六年、妹夫手術也十三年了,夫妻二人至今硬朗地生活著。去年,市政府終于動遷了老道外大雜院的居民住戶,表妹和表妹夫也從老房子里搬了出去,住上了新房。現在,外甥已是一所職業大學的系辦公室主任、副教授,孫女明年也要上中學了。他們老兩口從拿低保金也開上了可以維持生活的退休工資,一家人總算否極泰來。
當我和最好的朋友說起我表妹這最離奇、最不幸的經歷時,我的朋友感慨地說,你這表妹命也太苦了,怎么這么多不幸的事能攤到一個人身上呢?可我表妹卻不這樣看,她說,我雖然現在也不知道我的親生父母是誰,但我曾經有過四位都疼我愛我的養父母,還有現在一直關心、愛護我的舅舅、舅媽、哥哥、嫂子、妹妹,還有愛我的家人,我覺得我的幸福一點兒也不比別人少。
表妹,我永遠祝福你,也愿意看到你永遠這樣堅強、樂觀!
作者簡介:程穎剛,祖籍山東掖縣,祖輩上世紀30年代初闖關東移民哈爾濱。1977年恢復高考后,考入黑龍江大學中文系,1982年初到哈爾濱日報社工作,歷任記者、農財部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2001年11月任哈報集團社長、黨組書記。曾任中國新聞攝影協會副會長、哈爾濱市攝影家協會主席以及中國政法大學、哈工程大學、哈師范大學、哈爾濱學院等幾所大學的客座敎授。這幾篇人物紀事選自程穎剛的《老道外大雜院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