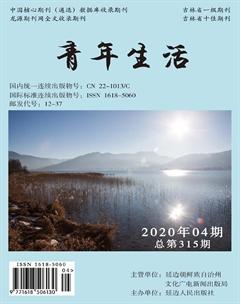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石原心蕊
摘要: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本文以認罪認罰從寬量刑規范化為視角,介紹立法困境,說明風險困境,提出方法路徑。
關鍵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目的是對違法犯罪人員,對照法律之規定,能寬則寬,當嚴則嚴,以體現刑事政策的適調性、打擊犯罪的適恰性。研究此政策,有不同的視角。而最常見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在庭審中對違法犯罪人員坦白、自首情節予以從寬處罰。本文以此為視角,研究認罪認罰從寬量刑規范化。
1.認罪認罰從寬量刑規范化面臨的立法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以下簡稱《量刑指導意見》)第3項第7款規定:“對于當庭自愿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依法認定自首、坦白的除外。”從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中可以看出,當庭認罪也是認罪的一種形式。因此,認罪的內涵不僅包含以自首或坦白為基礎的認罪,還應包含不以自首或坦白為基礎的其他情形的認罪。那么,對以自首或坦白為基礎的認罪而言,認罪的標準要高于純粹的自首或坦白中要求罪犯如實供述罪行的標準,對其從寬處罰的幅度也映大于自首或坦白從寬處罰的幅度。因此,我國刑法中的自首和坦白在內涵上既無法涵蓋完整意義上的認罪也無法為認罪的量刑提供足夠的容量空間,這就造成難以對認罪的罪犯適用與其人身危險性相適應的刑罰,致使認罪從寬的量刑規范化面臨著法律依據不足的困境。
對于認罰,我國刑法也沒有對其做出明確的規定。有學者認為,“認罰應當理解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認罪的基礎上自愿接受所認之罪在實體法上帶來的刑罰后果,不僅包括對訴訟程序簡化的認可還應該包括犯罪后嫌疑人的退贓、退賠。”雖然《量刑指導意見》中對罪犯退贓、退賠的量刑做出了明確的量刑規定,但這也并不表明罪犯的退贓、退賠就是一種法定的量刑情節,更無法認定這就屬于認罰的內涵。我國刑法中并沒有任何一個法定從寬情節可以涵蓋認罰這一量刑情節,認罰在司法實踐中只能作為一種酌定的量刑情節被適用,這就致使認罰從寬的量刑也面臨著法律依據不足的困境。由此可能會導致對同一認罰情節,由于不同的裁量者或不同的適用對象而會產生不同的適用結果或量刑幅度,使認罰從寬的量刑難以實現規范化。
2.認罪認罰從寬量刑規范化面臨的風險困境
對認罰從寬中的“認罰”往往需要以加害人的積極賠償作為基本條件,而加害人的積極賠償往往是以金錢為主要載體。“盡管我們可以說,讓犯罪人對被害人賠償一定數額的金錢,也是一種懲罰的現實措施,但是,行為人擁有財富的多寡將在此懲罰性運用上展現的參差不齊,刑法內涵也可能因為赤裸裸的金錢賠償而完全變色。”如果對以金錢為主要載體的認罰不加以立法規范化,在司法實踐中就很容易會以加害人賠償金額的大小作為認定認罰程度的主要依據,而輕視對罪犯本質上人身危險性的考慮。那么,這時的認罰從寬在實質上就很可能會異化為“以錢贖刑”,這與認罪認罰從寬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例如,“有兩起情節相似且危害程度相當的輕傷害案件,其中一起案件加害方家庭極為貧困,雖然希望認罰,但卻無力支付賠償費用,進而被提起公訴并被判處6個月有期徒刑。而另一起故意傷害案的被害人經濟條件較差,加害人經濟條件優越,該犯罪嫌疑人自事發后沒有探望過被害人也沒有道歉,只是答應支付130萬元的賠償金。被害人基于生活困難的考慮,對加害人予以諒解進而獲得了較輕的處罰。”因此,從上述所舉的兩則案例來看,罪犯對被害人的經濟賠償金額并不能作為認罰從寬的主要依據甚至是唯一依據。除了要衡量罪犯對被害人金錢賠償的情況更需要綜合考量全案案情來深究罪犯的人身危險性是否真的減弱,才能對其從寬處罰。由于刑法缺乏對認罰從寬的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就難以避免以金錢賠償數額的多少來作為認定認罰主要依據的做法,使認罰從寬有異化為“以錢贖刑”的潛在風險,不利于認罪認罰從寬的量刑規范化。
3.實現認罪認罰從寬量刑規范化的路徑
針對目前我國刑法對認罪認罰解釋容量不足的現狀,我國應在刑法中對認罪認罰的內涵予以明確的界定,并將認罪認罰規定為一種法定的量刑情節。認罪的內涵應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罪犯犯罪后被發覺之前投案自首并且認同司法機關對其罪行的定性,即此時的認罪是以自首為基礎,對此種認罪的從寬幅度要大于純粹自首的從寬幅度。如果罪犯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并不認可司法機關對其罪行的定性,此時對罪犯的如實供述只應認定為自首而不能認定為認罪。同樣,如果罪犯被動歸案后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并且認可司法機關對其罪行的定性,即此時應成立以余罪自首為基礎的認罪,對此種認罪的從寬幅度要大于余罪自首的從寬幅度。如果罪犯被動歸案后僅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并不認可司法機關對其罪行的定性,此時對于罪犯的如實供述只應認定為余罪自首而不能認定為認罪。二是罪犯被動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且認同司法機關對其罪行的定性,即此時的認罪以坦白為基礎,對此種認罪的從寬幅度要大于純粹坦白的從寬幅度。如果罪犯被動歸案后僅是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并不認同司法機關對其罪行的定性,對罪犯被動歸案后的如實供述只應認定為坦白而不能認定為認罪。三是認罪還應包含不以自首或坦白為基礎的審理過程中的認罪,例如罪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罪行并認可司法機關對其罪行的定性。從而避免既對認罪的情節評價又對其自首或坦白的情節進行評價,防止司法實踐中對認罪情節雙重評價的發生。同時,作為認罪的量刑情節其反映人身危險性的減弱程度和范圍比自首或坦白反映人身危險性的減弱程度更大、范圍更廣,基于罪刑相適應原則應將認罪規定為一種法定的量刑情節。而且,在刑法中將認罪規定為一種法定的量刑情節不僅可以提高罪犯認罪的積極性還可以規范量刑的自由裁量杈,從而有利于實現認罪從寬的量刑規范化。
參考文獻
[1] 陳衛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J],中國法學,2016(2).
[2] 陳偉.刑事和解在刑事實體法上的理念對接與完善[J],理論探索,2016(2).
[3] 姚顯森.刑事和解適用中的異化現象及預防對策[J],法學論壇,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