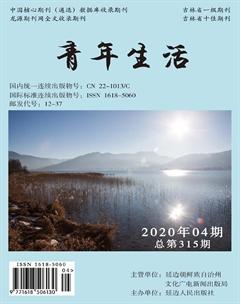淺談安全概念與“集體安全”的困境
楊澤華
摘要:安全是社會亙古持久的價值。國際關系中的國家安全概念建立在純粹的安全概念基礎之上,但亦有區別。處理國際安全問題的理想模型——“集體安全”在當下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難以突破主權權力與國際法效力之間掣肘沖突的狀態。然而“集體安全”的思想在當前非傳統安全領域仍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安全;國家安全;集體安全;利益
安全是人類和人類社會追求的一項價值。與諸如平等、自由等價值相比,安全并非處于當今人類社會價值順序的首位。原因在于,安全更多是其他價值實現的條件和前提,具有派生性和從屬性。舉例說明:安全確保私有財產、生命健康、平等自由等內容得以實現,并且能夠延展實現狀態的時長。“安全所指的是享受其他價值在時間上的真實的或被認知的延伸的可能性”。 除客觀上所追求的價值需求外,主觀上以安全為內容的人的心理歸屬和心理需求也應當被滿足。“人似乎還有一種歸屬的需要,這種需要其實是安全感的伴隨物”。 由此可得一種較為完整的樸素安全概念。安全為其他價值存在和延續提供保證;在現實上,維持一種穩定有序的狀態;在心理上,提供免于受損的安穩的感覺。如果強制性要求安全依靠一種公認且被普遍接受的規則實現,可能是一種路徑。漢斯·摩根索認為,“某種特定的現狀會經由法律的規定而得到穩定和永存”。 但另一方面,正如柏拉圖所認為,一般性規則不可能公正處理人際關系,因為其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很難找到一種普適實用的工具和方式確保實現安全,但人們依然有希望在實踐中找到可以妥協的處理方法。
國與國的安全概念在歷史中業已存在。中國古代每逢朝代更迭間,都會出現一段時間的亂世。雖然古代中國的割據紛爭主體,很難界定其為嚴格意義下的“國家”,譬如東漢末年紛爭的早期,各派政治軍事集團都還在維護名義漢室的正統。但是總歸是一種政治實體與另外的政治實體的戰爭。受到攻擊的政治實體面臨的是實際管轄和統治的威脅,即是一種類比國與國的安全威脅。西方古代史中,《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記載的雅典權力增長導致斯巴達的恐懼,戰爭不可避免發生,也是一例。但是,以上所述的國與國之間的安全概念不是當今國際關系所指的國家安全。一種觀點是,西方是當今國際政治領域“國家安全”概念的發源地,最早于1943年出現于Walter Lippmann的著作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逐步形成一個標準的“國家安全”的現代概念。 ?但是,到底什么是“國家安全”,缺乏一個具有統治力的界定。一眾學者都對安全概念的確定性有深刻的懷疑,并且有著各自的評價依據。譬如:有學者認為,安全是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解釋;有的學者以“安全”本身具備的價值負載多樣為由,斷定“安全”概念是模糊的;也有的學者根據安全本身的性質確定安全的概念,等等。 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在現代國際關系中,刨除非傳統安全所指代的譬如氣候、能源、糧食、金融危機、恐怖主義等領域的安全內容,“國家安全”問題多數情況是指主權國家實力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所引發的威脅與被威脅的危機狀態與危機心理的問題,尤其特指軍事安全領域。
傳統國際安全長期面臨挑戰,但并不失控。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法在確立國際安全框架,維系秩序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實踐先例。以近代國際關系開端的標志——《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為例。三十年戰爭的兩派及國家政治聯盟各方,通過談判協商,于1648年的8月和9月分別對《奧斯納布呂克和約》與《明斯特和約》的各項條款達成一致性意見,以國際會議的形式和平結束了三十年戰爭。基于條約建立起的體系破除了中世紀至此的羅馬主導的神權政體,形成了之后三百年的國際關系基本格局。 這種執行國際條約(國際法)以確定安全框架、解決紛爭的雛形給后世留下了參照。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分別形成了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兩個旨在避免依賴個體國家自身力量確保安全的傳統安全實現方法,并嘗試使用“集體安全”的方法處理國際關系的安全之需。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制度的設立運行以及《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中的若干條款的規定都是對“集體安全”概念的實踐。“集體安全”用摩根索的話來解釋,即是“可能的違法國家必須隨時想到自己有可能與由所有國家組成的共同陣線處于敵對狀態,這個共同陣線自動采取捍衛國際法的集體行動。” 這的確是一種理想的執行方式。摩根索認為的“集體安全”成立有三個條件:集體實力應對比違法者(侵略者),具有壓倒性優勢,使其不敢挑戰集體;滿足上述條件的集體應有共識;相互沖突的利益要服從共同利益。
然而,構建“集體安全”需要滿足的條件似乎有些苛刻,而且過于理想。人們似乎高估了“共識”的可靠程度,對“共識”的來源缺乏理解,以及無法預估為了實現“共識”,讓渡的利益能否確定不大于服從“共識”的利益。單單依靠價值觀共識維系的集體認同可能會對“集體安全”的形成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如果從個體國家利益的角度思考“集體安全”的可能性,答案會有些消極。原因在于,個體國家的安全政策是以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多個國家的國家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雖然理論上通過合作可以尋求最大共性,但是除去最大共性的利益競合部分,個體國家的保留部分與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相互排斥。況且,“集體安全”也存在著非正義的風險。國家利益很難用道德標準加以判斷,利益零和在國際關系當中常常發生。利益受損者通常會對加害于己的利益獲得者有批判和非議。“集體安全”系統當中,違法者不一定真的是違法者,共同維護的共識也不一定是真的正義。當“集體安全”的共識是非正義的,會出現一系列問題,譬如:“集體安全”可能會被利用,成為一些國家發動侵略行為的“合法”理由,從而淪落為謀求個體國家利益的工具。一些簡單的安全沖突也可能受“集體安全”機制的裹挾,使無關的國家被迫卷入沖突,從而擴大了沖突的范圍和影響,最終與“集體安全”框架的初衷背道而馳。極端情況下,若干區域性的所謂“集體安全”實體間的對抗反而會深化成更大規模的安全危機,等等。
國際法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法,與國內法所處的環境相比,應用國際法的國際社會并不存在凌駕于所有主權國家之上的司法體系和機構。行為體的約束力來源更多是約定義務、國家信用、國際道德、國際輿論等因素,其沒有強制力保障執行。當今的國際政治環境仍然是以主權國家為主構成的無政府狀態下的基本格局。主權的屬性從根本上講,是權力主體的絕對性排他性控制,絕對性控制是內部最高權力主體對資源的主導支配,要求不允許內部或外部主體質疑挑戰這種絕對支配地位。排他性實則為絕對性的延伸。假設存在外部權力力量,在調整一事或多事的資源分配中,嘗試干預、削弱、替代原有絕對控制力量。權力主體則會調動一切資源對抗、排斥這種嘗試,直至恢復絕對性的控制目標。主權國家擁有絕對性排他性控制是在歷史中長期發展并被普遍接受認同的既定事實。這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既有的絕對性排他性控制是各國共同維護的秩序價值,不可輕易違背;其次,既定事實是在共同認同的基礎上建立,控制受全體認可、尊重,具備“合法”控制理由,不會輕易改變。從國際法的屬性來看,國際法的約束來源主要是自我約束與共同約束,更確切說是:自愿接受的約定的履行與共同尊重秩序下的不得不履行。以上法理約束來源沒有出現強有力對抗主權的跡象,反而是在重申和鞏固主權的絕對性和排他性。第一種約束來源是自愿按照約定履行,自愿是對主權的極大尊重。在共同堅守的秩序規則中,履行的壓力并非來自體系全體的強制而被迫,更多是由于自身對共同秩序認同下的自覺。因此第二種約束來源沒有超過必要的限度,已盡最大可能維護了主權。再者,主權對國際法的司法機制也有足夠的抗拒力。主權國家可以拒絕出席國際司法裁判,也可以使用保留條款合理規避,排除管轄并拒絕執行裁決。若無強制則無裁判和執行的保證,因而國際法的效力確實是十分有限的。
法律效力與主權權力之間的羈絆和掣肘狀況致使國際法只能在主權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中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依賴法律實現“集體安全”存在不確定性。正如摩根索所認為的,“國際法比其他執法機構更加原始和虛弱,由于把執行法律這一任務完全寄托于侵權人和受害人間的權力分配的變化......把弱國的權利至于危險的處境。” 法律約束的集中性與主權獨立的分散性是一對核心的矛盾。國際法兼具了集中性與分散性的特點,在二者間搖擺。“人們嘗試賦予國際法集中化的體系時,國際法的分散性即出現頑強的抵抗。” 形成具有實際約束力和執行力的此類安全框架用以保證安全秩序存在困境。然而,我們仍然應當對這種安全框架思想保持樂觀。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相比較過去的幾個世紀,當前國際安全環境已經較為理性緩和。國家間軍事安全沖突的潛在風險依舊存在,但已非首要選擇。安全問題已逐漸出現在技術與能源安全、信息網絡安全、經貿與金融安全、恐怖主義安全威脅、極端主義安全威脅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且愈加頻繁。傳統國際安全出現了新的特征,非傳統安全的標的也已經不再局限于一定范圍內部,需要在多邊機制下由所有相關行為體參與協調,共同解決。因而“集體安全”框架思想對解決當下國際安全問題仍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Christian Bay, The Structure of Freedom (Stanford, 1958), P. 19.
[2]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1970), pp. 43~45.
[3]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4th ed. (New York, 1967), p. 418.
[4]The Statesman, transl. J. B. Skemp (New York, 1957), 294b.
[5]Peter Man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S. 2.
[6]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版),第177頁。
[7]方連慶、王炳元、劉金質:《國際關系史(近代卷)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第8頁。
[8]Hans J. Morgent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7th ed. , 2005, p304, p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