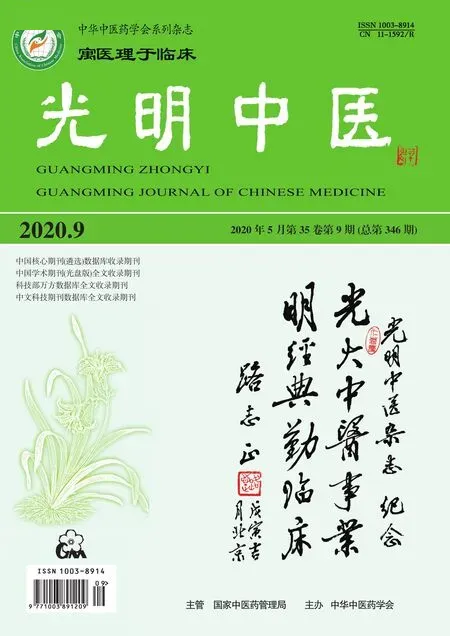清肺排毒湯再識*
張雯雯 柳越冬△ 陳 萌 張斯瑤 高 泉 冀文鵬 楊建宇△ 唐祖宣※ 祝之友※
1 清肺排毒湯處方組成
清肺排毒湯組方:麻黃9 g,炙甘草6 g,杏仁9 g,生石膏(先煎)15~30 g,桂枝9 g,澤瀉9 g,豬苓9 g,白術9 g,茯苓15 g,柴胡16 g,黃芩6 g,姜半夏9 g,生姜9 g,紫苑9 g,款冬花9 g,射干9 g,細辛6 g,山藥12 g,枳實6 g,陳皮6 g,霍香9 g。服用方法:傳統中藥飲片,水煎服。每天1劑,早晚2次(飯后40 min),溫服,3劑一個療程。調護:如有條件,每次服完藥可加服大米湯半碗。加減:如果不發熱,則生石膏的用量要小,發熱或壯熱,可加大生石膏用量;如果舌干津液虧虛者,藥后大米湯可服至一碗。療程:3天(劑)為一個療程,若癥狀好轉而未痊愈則服用第二個療程,若患者有特殊情況或其他基礎病,第二療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修改處方,癥狀消失則藥停。適用范圍:此方適用于輕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可結合患者實際情況合理化用。
清肺排毒湯全方用藥21味,其中有16味藥作用于肺,其它味藥作用于脾、胃、腎。《金匱要略心典》有云:“射干、紫菀、款冬降逆氣;麻黃、細辛、生姜發邪氣;半夏消飲氣”。麻黃開宣肺氣以平喘、開腠解表以散邪,石膏清泄肺熱以生津、辛散解肌以透邪,二藥一辛溫、一辛寒,一宣肺為主,一清肺為主,且均能透邪于外;紫菀瀉肺止咳,降逆祛痰,溫化寒飲,調暢氣機,與款冬花相配,亦為一宣一降,調理肺氣。四藥合用之中寓有相輔之意。柴胡苦平升散,黃芩降泄,二者配伍,為和解少陽之基本結構,和解少陽同時兼補胃氣,祛邪同時兼補正氣,則可使邪氣得解,胃氣調和;射干瀉肺降逆,利咽散結;半夏醒脾燥濕化痰,溫肺化飲;生姜降逆化飲,暢利胸膈,助半夏降逆化痰。此外,藿香、陳皮芳香化濕,山藥、枳實理氣健脾,諸藥配伍,共奏溫肺驅寒,健脾利濕,扶正祛邪之效。
2 清肺排毒湯處方組合簡述
清肺排毒湯包含多個中醫經典方劑,其中有小柴胡湯、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等,整個組方性味平和,集仲景經典良方之所成。此次新冠疫情,中醫辨為寒濕疫。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中有云:“寒濕者,濕與寒水之氣相搏也……體本一源,易于相合,最損人之陽氣……自表傳來,一由經絡而臟腑,一由肺而脾胃。水谷內蘊,肺虛不能化氣,脾虛不能散津……傷脾陽,在中則不運、痞滿,傳下則洞泄、腹痛。傷胃陽,則嘔逆不食,膈脹胸痛。兩傷脾胃,既有脾證,又有胃證也。”[1]此次疫情臨床表現包括呼吸道與消化道癥狀,正是“肺虛不能化氣,脾虛不能散津”“傷脾陽”之表現。
2.1 小柴胡湯 小柴胡湯原方為和解少陽之主方。《蘇沈良方》總結小柴胡湯,指出柴胡湯的解熱作用為諸證之先,可治療往來寒熱、潮熱、傷寒瘥后發熱等熱證。方中柴胡苦平,入肝膽經,透解邪熱,疏達經氣;黃芩清泄邪熱;法半夏和胃降逆;生姜、大棗和胃氣,生津,用后可使邪氣得解,少陽得和,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得和,有汗出熱解之功效。當代著名中醫學大師劉渡舟認為,小柴胡湯證,若兼見頭痛、發熱、脈浮等表證時,當減去原方中人參之礙表,加桂枝微發其汗,使表邪得解,即柴胡加桂枝湯,除解表證外,又能治療心悸、氣上沖胸等證[13],正是清肺排毒湯化裁之意。黃煌與史欣德調研16位擅長使用小柴胡湯的現代醫家,總結出使用該方治療流感、肺炎發熱時可去生姜、大棗,加金銀花、連翹、魚腥草、杏仁等[14],相對于生姜、大棗的和胃生津,更添加了清熱解毒的藥材,且有連翹引藥上行,可以使肺炎癥狀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王道瑞對小柴胡湯的藥方組成進行了分析,柴胡作為君藥,可透半表之邪;黃芩作為臣藥,它的苦寒可清泄少陽半表半里之熱邪;半夏、生姜一能安胃,二能辛散助柴胡透達表邪于外,對多種感冒、扁桃體炎、支氣管炎、肺炎、哮喘都很有效[15]。可見小柴胡湯雖善治少陽肝膽系疾病,但對于邪氣伏于機體半表半里間的病證也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和解”也是本方的一大特色。謝緯對曲敬來醫家對小柴胡湯的應用進行了分析,曲老認為流行性感冒病毒上呼吸道感染屬于時疫感冒與溫毒型范疇,病因為溫熱毒邪,病機為外感溫熱疫毒之邪,侵襲肺衛,毒邪伏于氣分,致陽氣郁熱,肺衛郁閉;臨床上表現為高熱、惡寒、咳嗽及肌肉酸痛等衛氣同病的癥狀。該方用于治療時疫感冒,只要見癥有發熱、咽痛、頭痛身痛等,即可應用,療效確切,在流行期間作為通方用于治療與預防皆有效。方中柴胡輕清升散,疏邪透表;黃芩解內郁之熱,使邪熱外透,其抗微生物作用的主要成分黃酮具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魚腥草清肺化痰,體外抑菌試驗表明其藥理成分魚腥草素對多種病毒有滅活作用;木蝴蝶、牛蒡子等利咽解毒;紫蘇葉、荊芥疏風解表、宣肺止咳;杏仁、紫蘇子止咳平喘、降氣化痰,與紫蘇葉、荊芥形成一升一降,調理肺之宣發肅降。此方組方嚴謹,體現外感熱病清、直、透之原則。且現代研究也表明,抗病毒單味中藥多為清熱解毒藥,多方文獻證實,魚腥草、柴胡、黃芩、桑白皮等具有抗包括甲型流行性感面病毒在內的多種病毒的功效[16]。
2.2 麻杏石甘湯 清肺排毒湯中,麻杏石甘湯具有辛涼宣泄、清肺平喘之功效。原方出自《傷寒論》第63條“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杏石甘湯”;第162條“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杏石甘湯”。清·尤在涇先生在《傷寒貫珠集》中說道:“發汗后,汗出而喘,無大者,其邪不在肌腠,而入于肺中,緣邪氣外閉之時,肺中已自蘊熱,發汗之后,其邪不從汗出而出之表者,必從內而并于肺耳。故以麻黃、杏仁之辛而入肺者,利肺氣,散邪氣,甘草之甘平,石膏之甘辛而寒者,益肺氣,除熱氣,而桂枝不可更行矣。蓋肺中之邪,非麻黃、杏仁不能發,而寒郁之熱,非石膏不能除,甘草不特救肺氣之困,抑以緩石膏之悍也。”到了近代,胡希恕先生在《經方傳真》中寫道:“今于麻黃湯去桂枝,倍用麻黃,增量甘草而加石膏,故治汗出有熱喘而急迫者。”《金匱要略》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飲邪隔拒,心氣壅遏,肺氣不能下達,音出于肺,金實不鳴。以麻黃中空而達外,杏仁中實而降里,石膏辛淡性寒,質重而氣清輕,合麻杏而宣氣分之郁熱,甘草之甘以緩急,補土以生金也。而在現代臨床應用中,麻杏石甘湯對肺系疾病的治療更是取得了顯著療效。例如黃萬貫等[2]在老年慢阻肺的臨床治療中發現,麻杏石甘湯合千金葦莖湯加減對于治療老年慢阻肺的效果要優于常規西醫治療,且不易復發;楊春等[3]在治療支原體肺炎的臨床治療中在西藥治療的基礎上加入麻杏石甘湯,取得了較好結果;秦新芳等[4]發現麻杏石甘湯加減治療肺炎喘嗽可縮短癥狀改善時間, 提高治療效果。此外在實驗室研究中,張輝果等[5]發現麻杏石甘湯能有效抑制肺炎鏈球菌所誘導的小鼠肺炎, 且以全方效果最佳;李玲等[6]的研究更是驗證了麻杏石甘湯作為有效的抗流感病毒中藥復方, 能有效地減輕肺部炎癥、保護免疫器官、調節細胞因子平衡這一結論;徐鳳等[7]在對于麻杏石甘湯能否有效降低哮喘模型小鼠的氣道高反應性的實驗中, 得出了肯定性結論,同時還得出了麻杏石甘湯具有抑制氣道重塑作用的結論。
2.3 射干麻黃湯 射干麻黃湯出自《金匱要略》卷上,“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具有溫肺化飲,下氣祛痰之功效,所治之證乃寒飲郁肺,痰結咽喉所致,與本次疫情臨床癥狀相符。寒飲郁肺,濁氣上逆,表現為咳嗽,氣喘;痰氣搏結于咽,濁氣與寒飲相結于胸,則喉間痰鳴喘嘯,胸中似水鳴音;濁氣不降而逆則胸膈滿悶,痰飲隨寒氣沖,則吐痰涎;苔白膩,脈弦緊或沉緊,皆為寒飲郁肺結喉之征。清·凌曉五先生在《凌臨靈方·哮喘》中寫道“老夫自服風哮有年,遇寒勞秋而發,咳逆痰稠,甚且不能平臥,脈弦滑浮,治宜降氣豁痰。方見肝氣痰飲,同王姓之方。肺風痰喘宜從《指掌》。肺傷痰喘之法加羚角犀黃竹瀝,或用小青龍湯,麻杏甘石湯,射干麻黃湯。”近代著名中醫曹穎甫《經方實驗錄》中的醫案中更是有對射干麻黃湯應用的記錄:“有張大元者向患痰飲,初,每日夜咯痰達數升,后咯痰較少,而胸中常覺出氣短促,夜臥則喉中如水雞聲,徹夜不息。當從金匱例投射干麻黃湯,尋愈。又有楊姓婦素患痰喘之證,以涼水浣衣即發,發時咽中常如水雞聲,亦用金匱射干麻黃湯應手輒效,又當其劇時,痰涎上壅,氣機有升無降,則當先服控涎丹數分,以破痰濁,續投射干麻黃湯,此又變通之法也。”到了現代,射干麻黃湯在臨床上的應用更是對中醫藥治療肺系疾病提供了支持。在臨床研究中,李年火等[8]在進行射干麻黃湯對于支氣管哮喘患者的實驗中得出了射干麻黃湯能有效提高患者的肺部功能,有助于患者的病情恢復的結論;齊紅俠[9]在對射干麻黃湯加減治療慢阻肺急性加重期(寒飲伏肺型)的療效分析的實驗中得出了在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期(寒飲伏肺型)患者常規西藥治療上,聯合射干麻黃湯加減治療,可提升療效,并具有改善慢阻肺癥狀、睡眠質量的效果,具顯著優勢;田國平[10]對于射干麻黃湯加味治療支氣管哮喘冷哮證的臨床實驗中,通過對比實驗得知,常規西醫聯合射干麻黃湯加味治療支氣管哮喘冷哮證的效果更為突出。此外,射干麻黃湯的功效在動物實驗中也得到了驗證,陳豪等[11]的關于射干麻黃湯對哮喘性肺炎大鼠肺部炎癥反應及免疫反應的影響的實驗證實了射干麻黃湯可以有效減輕哮喘,提示其可作為過敏性哮喘的治療藥物,為哮喘的治療提供了參考數據;王晶波等[12]在加減射干麻黃湯對哮喘大鼠氣道重塑及肺組織PCNA和ERK的影響這一實驗中,得出了加減射干麻黃湯能改善哮喘大鼠氣道重塑, 其機制可能是通過降低PCNA的水平, 抑制氣道平滑肌增殖及ERK、p-ERK、PCNA蛋白表達水平, 從而達到改善哮喘氣道重塑的目的這一結論。
2.4 五苓散 五苓散在《傷寒論》中原治蓄水證,乃由太陽表邪不解,循經傳腑,導致膀胱氣化不利,而成太陽經腑同病。水濕內盛,泛溢肌膚,則為水腫;水濕之邪,下注大腸,則為泄瀉;水飲凌肺,肺氣不利,則短氣而咳。治宜利水滲濕兼以溫陽化氣。方中重用澤瀉為君,以其甘淡直達腎與膀胱,利水滲濕。臣以茯苓、豬苓之淡滲,增強其利水滲濕之力。佐以白術、茯苓健脾以運化水濕。《素問·靈蘭秘典論》謂:“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17],膀胱的氣化有賴于陽氣的蒸騰,故方中又佐以桂枝溫陽化氣以助利水,解表散邪以祛表邪。近代醫家彭子益認為五苓散可治太陽中風,內有水氣,渴欲飲水,水入仍吐者。此是胃間有宿水未消,又外感邪氣郁結在表,阻礙相火下行之路。相火逆升自覺口渴,宿水未消,新水不容,所以飲水則吐,此方使用二苓、澤、術來泄水,桂枝以助疏泄,行小便以解表郁[18]。由此可知,五苓散雖為利水之劑,主要治療蓄水證,但同時具有解表的功效。清代醫家汪昂對此方的藥物組成進行說明:二苓甘淡利水,澤瀉甘咸瀉水,能入肺腎而通膀胱,導水以泄火邪,加白術者補土以制水,加官桂者,氣化乃能出也[19]。近代醫家左季云認為五苓散是治水而不是治渴,重在內煩外熱,用桂枝是逐水以除煩,不是熱因熱用,是少發汗以解表,不是助四苓以利水。所以本方除了治療諸濕腹滿、水飲水腫、嘔逆泄瀉等證之外,還可治療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煩渴、身熱頭痛等證[20]。左老的觀點明確指出五苓散乃治水之方,桂枝在此作用為除煩解表。現代醫家劉正江認為五苓散用桂枝助膀胱氣化而利小便,又能發汗解表,對蓄水證兼表邪者,服之可使經、腑之邪并除。若表證不明顯可用肉桂,更凸顯溫腎化氣,通利水道的作用;但若明顯具有表證之時,還是使用桂枝,既可行水利尿,又可行解表之功[21]。
3 清肺解毒湯經方經藥再論
清肺排毒湯涉及4個經方,小柴胡湯、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小柴胡湯,扶正祛邪,和解少陽,此乃針對新冠肺炎病實在肺位,病機在少陽之正邪交織、寒熱錯雜之疑難多變之證;麻杏石甘湯專清疫毒逆襲入肺化熱、與伏邪共奏壅遏于肺之毒,宣降肺氣,可以迅速改善由肺失宣降之發熱、咳嗽之急重病癥,使熱毒化,喘嗽平。麻杏石甘湯在瘟疫導致喘嗽之危急重癥中有立竿見影之功,當代名醫蒲輔周、鄧鐵濤先生亦多用之;射干麻黃湯,功在宣肺平喘、溫肺化痰、除飲燥濕、溫中健脾,功在宣肺散寒、化飲止咳。這樣,可以使入肺之寒濕、郁結之痰飲得清,氣逆之喘咳得平,迅速化解喘嗽之悶之苦;射干麻黃湯協同麻杏石甘湯達到挽救喘嗽之危急的效果。而五苓散溫陽化氣、利水滲濕,可使侵入膜原之寒濕之邪、壅郁在里之痰飲之邪,使入里之郁熱、熱化之毒邪一并隨所利之水、之濕而得以外出,給邪以出路。與方中所言,藥后服大米湯半碗到一大碗相呼應,利水而不傷陰津。尤其是,五苓散、麻杏石甘湯原文在漢朝時期是專用肉桂,而本方沿用現代用法,專用桂枝,可以說是恰逢其用,藥證相符。在此用桂枝而不用肉桂,改用了原文用肉桂重在治下焦之病,而本文用桂枝專治上焦之邪,可謂中醫臨床中藥學成果的又一重要應用實證。
綜上可見,清肺排毒湯,針對新冠肺炎之虛實、寒熱、濕毒諸邪,扶正與祛邪共施、辛溫與辛涼共用、清熱與燥濕并進、解毒與利水并行,共奏扶正抗疫、宣肺平喘、解毒化濕之功效!使毒疫得清,濕氣得化,邪氣外達,肺氣得宣,正氣得復。所以說,清肺排毒湯配方得當、用藥巧妙、療效卓著、名符其實。
清肺排毒湯在運用四大經方,小柴胡湯、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之時,對各經方中的一些藥用進行加減,劑量進行調整。如將小柴胡湯、射干麻黃湯中共有的大棗去掉,小柴胡湯中的人參、射干麻黃湯中的五味子也去掉了。而方中加入了山藥、枳實、陳皮、藿香之味,這些加減可以看出,毒疫感染之人并非都是元氣、氣血必虛、甚虛之人,所以去掉大補元氣、強補氣血之人參、大棗,而改用平補五臟之山藥,重調中州之陳皮,寬胸之枳實,除穢之芳香佳品藿香,針對此新冠肺炎毒疫多胸悶喘嗽、脾胃受損之癥,實乃達到中州健,邪得祛,藥到病除。此加減芳香化濁、顧護胃氣,祛除邪疫,頗有達原飲/柴胡達原飲之意,又合病機在少陽膜原之機。再仔細琢磨,如果本方用于預防用藥,又透著藿香正氣散之味道。
清肺排毒湯首選麻黃、重用柴胡,尤其是柴胡重用之16 g,乃全方之重品。新冠肺炎病實邪在肺,病機在少陽。麻黃宣肺平喘利水,可使病人之喘嗽得治;柴胡,清解少陽,熱得清,郁得解,使募原/膜原之濕毒濁邪得化、得清,正如《神農本草經》所言,柴胡有推陳致新之功,專治心腹腸胃中結氣、寒熱往來等癥。可知,柴胡扶助正氣、恢復元氣,加速新陳代謝,和解少陽,作用于心腹腸胃多臟器。從麻黃柴胡二藥之選用,不但是經方之必用品,更是中醫臨床中藥學之“經藥”理論的實證,是清肺排毒湯中之君臣藥、核心藥,而此用藥經驗之妙法。
4 結語
在日前公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中,清肺排毒湯列入中醫臨床治療期首選。該方將四個方劑21味藥組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方劑。
中藥復方“清肺排毒湯”作為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專門設計的方子,由復方“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等幾位藥、復方綜合而成。臨床上,適用發熱、疑似病例,輕型、普通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應用比較廣泛。原則是“宣肺、化濕”。
《素問·玉版論要》中有言,“病溫虛甚死”[4]。津液的盛衰與疫病的預后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在各階段治療中當時刻注意顧護陰津。由國家衛健委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5]中特別注明,“如有條件,每次服用可加服大米湯半碗,舌干津液虧虛者可多服一碗。”即體現了祛邪同時顧護陰津的中醫思想。相信全方位發揮中醫藥優勢,結合現代醫學中西并用,定能盡快打勝這場全民疫情阻擊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