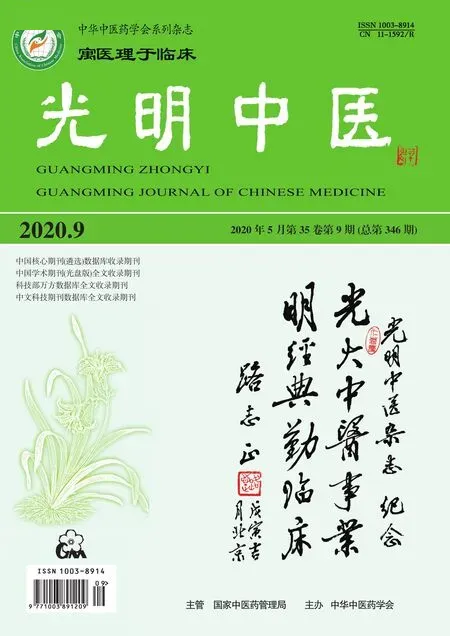苓甘姜附龍骨湯治療癲狂證驗案2則
張 峰 陳春娣
苓甘姜附龍骨湯出自清代著名醫家黃元御的《四圣心源》,用于治療癲狂證,其藥物組成是:法半夏、炙甘草、干姜、炮附片、茯苓、麥冬、煅龍骨、煅牡蠣。臨床中,筆者應用此方治療癲狂證患者數十例,療效滿意。現舉2則,試述其立法根源,以深入探討黃元御癲狂證治的學術思想。
1 病案舉例
病案1 陳某,男,35歲,工人,2012年1月6日來診。患者因恐懼流言蜚語出現疑心重、沉默寡言,懷疑他人加害自己,恐懼擔心,躲避人群,甚至夜間不能入睡,連續2日不飲不食。其家人曾將其送至廣州某三甲醫院就診,診為:精神分裂癥,給予利培酮、奧氮平口服治療,服藥3周,期間患者訴頭痛,恐懼心理未見明顯好轉,遂由家人送至我處擬中醫治療。刻診:患者體質量適中,面色黃白虛肥,精神萎靡不振,目光游移不定,對答尚清楚,反應略遲鈍。患者自訴心中驚恐,不敢與人同桌就餐,夜間枕下備刀,徹夜不眠,惶惶如被捕狀,精神困頓,莫名傷悲,飲食無味,不知饑飽,口渴不欲飲水,小便清,大便不規律。舌淡紅,苔白厚膩,脈沉細滑。診斷:癲狂證(癲證),證型:土濕木郁。治宜溫腎健脾,鎮驚安神,方以苓甘姜附龍骨湯治療。處方:法半夏15 g,炙甘草10 g,干姜10 g,炮附片(先煎)10 g,茯苓15 g,麥冬10 g,煅龍骨(先煎)30 g,煅牡蠣(先煎)30 g。6劑,每天1劑,水煎服。服藥期間,囑患者每天劇烈運動30 min。服藥6劑后,患者精神轉好,自訴已無驚恐被害之感,可以與人同桌進食,夜間亦能入睡,二便可,無不適。效不更方,遂守此方服用30劑,患者癥狀基本消失。春節后囑其堅持鍛煉身體,繼續規律服用此方3個月余后停藥,隨訪7年,未見復發。
按:本例患者正值壯年,氣血充足,血氣方剛,然而言語傷人,如無情刀劍,直趨臟腑,內傷七情,似較外感六淫更甚。患者飲食不調、不知饑飽,口渴不欲飲,是土為濕困之象;情志所傷,肝木欲發作而為怒,卻為中土水濕所遏,轉而成郁;土濕木郁,中氣損傷,肺腎氣滯則金水生寒,肺在志為悲,腎在志為恐,肺腎氣旺是以悲恐俱作;小便清、舌淡紅、苔白厚膩、脈沉細滑,皆是濕寒之象,濕寒動則寢食皆廢,故其根源乃是濕寒。方中炮附片大辛大熱,用以溫暖脾胃,除脾濕腎寒,補下焦之陽虛;干姜溫中散寒,暖脾陽,驅寒邪而達木郁;茯苓利水滲濕而培脾土;炙甘草益氣和中而補脾胃;麥冬清金潤燥而安心神;煅龍骨、煅牡蠣安魂定驚而秘精斂神;法半夏平沖降濁而和胃消痞,與炮附片相反相成。全方制方嚴謹,干姜、炮附片合用以溫脾腎之寒;茯苓、炙甘草共奏利濕培土之功;麥冬清肺、法半夏降逆,則升降平調而木郁自達;煅龍骨、煅牡蠣鎮驚安神則驚恐皆除。
病案2 袁某,男,18歲,輟學,2012年6月10日來診。患者半年前去廣州番禺打工,工作期間經常失眠,精神長期壓抑,不與他人交往,默默不語。返家后,患者性情大變,脾氣暴躁,動輒毆打家人,情緒激動時曾于凌晨砸毀銀行ATM取款機等公共財物,情緒低落時則連續數日躺臥家中,閉門不出。或終日不食,或暴飲暴食。患者及家屬懼怕西醫治療,遂至我處擬中醫治療。刻診:患者消瘦,面色黃白,精神萎靡,雙目少神,言語尚清楚,對答不配合。患者家屬代訴其沉溺網絡十余年,性格孤僻,不喜言語。近10 d來出現3次打人毀物、怒罵不休、狂暴不羈,發作時胃口奇佳,食量約為平時3倍,每次發作持續1~2 d不等,發作后則終日睡臥不起,不飲不食。小便可,大便不規律。舌淡紅,苔黃膩,脈弦細滑數。診斷:癲狂證(狂證),證型:土濕木郁。治宜溫脾利濕,清熱、安神。方以苓甘姜附龍骨湯治療。處方:法半夏15 g,生甘草15 g,干姜10 g,炮附片(先煎)10 g,茯苓15 g,麥冬30 g,煅龍骨(先煎)30 g,煅牡蠣(先煎)30 g。5劑,每天1劑,水煎服。處方開具后,考慮患者未必配合服藥,遂予以心理疏導半小時,患者表示愿意配合治療。服藥5劑后,患者來復診,自訴服藥后胸腹部清涼舒適,心胸中原有燥熱難受之感完全消失,全身舒暢,睡眠轉佳,飲食改善。診見患者精神愉悅,信心倍增,舌脈濕熱之象轉輕,遂予守方,囑其每周服藥6劑,堅持3個月,并鼓勵患者多參加團體體育活動,多與朋友交流。3個月后,患者家屬帶其再次復診,診見患者體質量增加,精神愉悅,眠食俱佳,舌淡紅,苔薄白,惟脈象略弦數,遂予中成藥加味逍遙丸,囑其堅持按時服用,堅持2個月。后隨訪6年,患者病情未復發。
按:本例患者為青少年男性,自幼沉迷于網絡,性格孤僻,對生活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較差,精神抑郁,久而躁狂。患者狂證發作則胃口奇佳,喜怒無常,為土濕木郁之象;脾氣不升,木火之氣郁而生熱,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濕熱內蘊故喜怒兼生;舌淡紅,苔黃膩,脈弦細滑數,均為濕熱之象。濕熱動則眠食皆善,然其根源仍是脾土之濕,脾喜燥而惡濕,非溫脾陽濕邪不能盡去,故溫脾燥濕為主,兼以清熱、安神,是為以熱治熱,反治之法。方中炮附片、干姜溫脾陽而蒸騰水濕;茯苓利水滲濕;法半夏健脾燥濕;生甘草清熱利小便;重用麥冬清熱以安心神;煅龍骨、煅牡蠣重鎮安神。全方以溫脾為法,利、滲、燥、清,濕熱之邪從便溺而去,輔以重鎮收斂之藥以安神,故心神得安,以收全功。
2 討論
癲狂病名出自《黃帝內經》,分為癲與狂,都屬于神志失常的疾病。癲病以沉默癡呆,語無倫次,靜而多喜為特征,狂病以喧擾不寧,躁妄打罵,動而多怒為主要特征,兩者往往相互聯系,相互轉化,常并稱為癲狂。癲狂證往往對應于西醫診斷中的精神分裂、雙向障礙、持續性妄想障礙、抑郁癥、分裂情感障礙等疾病。目前多數中醫教科書和專業參考書,將西醫的“精神分裂癥抑郁型”和“抑郁癥”參考“癲”病進行辨證論治;將“精神分裂癥與躁狂型精神病”參考“狂”病進行辨證論治”[1]。
現代醫學認為本病病因尚不十分清楚,大量研究表明,遺傳因素、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因素。抗精神病藥物的應用取得了一定的臨床療效,但多數藥物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應。比如:目前公認的治療躁狂癥的代表藥物碳酸鋰,其臨床治療的有效劑量與中毒劑量非常接近,需要密切監測血鋰濃度,不良反應包括惡心、嘔吐、震顫等。另外,利培酮可導致錐體外系不良反應、血清泌乳素的升高、消化不良等;奧氮平可使患者出現體質量增加、步態異常和代謝綜合征等。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本病的中醫藥治療。
中醫認為[2],癲狂的發病原因,多以七情所傷為主,或因思慮不遂,或因悲喜交加,或因惱怒驚恐,皆能損傷心脾肝腎,導致臟腑功能失調,進而產生氣滯、痰結、火郁、血瘀等蒙蔽心竅而引起神志失常。治療方面,癲病多虛,為重陰之病,主于氣與痰,解郁化痰,寧心安神,補氣養血為主要治則;狂病多實,為重陽之病,主于痰火,瘀血,治宜降其火,或下其痰,或化其瘀血。《素問·病能論》提出了節食和服生鐵落的治法。朱丹溪提出“鎮心神,開痰結……狂病宜大吐大下除之”。張景岳主張解郁化痰,藥用重劑。王清任創癲狂夢醒湯治療瘀血發狂。
黃元御認為:癲病者,安靜多悲恐,肺腎之氣旺也,狂病者,躁動多喜怒,肝心之氣旺也。肺腎為陰,肝心為陽,《難經》二十難曰:“重陰者癲,重陽者狂,正此義也。”可見,肺腎兩陰臟之氣同時偏盛則易發作癲證,肝心兩陽臟之氣同時偏盛則易發作狂證。黃元御進一步指出癲狂證的根源:勞傷中氣,土濕木郁。認為中焦濕滯,肺腎金水之氣不降而生寒,悲恐俱作而生癲;肝心木火之氣不升而生熱,喜怒并出而成狂。不僅如此,黃元御還更深刻地闡述了癲狂的轉化:癲緣于陰旺,狂緣于陽旺,陰陽相判,本不同氣,而癲者歷時而小狂,狂者積日而微癲。陽勝則狂生,陰復則癲作,勝復相乘而癲狂迭見。黃元御對于癲狂證的認識,是符合臨床實際的,對于癲狂證中醫辨證及臨床用藥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苓甘姜附龍骨湯立方十分精簡,藥物只有8味,卻體現出黃氏對后天脾胃在人體生理、病理中重要作用的認識至為精徹。黃元御治療癲狂證強調調中,復其脾升胃降之常,方能龍虎回環,陰平陽秘,而達愈疾之目的[3]。
中藥配伍禁忌“十八反”中烏頭與半夏是配伍禁忌的內容之一,而附片為烏頭子根的加工品,成分與烏頭大致相同,因此許多醫書記載附片不宜配半夏。黃元御所創苓甘姜附龍骨湯中附片、半夏同用,引起了諸多醫者與患者的質疑,然而在臨床實踐中,附片、半夏配伍使用后并未發生明顯毒副反應,反而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附片與半夏相伍同用,首推醫圣張仲景,《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并治》中寒飲逆滿證條文曰:“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即是附子配半夏治療中焦虛寒挾飲所致的腹滿腹痛的典范。后世歷代醫家對張仲景運用半夏配附片的經驗進行總結和發揮,已使其成為諸多名醫治療危急重癥和疑難雜癥的常用配伍[4]。據統計[5],《全國中藥成藥處方集》含十八反組對共411方,其中烏頭(附片)配伍半夏達163方,足見其在臨床應用中的普遍。黃元御的中醫思想與醫圣一脈相承,師古而不泥古,大膽創新,開辟出中醫治療癲狂的新路,對我們臨床治療本病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