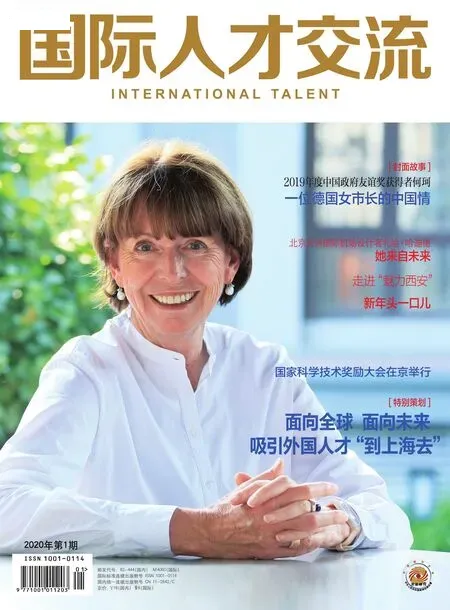張家界讀山
文/梁衡

張家界黃石寨
黃石寨,自然的偉力
晨8時車出發到龍門,開始登山。今天看的景點是黃石寨。進山即在谷中行走,谷底鋪有青石板路,倒不很費力,只是走得腳底又硬又疼。最可貴的是這石板路全部藏在密密的冷杉林中,我從未見過這樣好、這樣多的冷杉群落。在路邊休息,無論你向左右看,還是向上看,只有密扎扎的、直溜溜的樹干,就像有人將無數根筷子插在這里。而杉樹頂上枝葉茂密,將陽光遮擋得嚴嚴實實。我們就在這樣一個陰涼涼濕潤的,綠風滿谷浸衣袖的環境里一步步地登山。這時其實是看不見什么山的,只有樹、只有綠,甚至樹也看不清,只有密密的樹干,像在八卦陣中行走。綠,更多的是一種氛圍,一種蘊積,一種感覺。張家界是國家森林公園,這大概就是它本身的含義。
漸登漸高,終于扭過幾個“之”字升到半山。這時從樹的頂梢和空隙中,看到了山峰。天啊!哪里是山,簡直是一件人工藝術作品。但藝術品哪有這么大,這樣高!什么人又能造得出來呢?當地人和導游總是要附會出許多人性化的故事。其實張家界的好處就是人跡絕少。天下名山佛占盡,一般的山,特別是好山,總少不了廟,而這方圓百里竟無一座廟,只此一點就證明它是自然的山水,并沒有人為的歪曲和污染。陪同的是張家界報社的小卓,我問這里有沒有廟,她說:“哪有廟,有土匪。”說得極妙,湘西曾是有名的土匪窩。
當走到南天門時,迎面是幾座獨立的山峰。你說像石筍、石塔或者棒槌都行。承德有一個棒槌山,許多人爭著去看,但怎么能與這個比呢!使人難以理解,山怎么像樹一樣是從溝底里長出來的呢?在黃土高原上我們見過那些被洪水切割的溝壑和湊巧留下的土柱、土筍,這好理解,我眼睜睜地見過水是怎樣切割、沖擊土塊、泥沙。但這里是石頭啊。張家界的美,就在它的山峰是各自獨立、千姿百態的石峰。待登上山腰,鉆出杉樹林后,你就可以移步換景,一步一步地欣賞了。它所表現的,主要是偉岸、挺拔、奇險,以瘦硬、孤傲、冷峭偏多,偶有片狀的,就很薄,側看輕輕如紙,好像手指一彈,就可彈出一個洞。這是由于幾億年洪水對沙石巖的慢慢沖洗。山石不像北方的太行山,不是豎紋、壁立,而是橫紋。所以有的峰巖簡直是一摞疊著的紙牌,或是一摞疊著的銅錢。這疊摞當然是很隨意的,像賭局剛散,人去牌留,隨手將牌碼在那里。這是從來沒見過的景。隨著登高,總在想,這山是怎么造出來的?說是南天門,其實哪有門,是一座天然的石拱。我們門下小憩,面對山下一片石筍,筍上點綴著青松,百思不得其解。
登到石寨的最高處看山,群峰朝宗,這時你再看就很清楚了。一條莽莽蒼蒼的大壑,壑溝中許多山峰如駝群趕路,昂起它們的頭;又如帆船出海,于煙霧繚繞中,掛滿了帆,逶迤而來。這山不管它狀似塔、似柱、似筍,它們的峰頂基本在一條水平線上,像一座沒有造完的橋留下的橋墩。想當年,這里是一片石頭,廣袤千里,如現在的戈壁沙灘,黃土高原。洪水就這樣鼓起潮,推起浪,如鋸拉刀砍、斧修銼磨,日夜不停地加工,終于尋見一條細縫,然后一個浪頭鉆進去,轟然一聲,啃下一塊石頭。就這樣浩浩蕩蕩,轟轟烈烈地造山。現在黃河的壺口瀑布不就是這樣造成的嘛。登張家界,你首先感受到的是自然的偉力。但在這樣的大破壞、大再造之后,生命又立即去占領它。便是最高處,迎風的硬石頭上,也能長出青松來。山頂有一株株探出崖外的卷松,人們爭著去照相。背景是萬山如畫,峰立如壁,這時你又感到生命對自然的征服或是自然對生命的孕育,這是一曲自然界中自然力與生命力的交響曲。
登黃石寨,上山八里,下山七里,又走了十二里的金鞭溪,結果第二天一早起來,所有的人都腿疼腰僵得難以挪步。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講,來張家界也許此生就這一次,所以眾人還是鼓勁再登高峰。
今天登天子山。天子山在登山途中沒有什么好看的。直到登上山頂之后,看群峰隱現于霧靄霞光之中,千變萬化,極為壯觀。下山后走十里溝壑,群峰如畫,名“十里畫廊”。可惜路被洪水沖斷,滿溝卵石,留神腳下,常要分心。我又一次看到了,山就是這樣被水沖造成的。山水、山水,現在看到的無水之山,其實是許多年前水的加工;有水之山則是水正在對山進行加工。不知萬年之后張家界的山又會是什么樣子?
黃龍洞,洞里河山
上午看黃龍洞。因為在國內看過很多的溶洞,開始我真覺此洞意思不大,進去后才深感有必要一看。最大的特點是大,洞之高大,不可測,要用船進入。機船開十五分鐘進去,然后步行爬坡,七上八下不知何往。最奇的是中央大廳有無數石筍,有一根細如銀針,快要長到洞頂。而頂上有兩處,如天花板漏水,灑下細細的瀑布,可見有河就在我們的頭上經過。本來連爬了兩天的山,已經累得談山色變,今天主人說好是再不會讓大家爬山的,未想卻在洞里爬上爬下,我們說這是明爬變成了暗爬。沒有想到,水在外面造山,形成河,又到地下穿行,再切出洞內的山。洞里河山,風光無限。洞中有一巨石形如手,呈“八”字狀,據說這洞形成已有八億年。
在張家界我們讀的是自然,讀到了什么呢?是自然之力——水、風、雷電與火;是生命之力——林木、草苔、動物與人;還有無盡的時間,它們合作完成了一幅杰作。現代派的畫家,先是用線條、顏料來表現思想。后來不能滿足在平面上施展,就用木刻、用石雕、用銅塑,去占領空間。當藝術家正這樣一步步探索時,不知道大自然已經在這里創作了八億年,而且用的原料是如此之多,空間如此之大。
與其說我們從平地進洞,還不如說是到洞里去看山。因為我們下到洞底時,又開始繞著石筍、石柱上上下下地爬山了。當我面對六米高的“神針”石柱,看著天花板上簌簌而下的雨絲瀑布時,我想到了雁蕩山的大小龍湫,廬山瀑布。在地上水聚水散、水流水滲,本是極自然的。但想不到這水竟偷偷地溜進地下來,竟又造出這樣大的一個世界。自然藝術伸到地殼里來,從從容容地進行著它的創作。這有點像畫鼻煙壺的畫家,不滿足于在壺的玻璃外作畫,到壺里面去反手用筆作畫,別出一種效果。世上沒有神,沒有上帝,可是我們要求解這自然之謎,只能先假設一個神,一個上帝。正像解方程式,先假設一個X一樣。到現在,這個方程也還在求解的過程中。我們只能說是鬼斧神工,上帝之手。地球是上帝手里繡著的一個繡球,他一針一線地繡;又如雕琢的一個煙斗,一刀一刀地刻。我們看人工的藝術品,比如云岡石窟造了四十年,樂山大佛造了九十年,驚異于那一代人、兩代人、幾十代人的功力。但比起這件八億年的藝術品,人們怎么能不驚羨自然的耐心與執著呢?達摩修道面壁九年,不知他于沉沉黑暗中怎樣尋覓一線光明。一切有志于悟道的藝術家,都可以在這里得到啟發。
山要當作畫來讀
今天登上天子山峰頂看后山,群峰簇擁,如士兵列隊。巖壁線與面相互變幻,如油畫國畫兩種畫法并用。群峰盡情地舒展開去,于云霧光影之中。忽一石之突,如油畫之甩出一塊顏料,那云煙繚繞,又如寫意國畫的隨意一抹了,真感嘆于人力的微小、笨拙。
山是要當作畫來讀的。要是把山局限于像什么,就如外行看畫,說“畫得很像”便覺是好。我在南天門,正欣賞那一柱天南時,一回頭,后面之山是一幅美女出浴圖,側坐水邊,低頭撫水。急往前走幾步又不像了。像與不像全在你的聯想,能調動起你平常儲存的藝術形象,這便是審美,便是自然這位作者與你這個讀者的交流。不識古文不能讀唐宋,沒有藝術修養的人不能讀山水,或者讀不深,讀不出味。這就是為什么這里祖輩居住著山民,卻非要等到讓外面的人來發現這山水,特別要讓藝術家來發現,讓黃永玉、陳復禮來發現,他們是能夠讀懂山的人。我在寫泰山時說,許多讀懂泰山的人,感受到它的浩然之氣,下山后成就了他們的大業。這張家界每天約有二十萬人上山,有沒有下山后成其文業、藝業、政業的呢?沿途我就看見四五個持速寫本,于路邊揮汗讀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