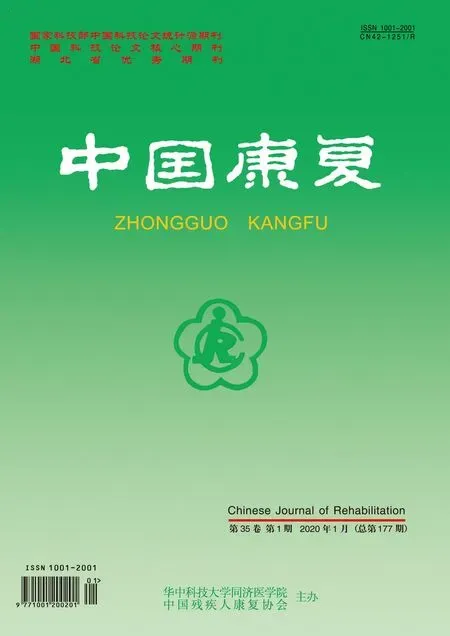不同強度的運動康復訓練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療效及安全性比較
茅溢恒,蘇敏,袁鵬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是由于各種病因所致的心肌收縮力減低,導致心輸出量減少、組織缺氧的一種復雜的臨床綜合征,其主要臨床表現是呼吸困難和疲乏[1]。慢性心力衰竭的發病率逐年提升,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心力衰竭的流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經濟負擔,在發達國家70歲及以上的人群中,CHF的發病率達到了10%[2]。目前,全球估計HF患病人數超過3770萬人,每年診斷出870,000例新病例[3]。現代基于循證醫學證據的治療方法和護理質量的進步大大改善了心衰患者的預后,1979年至2000年間,CHF的絕對5年生存率增加了9%,但CHF的發生和致死性仍然是醫療保健的重要問題,頻繁入院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4]。盡管美國心臟協會已經將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作為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可改變風險因素,但相當大比例的人群的身體活動水平非常低。對急性有氧運動刺激的適當反應需要來自肺、呼吸、骨骼肌和心血管系統的相互配合,而心臟收縮或舒張功能受損,則會造成由于疲勞和/或呼吸短促而導致的運動不耐受[5]。在過去的10年中,通過幾項隨機臨床試驗,確定了心臟運動康復訓練對美國紐約心臟協會(New York Heart Asociation, NYHA)分級Ⅱ級和Ⅲ級的穩定期CHF患者是有益的[6]。我院康復科觀察了高強度間歇訓練(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HIIT)/中等強度持續運動訓練(moderate-intensity continuous training,MCT)[7]和常規鍛煉(recommendation of regular exercise,RRE)對CHF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選取無錫市人民醫院自2016年5月~2018年1月收治的共254例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所有患者經由心內科門診入選。納入標準:明確診斷為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休息或運動時出現呼吸困難、乏力、下肢水腫癥狀及心動過速、呼吸急促、肺部啰音等體征,有超聲心動圖異常、腦鈉肽水平升高等心臟結構或功能異常客觀證據)[8],NYHA分級Ⅱ~Ⅲ級,經過完善的藥物治療并且病情穩定者。排除標準:1個月內曾因急性失代償性心力衰竭而住院治療的患者,合并其他內科疾病對于運動訓練難以耐受者,因精神異常或其他原因不愿或難以配合完成運動方案的患者。納入研究的患者以1∶1∶1的比例隨機分配至HIIT組、MCT組和RRE組,依據發病機制進行中心分層(缺血性和非缺血性),以避免治療差異引起的偏倚。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實施。所有患者均被認為接受最佳藥理學治療方案。所有患者中,由于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AE)導致9人退出,7人則因聯系中斷導致退出或隨訪不完全。在12周后對仍在組中的238名患者進行了評估,受監督的運動訓練次數的中位數為35(34~36)次,其中HIIT組和MCT組為36次,RRE組為4(3~4)次。最終納入研究的患者例數為:HIIT組81例,MCT組83例,RRE組74例,基線臨床資料見表1。3組患者的基線臨床特征無統計學差異。
1.2 方法 HIIT組和MCT組每周進行3次監護下的有氧運動訓練,在康復科的功率自行車進行,共運動干預12周。HIIT包括持續4min的高強度運動,目標是最大心率的90%~95%,間隔最大心率的60%~70%的持續3min主動恢復,共重復訓練4次,包括熱身和放松運動各5min,共計38min。MCT組則進行持續的中等強度訓練,目標是最大心率的70%~75%,持續30min。經預估,HIIT和MCT組能量消耗相似。根據目前治療指南的建議,隨機分配到RRE組的患者被建議在家鍛煉,根據個人情況選擇步行、上下樓梯、慢跑、踏車等形式,并且每三周參加一次中等強度訓練,運動強度為最高心率的60%~70%。運動時均有心電血壓監護。出現自覺不適癥狀、心電圖或血壓異常情況時及時終止運動。在所有實驗組中,在為期12周的干預后不再接受受監督的運動訓練課程,但研究者每4周與參與者進行電話聯系,以記錄臨床事件并鼓勵進行活動,隨訪共進行52周。
1.3 評定標準 入組時采集患者醫療史、人體測量、體格檢查作為基線資料、入組時、入組后12周及52周時,分別記錄如下觀察指標:①超聲心動圖:測量左室舒張末期內徑(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mension,LVEDD)、左室射血分數(LVEF,以百分數表示);②通過心肺運動試驗(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CPET)記錄峰值耗氧量(VO2peak,單位ml/(kg·min)、最大攝氧量時呼吸商(以比值表示);③空腹采血測定氨基末端腦鈉肽前體(NT-proBNP,單位ng/mL); ④使用醫院焦慮和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綜合情緒量表(Global Mood Scale,GMS)評估生活質量。⑤研究終點:主要研究終點是通過超聲心動圖比較各組LVEDD從基線到12周的變化。關鍵的次要終點是左心室射血分數和VO2peak的變化,后者也被認為是訓練效果的衡量標準。⑥運動訓練的安全性通過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AE)的比率來評估,SAE包括:a.全因和心血管死亡;b.需要住院或強化利尿治療的心力衰竭惡化;c.房性和室性心律失常;d.不穩定性心絞痛;e.不適當的植入式心律轉復除顫器電擊;f.其他事件導致入院或臨床評估。在監督運動訓練期間或訓練后3h內發生的SAE被認為是與訓練相關的[9]。

表1 3組患者基線臨床資料
LVEF:左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計量資料采用平均數(95%置信區間)表示,應用χ2檢驗對計數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驗證正態分布性和方差齊性,符合正態分布和方差齊性的3組計量數據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以Bonferroni's或Fisher's LSD事后檢驗方差分析進行組間兩兩比較,不符合的采用秩和檢驗,當P<0.05時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超聲心動圖和心肺運動試驗 3組LVEDD、LVEF、VO2peak、NT-proBNP等指標從基線到12周、基線到52周的變化情況在各組間比較,見表2。基線~12周,LVEDD的變化HIIT組與MCT組比較、MCT組與RRE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420,0.330),但HIIT組中LVEDD的變化明顯大于RRE組(P=0.040);基線~12周,VO2peak的變化HIIT組與MCT組比較無明顯差異(P=0.680),但HIIT組和MCT組較RRE組明顯升高(均P<0.05);LVEF及最大攝氧量時呼吸商、NT-proBNP變化的差異情況3組間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基線~52周,3組患者LVEDD、LVEF、VO2peak、最大攝氧量時呼吸商、NT-proBNP變化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2.2 生活質量調查 在基線、入組12周和52周時,對3組患者進行生活質量評估,醫院焦慮和抑郁量表、綜合情緒量表均未見明顯統計學差異,見表3。
2.3 SAE發生情況 在12周的運動干預期間,3組患者之間SAE發生情況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在13~52周隨訪期間,MCT組患者因心力衰竭惡化的入院率較RRE組和HIIT組明顯降低(均P<0.05),其余指標未見明顯統計學差異。見表4。基線~52周的SAE患者總數3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差異。52周時判定為因運動訓練引起的SAE事件數如下:HIIT,3例;RRE,1例;MCT,3例,組間無統計學差異。
3 討論
心衰康復計劃主要包括運動訓練、危險因素干預和心理護理,并對這些高風險患者進行密切隨訪和精細藥物調整[10]。大多數慢性心力衰竭治療指南建議將運動訓練作為穩定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效干預措施[11]。盡管如此,醫學界對于接受運動訓練作為患者管理的一部分仍有所疑慮,許多醫生仍然擔心高強度的運動計劃可能是慢性心力衰竭惡化的風險因素。在本研究中,對HIIT、MCT和RRE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進行了探究,并分析三者對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臟尺寸和功能的影響,為在中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開展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實驗提供理論依據。本研究中,HIIT、MCT和RRE均使患者的LVEDD、VO2peak等獲得改善,但除了運動作為藥物治療的輔助治療方式的作用以外,也與患者接受規范的藥物治療有關。HIIT組中LVEDD的變化與MCT組沒有顯著差異,但明顯大于RRE組,而MCT組與RRE組相比,LVEDD的變化沒有顯著差異,這一結果也佐證了HIIT與逆轉左心室重構的相關性,但本研究中HIIT和MCT對于逆轉左心室重構的具體作用并沒有明顯差異。目前的研究在這一問題上還存在爭議,HIIT對逆轉左心室重構的作用可能與運動方案和強度有關,但由于研究者們采用的方案各不相同,無統一標準,導致結論也各不相同。本研究發現12周運動訓練期間HIIT和MCT可以在相似程度上顯著改善CHF患者峰值攝氧量,顯著提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通氣能力,對于CHF患者的預后具有積極意義。52周時3組患者VO2peak已無明顯差異,說明運動訓練對于VO2peak的改善作用可能受運動訓練時間的影響,這些與部分研究者的結果相類似[12]。在本研究中,并未觀察到明顯的生活質量改善,3組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結果類似,這可能與RRE組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運動鍛煉相關,而不是部分研究中采用靜坐患者作為對照。安全性方面,本研究中HIIT和MCT的安全性較RRE并沒有明顯的劣勢,未發現HIIT組患者出現明顯的SAE發生率升高,運動訓練相關的SAE在各組間也未見明顯的統計學差異,這可能意味著本研究中所使用的HIIT方案是安全可靠的,但可能是因為本研究中患者特征和/或訓練方案的差異,也可能是因為HIIT組的運動強度還未到達臨界風險,而想要探究HIIT的安全性,還需要更加細化的運動強度分級,但同時,復雜的運動訓練計劃又會影響患者的依從性,這些都導致了研究HIIT安全性的困難[13]。目前還有許多問題未見解決,比如大量的研究結果來自于歐美人群,國內的研究較少,人群差異是否會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還不明確,需要在中國CHF患者中開展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實驗;本研究中HIIT和MCT對于LVEDD的改善作用并沒有明顯差異,LVEF的變化在各組未出現顯著性差異,因此HIIT對心臟尺寸和功能的影響仍然不確定,慢性心衰相關的分子標志物如NT-proBNP與運動訓練的相關性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究,HIIT的安全性也需要更進一步的考證。我們會繼續關注和跟進相關研究進展。

表2 基線~12周和基線~52周3組患者超聲心動圖、心肺測試指標及NT-proBNP變化的組間比較
與RRE組比較,aP<0.05

表3 3組患者入組前后生活質量調查結果比較

表4 3組患者SAE發生情況比較 例(%)
與RRE組及HIIT組比較,a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