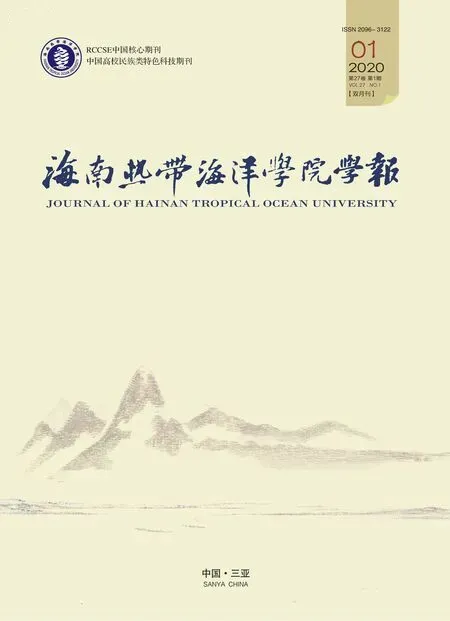從“惡婦”故事看宋朝婦女的主體意識
余慕珍
(西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重慶 400715)
“惡婦”故事是宋朝婦女敘事中的一種常見類型。學界較多關(guān)注“惡婦”群體的分類以及“惡婦”故事的事件性闡述,較少涉及宋朝“惡婦”故事的文本分析。作為宋朝婦女敘事中的一種常見類型,“惡婦”故事有其事實依據(jù)。即使有時夸大其詞、事涉荒誕,它所表達的敘事意圖也反映出宋朝婦女的實際生存狀態(tài)。在宋朝婦女婚姻家庭生活研究中,涉及“惡婦”較多。本文對宋朝“惡婦”的研究,并不贊同宋朝“惡婦”的“惡行”,而是想要深入剖析“惡婦”故事敘事的緣由以及“惡行”背后所隱藏宋朝婦女的生活境遇及其主體意識。對宋朝“惡婦”故事的文本分析有利于辨析“惡婦”故事書寫的實像與虛像,更準確地定位宋朝“惡婦”,從而關(guān)注宋朝婦女實際生存狀態(tài),并促使我們對宋朝婦女社會地位的進行思考。
一、 宋人筆下的“惡婦”分類
本文“惡婦”主要指悍婦、毒婦、妒婦等士大夫筆下不符合傳統(tǒng)女性賢良淑德的特殊女性群體。對于宋人筆下的“惡婦”,從行為上分類,大體包括妒婦、悍婦、毒婦三類。因妒忌而兇悍、而毒虐,因此妒婦是“惡婦”的核心問題,其記載數(shù)量最多。在宋人筆下,這種分類是對婦女失德的習慣性“譴責”,我們當然不能贊同此類“惡婦”的種種“惡行”,但我們更關(guān)心的那些婦女因何而成為士大夫筆下的“惡婦”。以下分類述之。
(一)妒婦
關(guān)于妒婦的故事各朝各代都不少,宋朝妒婦故事也是不絕如縷,詳見表1。妒婦大都為正室,她們或不允許丈夫納妾,或不允許婢妾靠近丈夫,或?qū)φ煞驅(qū)檺坻炬纳室猓瑢︽炬┡笆侄螝埲獭<啥适恰皭簨D”惡行的重要因素。
大部分婦女的妒忌都與丈夫?qū)檺坻炬蛘咄馐矣嘘P(guān)。宋朝社會允許男子納妾,妻子理應(yīng)接受丈夫的妾室。一旦妻子反對這種婚姻關(guān)系(如薛居正夫人、王欽若夫人不許丈夫置婢妾),被貼上妒婦標簽。若是妻子接受丈夫的妾室,但不允許婢妾靠近丈夫;或因忌妒對婢妾嚴苛,也被貼上妒婦標簽(如濟王夫人吳氏、楊郎中妻、蘄春太守妻晁氏)。丈夫納妾或養(yǎng)外室,“惡婦”或?qū)Ω舵炬版炬?如周益公夫人、胡宗甫妻等懲罰婢妾,張氏將丈夫在外所生庶子“擊堂柱”以致死亡);或?qū)Ω墩煞?如胡生妻張氏知其夫在外畜尼,不僅責怒更是“捽挽”其夫)。妒忌的婦女,不分階層,上至一國之母、朝廷命婦(如李皇后、濟王夫人吳氏、薛居正夫人),下至平民百姓(如楊郎中妻),上、中、下層婦女都難以避免。

表1 歷史文獻中的宋朝妒婦記載
注:按照成書年代排序。
(二)悍婦
在宋人筆下,與妒婦類似,悍婦也是對婦女失德行為的譴責,詳見表2。

表2 歷史文獻中的宋朝悍婦記載
注:按照成書年代排序。
從上表看出,一些婦女是因妒生悍,如夏竦妻楊氏、小吏妻等;另一些婦女并非因妒生悍,她們只是對丈夫或舅姑兇悍,如沈括的后妻張氏、呂等對丈夫兇悍無比,裴亞卿鄰家妻悍于事姑。還有部分婦女打破“女不言外事”[1]傳統(tǒng),參與公共事務(wù),也被貼上“惡婦”標簽,如曹圭妻、陸慎言妻。丈夫懼內(nèi)被視為妻子強悍的表現(xiàn),如安鴻漸。一些官員由于家有妒婦、悍妻而被降職甚至免職,如夏竦妻楊氏、王賓妻等。大澤正昭[2]在《“妒婦”、“悍妻”以及“懼內(nèi)”——唐宋變革期的婚姻與家庭之變化》談到,宋朝廷對“妒婦”問題采取的策略,比從前更明確。
(三)毒婦
在宋人筆下,除了妒、悍,還有一類婦女手段還殘忍惡毒,其施暴對象大都為婢妾,筆者將其歸為毒婦。詳見表3

表3 歷史文獻中的宋朝毒婦記載
注:按照成書年代排序。
由上可知,宋人筆下的“毒婦”多為正妻。施暴對象絕大多數(shù)都是婢妾,大多因妒而毒,手段極其殘忍,或箠之,或瘞之,或杖之,或殺之,各種手段層出不窮,視婢妾性命如草芥。婢妾大多年輕貌美而受寵,受到主母虐殺,如妾蓮奴、費錄曹妾、妾馬氏、妾眄眄等。正妻對懷有身孕或者有子婢妾心有忌憚,或殺孕婢孕妾,或沉婢妾子,以阻斷婢妾母憑子貴之路,如周令妻、周令妻、馬中行妻。在宋朝,法律塑造了妻-妾-婢的金字塔格局。正妻在家中居于主導,婢妾處于邊緣。對妻子而言,不管是婢還是妾,都是和丈夫有染或者可能與丈夫有染的一類。妻子憑借正室的權(quán)力與地位,對婢妾進行打壓,甚至虐殺。婢妾大都無反擊之力,最終落得悲慘下場。
二、 “惡婦”故事的內(nèi)在沖突
(一)“惡婦”故事的沖突結(jié)構(gòu)
通過分析宋朝“惡婦”故事,我們發(fā)現(xiàn)其大部分發(fā)生于家庭內(nèi)部之中,主要涉及到妻妾沖突、婆媳沖突、夫妻沖突。其中,“惡婦”與婢妾的沖突最多,與丈夫的沖突其次,與舅姑的沖突相對較少。
在封建大家長制中,舅姑在家內(nèi)是有相當大的權(quán)威的。婦人若是不孝舅姑,不僅會受到道德輿論的指責,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依舊有一些宋朝“惡婦”無視禮法,欺壓虐待舅姑。劉宰曾判過這樣一個案件,“有姑訴婦不養(yǎng)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3]12168。趙生妻李氏變成虎首,原因是“生時兇戾狠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鄰”[4]649-650。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斗,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捽拽顛仆至于死”[4]639。前文提及“鄰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于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4]47-48。村民謝七妻“不孝于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秔飯。頭面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4]430-431。這些“惡婦”與舅姑的沖突大都發(fā)生在下層階級家庭,上、中層階級“惡婦”與舅姑發(fā)生沖突的案例較少。
傳統(tǒng)夫妻關(guān)系大多以丈夫為主導,妻子處于從屬地位。正如《家范》記載“為人妻者,其徳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5]。但宋朝的一些“惡婦”卻反其道而從之,將丈夫收拾得服服帖帖。李大壯被稱“補闕燈檠”,一旦不遵其妻號令,“則叱令正坐,為綰匾髻,中安燈盌,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6]20。樂君家中米竭,樂君嬉笑對其妻說“少忍,會當有餉者”,妻氣極,“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走”[6]2660。張氏對沈括箠罵等,沈括未反抗[7]。周必大妻懲罰婢女,周必為婢取水,周必大妻譏諷其夫[8]。辛棄疾的岳父呂正已通宵飲酒狎妓,妻子呂踰墻相詈[9]。夏竦妻楊氏因丈夫?qū)檺坻炬煞虮挥放_彈劾降職[3]9571。士人妻得知士人將價值百金的書換了幾件銅器,大罵其夫[6]2929。究其原因,“惡婦”與丈夫的沖突是一方面由于丈夫?qū)檺坻炬缦鸟灯迼钍稀⒅鼙卮笃薜龋涣硪环矫妫齻兿氆@得家內(nèi)的控制權(quán),通過管制丈夫獲得更多話語權(quán)。
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盛行,妻妾斗爭向來都是常事。在正妻與婢妾的斗爭,正妻大多數(shù)時候都是勝利的一方,并不排除婢妾聯(lián)合陷害正妻的情況,但這只是絕少數(shù)。“惡婦”對婢妾的打壓虐殺毫不手軟,各種手段層出不窮。李后因為光宗心悅宮人的手而砍宮人的手送給光宗[3]8654,朱司法妻趙氏因丈夫?qū)檺坻眄矶鴮⑵渑皻⒌萚4]1341。妻妾斗爭的話題在筆記小說和正史中記載較多。根源即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法律賦予男人擁有多個女人。為了爭寵,女人之間斗爭在所難免,和睦相處的甚少。張邦煒《婚姻與社會宋代》提到,“正是一夫多妻造成了妻妾之間的爭風吃醋和相互殘殺”[10]。因此,妻妾斗爭是宋朝婚姻制度的產(chǎn)物。這種婚姻制度存在一日,妻妾斗爭必然存在。對于婢妾來說,她們的地位難以得到保障。為什么還有很多人趨之若鶩呢?除了生活的逼迫、家庭的壓力、自己的意愿等,還有什么原因驅(qū)使著她們呢?伊沛霞[11]認為,妾制度是階級統(tǒng)治的表現(xiàn)。封建社會除了在經(jīng)濟上榨取農(nóng)民,還用這種辦法侵占貧困階層的女兒,使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保持著緊密接觸,保證精英階層永遠不能完全切斷與普通人的道德、價值觀和生活經(jīng)歷的聯(lián)系。
(二)“惡婦”故事的沖突指向
“惡婦”與舅姑、丈夫、婢妾的沖突主要有三類。第一,爭奪家內(nèi)控制權(quán);第二,實現(xiàn)對丈夫的情感獨占;第三,爭奪公共事務(wù)參與權(quán)。其中第一、第二類“惡婦”較多,第三類“惡婦”相對較少。
第一類主要是通過與舅姑、丈夫斗爭實現(xiàn)的。爭奪家內(nèi)支配權(quán)最重要的是掌握家內(nèi)經(jīng)濟控制權(quán),與舅姑斗爭的核心主要圍繞家內(nèi)經(jīng)濟支配權(quán)展開。若舅姑管家,婦人對自己的嫁妝可以隨意支配,但很難在家內(nèi)擁有完全的經(jīng)濟支配權(quán)。“惡婦”與丈夫的斗爭,主要是通過讓丈夫“聽話”,從而在家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quán)與支配權(quán)。
第二類主要是通過與婢妾的斗爭實現(xiàn)的。婢妾的出現(xiàn),使得丈夫和妻子之間出現(xiàn)了第三者,妻子妒忌丈夫?qū)︽炬獙檺郏憷谜薜牡匚粚︽炬皻㈡炬詫崿F(xiàn)對丈夫的情感獨占。她們?nèi)菀子蓯凵剩啥噬坊蚨尽T趥鹘y(tǒng)社會婚姻制度下,多個女人共同擁有一個男人,婢妾與正室爭奪丈夫的寵愛。一旦妾室生育子嗣,會對正妻與嫡子產(chǎn)生威脅。因此,正妻不敢掉以輕心。
第三類“惡婦”并未在家庭中發(fā)生明顯沖突,只是打破“女不言外事”[1]的規(guī)定,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wù)中,卻仍然被貼上“惡婦”的標簽。結(jié)合前文的曹圭妻的故事以及胭脂虎的故事,曹圭妻與陸慎言妻并沒有與舅姑、婢妾沖突,只是“奪夫權(quán)在手”[13],也被記載者評價為“沉慘狡妬”[6]20“剛狠”[13]。陸慎言妻是由于“陸慎言政不在己”[6]20,被大家稱為“胭脂虎”[6]20。而曹圭妻則是因為“凡有男女訟于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13]。在當時的社會,婦人被認為應(yīng)該身處內(nèi)闈,處理家事,“男不言內(nèi),女不言外”[14]是整個社會都默認的事實,而不管是陸慎言妻還是曹圭妻都不滿足于內(nèi)闈,而是借助丈夫而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wù)中。而像她們那樣奪夫權(quán)在手,不被當時社會輿論道德所接受,她們被貼上“沉慘狡妬”[6]20“剛狠”[13]的標簽。這說明,“惡婦”是男權(quán)話語者對婦女的一種污名化解釋。他們想通過這種標簽把婦女困在內(nèi)闈,縛在家中。
分析“惡婦”故事發(fā)現(xiàn),各個階層都存在“惡婦”現(xiàn)象。但上、中層階級與下層階級“惡婦”內(nèi)在指向并不相同。上、中層階級“惡婦”故事類型中,“惡婦”與婢妾的沖突較多,與婢妾的沖突是為了實現(xiàn)對丈夫的情感獨占,其中較多地表現(xiàn)為妒婦,妒忌是這類“惡婦”故事的核心要素,由妒生悍、由妒而毒的案例數(shù)見不鮮。上、中層階級家庭大多有財有勢,納妾畜婢多,故女主人與婢妾發(fā)生矛盾的機會更多。下層階級“惡婦”故事中與婢妾斗爭案例較少,與舅姑沖突較多。這類婦女較多表現(xiàn)為悍婦,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爭奪以財產(chǎn)為主的家內(nèi)控制權(quán)。下層階級家庭面臨著基本生存的困境,迫于生活壓力難以支撐納妾畜婢的費用,從而女主人與婢妾發(fā)生矛盾的機會更少,而與舅姑接觸較多,故女主人與舅姑沖突較多。與丈夫的沖突存在于各個階層,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情感獨占和獲得更多的話語權(quán)與支配權(quán)。
三、 宋朝婦女的主體意識
(一)“惡婦”的實像與虛像
“惡婦”故事作為宋朝婦女敘事中的一種常見類型,必定有其事實依據(jù),但是書寫者所記載的“惡婦”與真正生活中的“惡婦”兩者之間是否有偏差呢?筆者認為這兩者之間肯定是有偏差的。歷史是客觀的,但記載歷史做不到絕對客觀,正如柯林武德所言:“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有一個由思想的過程所構(gòu)成的內(nèi)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過程,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15]且不論此觀點是否完全正確,但毋庸置疑的是,書寫者記載歷史的過程必定是一個進行思想加工的過程,不可避免會帶上一定的主觀色彩。
書寫者所記載的“惡婦”實際上只是宋朝“惡婦”的虛像,或者說表象,那些真實生活中的宋朝“惡婦”可能并沒有書寫者所記載的那么夸張。首先,從“惡婦”故事本身來看,“惡婦”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被記載者夸大化、神鬼化,比如《李氏虎首》[4]649-650、《謝七嫂》[4]430-431等故事,李氏的頭變成虎首,謝七嫂變成牛。這必定是由于記載者進行改編加工,從而警醒婦女行為,以符合社會道德規(guī)范。其次,宋人對婦人存在惡名化的描述,如《清異錄》記載:“朱氏女沉慘狡妬,嫁為陸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已,吏民語曰:‘胭脂虎’……俗罵婦人為冠子蟲,謂性若蟲蛇,有傷無補”[6]20。李昌齡《樂善錄》記:“大抵婦人女子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16]《洛陽搢紳舊聞記》載:“婦人之吝財與妒忌,悉常態(tài)也。以不妒忌疏財者,皆難事,況非治世。”[17]《袁氏世范》言:“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18]此類記載有失偏頗。在宋人筆下,“惡婦”的妒、悍、毒被稱為天性或者性格,如錢大夫之妻“天性殘忍”[4]423,趙氏“性慘酷”[4]1346,李皇后“性妒悍”[3]8654,晁氏“性酷妬”[4]742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婦女的主體意識。
同時,“惡婦”話語的書寫者都是男性,如洪邁、陶榖、張端義、周密等,屬士大夫階層。他們掌握話語權(quán),是男權(quán)話語的捍衛(wèi)者。作為記載者,他們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烙印與時人的主流思想,無法規(guī)避社會對于婦女的道德規(guī)范。“惡婦”的行為被夸大,以規(guī)范女性行為。
福柯認為,話語本身既是權(quán)力的產(chǎn)物,也是權(quán)力的組成部分。權(quán)力的實施,一方面會創(chuàng)造新話語,另一方面會加固或者削弱這種權(quán)力[19]。“惡婦”話語同樣是權(quán)力的產(chǎn)物,是男權(quán)話語的組成部分。統(tǒng)治階層支配著話語權(quán),同時想通過這種話語模式將女性一直束縛在內(nèi)闈,處于男權(quán)話語的陰影之下,從而穩(wěn)定社會秩序、鞏固統(tǒng)治。
社會對婦人如此嚴苛,婦人難道不會反抗?“惡婦”行為的實像是對男權(quán)社會的一種反抗。“惡婦”通過與舅姑、丈夫、婢妾的斗爭,通過自己的“惡”行來喊出她們內(nèi)心深處的吶喊,讓世人能看見她們,聽見她們的聲音。不管是與舅姑、丈夫,亦或是婢妾的沖突,都是對男權(quán)社會的不滿和反抗。與舅姑的斗爭,是在反抗封建大家長制;與丈夫的斗爭,是在反抗男權(quán);與婢妾的斗爭,是在反抗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她們的“惡行”是反抗男權(quán)社會對她們的不公和女性地位的從屬。由于時代的局限,她們的反抗不會激起大浪,但她們懂得去斗爭、去反抗、去爭取自己的地位,是主體意識初步覺醒的標志。
(二)“惡婦”故事所見宋朝婦女的主體意識
宋朝“惡婦”的惡名顯示女性對于男權(quán)社會的反抗以及主體意識覺醒。當然,這種覺醒與現(xiàn)代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絕,不可同日而語。宋代是封建王朝。這就決定其婦女主體覺醒的深度與廣度與今日情形不同。但是,至少宋朝“惡婦”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主體意識覺醒。
所謂女性主體意識是指女性意識到自己不是男性的從屬品,她們與男性平等,有權(quán)力質(zhì)疑男權(quán)與多偶制度。首先,“惡婦”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和男性一樣都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是社會主體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不是男性的附庸品;其次,“惡婦”通過跟舅姑、丈夫、婢妾的斗爭證明其人格尊嚴。她們不想受人支配,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擁有自由意識;最后,“惡婦”懂得去爭取作為一個擁有獨立人格的“人”應(yīng)有權(quán)利和地位,擁有了權(quán)利意識。在宋朝“惡婦”惡名之下,實際上卻是一場屬于自己的保衛(wèi)戰(zhàn)。
“惡婦”通過與舅姑、丈夫、婢妾的斗爭來爭奪自己在家內(nèi)的控制權(quán),捍衛(wèi)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她們斗爭的目的是以母親的身份為兒女鋪路。但他們大多并未將自己看成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而是以母親的角色。但這至少不是一味地依靠男人,懂得去爭取自由。
曹圭妻、陸慎言妻等沒有與舅姑、丈夫、婢妾發(fā)生明顯沖突,卻因為借助丈夫參與社會公共事務(wù),被貼上“惡婦”的標簽。女性走出閨門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wù)之中,以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wù)。這對被禮法束縛在家內(nèi)的宋朝婦女尤為可貴,是主體意識覺醒的主要代表。她們與為士大夫所贊揚的賢婦、孝婦、節(jié)婦等“順?gòu)D”不同。“順?gòu)D”一舉一動都符合古代社會的規(guī)范——上孝舅姑,下養(yǎng)子女,以夫為天,勤勤懇懇。她們甘心為男性生、為男性死,默認了自己作為男性附庸品的從屬地位,沒有獨立人格,強化了父權(quán)制的統(tǒng)治。而“惡婦”不遵守當時世人對女性的規(guī)范,或妒或悍或毒,肆意妄為、聽憑自己想法做事。她們或跟舅姑斗爭,或跟丈夫斗爭,或跟婢妾斗爭,或走出閨門、參與社會公共事務(wù),在當時社會為人詬病、不符合女德。但是,她們對男權(quán)社會的一種反抗,是對自己權(quán)利與地位的捍衛(w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