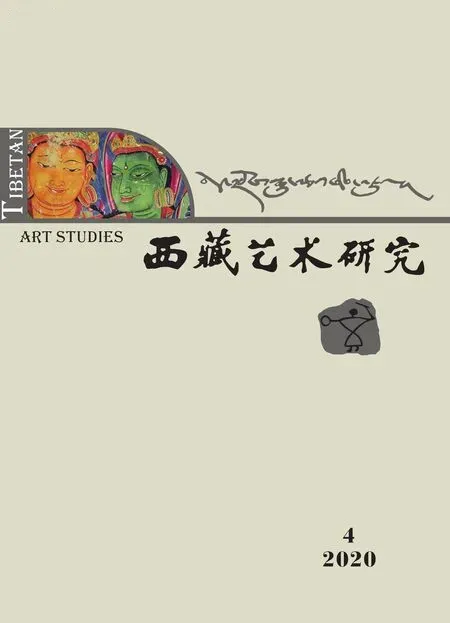變與不變:“覺囊梵音”三期田野的觀察與思考
盧 婷
一、問題的提出
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出臺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各國政府紛紛加入,推動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中國作為最早加入的國家,從政府到學界,官方到民間,全國上下共同參與到這場聲勢浩大的“遺產運動”中。這項工作從啟動到實踐的十余年里,不同的主體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帶著不同的目的和訴求介入其中,作用于各個“遺產”的當下存在和未來方向。長期從事少數民族音樂田野工作的蕭梅教授針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出了“誰在保護?為誰保護?保護什么?怎樣保護?”①蕭梅:《誰在保護? 為誰保護? 保護什么? 怎樣保護? 》,《音樂研究》,2006年第2 期。的問題,筆者循著這個思路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覺囊梵音”的傳承與保護工作給予了長期的關注。
筆者對覺囊梵音的關注緣起于碩士期間對藏傳佛教覺囊派中壤塘確爾基寺歲末驅魔法會音樂的考察。2009年到2012年期間,筆者在四川省阿壩州壤塘縣中壤塘鄉對覺囊派確爾基寺的歲末驅魔法會音樂進行了長期而深入的田野調查,對覺囊梵音的原生型態有了一定的了解。申遺之后,覺囊梵音走出古剎,走出偏遠的藏地,來到都市,進入音樂廳。筆者追隨著“覺囊梵音” 展演的腳步,完成了第二期田野——作為非遺展演的“覺囊梵音”的調查。面對申遺前后覺囊梵音呈現出的兩種不同的畫面,引發了筆者的一些思考。最核心的幾個問題,比如:“覺囊梵音”作為一種宗教音樂,它有寺院自己的傳承方式,為什么要加入申遺的行列呢?“非遺”會給“覺囊梵音”帶來怎樣的影響?“非遺”是否會改變“覺囊梵音”? 帶著這些疑問,筆者展開了對覺囊梵音的第三期田野,試圖能夠從中找到答案。
二、第一期田野:寺院法會中的“覺囊梵音”
覺囊派發端于公元12 世紀,是藏傳佛教中教義獨到而重要的一派,它以“中觀他空”為宗見,以修無上瑜伽續的“時輪金剛”法為主要特征,以“音聲供養”和“音聲佛事”見長。“覺囊梵音”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中壤塘鄉,這里保留了西藏覺囊文化的法脈和“梵樂”傳承。
壤塘縣位于阿壩州的西部,東部是馬爾康,東北部與阿壩縣接壤,南與金川縣毗連,西邊和南邊與甘孜州色達縣、爐霍縣、道孚縣相望,北鄰青海省班瑪縣。平均海拔3285 米。中壤塘鄉位于壤塘縣的北部,則曲河中游,為農牧區交界處,距縣城42 公里,面積約560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60 米,有4 個行政村,3600 余人。覺囊派自1378年傳入阿壩州壤塘縣中壤塘鄉,目前這里已經成為藏區的覺囊文化中心和根本道場,境內有藏哇寺、確爾基寺、澤不基寺等9 座寺廟,顯密體系完備。藏哇寺是其中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寺院,現有僧人600 余人。覺囊派的法脈和“梵樂”在這個區域得以完整保存并傳承至今。
覺囊派的歲末驅魔法會是通過誦經和金剛驅魔神舞——羌姆,來達到驅邪除魔的宗旨。法會前五天為誦經儀式,是僧侶內部的修供,后兩天舉行的金剛神舞儀式則可視為公開性的集體修供。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法會。在歲末驅魔法會中,音聲貫穿始終,是法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誦經儀式
藏傳佛教的的理念認為,“法會中的誦經儀式是通過其形式和內容作為手段,與各種佛教神靈進行溝通、對話的一種宗教儀式。”①多杰仁宗、滿當列、晁元清、王玫:《青海藏傳佛教音樂文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1 頁。藏傳佛教各宗派,都有不同的神靈供奉系統,這些神靈在不同宗派的寺院里有著各自的角色,或是主神,或是本尊,或是護法神,各自的身份和職責十分明確。法會中的誦經儀式實際上是寺院為諸尊神佛舉行的一次祭祀儀式,通過祭祀,把諸尊神佛請到法會的壇城中來,請他們來協助完成驅魔的任務。每一尊神佛都有其相應的經文,誦經的時間也有長有短。確爾基寺歲末驅魔法會中的誦經儀式分別在大殿內和大殿外進行,誦經內容及誦經中的法事活動見下表:

表1 誦經儀式內容
以上是每年藏歷12月23日至28日期間舉行的誦經儀式。大殿內的誦經以祈求、贊揚及迎請為主。誦經的同時伴隨著相應的祭祀、供奉儀式。誦經從23日起一直持續到28日凌晨,這期間僧人每天從早到晚不間斷地誦經。大殿外的誦經是在28日上午進行,誦經過程中通過“神飲”“調動”“咒”“焚燒朵瑪及靈嘎”達到驅邪除魔的目的。
(二)金剛神舞儀式
金剛神舞儀式是藏傳佛教寺院的一種密宗法事,它通過樂舞的表現形式,來達到祭祀神靈、驅邪除魔、弘傳佛法教義的目的。它既有強烈的觀賞性和表演性,更重要的是它蘊含著藏傳佛教密宗的深刻內涵。金剛神舞儀式由序幕、金剛神舞、尾聲三個部分組成,其中的音樂類型包括:誦經音樂、神舞中的器樂伴奏、儀仗行樂以及各種類型的迎請樂。“誦經音樂”指僧侶念誦經文時的聲樂(即各種誦經調),以及在誦經段落之間,穿插演奏的間奏性的器樂音樂,這部分音樂以聲樂為主,器樂為輔。“神舞中的器樂伴奏”是指神舞中統一舞蹈動作、控制整個舞蹈節奏的各種伴奏性器樂;“儀仗行樂” 指寺院儀仗隊在行進過程中的器樂;“迎請樂” 是指在神舞前寺院儀仗隊迎請法座的大型鼓吹樂、神舞中迎請法座的大型鼓吹樂以及神舞段落中迎請諸神出場時的中、小型鼓吹樂。音樂在儀式中的運用情況如下:

表2 金剛驅魔神舞儀式過程及音樂
在歲末驅魔法會中,音樂貫穿始終,是法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歲末驅魔法會中的音樂主要分為“俱生樂”和“緣起樂”兩類。俱生樂是指通過自身身體器官演唱的音樂,即聲樂。緣起樂指依賴一定的因緣而生的音樂,指人通過樂器演奏的音樂。法會中的“俱生樂”是指法會中誦經音樂中的聲樂部分,即各種誦經調。而“緣起樂” 是指法會中各種器樂音樂。歲末驅魔法會包括了“覺囊梵音”的所有類型,因此,法會是“覺囊梵音”原生型態的完整呈現。
三、第二期田野:作為非遺展演的“覺囊梵音”
伴隨著自上而下展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諸多傳統音樂被納入其中,“覺囊梵音” 也不例外。2009年7月,“覺囊梵音”被四川省文化廳列入第二批省級“非遺” 代表性名錄(項目編號:Ⅱ—7);2009年10月,覺囊派藏哇寺第47 代法主嘉陽樂住上師,被列入第四批省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2011年5月被國務院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遺”擴展項目名錄(項目編號:Ⅱ—138);2011年11月,覺囊派藏哇寺所在地被中國文化部列入“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阿壩州政府提出建設“覺囊文化中心”將其作為重點文化建設項目。2012年12月,嘉陽樂住上師被文化部公布為第四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代表性傳承人。2014年6月,覺囊傳統手工技藝傳習基地(覺囊梵音、覺囊唐卡等)被四川省文化廳公布為第一批省級非遺傳習基地。
從2009年12月起,應中華文化促進會的邀請并全程主辦,藏哇寺覺囊梵音展示團先后赴星海音樂學院、南京藝術學院、東南大學、上海音樂學院、浙江文化藝術研究院、武漢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北京大學、中央音樂學院、四川音樂學院等高校以及都市的劇院、音樂廳進行了10 余場次的巡回展演。

表3“覺囊梵音”展演情況
筆者現場觀看了2009年12月28 晚“覺囊梵音” 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的展演以及2015年12月10日在成都金色歌劇院兩場展演。兩場展演從內容到形式基本相同,第一部分為金剛舞,第二部分為普賢云供禪樂。以2009年12月28 晚“覺囊梵音”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的展演為例,在展演開始前,活動主辦方——“中華文化促進會”,高校學者以及“本文化持有者”分別對“覺囊梵音”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對于此次活動的主辦方——中華文化促進會認為:
“這不是一場通常意義上的音樂會,而是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演; 它既是中國藏傳佛教覺囊派梵音古樂的文化遺產,也是當地的地方文化遺產;它不僅是一種信仰的方式,而且是一種生活的方式。”①2009年12月28日晚“覺囊梵樂”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展演時中華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王石先生語。
高校學者認為:
‘覺囊梵音’ 是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今藏傳佛教中所保留的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古老品種。”②2009年12月28日晚“覺囊梵樂”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展演時中央音樂學院袁靜芳教授語。
“覺囊的梵音古樂是藏傳佛教傳統悠久的、古老的音樂,它是非常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也是有高度的文化價值的。舞臺上的覺囊梵音是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它不是世俗性的表演,而是宗教儀式的展示。”③2009年12月28日晚“覺囊梵樂”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展演時中央音樂學院田聯韜教授語。
對本文化持有者——嘉陽樂住上師而言:
“覺囊梵音古樂本身是僧侶修學的千年傳承法門,梵音古樂的旋律是智慧與慈悲的表現,本身就有加持力。無欲才能得其妙,以無我忘我的狀態感受天籟,啟迪心智。覺囊梵音古樂的展示一如僧侶日常進行的法事、功課,是平靜、自然、舒暢的生命狀態,所要表達的是生命內在最本質的心境與慈悲,聽者勿從中期待‘情緒流露、起伏轉折’。千年以來,它唱誦的是自己,聆聽的也是自己,不是為了展現什么,而是互為道場、互為主源,在神圣的狀態、氛圍中凈化、啟迪、提升自己的心智,展現自己的本來面目。這便是千年來梵音古樂修學者和實踐者的禪定修行狀態。修行者都能夠在梵音古樂中培養自己正面的情緒,發現自己內心的本來靈性,通過訓練使自己生命的正氣得以凈化、提升、超越,喚醒久違的文化記憶,重新開始與道的果位契合、與生命的果位契合、與本尊的果位契合、與覺囊文化脈象的果位契合。”①2009年12月28日晚“覺囊梵樂”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展演時嘉陽樂住上師語。
由此可見,對于舞臺上的“覺囊梵音”,不同文化身份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2015年12月10日,“覺囊梵音”作為“四川省第二屆藏傳佛教論壇”系列活動之一,在成都金色歌劇院上演。這次展演在內容上與之前的并無差別,也是由金剛舞和普賢云供禪樂兩部分構成。為了從更多角度了解人們對舞臺上“覺囊梵音”的看法,展演結束后筆者分別對現場觀看此次展演的普通觀眾和宗教界人士進行了訪談和問卷調查。
在訪談中,寧瑪派甲雍喇嘛談到:“在劇場觀看、聆聽‘覺囊梵音’跟自己在寺院的感受是一樣的,非常殊勝。劇場的展演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儀軌,剛開始是準備壇城,然后是迎請本尊、護法或空行,然后再祈請他們就位,再供養、祈禱、然后再修這個本尊,最后再請回他們的凈土,再回向,再頌吉祥。它的過程是完整的,像一個短片。”②③2015年12月11日,成都金牛賓館“四川省第二屆藏傳佛教論壇”筆者對寧瑪派甲雍喇嘛的訪談摘錄。
談到“‘覺囊梵音’走出寺院,在城市里做這樣的展演,這種形式好嗎? ”這一問題,甲雍喇嘛認為“這種形式是很好的,因為現代科技越來越發達,現在佛法也是按照現代的方式來弘揚和傳播,有些師傅講課,也是用PPT、音響、話筒、電腦等各種各樣的手段,現在佛教的很多經文都是用網絡的平臺來弘揚和傳播,社會很需要這樣子。在藏地來講,去參加法會、拜佛是很常見的,但在漢地,這樣的機會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讓大家感受一下這些殊勝的時刻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需要的。因為現在的人都很需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把自己的心靈凈化。在藏地跳金剛舞也是跟昨天一樣,也是給大家展示佛的凈土、本尊、護法這些,就是在法會那天給當地所有的老百姓看,昨天的展演也是一樣。”③
四川省甘孜州新龍古魯寺仁真郎加堪布認為“‘覺囊梵音’的展演,在法器的演奏以及唱誦方面與寧瑪派都有些不同,有它特別的地方,這樣的展演非常好,喇嘛們的念誦整整齊齊,很有程序,儀軌也是圓滿完成。”④2015年12月11日,成都金牛賓館“四川省第二屆藏傳佛教論壇”筆者對甘孜州新龍古魯寺仁真郎加堪布的訪談摘錄。
從上面兩位宗教界人士那里可以了解到本文化持有者的觀點:舞臺上的“覺囊梵音”和寺院里的法事或念經是一樣的,是在短時間內的一個完整的儀軌。
在問卷調查部分,共發放20 份調查問卷,收回16 份。調查對象均為高校在讀學生,學科背景分別為為人類學、音樂學、旅游、管理學;男生4 名,女生12名;學歷結構:本科2 名,碩士研究生11 名,博士研究生2 名,博士后1 名;民族:漢族12 名,藏族2 名,苗族1 名,回族1 名。在被調查的16 名觀眾中,有3/4的人去過藏地,近1/2 的人了解藏傳佛教,超過1/2的人去過藏傳佛教寺院,近1/2 的人在藏地寺院聽過僧人誦經,3/4 的人認為寺院的誦經和舞臺上的誦經是有區別的,3/4 的人認為舞臺上的“覺囊梵音”是一次宗教藝術的展演。這些數據表明,從局外人(普通觀眾)的視角,舞臺上的“覺囊梵音”是一次宗教藝術的展演,它有別于寺院的誦經和宗教法事。
四、第三期田野:法會與展演之間
因為“非遺”,從而有了兩個反差強烈的畫面的呈現。從局外人的角度,寺院法會中的“覺囊梵音”和作為舞臺展演的“覺囊梵音”呈現出來的是兩個既相關又相悖的型態。

表4 不同空間的“覺囊梵音”

圖1.寺院法會中的“金剛舞”

圖2.非遺展演中的“金剛舞”

圖3.寺院法會中的誦經儀式

圖4.非遺展演中的“普賢云供禪樂
相關是因為:舞臺上所呈現的“覺囊梵音”從內容來說它是從法會儀式中截取的一個片段。
相悖是因為:寺院中的“覺囊梵音”是僧人修行的法門,是重要的密宗儀式。對于信眾來說,法會是領會佛教教義的重要途徑,觀看、參加法會是接受密宗眾神的加持。而舞臺上的“覺囊梵音”,更多的是一種佛教藝術的展現,它將“覺囊梵音”從法會儀式中抽離出來,從而使它喪失了它本該具有的宗教功能。
由此可見,從局外人的角度,非遺給“覺囊梵音”帶來的改變是毋庸置疑的。“覺囊梵音”作為一種宗教藝術,它不同于民間音樂,寺院作為“覺囊梵音”的傳承載體,它有自己完整的傳承方式,為什么還要申遺呢?“覺囊梵音”在全國各地進行了多場展演,這些展演會給它帶來哪些影響呢?“非遺”是否會改變“覺囊梵音”呢? 這些問題,只能從本文化持有者那里得到答案,因此筆者對“覺囊梵音”的代表性傳承人覺囊派藏哇寺第47 代法主嘉陽樂住上師進行了訪談,內容如下:
“覺囊梵音已經傳承千年,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各種文化碰撞激烈的時代,梵音卻逐漸被邊緣化,面臨著失傳的境地。作為當代的僧人來講,有責任去保護和弘揚這樣的文化。我們應該從從文化的視角,從生命的視角,各個不同的角度來重新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不能說這只是一個宗教的、寺院的。作為我們繼承人來講,我們要清楚它的價值,它在生命層面的意義,這些都是我們有待于理解的,不是停留在這個是用來贊嘆佛的,這個是用來打鬼的,這些語言有一些誤導,我們自己作為繼承的人,我們要重新理解它。我們在整理、保護梵音的過程中正好遇到‘非遺’這件事情,跟它比較契合。佛教本來就有文化的這一面,我們可以從文化的角度去做這件事情,有這么好的一個和合點。我們進入學校是把我們當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這么好的一個切入點,這是多好的事情。”①2015年11月3日,成都市錦江區水錦界錦官驛街余慶會館筆者對嘉陽樂住上師訪談摘錄。
在對“覺囊梵音”的保護和傳承過程中嘉陽樂住上師及僧團已經對覺囊梵音300 多首央移樂譜進行了整理,使這些孤本得到了及時的保護。壤塘縣人民政府創建了“覺囊梵音傳習所和陳列館”,廣泛征集覺囊梵音文物,陳列覺囊梵音文物及圖片,并活態傳習覺囊梵音。如今藏哇寺有專門的梵樂團,將梵音如實、活態的傳承下去。
2016年9月年筆者對阿壩州文化局副局長、文聯副主席莊春輝進行了訪談,在談及“‘非遺’為覺囊梵音帶來了哪些影響”這個問題時,他這樣回答:
“從覺囊文化保護工作取得的成績可以看到,藏傳佛教傳統覺囊文化不但沒有‘遭到毀滅’,而且在新時代、新時期得到了科學、有效的保護、繼承、弘揚和巡回展示,煥發出了從未有過的生命活力和藝術魅力。覺囊梵音已經開始從寺廟步入內地大城市高等藝術院校音樂殿堂,從傳統的佛教走向人間化的佛教,從念誦的佛教邁向唱念的佛教,從宗教性到藝術性的展示,表現了大乘佛教慈悲普度、關心社會和諧、關心民族團結、關心國富民強、關心人類終極幸福與世界和平的胸襟和氣概,從信仰層圈擴散到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走出了藏傳佛教音樂搶救性保護的新路徑。我們期盼,覺囊梵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活態傳承更上一層樓,響徹妙高峰,聲聞三千界,莊嚴中華土,利樂有緣人。”②本次訪談于2016年9月15日通過電子郵件,采用書面一問一答的方式進行。
結語
隨著一次次田野的展開,筆者對“覺囊梵音”的理解也逐漸深入。“覺囊梵音”是與佛教教義、理念緊密相聯的。因此,對它的理解是建立在唱誦者、聆聽者對佛法的理解與修為的基礎之上的。對于沒有佛教信仰和佛法修為的普通聽眾,只能從藝術的角度去聆聽、去欣賞;對于佛教信徒來講,聆聽梵音的過程就是一種禪修,是對自己的“心”的發現;對于唱誦者本人,梵音則是對佛法的參悟、對佛的禮贊,是一種修行的方式,更是一次次佛法的布施。
“非遺”之后,“覺囊梵音”走出寺院,讓更多有情眾生聆聽到梵音,沐浴到佛法;讓梵音的傳承與保護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讓傳承者能從更多的角度,更加深入地理解自身文化的價值。“非遺”雖然改變了“覺囊梵音”的外在呈現方式,但其精神內核并沒有改變。在今天文化交融、碰撞激烈的時代,“非遺”與“覺囊梵音”的結合無疑是一段善緣。只要佛法駐世,信仰尚存,音聲便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