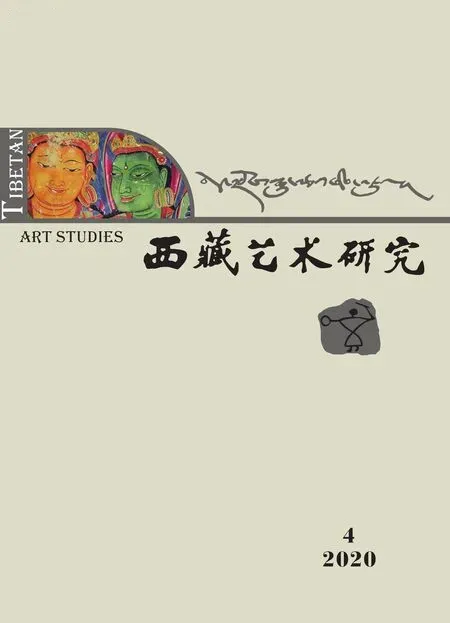嘉絨“甲扎爾甲”山窟壁畫遺存分析
澤仁曲措
甲扎爾甲山窟位于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市白灣鄉大石凼村甲爾扎甲山,2013年政府對此認定為明清時期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調查過程中未發現這記載中的其它佛塔,認為甲扎爾甲的命名很可能與其它文本有關。
沿著杜柯河,在離馬爾康白灣鄉政府駐地約五公里的公路邊,爬山一小時到達了甲扎爾甲山洞窟,它坐落在杜柯河南岸方向,洞窟坐北向南,在白灣鄉大石凼村甲扎爾甲山南側中上部,地理坐標為北緯31°48′20.6″,東經101°54′6.4″。據當地人介紹這里面的塔是當年刺殺吐蕃末代贊普俄頓贊普的拉隆貝多為贖罪而建,所奉108 座佛塔中的最后一座,因此被命名為甲扎爾甲。山洞窟立了一尊石碑,上面寫著“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甲扎爾甲山洞窟壁畫”,中間有甲扎爾甲山洞窟壁畫這幾個字的藏文寫法石碑背后有簡短的漢文簡介,(甲扎爾甲山洞窟壁畫,位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市白灣鄉大石凼村甲扎爾甲山南山腰處)2013年3月5日被列為第七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文物年代被認為明至清。甲扎爾甲洞窟壁畫內容豐富,人物神形兼具,形象逼真,是目前大渡河上游地區發現內容最多,繪畫面積最大的明清時期的洞窟壁畫。崖壁壁畫中僅有一幅位于洞口西側崖壁,其余都在洞內東側崖壁,壁畫依崖壁表面斷續相連呈片狀分布。隔墻壁畫總面積8.05 平方米,壁畫單獨分布于隔墻立面。“關于內窟的壁畫結構材料分析有相關專家細致的研究報告”①謝振斌、趙凡、劉建成(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四川文物》2017年第6 期,總第196 期.,此處筆者不再贅述。內窟中的壁畫研究對了解明末清初川西北高原藏傳佛教繪畫藝術、藏傳佛教的傳播和弘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據調研和史料確定甲扎爾甲山洞窟又是唐時藏傳佛教“七覺士”之一、藏族著名譯師毗盧遮那修行的地方,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一、壁畫的前世今生
藝術中的信仰與信仰中的藝術二者緊密配合,相得益彰,真正偉大的藝術總有偉大的信仰相融相伴。
壁畫的文化表征在特定的概念或空間中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意義。壁畫以畫風而流派紛呈,壁畫除了繪制佛像之外,題材廣泛描繪生活場景、歷史故事、民俗風情等,就其內容和社會功能而言,就其一開始展示的民俗化之外,在其發展環境中宗教化凸顯,也不斷地延續世俗化,并吸收了外來多方面的影響,表現出了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或許沒有一個純粹的當地文化,也沒有一個純粹的原生態,只是文化碰撞的火花帶來了更多的視覺與藝術盛宴。伴隨藏傳佛教的上下路兩次弘法,現今的涂繪壁畫研究一般都聚焦于以布達拉宮、阿里古格王朝遺址、托林寺、日喀則的薩迦寺、夏魯寺為代表的藏傳佛教寺院,這些寺院的壁畫完成了對印度和尼泊爾藝術的學習階段,以阿里和那曲地區為代表的雕刻壁畫,這些內容已有壁畫研究者和畫家、考古學家深入調研分析,對于嘉絨藏區這樣地處邊緣中的邊緣而言,苯教文化在此有許多歷史活動現存至今,或許就是基于這樣的地理位置,苯教或者嘉絨文化在藏文化中心的邊緣保持著它的活力,在持守和保留上展現著它自身的歷久彌新。
二、甲扎爾甲山洞窟內的壁畫內容界定
甲扎爾甲山洞窟的最外間有泥塑佛塔兩座,塔座塔身用礦物顏料,東巖壁上均繪有大量各式佛教壁畫,壁畫總面積約為七十平方米,從彩繪壁畫佛像來看屬于藏傳佛教神祇,唯一一個石刻文字是藏傳佛教皈依經,從藏文字體、文風、語法結構和正字法考量,是藏文文字第三次厘定之后,應該不是很早。所有手繪壁畫,主色單調,每尊佛像均由一種顏色繪制而成,佛光、身光、背光三個分別為三種不同的顏色,且這三種顏色所用和順序一致。以作畫人物涂繪、人物形態和所用顏色三個能見得因素考究,應該是十四世紀以前的作品。按照當地口述來看是拉隆貝多所建108 座佛塔中的最后一尊一說來看,壁畫應完成于唐武宗年間。

甲扎爾甲山洞窟門口,有簡單的扁石砌成的石墻將其分隔為外、中、內三間。按照情況應該不是早年就有的。

無量光佛,按作畫風格屬于傳統勉唐派,明顯有重繪的痕跡。也是洞窟內唯一一個繪畫顏料不同的壁畫。

山洞窟被命名為甲扎爾甲的佛塔,塔面四周均有畫。


這兩張為塔身壁畫,第一張左邊為喜金剛,右邊勝樂金剛。下面為五方佛,蓮臺下裝飾。造型比例嚴謹,此時西藏繪畫的線描都是不求變化的“鐵線描”,應是畫師資質的鼠須細筆所勾,顏色仍舊為青、白、紅三色。
第二面左邊佛像是大威德金剛十三部。右邊坐騎為牛的佛像損毀嚴重無法識別,根據能辨別出來的坐騎牛,應為紅閻魔敵。底座下面為五方佛。塔面上能辨認出來的有三尊佛像,這三尊佛像中缺密集,否則可推斷為格魯派無上瑜伽密法法系中最注重的本尊。究其溯源,本尊的修持可以說最早都從噶舉派的母續十三續部中延伸。

隔墻壁畫
時輪或者勝樂金剛,沒法從圖像志上描述。上面對此有描述,不再贅述。

佛教皈依經(皈依佛法僧)內容較為清晰,應是后期補刻的。



以上為窟面壁畫,每一副為一尊,裸體,佛身全用單色作畫。左手放置胸前,右手舉在半空中,無底座,左腿站立,右腿為半收式,耳垂長,雙眉間有畫點,發長而中部有綁著的發髻,兩邊披發,是金剛亥母,藏密無上瑜伽部母續的本尊。右手無法器的,屬于金剛亥母中的一種。

最左像是一尊金剛總持,中間為無量佛,右邊為釋迦牟尼佛像,流派應屬于齊吾崗畫派相關或者有相聯系的一種。


第一張佛母為紅色,佛像的大背光為靛青,身光為紅色。畫像大背景為靛青,兩張均為勝樂金剛。
畫像中無法辨清具體手印,按現能見度來看應是法定界印,佛像頭頂發髻來看是無量光佛。佛身均為白色,畫像人物眉目間哀愁,佛像有兩層背光,第一道為身光,靛青,第二道為白色大邊和紅色的鑲邊,袈裟顏色為白色。腹部下半已損毀,畫像人物眉目間哀愁底座已損毀不清。

這是壁畫唯一著白色袈裟的佛像,結跏趺而坐,法定界印。為阿彌陀佛,整體統稱為千佛。

雙手食指與拇指相接,其余三指微微彎曲,置于胸前,為結說法印,著紅色袈裟,為強巴佛(三世佛中的彌勒佛)。



人物所戴帽子為“貝霞”,意為蓮花狀的帽子,身著灰色或靛青長袍裹腳結跏趺坐,外批一件無袖肩聳式坎肩。

這尊像除了面部幾乎被損毀,但可以看出色澤單調,全部由黑白兩色構畫而成。帽子像是頭盔,人物神情較為嚴肅緊張,可能是一位戰神。

呈蹲坐姿,腳踩魔鬼,一面兩臂,雙臂抱一寶杖,右手持鉞刀,左手持髑髏碗。身上以五髑髏冠為頭飾、以骷髏項鏈和骨飾等為莊嚴,多處鑲嵌寶石,發上豎呈火焰狀,造型來看像是寶帳怙主。
窟內崖面壁畫均凹凸不平,整體呈現不完整,有自然或者人為因素的破壞的明顯跡象,有些壁畫按崖壁本身的形狀稍作鋪平寫作,有些則用泥土做平鋪做地杖,鋪底很薄,背景顏色采用大多為黑、白、紅,顏色使用相對單一。
在人類學的范疇或分類中,藝術人類學可能比較新而冷門,但藝術又是研究的熱點,是與物質文化、儀式、表演、身體、情感、感官等轉向互存的。以研究視野來看,人類學獲取了更為豐富的解釋視角,對于靜態模式的研究法則得到了學術范式的轉換。在這個過程中,藝術本身被視為最為突顯的能動性文化實踐而被重視。對于這種藝術實踐的創造,人類學家不認為是社會文化發展的必然“果實”,也不完全是文化交流與傳播,是這種文化實踐與社會發展互動的結果,并由此帶來的多樣性與留存。
人類學關注從社會與個體實踐之間互動的視角討論藝術的變遷和交換體系。大致有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是分析藝術生產的關系與因素,另外則是關注藝術本身產生的過程。對藝術的研究能對當下人類學在實踐、體驗、情感以及個體能動性與創造力等熱點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討論。
三、結語
以上的所見所感都是一個當代社會中的記錄,對于這高難度的山洞窟壁畫有一個賞心的文化感受,沒有體驗式的參與觀察法,對于當時的文化實踐者自身的選擇和態度,以及理解這種文化演繹和個人、群體、社會的關系都缺乏情緒感受。
西藏壁畫是藏族表達群體認同和復雜關系中訴諸行動的重要表征,這樣的文化表征在特定的概念或空間中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意義。因此,對于這些廣泛的壁畫發現都應是藏族文明發展中所產生的意料之中的收獲。除去宗教膜拜和記錄歷史、藝術之外,壁畫不像唐卡能被流通成為商品和藝術品。
我們無法追究這些壁畫的作畫者,究根結底這些都是百姓與藝術的先行者們共同推動。無法把握僧人及信教群眾與宗教圣物間的情感聯系。諸多植根于嘉絨的藝術氣息涌現在六月的甲扎爾甲。2015年,國家發改委核準四川大渡河雙江口水電站,地處水電站庫區的這一國寶級文物或將淹沒沉于庫底,對古代文化遺址保護歷史場景和文化場景都會遭到無法修復的損失。既然不能將遺址本身保持原樣,將盡所能把感受考察過的嘉絨藏族的文化氣場記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