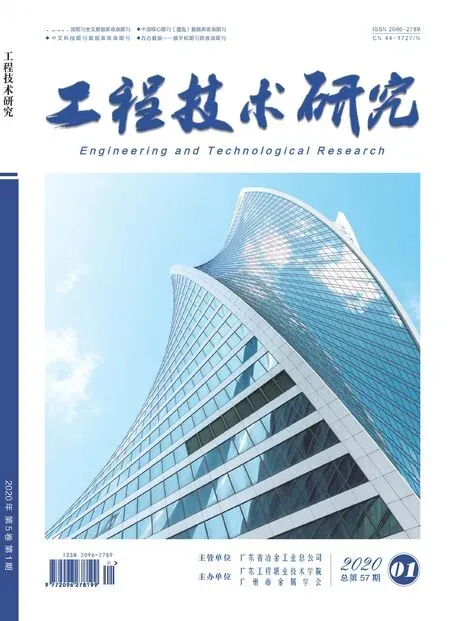不同而和:中國視野下亞裔美國文學對民族主義思想的“內在超越”*
張習濤,何 新
(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0)
亞裔美國文學是美國多元文化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構建亞裔美國人的族裔“想象共同體”意義重大。面對融入主流社會的排斥歧視以及民族主義壓制的“挑戰與應對”,華裔美國人用文學創作實績和文學研究成果躋身于美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中堅。無論亞裔作家如何與美國其他民族如何不同,他們都將適應和融于美國文化生活中,卷入創造個性化的具有華人文化屬性美國主流文學的文化身份中。
1 “不同而和”:亞裔美國文學的中國視野
亞裔美國文學的形成肇始于1960 年代末,受美國各地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和黑人平權運動、反越戰浪潮的大背景下,亞裔美國文學作品與研究應運而生、蓬勃發展,它是美國多元文化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亞裔美國人構建族裔“想象共同體”意義重大。美國華人作家作為亞裔美國文學的旗手和其作品在美國學院派文學研究中是與日裔、韓裔、菲律賓裔等其他亞裔作家作品被視作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的。然而,遍覽“亞裔美國文學”創作實績和文學研究成果,華裔美國文學是一枝獨秀的存在。這既是華裔美國作家對中國文化中“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崇尚,又是羈旅于美“發憤著書”的際遇決擇。從某種意義上講,“亞裔美國文學”和“華裔美國文學”在文學史的追溯與論述中是一對互為敞開、可以通約的文學類型。華裔美國作家作品作為詮釋亞裔美國文學的范本,為亞裔美國人贏來了文學成就上的世界性榮耀,構建了“亞裔美國文學”共同的體驗和形象,是美國主流文化的獨特風景,在美國多元文化語境中展示著弱勢族裔文化參與主流文化建構的努力。
“中國視野”與“全球化視野”是互動統一的。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必然的趨勢,“全球化視野”是個包容的存在,既體現各文化的軟實力又相互吸收兼容并蓄。在文學意義上,以“諾貝爾文學獎”類的文學評論機制等“全球化視野”成為考量世界文學作品的重要標尺,“中國視野”雖然作為亞洲經濟文化的代表和最重要的一極長期處在被遮蔽的位置。然而,在亞裔美國文學研究中,“中國視野”理應是引領亞裔美國文學研究的主流而非支流。在這一點上,華裔文學的創作實績奠定了“中國視野”的高度和廣度。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天然需要自然情感的潤澤、需要個性化的表達和獨特的情感體驗,越是個性、獨異越具有“文學性”。文學需要“全球化視野”,但這個視野是“散點透視”的,絕不是西方的或是某一國別的“獨木成林”,必須建立在有對話、有互動的基礎上,因而,“中國視野”“西方視野”應是雙向互動與融合關系,構筑起“和而不同”相相得益彰的文學研究格局。
“中國視野”立足于中國文化豐厚大地,融合亞洲文化色彩,眺望和審視“飛地”上的美國亞洲后裔,因而呈現出的獨特視角和理論關照具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基于此,本文以作品為中心尤其是以成果斐然的華裔美國作家的作品為中心,以“中國視角”來進行研究闡釋。
關于“中國視野”的內涵,由來已久,近年來成為“文化自信”的重要概念,成果日豐。在文學研究上,有借鑒“外位性”和“主體間性”理論,強調亞裔美國文學及研究的“唯一性”,并以發展的眼光而非“尋根”的態度,“并非想追尋亞裔裔美國文學中的族裔文化源頭,也無意以文化沙文主義的態度追溯中國文化對華裔美國文學的影響,更不是想鑒別華裔美國文學里所呈現的族裔傳統文化的真偽”,而是探討多元文化語境中弱勢文化的建構。有比較“臺灣視角”和大陸“文化中國”提出“整合之路”,擯棄地域偏見和政治、文化歧見,以文學母題為切入口,建構“文本聯盟”,突破研究者內部的歧見和紛爭,形成更加明晰的界定和認同。有學者從“東方主義”批評路徑研究“華人話語”建構,觀察研究“大中華情結”。此類研究均從民族化的角度試圖勾勒亞美文學中永恒的故鄉回望,延續母國文化,構筑“游子”精神家園,有著天然的“成見”和各個不同的局限。本論文中使用的“中國視野”從“和”“合”視角出發,正如華人學者林澗指出,在研究華美文學中不是去追問“誰是中國人?誰是美國人?”而是要問“為什么中國人就不能成為美國人?美國人就不能成為中國人?”這一深刻命題,探討亞裔美國文學的“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合”。
“不同而和”極易讓熟悉中國文化的人想到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本文使用此概念不僅于此,兼具中西文化思想。在西方,賀拉斯《書札》中的“不同而和”的概念是一種哲學思想,最初解釋為世界四大要素之間永恒沖突以及不和諧的統一,后被理解為一種不一致的和諧狀態或者一種對立物之間的平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是反過來理解的,和諧而個性斐然的對立統一也被認為是正道。
2 “身份焦慮”:構建亞裔族裔“想象共同體”
亞裔美國文學要融入主流文學最需要直面的就是現實人生“身份焦慮”。身份指的是生活方式,它還指社會尊重,也就是依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來賦予他或她以尊重和仰慕。在階級分層、種族林立的現實人生中,亞裔作家不可避免帶著身份焦慮。“來自彼岸的陌生人”華人移民自不待言,他們被認為是“生錯了皮膚”,是美國法律默許下的膚色歧視的受害者,為了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可不得不加倍努力。雖然華裔所遭受的不公明顯減少,然而當代美國華裔作家的作品都證明這種種族偏見依然存在。劉裔昌、湯婷婷等一批作家的小說中展示出的那種追尋美國夢的種種阻撓和挫折、封閉隔離的唐人街依然是華裔文學的重要主題。正如一位華裔所說:“生活在美國,生活在美國社會里,任憑是誰,只要他是白人,就能完全融入。但對我來說,不論我的思想多么西化,我的英語說得多么標準,我都無法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員。白人只要一看我的膚色,就想從我的英語里找出所謂華人口音。”
正是這種與生俱來的身份焦慮,反而讓他們團結起來,借助全球化的文化雜交和獨特的地緣因素和文化相近性。亞裔作家,包含但不限于華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韓裔美國人等漸次聚合,生成向主流文學抗爭的亞裔美國文學,而在這種抗爭與妥協的策略中融入美國主流文學。無論亞裔作家如何與美國其他民族如何不同,他們都將卷入創造美國主流文化,適應和融合于美國文化生活中去。
從這個意義上講,“亞裔美國文學”不僅僅是簡單的“文本聯盟”,更富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抗爭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包括流散移民集體身份焦慮的“想象共同體”,抗爭“身份焦慮”現實人生的約定。
外來移民包括其后裔要面對這樣的宿命,內在的本能的身份確認與飄搖的身份認同,在建構自我的安全感和認同中承受焦慮沖突。這種心理焦慮和心靈抉擇源自現實人生的體驗,包括語言壓制、族裔身份、社會地位、階層階級,在面對種族主義威壓,又兼有生存的壓力、成功的煎熬,以及事實存在的反亞裔情緒和束縛他們向更高層級發展的復雜現實,美國亞裔作家趨于選擇“文本聯盟”,體現出“相對功能主義”的策略,以獲得文學市場的一席之地。亞裔美國文學中的身份焦慮的表征為被措置的身體與受歧視現實的沖突,正是這種拘束的現實和自我設定的心理遭遇,世界起伏不定,讓亞裔族裔“想象共同體”獲得成長的空間。
3 “內在超越”:從“憤青”“中間人”到和諧共融
這種激烈的“沖突-重構”式的“內在超越”集中體現在一批華裔美國作家的創作中。
趙健秀自稱第五代華裔美國人,曾在華人學校讀過書,熟悉中國傳統文化。在《雞窩里的中國佬》中,趙健秀寫華裔和日裔青年“尋根”“尋父”和“尋我”的主題,主人公譚林先被刻畫成充滿矛盾糾結的“憤青”形象,對各“黃色湯姆叔叔”充滿嘲諷和批判,思維深刻而偏激。他腦海中“中國佬都是糟糕的父親”,同時又尖銳指出語言的壓制:“中國佬是制造出來的,而不是生出來的”。他認為語言是文化及感情的媒介,華裔不會講中國話,只會咿呀的幾個粵語詞匯是不能稱作華裔的,白人一直利用“語言專政”來壓制亞美文化,將其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事實也是如此,因而,白人評論家的確對這部劇表示不滿,并評論劇中人物“不像東方人”。這正應驗了賽義德的研究:“從19 世紀開始,歐洲人的書寫如何建造了一個作為奇異的、富有魅力而又危險的‘東方’的概念。然而這種假想的、簡單的構架依然被當做理解東方文化的強有力的文化隔欄而起作用。”
趙健秀一直在為重塑亞裔美國人的刻板形象斗爭。早在1973 年,趙健秀就創辦了亞裔美國人戲劇講習班,“為亞裔劇作家提供實驗場所”。次年,《哎——咿!》的出版被認為是“亞裔美國文藝復興宣言”。趙健秀在書中猛烈批判“刻板模式亞裔美國人”,批判傅滿洲、陳查理、容閎、林語堂、黃玉雪等作家迎合美國主流獵奇心理,旗幟鮮明提出亞裔美國人的獨特文化,并通過作品搖旗吶喊。《唐老鴨》就是趙健秀探索亞裔文化“獨立”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描述的是一個少年接受中國文化洗禮的成人儀式,推崇著中華男性英雄主義又批判盲目仇視美國主流社會,他試圖以新移民的語言優勢證明身份優異性。主人公唐納德由蔑視中國文化逐漸轉為認同和擁護中國文化,體現了華人反抗美國白人主流社會,重構主體自我的過程。趙健秀借用《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孫子兵法》等古老中國的“英雄”之血氣補足亞裔美國人文學形象上的陽剛勇猛,公開宣稱“寫作即是戰斗”“生活即戰爭”,試圖在紛擾的沖突中用英雄主義來重構自我,完成身份上的“內在超越”。
湯婷婷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重構亞裔美國人的身份。她對亞裔文學起到了奠基作用,她的作品《女勇士》《中國佬》《孫行者》暢銷全美,獲得獎項和榮譽無數,開啟亞裔文學進入美國主流文學的先聲。湯婷婷的作品給人印象深刻的是采取“不同而和”的文學重構策略,大膽借用亞裔故土文化遺產,在內容和取材上采用“中國手法”,在模式和風格上是“美國風格”,形成獨特的“中國神話美國故事”式的華裔風格。在《女勇士》中,湯婷婷借女主人對話隱喻亞裔美國文學的這種“內在超越”:“我們已成全球人了,媽媽如果我們和某一具體地點斷絕了聯系,我們不就屬于整個世界了嗎?媽媽,你明白嗎,現在無論我們在哪兒,腳下的土地都屬于我們呢,和其他地方沒有任何區別。”
任璧蓮和譚恩美對亞裔身份探討同樣深刻。任璧蓮的長篇小說《典型的美國人》展現了亞裔移民因移居美國而從較高階層跌落到貧民階層的身份焦慮,甚至陷入“中間人”的尷尬境地。譚恩美的《靈感女孩》對混血多族裔身份的探討同樣秉持“不同而和”的觀念。小說的女主人奧利維亞不僅自己是中美混血,她的丈夫還是中美英混血,這種混血身份“體現著諸如美國亞裔等少數族裔的文化混雜”。出身的混雜使他們在文化身份上難以歸屬于任何單一文化,產生難以言說的傷痛和內心深處的割裂。在日常生活中同樣面臨著行為和心靈抵觸的怪異現象,最后只有通過文化身份的互融,形成新的自我身份觀。“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在抗拒自己身體里屬于中國的那一半。我厭惡它。但是此刻,我終于不再需要在兩個身份之間搖擺。我一腳跨過了那道分隔我身體里中國和美國的兩個部分的門檻,卻猛然間發覺,這條分界線不過是我自己想象出來的罷了。我還是我自己,沒有變化,而且我不需要因自己本來的樣子而否定自己。”小說結尾,奧利維亞的兩種文化自我的對望象征著不同性質的文化在她的身上和諧互融。
4 結束語
對亞裔美國文學來講,“內在超越”的實現象征著亞裔美國作家以更自信的姿態坦然擁抱美國主流文學,另一面也是更自在地面向自己亞裔血脈里亞洲母國潛藏的文化基因。從身份的焦慮到“想象共同體”的再認同,從“憤青”“中間人”到坦然面對自己本來的樣子,亞裔美國文學作品表現出的“不同而和”的文化氣質對瓦解美國民族主義思想傾向具有很強的催化作用。對中國學者來說,研究亞裔美國文學不管是以“局外人”的身份還是從全球化語境下的“局內人”視角,“中國視野”都是具有巴赫金所指的“外位性”的。在亞裔美國文學的文化重構的“變化”中,“亞裔美國作家的文化實踐”遠比學者們的想象扎根更深入,吸收的母國傳統文化要多,創造性轉化的文學經驗更豐富。“中國視野”尤其是“中和”“不同而和”等理論已經開啟了研究亞裔美國文學新的闡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