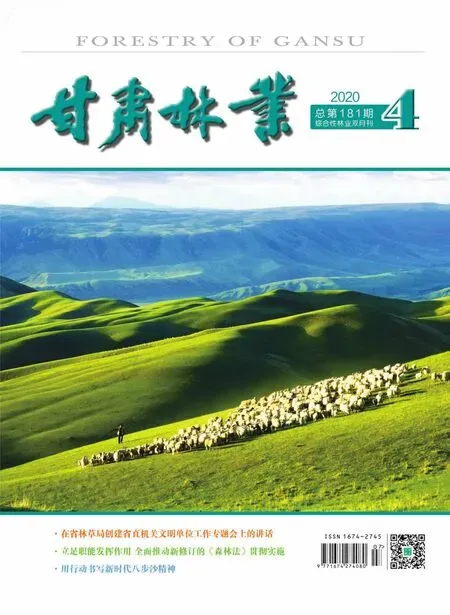守 候
“你老家是哪里的?”
“秦安的!”
“秦安人怎么會在張家川工作?”
當我問出這句話的時候又后悔了。我又是哪里人?為何在這里工作?或許在我心里想問的是離家這么遠,遠在異鄉的林區,在這空蕩蕩又滿是林木的關山林場,一個人的鄉愁會是什么?和我們困守在高樓大廈之間的會有什么不同?
初春的草木已然蘇醒,小河在日漸薄開的冰下流淌著,水聲潺潺,鳥兒繼續著它們的啼鳴。其實對于這座山林,我多年一次的到訪,只是它們見過的陌生人中的一個。對于他而言也是如此,他熟悉這山里的每一個林班,每一個樹種,每一片山坡的造林年度,哪個山溝里所居住的幾戶人家,每一種鳥鳴,每一個季節,但對于我而言他是陌生的。已是多年,我已忘記他姓甚名誰,但仍記得,他是一名關山林場的職工,他一個月要把所有的星期天攢起來,才能回一次遠在張川縣城的家。
由此,我又想到我的公公,一名小隴山林場司機。公公幾十年在山里,一年里為數不多的幾次回家,都是在天黑進門,一大早出門。孩子知道父親回來過,是因為家里多了一把山里的野菜,多了一些核桃。在通訊不發達的歲月,一封信輾轉好幾天,告知家里的情況,老人生病了,孩子今年上不上學,姑娘談對象了,不談及想念,不談及孩子被人欺負說是沒有爸爸的孩子,不談及這一月隨了幾份人情,給孩子報完名,生活費所剩無幾,不談及生日,不談及節日。好像所有不談及的事情都不必一一澄清,在一個維持生計的女人與困守山林的男人之間,一切都有了約定俗成。在老公他們幼小的心靈里,那時爸爸很遙遠,只有到了寒冬臘月,才能真實體會父親的存在,可以為兒子制作一個鐵環,可以為姑娘修修自行車,劈柴生火,買一次菜,只是好像還缺點什么?
不管是我叫不上名字的那名職工,還是公公,他們都有草木一樣純凈的眼神,有生活中的樸實。那時候我的孩子還小,當我每天抱著幼小的兒子急匆匆出門,總能看到退休多年的公公早已站在每天接孩子的地方。有幾次出門晚了,等我們出門時他已經在小區門口等待多時。在家人面前,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公公因為工作辛苦而抱怨過,也從來沒有因為一千多塊錢的退休金而抱怨過。從他身上,我看到老一輩林業人的堅守、付出。
如今林區職工生活條件得到很大改善,通往每一個林區的路也修好了,車越來越多,信息化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縮短了,但更多的年輕人卻不愿意留在山里。
但從大多數林業人身上,你依然能看到那份大山一樣的沉默,依然能看到那份草木一樣的質樸。或許正是這樣,走近他們才讓人倍感親切。與我相比,他們才是森林的真正守護者。
一條上山的路比回家的路更熟悉,職工宿舍門口的云杉,松樹,從林子里跑出來的一只松鼠,都比女兒更熟悉。他們知道每一種植物的習性,卻不熟悉兒子的脾氣;了解山里哪片云彩會下雨,卻不知道家中冰箱里會有什么食物。很多人都知道醫生辛苦,老師辛苦,卻很少有人知道林場職工更辛苦。這些守護在大山林子里的一線職工,他們將心里的一份責任,分散給林區里的每一棵樹,每一棵草,甚至宿舍屋檐下的那一窩燕子。對他們而言,生活中的喧鬧或許是清晨鳥兒比鬧鐘更準時的鳴叫;對抗寂寞、潮濕晚上喝幾杯小酒之后的宣泄。除此而外,便是爬山、種樹,早出晚歸,再就是象盼望兒女一般,期待著一片林子長大、成熟。
一代又一代的林業人把青年、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留在大山里;把幸福、困惑、憂愁、痛苦,一個人一生的境遇留在森林里;把一個人一生的守候、期盼留在山溝里。當他們把山一樣的沉默帶出山的時候,他們已然老去。在他們的夢里,之前是父母,是童年,是妻兒,是想見而不得見的人;之后會是山,是樹,是相見不得見的山與水。
只是,他們從來都沒有說出來,是一座山讓他們守候一生,是滿天星斗守候了他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