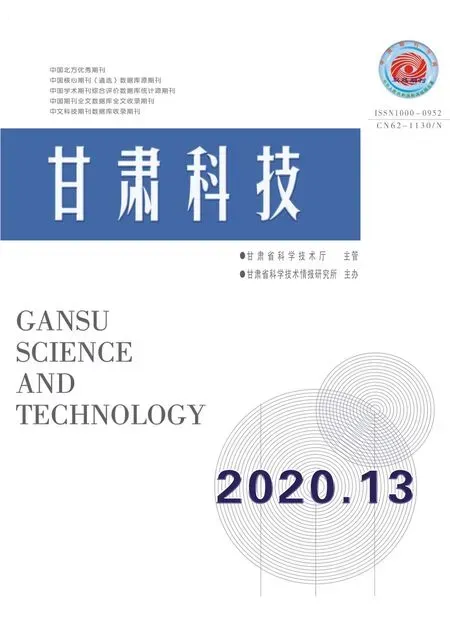高職院校辦學風險及其防控策略研究*
牛國林
(渤海船舶職業學院,遼寧 興城 125105)
《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出臺,開啟了高職教育“跨界、整合與重構”[1]的新時代。龐大的辦學規模、復雜的組織功能、多元的利益關系、激烈的院校競爭和市場的不確定性,使得高職院校日漸成為 “開放的復雜巨系統”[2]“人類最難管理的組織之一”[3],辦學風險不斷上升。如何應對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有效防范辦學風險,成為高職院校管理者不容忽視的現實課題。
1 高職院校辦學風險的主要類型
1.1 戰略決策風險
戰略決策風險指領導班子重大決策失誤導致喪失重要發展機遇,學校戰略目標無法實現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嚴重性。戰略決策涉及學校的發展方向、辦學定位、改革路徑、組織文化、辦學效益和競爭力。這類風險主要表現為重大問題決策失誤、重大規劃偏離方向、規章制度框架失靈、思想政治建設缺失等[4]。
1.2 校園安全風險
校園安全風險指特定時間內學校師生生命健康受到損害、財產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嚴重性。主要有地震、極端天氣等自然環境風險,群毆、盜竊等社會治安風險,食物中毒、傳染病等公共衛生風險,火災、擁擠踩踏等事故災害風險,非法集會、游行等社會政治風險,以及車禍、猝死等校園意外風險等。
1.3 財務管理風險
財務管理風險指學校各種財務活動中,實際財務成果與預期財務成果相背離,學校蒙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嚴重性。這類風險主要由籌資風險、投資風險、資金回收風險和收益分配風險等構成[5]。主要表現為資金結構失衡、債務負擔過重、預算流于形式、資金短缺、財務違規、投資虧損等。
1.4 辦學質量風險
辦學質量風險指辦學治校理念不清、師資隊伍力量薄弱、專業課程設置失當、管理評價導向不明、辦學設施陳舊落后等因素,導致學校綜合實力和競爭力下降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嚴重性。主要表現為教風學風不良、教學質量下滑、招生就業困難、優質師資流失、學術失范頻發、社會形象不佳等。
1.5 廉潔從業風險
廉潔從業風險指干部和教師工作中由于思想道德偏差、制度約束不力、崗位職責失范、權力制衡缺位等引發腐敗行為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嚴重性。主要表現為濫用職權、任人唯親、失職瀆職、以權謀私、學術造假、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等。這類風險主要發生在招生、考試、財務、基建、干部任用、校辦企業和后勤服務等領域。
1.6 信用違約風險
信用違約風險指學校或利益相關者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或不能按照合同履行約定義務,致使學校信用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嚴重性。主要表現為學生惡意拖欠學費、對內對外合同糾紛、招生就業失信、征信造假等。這類風險大多發生在人力資源、招生就業、財務后勤、合作辦學、科學研究、學生資助等領域。
2 高職院校辦學風險的主要來源
2.1 社會環境因素
一是意識形態方面。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利用其掌握的網絡資源和技術優勢,制造大量混淆視聽的負面輿論和有害信息,導致極少數學生否定和排斥主流意識形態。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高發頻發,一些社會問題對學生思想觀念產生沖擊,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泛濫,少數學生關注物質利益、輕視意識形態。二是經濟方面。高職院校規模擴張導致政府財政壓力增大,政府拖欠教育經費。欠發達地區學校爭取社會性投資的可能性很小。資金短缺帶來的辦學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等問題,導致一些學校招生困難、人才流失嚴重。一些學校盲目擴建、過度貸款,由于流動資金短缺,容易出現財務違規問題。產業結構調整沖擊學校人才培養模式,造成畢業生就業困難。三是文化教育方面。國際交流擴大和外來文化沖擊,給學生教育管理帶來諸多變數。重“學”輕“術”教育傳統,造成對職業教育的獨特價值認識不到位,容易出現工匠精神缺失的質量風險。
2.2 校內環境因素
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往往是風險產生的根源。權力過于集中、行政權力強勢、監督制約不力、權責錯位缺位、責任道德淡化等問題引發的風險不容忽視[6]。師生參與民主管理和監督的機制欠缺、渠道有限,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得不到落實,容易出現亂決策、違法決策、專斷決策、拍腦袋決策,進而基層執行決策時陽奉陰違、各行其是,給學校運行帶來風險。權力集中在學校層面,職能部門擁有更多的資源支配權和行政主導權,管理事務繁雜且效率不高。院系承擔了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主要辦學任務,自主權卻很少,從而缺乏參與學校事務的積極性。基建、后勤、財務等部門制度不健全,給權力尋租者留下變通空間。在校生規模超越生態承載能力,學校資源環境與質量、規模和效益的共生狀態失衡。實用主義的人才培養方式缺乏對全面發展和創新能力的關注和培育,束縛了學生個性發展,容易誘發質量風險。重科研、輕教學有悖于高職教育根本任務和教師基本職責,對人才培養質量構成威脅。
2.3 學校管理者
戰略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不足,風險認知差異,道德操守匱乏,價值取向嬗變等主觀因素,導致管理者做出的決策具有風險性。一是知識能力因素。有的學校領導理論素養、法制觀念和管理經驗缺乏,對關系師生切身利益問題處理不當,容易引發群眾不滿情緒。有的學校領導受社會浮躁及趨利風氣熏染,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急于求成,追求政績,容易出現違規辦學問題。二是性格習慣因素。有的學校領導敢于冒險,不善于聽取各方面意見,容易導致決策失誤。有的領導優柔寡斷,瞻前顧后,不能適時決斷,容易錯失發展機遇。有的學校領導開拓進取意識不強,習慣于等靠要,深層次矛盾長期累積。三是道德操守因素。有的學校領導不注重自我修養,宗旨意識淡化,紀律規矩淡薄,官僚主義、享樂主義抬頭,個人私欲膨脹,容易出現權力尋租和腐敗行為,引發廉政風險。倫理道德和職業操守的邊緣化往往表現為權力異化,只追求“善行政”,卻不能“行善政”。
2.4 多因素交互作用
各類風險源交互作用催生了學校辦學風險結構。有時一個風險源催生另一個風險源或者同時發生,對風險擴散起到推動作用。學校與行業、企業和社會聯系緊密,這種強感染性和高關聯度會使不同節點上積聚的風險源交互作用,形成風險擴散。比如,國家職業教育政策重大調整,使學校先期承諾與現行政策矛盾,得不到兌現,而學校違約可能導致企業上訪、學生抗議等連鎖反應。有時一種風險源會一定程度催化另一個風險源變異,形成新的風險。學校辦學風險源的積累和釋放還取決于管理者的決策,可以在風險源演化為現實危害之前,從根本上改善風險結構。比如,擁有權力的學校職工都有發生腐敗的可能性,關鍵取決于行為人自身選擇。“想腐”來自主體風險源,“能腐”基于內部風險源,“敢腐”涉及外部風險源。而廉政風險防控的目標是通過教育、制度、監督和懲治,使行為主體“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從而營造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
3 高職院校辦學風險的防控策略
3.1 樹立積極風險理念
“風險在現代社會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具有多維度、多層次、多領域的復雜性,但也是可以治理的。”[7]積極風險理念主張客觀理性地認識、積極主動地應對風險。學校管理者要強化風險意識,承認風險的客觀存在,而風險的內容、來源和大小,需要通過主動研究做出理性判斷。基于理性的樂觀是面對風險的應有態度。要堅持責權利對等原則,如果學校管理者輕視甚至無視風險導致重大決策失誤,應承擔相應責任;如果對風險進行理性權衡之后做出了正確決策,規避了重大風險損失,應給予相應激勵。
3.2 建立風險評估機制
風險評估主要是對風險代價、發生概率、是否可控等進行研判,以便于作出正確決策。評估的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合法合規性評估,看決策主體、內容和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和政策。二是合理性評估,看決策事項是否符合師生利益,措施手段是否適當,是否侵犯師生合法權益。三是可行性評估,看決策實施的時間、空間、人力、物力、財力等條件是否具備,實施方案和配套措施是否可行。四是可控性評估,看決策是否可能引發嚴重影響穩定的問題,以及有無預警措施和應急預案[8]。
3.3 提高風險識別能力
風險識別是從錯綜復雜的環境中找出面臨的主要風險,以及對風險發生的概率、可能造成的損失等進行判斷。學校治理的復雜性,風險觸發的未來性,決定了風險識別具有一定難度。風險識別可以通過調查問卷、事故記錄分析、專家訪談等途徑來進行,也可以借助大數據技術,綜合利用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構建風險評價和預警指標體系,實現對風險因素的實時監控與分析、對風險的實時甄別與篩選,在精準識別的基礎上,通過提前規避、風險控制或風險補償等措施進行有效治理。
3.4 完善風險應急機制
潛在風險一經觸發,就容易演化為突發事件。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包括控制事態、調查分析、制定對策并組織實施、評估結果、總結經驗、重塑形象[9]。應急機制一般由事前預警、事中處理和事后安排三個環節構成。事前預警到位有利于管理者做出準確決策,減少損失或者避免事態擴大。事中處理是根據預警信息對事件迅速做出正確判斷,當機立斷做出恰當的處置決策,并組織實施。事后安排主要是恢復和重建,涉及責任問責、心理調適、思想教育、總結反思等活動,進一步優化防控措施,在實踐中不斷增強駕馭風險本領。
提高辦學風險防控能力是高職院校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實踐中既要警惕小概率、難以預測的黑天鵝事件,也要重視大概率、可以預測的灰犀牛事件;[10]既能平息大的動蕩,也能把風險遏制于萌芽,防止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局部風險演化為系統風險,營造向新向好向上的發展態勢,是高職院校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破障之道、固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