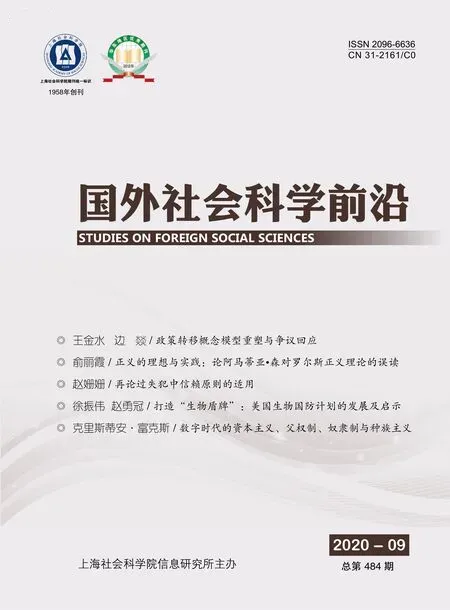再論過失犯中信賴原則的適用
——對深町晉也教授化解危險接受困局思路的揚棄 *
趙姍姍
內容提要 | 在新過失論的構造下,信賴原則是有關過失犯客觀預見可能性的原則。這一原則,對判斷現代社會中過失犯的成立與否具有重要價值。關于信賴原則的適用,日本深町晉也教授借助該原則剝離出危險接受案中具有刑法意義的過失的思路具有啟發意義,但以“理性”為基礎的經驗法則因過于主觀而不十分可靠。在對深町教授之見解的揚棄過程中,應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實情,重構信賴原則的適用規則。即,將規范信賴作為事實信賴的依據,并針對危險接受案、監督過失案、交通事故案的具體類型,適用不同的處理路徑,以判斷是否成立過失犯。
一、有關信賴原則的觀點聚訟與研究現狀
(一)觀點聚訟
所謂信賴原則(Der Vertrauensgrundsatz)的最初含義,是指“一切交通關系的參與者,在依據交通規則而信賴其他參與者會采取適切行為的場合,對于該其他參與者之不適切行為所導致的結果,不承擔責任的原則”。1西原春夫 《交通事故と信頼の原則》 成文堂,1969,14頁。首次適用該原則的刑事判例是德國1935年12月9日帝國裁判所的判決,2RG St 70-71.其后聯邦裁判所在1952年7月8日的判決中最先明確采該原則。3BGH St 3-49.1959年,信賴原則經由西原春夫教授引入日本,并在日本1966年的判決中第一次被正面適用。我國臺灣地區適用信賴原則的判決始于1981年,該判決稱:“汽車駕駛人應可以信賴參與交通行為之對方,亦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相互為遵守交通秩序之適當行為,而無考慮對方將偶發的違反交通規則之不正當行為之義務。”41981年臺上字第6963號判決。其后,歷經1985年判決對適用規則的進一步說明與諸判決的闡釋,51985年臺上字第4219號判決。我國臺灣地區“信賴原則之適用,已無任何爭議矣。”6廖正豪:《過失犯論》,三民書局,1993年,第206頁。
關于信賴原則在階層犯罪論體系中的位置,學界見解不一,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主張:首先是,否定構成要件該當性說。該說中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過失犯中的客觀注意義務由客觀的結果預見義務與客觀的結果回避義務構成,采納信賴原則,是將客觀注意義務的內容加以具體化的原則。7參見陳子平:《刑法總論》,元照出版公司,2017年,第222頁。具體而言,有的學者認為,信賴原則關乎的是預見可能性。例如,學者指出,“信賴原則,是將客觀預見可能性這一抽象標準進行具體化的原則”;1曾根威彥 《刑法総論(第4版)》 弘文堂,2008,176頁。“ 舊過失論下,信賴原則在體系上無從定位。然而,作為預見可能性對象的行為不單是行為,而是對法益有實質危險的行為。……在信賴原則發揮作用的場合,行為人的行為便不具有實質危險性,從而便從預見可能性的對象中被排除。據此,信賴原則關聯的是預見可能性問題。”2堀內捷三 《刑法総論(第2版)》 有斐閣,2004,130頁。此外,一部分學者的關注點并不在客觀的預見可能性,而是認為信賴原則關乎客觀結果回避義務。例如,學者指出,“信賴原則,從行為危險性的角度來看,是限定結果回避義務的原則”;3山口厚 《刑法総論(第3版)》 有斐閣,2016,257頁。“ 如果預見可能性僅有危懼感就足夠了,那么,信賴原則并非是否定預見可能性的原理,而是免除風險負擔、否定結果回避義務的原理。”4高橋則夫 《刑法総論(第3版)》 成文堂,2016,232頁。上述兩類觀點以外,在否定構成要件該當性說中,有的學者并不從注意義務的內容上探討信賴原則的機能,而將信賴原則的作用機理聚焦在因果關系上,認為適用信賴原則的場合會產生與因果關系的交錯,并通過否定相當因果關系,進而否定構成要件的該當性。5參見岡野光雄 《刑法要説総論(第2版)》 成文堂,2009,199頁。其次是,違法阻卻事由說。主張此見解的佐久間修教授指出,“信賴原則具有決定如何在加害者與被害者間分配注意義務的側面,與交通領域中危險分配的法理存在表里一體的關系。基于這一意義,信賴原則是將被容許的危險或適度的危險具體化的法理,左右著過失犯的違法性。”6佐久間修 《刑法総論》 成文堂,2009年,153頁。再次是,否定或減輕責任事由說。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中,有的學者認為,“在有合理根據可以信賴對方能夠采取適切行動的場合,否定行為人主觀上的注意義務”;7神山敏雄 “信頼原則の限界に関する一考察” (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文集(第二卷)》,1998,成文堂),49頁。“ 信賴原則的機能無非發揮在注意義務的領域……乃是否定作為責任要素的主觀注意義務的原則。”8立石二六 《刑法総論(第4版)》 成文堂,2015,253頁。但有的學者卻認為,適用信賴原則并非是對主觀注意義務的全部否定,而是“在新過失論中,適用信賴原則減輕了行為人的責任”罷了。9大 越 義 久 《刑 法 総 論(第5版)》 有 斐 閣,2012,141~143頁。最后是,既否定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又否定責任說。這一立場的代表學者為林干人教授,其指出,“信賴原則既可以否定客觀注意義務,也可否定責任,哪一方也無法一家獨大。”10林幹人 《刑法総論(第2版)》 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298頁。
以上聚訟源自學界對違法性本質認識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了學者對過失犯構造的理解。例如,立足于行為無價值的新過失論者通常認為,信賴原則應被定位于構成要件該當性階層,只是對該原則具體影響了何種要素(客觀結果預見可能性、客觀結果回避義務或因果關系)存在分歧。而結果無價值論者則分為兩派:舊過失論者不承認構成要件的過失,故適用信賴原則的場合只能主張否定責任;而修正的舊過失論者因承認過失實行行為,故也在構成要件該當性階層檢討信賴原則的機能。在部分修正的舊過失論者看來,過失實行行為是對法益具有實質危險性的行為,而所謂的“危險”意味著客觀的預見可能性。11曾根威彥 《刑法における実行·危険·錯誤》 成文堂,1991,62~68頁。既然適用信賴原則否定了這種預見可能性,自然也否定了實質危險,進而否定了過失實行行為的存在。
(二)當前理論研究的不足
溯究信賴原則產生的理論基礎可以發現,其脫胎于被容許風險的法理所確認的風險分配理論,或者說與被容許風險、風險分配理論互為表里,承擔著縮小注意義務的范圍、適應現代發展需要的機能,具有進步意義。盡管關于信賴原則的體系位置尚存在諸多分歧,但是,既然學界承認該原則在體系上有所定位,則無異于認同其在限縮過失成立或減輕過失責任方面的價值。因此更多的學者主張,信賴原則可以適用于交通事故以外的其他領域。對于這一主張,早在該原則被引入日本之初,西原春夫教授即提出,“在過失犯的場合,特別是由第三人或被害人的行為惹起結果的場合,可將信賴原則廣泛用于過失犯的認定。”1西原春夫 《交通事故と信頼の原則》 成文堂,1969年,14頁。在后來的研究中,學界通常認為信賴原則可用于劃定醫療過失、公害過失、企業災害、監督過失中注意義務的范圍。2參見蘇俊雄:《刑法總論Ⅱ》,1998年,第494頁;廖正豪:《過失犯論》,三民書局,1993年,第210~233頁;佐久間修 《刑法総論》 成文堂,2009年,152頁。但不盡人意的是,該原則雖曾備受關注,但在近四十年中有關信賴原則的研究卻無突破性進展。對適用規則的歸納也主要局限于交通事故領域。例如,通說認為,在行為人本人違反交通法規、容易預見對方會違反交通規則、不能期待對方(如年老者、幼兒、殘疾人、醉酒者等)遵守交通秩序、在道路有冰雪而事故可能高發的場合等,不得適用信賴原則否定過失。3參見岡野光雄 《刑法要説総論(第2版)》 成文堂,2009,197~198頁。而在現代社會頻發的醫療事故、公害事故、企業災害、監督過失等領域如何適用“信賴”,至今并無公認的規則。在相關研究中,日本的深町晉也教授將信賴原則用于化解危險接受困局的思路具有啟發意義。筆者將在下文引介這一思路,通過剖析其優勢與不足,嘗試構建信賴原則在不同領域的適用規則。
二、適用信賴原則的新嘗試:日本深町教授化解危險接受困局的觀點引介
(一)危險接受的歸責路徑之困
以信賴原則判斷危險接受案件中過失的成立與否,可謂深町教授頗具開創性的見地。所謂危險接受,旨在描述被告人基于被害人的意思對被害人實施了危險行為,卻違反了被害人的意思而導致法益侵害結果的場合。4參見山口厚 《刑法総論(第3版)》 有斐閣,2016,183頁。也即,被害人已認識到他人行為的危險性,對該行為對自身法益可能造成的侵害存在認知,但仍基于自身意志置身于危險之中,以至導致了危險的現實化。5參見恩田祐將,2010,“危険引受けにおける承諾型と非承諾型の區別” 《通信教育部論集》 13:67~86。此類案件的難點在于,在雙方事實上的過失導致了法益侵害結果的場合,如何對被告人的行為作出定性。對此,學界基本的立場是,危險接受中被害人接受的只是行為,而非結果,故危險接受的理論構造不同于被害人同意,從而無法將接受危險作為違法阻卻事由。至于究竟如何解決對行為人的定性問題,學界亦是歧見迭出。當前較為有力的主張是在雙方過失中確定一個具有支配性的過失,如果被告人的行為具有了支配性,那么其至少符合過失犯的構成要件該當性。對此,德國早已存在一個事實支配理論,以危險在事實上由誰支配來探討歸責——在被害人起支配作用的場合,德國的通說認為被告人在原則上不可罰;但在被告人起支配作用的場合,德國至今也未達成一致見解。6參見島田聰一郎:《被害人的危險接受》,王若思譯,《刑事法評論》2013年第1期。我國提倡該理論的學者為張明楷教授,其主張先基于一定的標準對案件進行分類,再基于分類適用不同的歸責路徑。劃定分類的標準為事實上哪一方支配了結果的發生:在被害人起支配作用的場合,屬于自我危險化的參與類;在被告人支配的場合,則歸入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類。1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中危險接受的法理》,《法學研究》2012年第5期。對于前者,張明楷教授認為,應以共犯從屬性理論為依據,若正犯的行為不符合構成要件,那么共犯的行為亦不可罰,例如:
海洛因案:甲、乙均為吸毒者,甲稱有海洛因,邀乙一同吸食,但提出由乙幫忙買注射器,乙同意。在二人使用乙購買的注射器各自注射后,甲因攝入毒品過量而死。2BGH Urteil vom 14.2.1984.
張明楷教授認為,甲明知吸毒危及生命仍選擇吸食,居于侵害自身法益的正犯地位。鑒于當前各國皆否認自損行為的構成要件該當性,故甲不成立正犯。既然不存在正犯,那么根據共犯從屬性原理,參與者乙則不成立共犯,從而乙也不可罰。
至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類,按照事實支配理論,此類別中被告人的行為起了支配作用,在客觀上該當了構成要件。在違法性階層未保護更為優越利益的場合,則不存在阻卻事由,從而成立過失犯。3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中危險接受的法理》,《法學研究》2012年第5期。例如:
冰面駕駛溺水案:丙、丁在河畔游玩時,丙見冰面較厚,認為可以承載其車,遂提出駕車穿過冰面到對岸的建議,丁同意。當丙駕車載丁駛至河岔中心時冰面破裂,汽車墜入水中。最終,丁溺亡,丙得以生還。4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6)一中刑終字第1871號。
根據事實支配理論,甲作為汽車駕駛人,其過失起到了支配了作用,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
不過,在筆者看來,事實支配理論存在三點問題:其一,“支配”具有過失相抵的意味。也即,承認被支配方存在過失,只不過作用力過小,被支配方的過失所左右了。在此值得思考的是,這種帶有過失共同正犯意味的“相抵”,在不承認過失共同正犯的我國刑法語境下,究竟有多大的適用空間。同時,“被支配”的過失畢竟在客觀上是存在的,是否應當減輕支配方的責任;如果減輕,又如何量定其作用力的大小,事實支配理論沒能解決這一問題。
其二,可能導致類別劃分的曖昧。關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張明楷教授另外提出,具有優越認知的一方居于支配地位。例如:
賽車同乘案:戊系賽車初學者,為得到行駛指導,邀請富有七年競技經驗的教練己坐在副駕駛座,并遵照其指示,使用了自己不熟悉的方法高速行駛。因減速不足,戊駕車撞上了防護欄,致使教練己死亡。
張明楷教授指出,相對于初學者戊,教練己具備駕駛賽車的優越認知,系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即便戊親自操縱賽車,但只處于間接正犯的位置。根據張明楷教授的論斷,本案應被劃入自我危險化的參與類。而學界在探討此案時,通常將其劃入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類中。在筆者看來,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正在于事實支配理論對“支配”的判斷略顯恣意:如果著眼點在于無論戊是否遵照了他人的指示,其終究是具備正常判斷能力的駕駛人,那么本案便可歸入自我危險化的參與類;如果以優越認知為標準,便應歸入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類。不可否認的是,現實生活中具備優越認知的群體多左右著事態發展的進程,但認為具備優越認知便應承擔更重的注意義務,不免有以“主觀說”判斷注意能力之嫌,恐面臨著“懲勤獎懶”的批判。
其三,并非所有危險接受的案件都能夠劃分清晰支配關系。在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事出偶然的場合,事實支配理論將面臨困境。如“蘑菇案”:野外遠足的情侶共同煮食野蘑菇食用,二人皆知曉其中可能混有劇毒的蘑菇,仍出于僥幸心理決定食用。在各自進食而一人死亡的場合,一般不存在過失犯的問題;在一方表達恩愛而給另一方喂食致其死亡的場合,是否應判定喂食的一方起到支配作用?如果是,對這種行為又有多大程度的處罰必要,值得思考。
關于危險接受案件困局的化解,日本學者提出了被允許的危險說、特別責任阻卻說等主張,但這些主張多圍繞體育競技展開,并不具有普適性。1主張“被允許的危險說”的學者為須之內克彥教授,參見須之內克彥“スポーツ事故における同意と危険の引受け”(日高義博等編 《刑事法學の現実と展開:斎藤誠二先生古稀記念》,2003,信山社),115頁;主張“特別責任阻卻說”的學者為神山敏雄教授,參見神山敏雄“危険の引き受けの法理とスポーツ事故”,(《宮澤浩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二巻》,2000,成文堂),25~26頁。另有日本學者主張社會相當性說、否定行為危險性說、自我答責性理論2主張“社會相當性說”的代表學者為奧村正雄教授與十河太郎教授,參見十河太郎,1999,“危険の引受けと過失犯の成否”《同志社法學》 50(3):341頁以下;奧村正雄,1999,“被害者による“危険の引き受け”と過失犯の成否” 《清和法學研究》 (6)1:105頁以下。主張“否定行為危險性說”的學者為山口厚教授,參見山口厚 “‘危険の引受け’論再考”(日高義博等編 《刑事法學の現実と展開:斉藤誠二先生古稀記念》2003,信山社),96頁以下。主張“自我答責性理論”的代表學者為鹽谷毅教授,參見塩谷毅 《被害者の承諾と自己答責》法律文化社,2004,369頁。等,針對學界對這些觀點的批判,筆者亦表示認同,在此不再贅述。對于危險接受的論題,德國有學者認為,在被害人自我選擇而進入危險境地的場合,被告屬于未創設法所不容許的風險,刑法無需介入保護。3轉引自陳璇:《刑法中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62頁。我國臺灣地區的許玉秀教授也持這一見解。4參見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449~450頁。既然被害人接受危險的場合非屬被告創設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那么在客觀歸責理論中便排除了歸責。這一思路也得到我國部分學者的認同。5參見王俊:《客觀歸責體系中允許風險的教義學重構》,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93頁;馬衛軍:《被害人自我答責與過失犯》,《法學家》2013年第4期。在筆者看來,客觀歸責理論能夠解決一部分危險接受的難題,但困局難言得到充分的化解。理由在于,究竟應如何理解“被容許風險”。如果從此概念產生之初的蘊意來看,應含有“社會有用性”之意。因為自卡爾·賓丁(Karl Binding)創制該概念后,卡爾·恩吉施(Karl Engisch)在1930年首先強調,其規范意旨著眼于對危險行為之“社會價值”(Sozialwert)的考量,需要考慮所追求目的之大小、發生范圍、成功的機率以及法益侵害的大小與蓋然性。6參見[德]Karl Engisch:《刑法における故意·過失の研究》,荘子邦雄、小橋安吉譯,一粒社,1989年,第350頁。換言之,被容許風險的合法依據來自將行為之有用性、必要性與法益侵害危險性進行衡量后的結論。7參見小林健太郎,2005,“許された危険”《立教法學》69:43~66。這一理解在日本得到了平野龍一、曾根威彥、前田雅英等學者得支持。8陳子平:《刑法總論》,元照出版公司,2017年,第224頁。我國臺灣地區的蘇俊雄教授亦認為:“所謂‘冒險利益’乃屬一種‘社會價值’的考量。”9參見蘇俊雄:《刑法總論Ⅱ》,1998年版,第481頁。那么,被容許的風險本身應具有積極的社會價值(畢竟沒有積極意義的“風險”并無被容許的理由),否則便與創制這一概念的初衷相悖。如此一來,將被容許風險用于危險接受中以否定過失的空間是非常狹小的,因為危險接受案多發生于一般生活場合,與具有社會進步意義的風險領域未必相關。此外,對被容許風險還存在另外一種理解,即,如果風險發生在社會倫理規范或社會相當性范圍之內即可以被容許。這一理解并不包含利益衡量的色彩,可以將對社會無害的行為囊括其中。例如,克勞斯·羅克辛(Claus Roxin)教授所歸納的創設不被容許的風險表現為:(1)違反具體規范;(2)違反交往規范;(3)無信賴原則可以適用;(4)未盡詢問義務與不作為義務;(5)于社會并無用途與價值等。1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716~734頁。依據這些規則,任由他人接受屬于自決權范圍內的風險的行為未違反(2)之交往規范,故屬于被容許的風險。不過細究羅克辛教授歸納的上述規則可以發現,其與新過失論中違反客觀注意義務的情形并無二致。如果客觀歸責理論中的制造法不容許的風險等同于新過失論中對注意義務的違反,那么此時面臨的便是對過失犯構造的選擇問題。考慮到構建在行為無價值論基礎上的新過失論更具有引導國民遵守一般準則的功能,筆者傾向采納新過失論探討過失犯的相關問題。
(二)以信賴原則化解危險接受困局的嘗試
關于信賴原則的體系地位,深町教授認為該原則所影響的是客觀結果預見可能性,且不必然局限于交通領域。關于如何影響預見可能性,深町教授借助了“經驗法則”這一概念,認為危險行為所關聯的結果之發生或不發生,是由多種次元的危險增加要素與危險減少要素所組成的。依據一定的經驗法則,如果危險減少要素增加了,那么正常的發展邏輯是侵害結果不出現。同時,出現的結果即屬罕見。既屬罕見,便能夠否定相當因果關系或客觀歸責。深町教授認為,在行為人信賴經驗法則且在具體情形中無法預見存在打破經驗法則之事由的場合,難言其對結果的發生存在高度的預見可能性。對于缺乏預見可能性的行為,自然無法作為過失定性,故過失犯的構成要件該當性不成立。
關于“經驗法則”的內涵,深町教授將之解釋為“被害人的自我保護”。然而,問題在于,從危險分配的法理出發,通常情況下明確規定被害人“必須自我保護”的法規范并非普遍存在。對此深町教授的回應是,法規范不存在無法論證出經驗法則不成立,“被害人的自我保護”這一經驗法則在某些條件下仍可以得到肯定。因為一個“自律”的法益主體皆有自我保護的本能,面臨對自身法益的侵害能夠采取回避的舉動。但深町教授亦認為,經驗法則并非無條件啟動,而首先有賴于法益主體的主觀認知,或者可以說,是從“危險認知——本能地保護自身利益”這一過程里推斷出來的。不過,對危險的認知僅是必要條件,即便被害人對危險有所認知,也存在經驗法則不成立的情形。例如:(1)被害人缺乏答責能力;(2)被害人當時無法回避危險;(3)相對于被害人,行為人居于更易回避危險的地位等。2參見深町晉也,2000, “危険引受け論について” 《本郷法政紀要》9:121~162。深町教授用上述思路分析了“賽車同乘案”,認為教練已諳知賽車的危險性,相對于戊具備優越認知,并通過對戊的駕駛指導,在一定程度上有遏制危險的機會。由此判定,戊信賴己能夠提供適切的指導。換言之,案中的己能夠通過適切的指導以控制危險減少要素,故存在“己可以回避侵害結果(可以自我保護)”的經驗法則。因此,戊對己的死亡不存在具體的預見可能性。同時,深町教授分析了“河豚案”。該案的基本案情為:明知河豚肝臟可能帶有劇毒的顧客仍于某料理店食用了河豚肝臟,提供河豚肝臟的被告系取得河豚料理資格的廚師,盡管如此,最終顧客還是中毒身亡。3最決昭和55年4月18日判例 《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34(3),149頁。在深町教授看來,面對已取得河豚料理資格的廚師,顧客可以對其抱有“能夠提供安全食物”的信賴;基于此,廚師便無法對顧客適用“自我保護”經驗法則,從而不能否定廚師過失的成立。
三、拿來的辯證:事實到規范的過渡
(一)深町教授觀點的啟示:剝離出刑法上的過失以回避“過失相抵”
危險接受困局的核心在于,在雙方事實上的過失均對結果產生作用力的場合,如何剝離出其中具有刑法意義的過失。顯然,在深町教授看來,適用信賴原則的場合一方對結果的發生沒有預見可能性,故沒有過失實行行為。也即,其中一個事實上的過失未被評價為刑法上的過失。這一觀點令危險接受案的處理思路清晰些許。而在事實支配理論下,需從雙方事實上的過失中找到起支配力的一方,那么“支配”的判斷過程多少帶有過失相抵的意味。畢竟過失相抵通常以“斟酌考慮受害者的過失從而限制加害者的損害賠償債務”這一形式去呈現。1[日]圓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權行為法》,趙莉譯,法律出版社,2008,第216頁。但事實支配理論無法充分說明,既然雙方過失均對結果產生作用力,被支配的過失是否減輕被告的責任;如果能夠減輕,幅度又是多少。我國既有的判決雖未言明采納了過失相抵,但事實上也帶有這一色彩,處罰結果無非也是“各打五十大板”,難言能夠劃分清雙方應承擔的責任。例如:
田玉富案:田某之妻康某因違法生育第三胎,被計生人員帶至計劃生育指導站實施結扎。田某為讓妻子逃走,用備好的尼龍繩系在康某胸前,將其從窗戶吊下。途中繩子斷裂,康某墜樓身亡。
法院認為:田某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嚴重的后果卻沒有預見,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2湖南省麻陽苗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05)麻刑初字第111號。同時實務觀點指出,案中二人均存在過失,但我國尚不承認過失共同犯罪,故無法將二者的行為進行整體評價,只能單獨評價被告人的行為。在被害人有明顯或重大過錯的場合,可以對被告人從輕處罰。3楊建華:《田玉富過失致人死亡案》,《人民法院案例選(分類重排本)4·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第1777頁。如此結論,顯然是民法處理與有過失的邏輯歸結。
所謂“與有過失”,亦為民法上侵權責任部分的概念,是指侵權人與被侵權人對同一損害的發生或擴大均存在過失原因力,乃雙方過失造成了同一損害結果的情形。4參見楊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與案例評注·侵權責任篇》,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76頁。與有過失的后果即過失相抵,在日本稱為“過失相殺”。我國民法典中亦有過失相抵的規定,例如第1173條規定:“被侵權人對同一損害的發生或者擴大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根據我國的民法學通說,過失相抵的理論基礎為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可以使損害在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得以合理分配。5參見程嘯:《過失相抵與無過錯責任》,《法律科學》2014年第1期。
雖然事實支配理論與實務的處理方式多少帶有過失相抵的意味,但細解深町教授的主張可以發現,適用信賴原則的場合并未給過失相抵留下空間。因為信賴所依據的“被害人的自我保護”這一經驗法則并非無條件地啟動。在符合信賴條件的場合,一方的過失在刑法上得以被否定。這一理解也符合最早將信賴原則引入日本的西原春夫教授的觀點。西原春夫教授認為,盡管信賴原則發揮作用的過程與過失相抵十分類似,但并未援用過失相抵理論。理由在于,過失相抵的法理以雙方皆有過失為前提,被害人的過失并非減輕或否定加害人的過失,只是減輕加害人應償付的金額罷了。而信賴原則的作用機理卻是,在被害人有過失的場合,加害人基于對被害人的信賴否定了自身過失。在不存在雙方過失的場合,始無“相抵”之余地。6參見西原春夫 《交通事故と信頼の原則》 成文堂,1969,24~25頁。
在筆者看來,西原春夫教授的上述闡述仍未觸及信賴原則與過失相抵間差異的本質。筆者認為,民事侵權可適用“相抵”,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民事侵權不排斥共同過失,這一點在日本與我國均有體現。例如,日本民法第719條(共同侵權行為)第1款規定:“因數人共同實施侵權行為加害于他人時,各加害人負擔連帶賠償責任,不知共同行為人中何人為加害人時,亦同。”此條文中的“共同”“加害”如果用置于刑法學領域,通常僅用于描述故意。但根據作為日本民法學通說與判例立場的客觀關聯共同說,只要兩個(及以上)侵權行為間存在客觀關聯即可成立共同侵權,并不以共同的主觀認識為必要。1參見于敏:《日本侵權行為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426頁。也即,在雙方均為過失的場合也可以成立共同侵權。從我國民法典第1173條(受害人過錯)與第1168條(共同侵權行為及責任)等侵權責任的一般規定來看,亦未明確否定過失共同侵權的成立。例如,第1168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未將共同侵權的主觀方面限定于故意。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則明確使用了“共同過失”之表述,其中第3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致人損害,或者雖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構成共同侵權。”從上述法律與司法解釋的表述來看,民法上共同侵權的成立未嚴格區分故意與過失。關于共同侵權的本質屬性,雖然我國學界一直存在共同過錯說、意思聯絡說、共同行為說、關聯共同說等主張,但我國的司法實踐與理論研究基本采納的卻是共同過錯說。2參見楊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與案例評注·侵權責任篇》,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38頁。亦即,“當一致行動的意思中含有侵害他人的目的指向時,便表現為共同故意;而當一致行動的意思中雖不含有這樣的目的指向,但行為人可以預見共同作出的行為會導致他人損害,并且可以避免這樣的損害發生時,便表現為共同過失。”3葉金強:《共同侵權的類型要素及法律效果》,《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關于接受共同過失的理由,民法學者指出,共同侵權行為及連帶責任的立法基礎之一在于“置民事權益受損害之人以更為優越的法律地位”,故“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1169條沒有表述共同侵權行為的本質特征無可非議,只要規定共同侵權行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即可。”4楊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與案例評注·侵權責任篇》,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40~41頁。換言之,民法乃調整平等私人關系的法律,侵權責任的最基本功能是填補損害,故主觀心理狀態究竟是故意,抑或是過失并無關緊要。民法上的故意與過失原則具有相同的價值。5參見葉名怡:《侵權法上故意與過失的區分及其意義》,《法律科學》2010年第4期;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9頁。
鑒于現有的規范環境與理論基礎,我國民法典關于過失相抵的規定,實則構建在承認侵權人與被侵權人成立共同過失的基礎之上,只不過侵權責任中過失的對象一定是本人之外的其他人,故被侵權人的過失并非侵權責任中“真正的過失”。“基于權利的對世性,只有權利人之外的人才負有不侵害絕對權的義務……權利人對自己無義務,也不會有過失。此處的過失,只是為進行對侵權人責任的限定而由法律擬制出來的‘不真正過失’。”6滿洪杰、陶盈、熊靜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釋義》,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頁。
然而,刑法的立場卻截然不同。無論是結果無價值一元論,還是結果無價值暨行為無價值二元論的主張者,皆認同刑罰的機能在于報應與預防,而非被害人補償。僅就報應而言,過失與故意反映出的主觀惡性不同,處罰理應有所區別。既然刑法上的過失與故意并不具有相同的價值,那么刑法對過失共同正犯的成立也頗為審慎。在西原春夫等主張共同意思主體說的學者看來,欠缺共同意思聯絡的場合無法成立共同正犯。1參見內海朋子 《過失共同正犯について》 成文堂,2013,56~70頁。從而才得出以接受共同過失為前提的過失相抵與信賴原則有著本質的不同。盡管日本最高裁判所在1953年開始承認過失共同正犯,但肯、否二說間的論戰從未停休。2參見內海朋子 《過失共同正犯について》 成文堂,2013,52~101頁。在我國,學界雖不乏肯定過失共同正犯的呼聲,但就當前的通說與實務立場而言,對過失共同正犯的成立依舊持否定態度。因此,更宜回避帶有過失相抵色彩的處理路徑。適用信賴原則,在事實上的過失中剝離出刑法上的過失,避免陷入過失共同正犯的爭議,是信賴原則化解危險接受困局的優勢所在,亦是符合我國理論與實務現狀的破題之路。
(二)深町教授觀點之不足:有賴“理性人”概念的“經驗法則”之困
以信賴原則化解危險接受困局有賴于經驗法則的運用。也即,依據一定的經驗法則,在行為人能夠信賴被害人可以自我保護的場合,認為行為人對其危險行為所導致的結果無預見可能性,從而否定構成要件該當性。此處的問題在于,賴以判斷信賴的經驗法則是否可靠。
所謂經驗法則,原系圍繞法官的內心認知所提出的概念,旨在描述人們在生活經驗中歸納得出的關于事物屬性或因果關聯的法則。這一概念其后多在大陸法系的訴訟法與證據法中用于推定事實或認定證言。3參見張衛平:《認識經驗法則》,《清華法學》2008年第6期。既然“經驗法則并不是具體的事實,而是作為判斷事物之前提的知識或法則。大凡人們在對事物進行合乎邏輯的判斷時都必須以經驗法則為前提。”4[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75頁。那么,拋開訴訟階段中法官對事實的認定,在案件的進行過程中,行為人依據經驗法則來判斷被害人的下一步舉止亦無不可。然而,經驗法則需以事物一般特征的正確性與有效性確認為基礎,在意大利學者米凱爾·塔如弗(Michele Taruヵo)看來,適用經驗法則時難以回避對“實質假前提”的擔憂:如果一些法則既非基于科學上確認,亦非出自實證驗證,而只是基于所謂的“經驗”,那么人們便不知、亦無法知曉該法則參照了何者之經驗及所得結論的認識基礎,無法把握形成該法則的經驗內容。如此一來,人們便不能掌握法則可能出現的錯誤概率,得出的結論可能既不具有邏輯性,也不具有認識和推論的基礎。對此塔如弗提出,經驗法則的運用需要更多的限制——在以自然科學或有效一般性常規為前提的場合,得到的判斷便具有結論性,亦即屬于被確證的事實;而在基于假的一般性常規或者原本不存在所謂一般性特征之表現的場合,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錯誤的。例如,一些經驗法則可能只是依據非確證的可能性概率所得出的,一般表現為“通常會……”,“很可能會……”等,“這樣一來實際上支撐經驗成為法則的基礎就只是所謂的‘經驗’了。”5參見[意]米凱爾·塔如弗:《關于經驗法則的思考》,孫維萍譯,《證據法學》2009年第17卷(2)。此時的結論將不可避免地帶有模糊性。深町教授提出的“被害人的自我保護”即偏屬后者。對此不妨以實際案例進行說明:
防凍液案:王某與盧某在井下作時,看到吊機車上放有一瓶綠色液體。王某問盧某能不能喝,盧某稱是防凍液,可以喝。王某不信,與盧某打賭稱,如果盧某將液體喝掉就把手表輸給他。盧某喝下后,中毒身亡。6山東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14)新刑初字第337號。
對于此案我國有學者認為,謹慎的公民不會喝下不明液體,故不能認為盧某可以自我保護。1參見莊勁:《團結義務視野下的被害人自陷風險》,《月旦刑事法評論》2017年第5期。依據深町教授的見解應當也能得出這一結論。然而,“謹慎”的標準在事實上并不明確。相比之下,學理上更常使用“理性”代之。細究深町教授所提出的、“自律”的被害人在認識到身處危險時會自我保護的這一經驗法則,實則來自康德提出的“理性——意志自由——自律”這一邏輯。2參見王嘯:《自由與自律: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但是,“理性人”概念與自然法如影隨形,且考量因素未排除習慣與道德,3參見張建肖:《法律上理性人芻論——源流、界定與價值視角的分析》,《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故法系間理解的不同導致了各國適用上的差異:英美將其用于刑事案件的認定;4英美刑法中首例適用并確立理性人標準的案件為R. v.Welsh(1869)案,R. v. Welsh,11 Cox C. C. 336(1869)。大陸法系的國家中卻主要用于民事上的表見代理、外觀主義、善意取得、權利失效等制度,以保護合理信賴等私法價值。我國部門法中尚無關于理性人的明文規定,學理探討也主要集中在民法學領域。例如,有學者認為,民法上“善意取得”中的所謂“善意”,系“相對方的信賴是否合理。所謂合理,是指可被一般公眾所接受,參照各國判例和司法實踐,普遍傾向于以理性人作為其判斷標準。”5張建肖:《法律上理性人芻論——源流、界定與價值視角的分析》,《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在我國有限的論及理性人的刑法學論作中,有學者主張將此概念用于過失犯預見能力的判斷標準,6參見谷永超:《英美刑法的理性人標準及其啟示》,《中國刑事法雜志》2017年第4期。但在筆者看來,該主張本質上仍未脫離現有的折衷說,且對理性人的文化根基與在我國刑法環境中的適應性并無論證。甚至該學者自己也承認,理性人存在“標準模糊”“不合理”等缺陷。總體而言,相當于民法,我國刑法學界對理性人的研究尚欠缺深入、系統的探討。
關于民、刑間對理性人關注差異的原因,筆者認為,根源仍在于民、刑機能的不同。民法意在處理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故多以主觀意思為準;而刑法的機能卻在于法益保護、秩序維持與自由保障。7參見佐久間修 《刑法総論》 成文堂,2009年,4~5頁。因此,刑法學者不得不直面的問題是,在法益保護與公民自決權相沖突的場合,究竟以何者優先來判斷“理性”。依據深町教授的見解,“自律”的公民應當自我保護;而在美國法哲學家喬爾·范伯格(Joel Feinberg)看來,完全正常的理性人為追求某些快感也甘愿自冒風險。8[美]喬爾·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三卷),方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47頁。這一觀點也得到了我國部分學者的認同。9參見王俊:《客觀歸責體系中允許風險的教義學重構》,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96頁。應當承認的是,理性是一種心理活動,行為人之理性未必是法律上的理性,個人選擇自己接受風險或許是理性的,但對社會而言,將其作為標準卻不合理。10參見張建肖:《法律上理性人芻論——源流、界定與價值視角的分析》,《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如果以具有理性人色彩的“自律”作為“被害人的自我保護”之經驗法則的前提,恐怕需要社會成員整體具備基本的、平均的理性。且不言這一狀態在地域發展不平衡的我國當前階段難以實現,細究深町教授所主張的信賴原則,事實上也并未建立在基本、平均的理性之上,相反卻帶有明顯的主觀色彩。例如在“賽車同乘案”中,深町教授認為,戊信賴教練己可以自我保護的原因是對方具備優越認知,而非來自教練這一規范身份;“河豚案”中廚師之所以不能信賴顧客可以自我保護,并非緣自廚師應提供安全食物這一規范要求,卻來自作為廚師不能信賴顧客采取自我保護。深町教授的論述中滲透著對規范要求的考量,但卻沒能論述透徹,似乎信賴與不信賴并無明顯的界限,最終只是一廂情愿罷了。
綜上所述,深町教授借助信賴原則剝離出危險接受案件中具有刑法意義的過失的思路雖然具有啟發意義,但以“理性”為基礎的經驗法則因過于主觀而不十分可靠。那么,在對深町教授之見解的揚棄過程中,如何劃定一個符合我國實情的、客觀上“應當信賴”的標準,并以此作為事實信賴的依據,或許才是我國學界從危險接受困局中實現突圍的可行性路徑。
四、一個符合我國實情的路徑構想:事實信賴需以規范信賴為依據
(一)我國當前階段應以規范信賴為依據
深町教授主張的“信賴”固然因過于主觀而不可取,事實上,在危險接受的案件之外,當前學界所歸納的信賴原則在其他領域的適用也存在主觀信賴與客觀信賴的交織。例如,在交通事故中,駕駛人信賴其他駕駛人會遵守交規屬于客觀的信賴,畢竟取得駕駛資格的人經過專業的訓練,社會有理由信賴其能夠遵守行駛規則;但步行人的場合卻另當別論。步行者能否遵守交規恐怕與其受教育程度和個人素養有關。如果有人愿意信賴其會遵守交規,那么這一信賴便具有主觀性。同理,在監督過失中,酒店老板能否信賴被雇傭的焊接工可以安全作業,進而在發生火災時借助該信賴否定監督過失,亦恐并非“愿意”便可構建。如果任由主觀信賴去否定過失,可能導致實務中的被告人動輒以信賴原則脫罪。
誠然,日本從德國判例繼受的適用規則呈現出了對主觀信賴的接納態度。在日本的交通領域,信賴原則的適用限制僅是,在行為人本人違反交通法規、容易預見對方會違反交通規則、不能期待對方(如年老者、幼兒、殘疾人、醉酒者等)遵守交通秩序、在道路有冰雪而事故可能高發的場合等不適用信賴原則。可見,日本學者將老人、幼兒、殘疾人、醉酒者以外的社會一般人擬制為具備同等社會認知水平的群體。但這一擬制無不依據。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日本的高中教育已充分普及,截至2018年,25~64歲人口中的半數接受了高中教育”,“80%的年輕群體完成了高中教育,日本是OECD(經合組織)中高中進學率最高的國家之一”。1《2019年版(カントリー·ノート:日本(PDF:1380KB※OECDのウェブサイトへリンク))》,https://www.mext.go.jp/b_menu/toukei/002/index01.htm。相比之下,我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僅占全人口數的11.8%,2《3-1 全國分學業完成情況、性別、受教育程度的6歲及以上人口》,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且各地區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從1.8%到32.29%不等。因人口基數大,即便在我國文盲率最低的地區也達到333098人,全國高達54190846人。3《1-9各地區分性別的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這些群體不僅集中于鄉村,同時也在向城市轉移。根據上述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鄉村離開戶籍地的省外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0%。4《1-4c各地區分性別的戶口登記地在外鄉鎮街道的人口狀況(鄉村)》,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這其中不乏對規則認知度偏低的群體。如果僅從機動車數的激增與道路設施的改良便認為我國已具備適用信賴原則的條件,那么在保證城市運轉效率的另一面,可能難以保障因受教育程度所限而對規則認同度偏低的群體的權益。
危險接受中對信賴原則的適用應服從信賴原則的一般規則。鑒于信賴原則以常識的普及與規則意識的整體提升為前提,考慮到國民的受教育狀況,筆者認為我國雖然可以借鑒這一原則,但應當設定更多的限制。總的原則是,主觀上的事實信賴,需以客觀、規范上的“可以信賴”為依據。這一限制的優勢在于:其一,規范上的“可以信賴”緣于被信賴方的“特殊態樣”,實則為社會成員對社會公認交往模式的認可,具備高度的可信賴性。“特殊態樣”需獲得國家公權力的肯定或許可,從而使特定社會成員的業務能力具備規范上的高度被信賴性。關于這一要求,誠如京特·雅科布斯(Günther Jakobs)所指出的:“對于已經設立的規范,個體不能夠提出任何抗辯,不能提出他缺乏遵守規范的興趣、不能提出他有更重要的事做、不能提出遵守規范給他帶來的損害。”1[德]京特·雅科布斯:《規范·人格體·社會——法哲學前思》,馮軍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81頁。例如,社會可以信賴取得執業資格的護士能夠合規操作,但不應對未取得資格的實習生抱此信賴;路人可以信賴機動車駕駛員會遵守交規,但駕駛員不應對路人“一定不會闖紅燈”抱有信賴,因此在通過交差點時仍需減速慢行。基于規范上“可以信賴”而信賴,避免了主觀的任意性,更具有刑法上的探討意義。其二,利于法定犯時代社會規范意識的內化。風險社會的深化推進了法定犯時代的到來,風險愈高的領域,法定犯的規定愈密集。風險領域的作業員作為掌控風險的主體,故不得在規范允許的范圍之外信賴他人可以回避風險。如此可以避免不合理的風險分擔,有利于敦促風險領域的謹慎作業。
(二)對信賴原則適用規則的類型化構想
由于過失犯存在多種態樣,故信賴原則的適用也應根據類型區別對待。在本文看來,信賴原則主要被用于三類案件:危險接受類,公害、醫療、火災等事故相關的監督過失類,交通事故類。
其一,危險接受類。此類案件的特點在于存在雙方事實上的過失,故可能存在針對彼此的信賴。根據前述深町教授思路的啟示,應借助信賴原則剝離出其中具有刑法意義的信賴,進而確定刑法上的過失。具體而言,可以將該類型再細化為兩類:(1)一方具備特殊態樣的類型。其中,具備特殊態樣的一方并無信賴對方可以自我保護的規范依據,故其事實信賴不能否定對結果的預見可能性,從而無法否定刑法上的過失。與此相對,不具備特殊態樣的一方在規范上有理由信賴對方可以保護自己(被害方)的法益,即便(無特殊態樣的一方)接受了危險,但刑法仍認為其對危險的現實化無預見可能性,因此不成立刑法上的過失。以“河豚案”為例,顧客有理由信賴取得執業資格的廚師會提供安全的食物,因此可以降低謹慎選擇食用。即便發生死亡結果,也可以判定顧客的這一事實信賴存在規范依據,故對死亡結果不具有預見可能性。相反,廚師因特殊態樣而負有更多的注意義務,規范不允許其信賴顧客去自己我保護,由此不能否定廚師對死亡結果的預見可能性。簡言之,案中只有廚師的過失被評價為刑法意義上的過失。在“賽車案”中,學員基于教練之特殊身份,有規范上的理由去信賴教練的指點是安全的,從而對事故的發生沒有預見可能性。與此相對,教練并無規范上的理由信賴學員可以安全駕駛,故只有教練的過失具有刑法上的評價意義。在導致教練死亡的場合,只能認定學員無罪,應由教練自我答責。(2)雙方皆不具備特殊態樣的類型。此類案件中,因雙方皆不負有保護對方的注意義務,在基于合意接受了危險進而導致危險現實化的場合,因無法剝離出刑法上的過失,故只能由雙方自我答責。例如,“冰面駕駛案”并非發生在交通領域,駕駛人這一特殊態樣在此案中并無規范上的被信賴性,加之駕車駛過冰面系二者合意為之,故無法剝離出其中具有刑法意義的過失。據此筆者認為,本案應定性為民事案件,依據民法典相關規則處理。
其二,在監督過失的場合,1此處的監督過失僅指對人監督,也即狹義的監督過失,一般表現為上級人員對下屬的監督,不包括廣義的監督過失中的管理過失。考慮到社會運行體制中監督義務的規范色彩,亦應區分為兩種類型,以適用不同的處理規則:(1)對于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間存在規范分工的類型,可適用信賴原則否定監督者的預見可能性。例如,甲對乙的作業負有監督職責,但甲之所以雇傭乙,是因為乙取得了甲所不具備的專業資格。此種場合,應允許甲信賴乙可以安全作業。但應強調的是,這一場合存在例外。即,在監督者明知法益侵害結果幾近確定發生的場合不適用。因為,規范僅是社會一般經驗的總結,未必能真實反映一切因果流程。在法益侵害幾近確定發生的場合,基于對效益的考量,可能被侵害的法益應優位于原本貫徹體制運作的集體利益。2參見周漾沂:《反思信賴原則的理論基礎》,《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法學與風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第59頁。( 2)在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間僅存在監督關系,卻不存在規范分工的場合,不能適用信賴原則否定監督者的結果預見可能性。例如,甲明知乙未獲得乙炔切割的專業技術資格,仍雇傭其進行切割作業。即便甲深知乙具備多年的焊接經驗,信賴乙能夠回避風險,這一信賴也只是不具備規范依據的主觀信賴。由于缺少規范依據,該信賴不能否定甲對結果的客觀預見可能性。對于乙造成的法益侵害,甲至少符合監督過失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其三,在交通事故的場合,仍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1)事故雙方系機動車駕駛人與機動車駕駛人以外的人員之類型。此種場合,應以不適用信賴原則為原則,適用信賴原則為例外。理由在于,基于我國人口普查所顯失的地域受教育年限數據及大量鄉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現狀,應避免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群體分擔過多的城市風險——故暫時不宜認為社會成員皆具備同一程度的規則意識。機動車駕駛人原則上不得以“信賴對方會遵守交規”為由主張對事故結果不存在客觀預見可能性。但是,在與教育水平無關的場合可以例外地適用信賴原則。對此筆者贊同在我國城市快車道、國道、高速公路等領域適用信賴原則的主張。3參見談在祥:《刑法上信賴原則的中國處遇及其適用展開》,《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4期。例如,在設有明顯隔離欄的城市路段或封閉的高速公路所發生的事故,機動車駕駛人可以以“信賴無人會翻越隔離欄”而主張對事故不存在客觀預見可能性。因為設有隔離欄的地段即以物理的方式明示告知“不得跨越”“不得進入”,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群體也可以領會。(2)對于事故雙方均為機動車駕駛人的類型,原則上可以適用信賴原則。畢竟取得駕駛資格需要經過專門的訓練,可以擬制雙方駕駛人均對交通規則存在認知,故被告方可以借助信賴原則否定預見可能性。但是,這一類型也存在例外。即當被告人明知對方無證駕駛的場合,不得肯定其信賴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