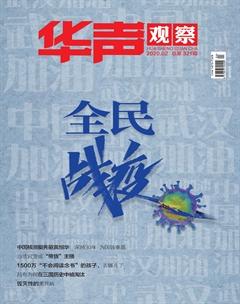72歲高位截癱患者用意念喝可樂
吳雅蘭 柯溢能
張先生今年72歲,兩年前因為車禍造成第四頸髓層面損傷,四肢完全癱瘓。經過系統訓練,現在他不僅可以握手,還能拿飲料、吃油條、玩麻將,只不過這些動作不是用他自己的手來做的,而是他用“意念”控制外部機械臂及機械手來完成。
“太不容易了!對四肢完全癱瘓的人來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今天,通過腦機接口,他做到了!” 浙大二院神經外科主任張建民激動地說。
日前,浙大二院張建民教授團隊與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鄭筱祥教授、王躍明教授團隊在“植入式腦機接口臨床轉化應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該團隊在國內首次通過對一位高位截癱志愿者腦內植入Utah陣列電極,從而用意念控制機械手臂的三維運動完成進食、飲水和握手等一系列上肢重要功能運動。該研究的成功標志著我國腦機接口技術在臨床轉化應用研究中已躋身國際先進行列。
高位截肢患者“動”了起來
2019年8月,研究方案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并征得張先生和家屬的知情同意及簽字后正式啟動。8月底,在精準定位下順利完成了國內首例開顱,將Utah陣列電極植入到控制右側上肢運動的運動神經皮層的手術 。由此,張先生開始了用意念與機械臂“對話”的生活。
每天,張先生結束午休后,就會開始一天的訓練。從開始的電腦屏幕上操控鼠標運動到后期控制機械臂三維運動。花樣不斷翻新,難度不斷增加,效果不斷提高。
在近期的訓練中,工作人員把一個盛著油條的杯子,放在機械手的旁邊,張先生用“意念”讓機械手對準位置,張開手指,握住杯子,一步一步往嘴邊挪。挪的過程不算順暢,有時往左偏一點,有時往右偏一點,張先生得“使勁”想著“往右”或“往左”,調整機械臂的方向。經過近半分鐘的努力,機械手終于把杯子挪到嘴邊,張先生吃到了油條。
抓、握、移,這些對常人來說再簡單不過的動作,背后卻是信號發送、傳輸和解碼等一系列復雜的過程。因此,這種“轉念”對像張先生這樣脊髓神經損傷、運動功能喪失的殘障人士而言,如果沒有“腦機接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手術機器人植入、個性化算法

在國際上已被報道的植入式腦機接口患者,均為中青年人。他們在體力、注意力、情緒配合等方面,也相對更穩健,而老年人則相對較弱。面對72歲高齡的張先生,國際上尚無先例可循,團隊所要探索的顯然更多,測試難度也更大。
如何在盡量減少損傷的情況下,將微電極準確無誤地植入患者大腦所在功能區,是此次研究的第一道關卡。
張建民說,大腦運動皮層神經元共分為6層,實驗需要將電極植入到第5層的位置。這個過程中,電極植入不能有毫厘之差。植入位置太淺或太深,都達不到效果,還會損傷其他神經,“這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手術,難度非常大”。
傳統人工植入手術,精確程度沒法達到最佳狀態。張建民團隊利用步進為0.1毫米的手術機器人,準確地將兩個微電極陣列送入既定位置,誤差僅在0.5毫米以內。這也是全球首例成功利用手術機器人輔助方式完成的電極植入手術。
接下來的關鍵一步,就是如何實現“意念操控”。
“在4毫米×4毫米大小的微電極陣列上有100個電極針腳,每一個針腳都可能檢測到1個甚至多個神經元細胞放電。電極的另一頭連接著計算機,可以實時記錄大腦發出的神經信號。”浙江大學王躍明教授說。
如何把收集的神經信號,準確地轉化成機械臂的動作指令,既依賴于機器算法的設計,也會受到試驗者個體腦電信號特征的影響。
目前,全球尚無統一標準化的信號采集、解碼等分析手段。一開始,團隊采用國外的幾套線性算法,但效果都不太好。后來,團隊引入非線性、神經網絡算法,設計了一套針對這位高齡患者的個性化解決方案。
“我們設計的非線性解碼器,更能‘讀懂老年人的心思,幫助患者更好地學習操控機械臂、機械手。”張建民說。
團隊采用循序漸進的訓練方法,先讓張先生在電腦屏幕上操控鼠標來跟蹤、點擊二維運動及三維虛擬現實運動中的球,再練習指揮機械臂完成上下左右等9個方向的動作,最后才是模擬握手、飲水、進食等動作。訓練耗費4個多月,才有了現在這樣令人激動的成果。
腦機接口的臨床應用希望無限
盡管此類植入在國際上都處于試驗階段,效果也是非永久性的,但對張先生而言,腦機接口已改變他的生活,更讓這類人群看到了提高生活質量的希望。
而今,張先生通過腦機接口,餓了就能吃,渴了就能喝,能夠自己“做”一些事情了。工作人員得知張先生喜歡打麻將,還特地設計一套程序,讓他能通過控制鼠標,玩電腦麻將游戲。“剛進病房的時候,張先生心情很低落。我們跟他說話,他都不怎么吭聲。現在,他開心多了。”護士長說。
“任何基礎醫學研究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應用到臨床,為病人解決實際問題,這就是所謂的‘轉化醫學”,張建民說。腦卒中后偏癱、頸髓損傷后的高位截癱、肌萎縮側索硬化及閉鎖綜合征等運動功能嚴重障礙患者,有望應用腦機接口技術,并借助外部設備,重建肢體運動、語言等功能。
隨著腦科學的不斷發展,這一領域的臨床應用,將從現有的以運動功能為主的功能重建,逐漸推廣到語言、感覺、認知等更多更復雜的功能重建上。
摘編自微信公眾號“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