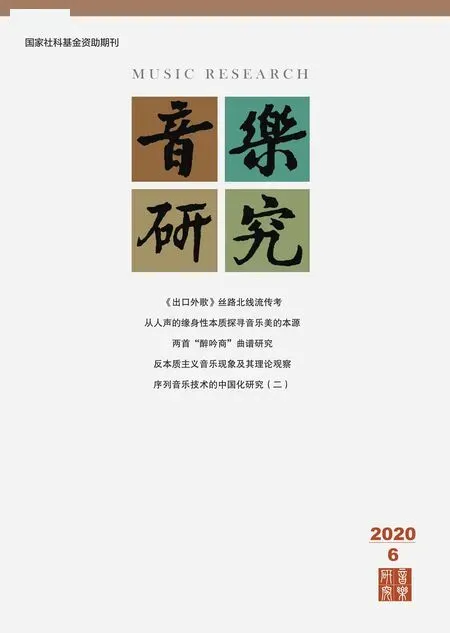論姑娘腔、柳子腔名實及聲腔歸屬
文◎馬 莉
清代小說《林蘭香》第二十七回的批語中寫道:“昆山、弋腔之外,有所謂梆子腔、柳子腔、羅羅腔等派別。”①轉引自廖奔《中國戲曲聲腔源流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1 頁。柳子腔,即清代戲曲四大聲腔“南昆、北弋、東柳、西梆”中之“東柳”,是清代戲曲史上影響很大的聲腔。今山東柳子戲聲腔也因包含齊言柳子腔(簡稱“柳子”)而得名。然而,柳子戲唱腔的主體并非柳子腔,而是以【黃鶯兒】、【山坡羊】、【鎖南枝】、【娃娃】(又稱 【耍孩兒】)、【駐云飛】等“五大套曲”為常用曲牌,因此,柳子戲又歸屬于弦索腔系聲腔,河南的大弦戲與其同源。與“東柳”一樣馳名清代劇壇的還有姑娘腔,又名山東姑娘腔、唱姑娘等。清代李聲振《百戲竹枝詞》有載:“齊劇也,亦名姑娘腔。以嗩吶節之,曲終必繞場宛轉,以足其致。”②參見楊米人等《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58 頁。可見,清時的“齊劇”,即是“山東姑娘腔”,當時應該已經傳播至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許多地區。
關于“柳子腔”和“姑娘腔”的名稱來源,學界存在多種說法。因這兩種名稱由來,對認識清代以山東、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劇壇的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學界對“柳子腔”和“姑娘腔”的名實辨析一直沒有停止。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通過爬梳文獻,以及跨區域、跨劇種的比較,結合田野調查資料和聲腔辨識,發現二者在名稱上有著清晰的歷時性關聯;并且,在進一步厘清相關聲腔劇種關系的基礎上,對相關聲腔的歸屬問題提出自己的處理意見。
一、姑娘腔與巫娘腔
一些學者認為,“姑娘腔”一名最早出現在明萬歷年間抄本《缽中蓮》傳奇中,但另一些學者將《缽中蓮》與清初傳奇《長生殿》《長生緣》及清代演出劇本選集《綴白裘》比較后認為,《缽中蓮》是清初甚至是清代中期的梨園整理本。③參見胡忌《從“缽中蓮”看“花雅同本”的演出》,《戲劇藝術》2004 年第1 期;黃振林《論“花雅同本”現象的復雜形態》,《戲劇》2012 年第1 期;陳志勇《〈缽中蓮〉寫作時間考辨》,《戲劇藝術》2012 年第12 期。在清代劇壇或戲曲作品中,【姑娘腔】作為曲牌出現于昆曲《麒麟閣》“反牢”一出和《虹霓關》等劇目中。此外,乾隆年間劇本《梁上眼》中亦有“你兒子在山東每日聽得都是些‘姑娘戲’”這樣的道白,這里的“姑娘戲”,顯然指唱“姑娘腔”的戲。可見,“姑娘腔”一名最早可能出現于清代。
清初劉廷璣在《在園雜志》中討論當時的戲曲聲腔時提道:“近今且變弋陽腔為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為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那腔、羅羅腔矣。”周貽白在其《中國戲劇小史》中認為:“姑娘腔當即巫娘之音訛”④周貽白《中國戲劇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 頁。,“姑”是“巫”的音變。之后,周氏在所著《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中進一步指出:“巫娘腔似即姑娘腔……或謂今之柳琴戲,亦名周姑子,即為此一唱調之遺音。”⑤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377 頁。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在討論河南調“女兒腔”時指出:“女兒腔,群眾也把它叫作姑娘腔、巫娘腔,因為它的唱腔是從姑娘(妓女)們所唱的弦索調演變來的。所謂女兒是姑娘的同義語,‘巫娘’即是‘姑娘’的音轉。”⑥張庚、郭漢城主編《中國戲曲通史》(下),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 年版,第31 頁。可見,《中國戲曲通史》是將河南調“女兒腔”與山東“姑娘腔”當作同類來看待的,并將“巫”看作“姑”的音變。較為奇怪的是,1992 年修訂版《中國戲曲通史》則刪除了這段論述。徐扶明對于將巫娘腔、姑娘腔與女兒腔三者視作一個東西,且都歸屬為“弦索調”的看法,提出了質疑 ,認為“只靠‘同義語’‘音轉’之類的方法”來認知聲腔是不可靠的。⑦參見徐扶明《元明清戲曲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359 頁。
徐氏所言不無道理,聲腔史研究也確實存在因名稱相近,誤將兩個甚至幾個不相干的劇種,視為相同劇種或者相關聯劇種的情況,如清代文人筆記中就已出現將明代弦索調與清代《太古傳宗》中“弦索調時劇”及清代亂彈之弦索腔簡單視作一物的現象。筆者以為,不妨把這些由民間得來的稱謂當作口述史材料,并將相關聲腔放入其歷時的生存語境中,結合其他活態材料,來綜合分析音義轉換背后的聲腔演變軌跡。
關于姑娘腔與巫娘腔的聯系,紀根垠用文獻與大量民俗學資料互證的方法,在《談【山東姑娘腔】》一文中指出姑娘腔與民間“還愿驅邪的巫覡”有一定的關系。⑧紀氏認為,“民間帶宗教色彩、為村民還愿驅邪的巫覡,也唱【姑娘腔】,敲狗皮鼓,演《魏九郎過關》故事,也演《休丁香》《長生樂》等節目。”參見紀根垠《談【山東姑娘腔】》,《戲曲研究》(第42 輯)1992 年9 月。該文首先討論了清代傳奇《缽中蓮》中【山東姑娘腔】,與《綴白裘》第七集《忘記閣》中“反牢”一出【姑娘腔】,昆曲《虹霓關》第九出“罵城”中程咬金所唱【姑娘腔】⑨分別見蘇州仁堂刊印版和《國劇畫報》第一卷第6 期。,以及山東民歌詞義的關聯;其次揭示了【姑娘腔】與山東民間歌曲的聯系;⑩據孔培培的研究,乾隆年間問世的《梁上眼》劇本第八出“義圓”中【姑娘腔】的結構也是七字上下句。參見孔培培《“姑娘腔”考辨》,《戲曲研究》(第72 輯) 2007 年1 月。再次通過比較山東柳琴戲老藝人趙崇喜、莒南縣老藝人張從龍、臨沂地區柳琴戲老藝人馮士選的口述資料,與蒲松齡《聊齋志異》第六卷對“濟俗”(即山東民俗)、“跳神”、海州童子戲、安徽端公戲、洪山戲及薩滿神歌等儀式環節的記載,再結合對【姑娘腔·迎神調】上下句詞格、“似歌又似祝”唱法等類同性和相通性的分析,支持了《中國戲曲通史》所持“‘巫娘’即是‘姑娘’的音轉”一說。
從種種跡象來看,筆者以為,“姑娘腔”是因為這些儀式中需要扮演神婆或稱女神而得名,山東稱“巫娘”“裝姑娘”“姑娘戲”,遼寧民香稱“唱姑娘”,河南稱“女兒腔”。所謂“巫娘”,是指扮演者的神職身份,而“姑娘”,則是附體于“巫娘”的“仙姑”[11]據調查,肘鼓子老藝人稱表演時在主人家所懸掛的“軸子”所繪為“北山二仙姑,或南山三仙姑”。,因此,“姑娘”和“巫娘”是一種事物的兩種叫法,二者并不存在音轉或音訛的問題,如此,所謂巫娘腔、姑娘腔實際上也是一回事。
總之,隨著研究的深入,對于清代以來,以山東為中心的戲曲聲腔“姑娘腔”的民間宗教起源,學界已形成基本共識。
二、肘鼓子與柳枝(柳子)
與姑娘腔相關的是民間宗教儀式“周姑子”,也稱“肘鼓子”。紀根垠根據已故柳琴戲表演藝術家相瑞先的回憶,認為從早期演出“焚香擺供”“奏樂請神”“敲狗皮鼓伴唱”等環節看,“早年不少柳琴戲的男演員也兼演肘鼓子、兼唱【姑娘腔】 。”[12]紀根垠《談【山東姑娘腔】》,《戲曲研究》(第42 輯)1992 年9 月,第37 頁。這說明,民間肘鼓子與姑娘腔甚至成熟的戲曲形式拉魂腔有伴生關系。周貽白認為,“肘鼓子”系“肘懸小鼓按節奏而得名,或叫秧歌腔,則明示其來源”。又謂“周姑子流派頗多,如山東的柳腔、茂腔、五音戲、燈腔,在昔名周姑子,亦作肘鼓子。”[13]同注⑤,第509、377 頁。
肘鼓子在山東又稱單鼓,類似的鼓,在河北和山西稱“扇鼓”。20 世紀末以來,學界逐漸認識到,肘鼓子作為民間宗教儀式,與同源的東北單鼓、太平鼓、兗州砰砰鼓、陜西羊皮鼓、甘肅檳鼓甩辮子、安徽端鼓或喜鼓子、海州童子戲、洪山戲中單面鼓一樣,多用于跳神、祭祀。[14]曲六乙發現,“這種扇鼓曾流行于東北、中原地區,為滿族、漢族通用的打擊樂器。”參見曲六乙《儺戲·少數民族戲劇及其他》,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版,第71 頁。
有學者調查發現,遼寧地區的民間“燒香師傅”,將民香中與肘子鼓有密切聯系的唱腔,稱作“唱姑娘”或“唱單姑”。筆者認為,“唱單姑”實際上是指“唱單鼓”,即肘鼓子,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山東肘鼓子對遼寧民香的影響。
有史料表明,清代山東地區巫風盛行,為肘鼓子的盛行提供了深厚的社會文化土壤。據《聊齋志異》第六卷“跳神”載: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日“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婦女,時自為之。堂中肉于案,酒于盆,設幾上。燒巨燭,明于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撾如雷。蓬蓬聒人耳。
如前文已述,除山東之外,江蘇、安徽、遼寧等地乃至北方蒙古族、滿族的宗教儀式中,也有與肘鼓子相似的文化表征,它們具有相同的文化內涵,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其一,鼓的形制與“九”相關的符號學聯系。前述《聊齋志異》所記的“老巫擊鐵環單面鼓”,據柳琴戲老藝人趙崇喜介紹,這種單面鼓“把柄末端彎或圓圈,套綴九個鐵環”[15]同注[12],第33 頁。。這種形制不禁令人聯想到科爾沁蒙古族薩滿中稱作塔拉哼格日各(漢譯作“單面鼓”,俗稱“神鼓”)的鐵柄單面鼓。如圖1 所示,三個大環每環各套三個小環,共有九個小環。與之相應的是,科爾沁蒙古博“過關”儀式常常選在農歷九月初九,使用的腰鏡是九塊,其過“九道關”所需的器具、祭品中,“凡器必九:鍘刀九、犁鏵九、烙鐵九、羊九、牛九……并要有九個以上博師傅參加。”[16]劉桂騰《搭巴達雅拉——科爾沁蒙古族薩滿“過關”儀式音樂考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 年第1 期,第54 頁。可以說,整個儀式都貫穿著對圣數“九”的崇拜。

圖1 科爾沁蒙古族薩滿使用的塔拉哼格日各[17]圖片摘自劉桂騰《科爾沁蒙古族薩滿祭祀儀式音樂考》,《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4 年第1 期,第53 頁。
其二,魏九郎傳說及其同主題戲曲劇目(又是一個以“九”為圣數的意象)。據紀根垠的研究,肘鼓子儀式,要在供桌后面懸掛包括“三代宗親、城隍出巡及魏九郎過關圖像”。演戲表現的多是《魏九郎過關》等神話題材的劇目。對于魏九郎的來歷,紀氏認為,或傳九郎系魏征之第九子,死后封為“請客神”。兗卅砰砰鼓有《九郎上馬》,海州童子戲有《九郎借馬》,安徽端公戲有《魏九郎背表》,洪山戲有《魏九郎救父》,東北太平鼓也有九郎神故事。[18]參見注[12],第34 頁。這些戲曲表現的都是在唐太宗游冥府背景下,魏征第九子魏九郎打表請神系列神話題材。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圣數九的崇拜,應當是借鑒中原道教文化的結果。
其三,儀式中有共同的“請神、安神、送神”環節。肘鼓子演《魏九郎過關》時要唱【點神調】【迎神調】【安神調】【送神調】,說明儀式要經歷請神、安神、送神環節。無獨有偶,海州童子戲諸環節中,必有請王、安坐、送圣等儀式。兗州砰砰鼓中鋪壇和取水之后的演出,其內容也包括請神、安神和送神。同樣,科爾沁蒙古族薩滿搭巴達雅拉(“過關”)儀式也包括獻牲、請神、送神等環節。這些在“請神、安神、送神”環節中所唱的【點神調】【迎神調】【安神調】【送神調】,形成了【姑娘腔】的曲調庫,這使肘鼓子與【姑娘腔】表現出了互為表里的關系。當然,各種儀式都會按各地實際情況有所損益,如海州童子戲,除請王、安坐和送圣之外,還有開壇、獻豬、踩門、吹刀、出關、升文和發表等其他環節;科爾沁蒙古族薩滿“過關”儀式在請神與送神之間,穿插有“扎都(走鋼刀)與霍書(踩犁鏵)”“點書嘎(咬烙鐵)”“嘎拉都日瑪(攏火)”等環節,這些帶有深厚早期原始薩滿意味的環節,體現了各個儀式在同質基礎上的豐富多樣性。
其四,共同的功能訴求。這要從中國傳統的巫文化功能來解釋。《漢語大詞典》將“巫”解釋為:“古代從事祈禱、卜筮、星占,并兼用藥物為人求福、祛災、治病。”在具體儀式中,肘鼓子的功能與“巫”的功能是相同的,如柳琴戲老藝人便常從事這種“開鎖子、念神歌、驅魔鎮邪”的活動。海州香火會同樣有基于“逐疫癘,御旱潦”的功能。[19]宣鼎《夜雨秋燈錄》卷6“巫仙”條。肘鼓子正是因為依附于“巫”的祛災、治病功能,才得以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傳續。
進一步探究,“祛災、治病”最首要者是保護子孫繁衍(由孕育到成長),這應該是中國傳統社會歷久未變的、有終極意義的訴求。如蘇北香火執事者“香火童子”“香童”“童子”的稱謂,以及海州香火會、南通香火戲等稱謂,均暗示了儀式最初或者核心功能的護生保童性質。從這一視角切入,可以揭示“柳子”一名的來歷,或者說獲得對“柳子”一名功能意義的解釋。
對于柳子一名的來歷,學界目前也沒有統一的認識。周貽白比照湖南北部一帶對花鼓戲的稱謂后提出:“山東的柳子戲把一種近似梆子的聲調叫作柳子調而來代替一般民歌小調。”[20]同注⑤,第504 頁。湖南北部石門、慈利一帶,將該地流行的花鼓戲稱為柳子戲(又名楊花柳、大筒戲),該地所謂“柳子”,就是指在當地流行的(諸如《四季》《五更》《十二月》之類的)民歌小調。湖南與本文涉及的以山東為中心的內蒙古、遼寧、河北、河南、安徽和江蘇等地的文化不接近,人文地理相距更遠,將湖南柳子戲與本文柳子戲類比,從形態上看難以令人信服。但如果從護生保童的角度來看,二者似乎有聯系,因為全國各地花鼓戲的生存環境,都與生殖崇拜有一定的關聯。
山東柳琴戲(目前歸屬于肘鼓子腔系)與山東花鼓戲音樂,在拉腔、襯詞和音調上有密切聯系,二者表現出共同文化內圈的關系。關于柳子(柳枝)與肘鼓子的聯系,可以借助跨民族文化比較的方法,從儀式功能角度獲得一些認知。滿族薩滿文化的“佛多”信仰值得關注。在滿語中,“佛立”意為神龕,“佛多”乃柳枝(柳子)。清代滿族皇室在坤寧宮所祭祀的是佛立佛多鄂漠錫媽媽(Fere fodo omosi mama),其中omosi 是滿語,為“眾孫”之義,“鄂漠錫媽媽”則是指子孫奶奶,“佛立佛多鄂漠錫媽媽”就是滿族共同信仰的生育神和兒童保護神,民間習慣稱這位女神為“佛多媽媽”(fodo mama)或“佛他媽媽”(fuda mama)。fodo 意為柳枝,fuda 意為繩子,鄂漠錫媽媽就是滿族民間為保嬰、育嬰而祭祀的女神。[21]參見孟慧英《佛立佛多鄂漠錫媽媽探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2 期。這就找到了肘鼓子與柳子(柳枝)的文化聯系:一個作為儀式的法器,一個為祭祀的對象代碼,二者同樣承擔著保佑子孫繁衍的功能和目的。可見,柳子被賦予了“神”的意義,所以山東柳子腔藝人將《馬二頭送崇》中的柳子腔稱為【神柳】。
至于柳子到底是源于漢族文化還是源于滿族文化,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柳子、柳子腔與肘鼓子的聯系,是在清朝統治下,漢族文化與滿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同時,這也解釋了蒙古族薩滿與肘鼓子等在儀式功能上的聯系,其內在原因是滿族薩滿與蒙古族薩滿有太多的文化關聯。
三、【姑娘腔】【柳子腔】的調與“腔”
由上文論述可知,清代【姑娘腔】的音調,就是亂彈諸腔中普遍存在的【柳子】(或稱【柳子腔】【柳枝腔】)的源頭。從清代傳奇《缽中蓮》、場上演出底本《綴白裘》、昆曲《虹霓關》,到乾隆年間問世的《梁上眼》可以看出,【姑娘腔】的詞格多表現為齊言上下句結構,由此可以想見,其唱腔音調同樣應該為上下句結構。這一曲體結構特征,正是今山東柳子戲、河南大弦戲、山東聊城八角鼓、膠州八角鼓、濟寧八角鼓、萊陽彈詞、京劇(雜腔小調)、北京曲劇、北京八角鼓、遼寧海城喇叭戲、二人轉、黑龍江拉場戲、江蘇揚州清曲、上海京劇(雜腔小調)、浙江杭州灘簧、福建閩劇羅羅腔、北路戲雜調、河南羅戲等劇種、曲種中,被分別稱為【柳子】【柳子腔】【柳枝腔】【贊子】【序子】【羅羅調】【小上墳】【小上墳調】【鶯歌柳】【小柳子調】【武贊子】等曲牌音調的共同特點。據相關研究,以上30 多個【柳子】類腔調,都是在兩個基礎音調上發展起來的:一是上句do 結尾,下句re 結尾,如山東柳子戲《打登州·黃桑店》中的【柳 子】[22]譜例詳見《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中國ISBN 中心1996 年版,第1125 頁。等;另一個是上句mi 結尾,下句sol結尾,如山東柳子戲《火焰山》中的【鶯歌 柳】[23]譜例詳見注[22],第1123—1124 頁。。這與【姑娘腔】的詞格是吻合的。
清代【姑娘腔】的另一個特點是“浪腔”。如昆曲《麒麟閣》“反牢”一出中所用的四次【姑娘腔】,在唱詞的下句或整個唱詞的最后多次出現“浪腔介”或“浪調介”字樣;又如,《綴白裘》第六集《亂彈腔·陰送》中出現“急板浪”“急板浪,地方鬼渾介”字樣,同集《搬場拐妻》出現“貼唱場上先浪調”字樣。對于這些不同名稱,但指義較明確的表演形式,徐扶明認為:“大概是耍腔或者過門,再配合一些表演動作。”[24]同注⑦。徐氏所言極具啟發意義。筆者以為,所謂“浪腔介”,應該是為了渲染戲曲表演氣氛,由演員個人拉腔,或由嗩吶類樂器代替人聲拉腔,或為眾人合腔。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記載和與肘鼓子腔相關的劇種中尋找蹤跡。
周貽白認為“拉魂腔”的本源出自肘鼓 子,[25]同注⑤,第510 頁。“拉魂腔”系早期對今天山東柳琴戲、安徽泗州戲、江蘇淮海戲的稱謂。據口傳資料,有人因唱腔中常使用尾音高八度的拉腔,將周姑子(即肘鼓子)稱為“拉呼腔”“拉后腔”;后雅稱為“拉魂腔”,以贊美其腔有動人心魄之意。被山東戲曲界歸屬為“肘鼓子腔系”的茂腔,是由當地人稱唱腔中有“打冒”“打鳴”的諧音演化而來,因它源于肘鼓子腔,又被稱為“茂肘鼓”。另有研究表明,“浪腔”或由尾句拖音,由嗩吶或人聲幫腔而來。張善堂、王曉家提道:“‘本肘鼓’之所以又稱‘老拐調’或‘哦嗬唵,是因為當時其基本唱腔,由一人唱眾人和,每句在開頭和結尾時,往往由全體演員齊聲幫腔,尾句拖音下降,或吹嗩吶幫腔所致。”[26]張善堂、王曉家《五音戲源流考略》,《齊魯藝苑》1989 年第4 期。孔培培也關注到劇白中“你唱我幫腔,我唱你幫腔”為【姑娘腔】的表演形式。[27]孔培培《“姑娘腔”考辨》,《戲曲研究》(第72 輯)2007 年1 月。清代旅居北京的吳長元,曾留下了“吳下傳來補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的詩句,其中的“低低打打”,正是唱【柳子腔】時嗩吶作為每句句尾接音幫腔的擬聲詞,至今民間流行的《釘缸調》仍保留了這種唱奏結合的形式。
余 論
行文此至,另一個延申出的問題,仍需要做一些討論,那就是—東柳是屬于拉魂腔系、肘鼓子腔系,還是屬于弦索腔系?
在清代四大聲腔“南昆、北弋、東柳、本梆”中,南昆、北弋、西梆各自具有獨特的區別性特征,它們的聲腔構成各自已經自成體系,并且對其他眾多劇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界對三者的“腔系”也沒有分歧,但是,對“東柳”作為“腔系”地位的認識,無論從它的體系自洽性,還是對其他劇種的滲透能量,都還有討論的余地。余從在《戲曲聲腔》中對“明清俗曲(弦索)聲腔系統”有這樣的看法:
“東柳”一枝,我認為就是明清俗曲系統,也就是弦索腔系,它屬小曲而非南北曲,但形成戲曲聲腔和劇種,則對昆、弋多所吸收、借鑒。曲調眾多而又不似昆、弋體制謹嚴。因此,我認為它既是一個腔系,又是一個可以從它的眾多曲調中生發出新腔系的群體。[28]余從《戲曲聲腔》,載《戲曲聲腔劇種研究》,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年版,第128 頁。
路應昆也認為:
“曲調眾多”、來路紛雜,確實是被稱為“俗曲”(弦索)的這堆東西的實際狀況,而且其中的不少曲調也確實能“生發出新腔系”,因此在研究者面前便有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把這堆東西說成“一個腔系”似乎太籠統、太簡單化,但要說這個“群體”中還包含了不同的腔系,那么那些腔系又應該怎樣劃分呢?[29]路應昆《戲曲聲腔研究70 年回顧與反思》,《戲曲研究》(第111 輯)2019 年第3 期。
目前,山東戲曲界傾向于將柳琴戲、五音戲、茂腔和柳腔歸屬為“肘鼓子系統”,將柳子戲、大弦子戲、羅子戲和亂彈歸屬為“弦索系統”。[30]參見李趙壁、紀根垠主編《山東地方戲曲劇種史料匯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然而,這并不是一個能夠自洽的歸類,雖然柳琴戲、五音戲、茂腔和柳腔是從肘鼓子開始的,但是,“柳子腔”作為腔調在其中的占比并不多,這些劇種也多唱【耍孩兒】【山坡羊】曲牌,如五音戲里有【娃子】和【羊子】,柳琴戲里有【八句娃子】和【十二句羊子】,而這兩個曲牌屬于弦索腔系的“五大調”。弦索腔系中的劇種雖然也唱“柳子腔”,柳子戲也因唱“柳子腔”而獲得柳子戲這一劇種名稱,但是柳子戲卻以【黃鶯兒】【山坡羊】【鎖南枝】【娃娃】(又稱【耍孩兒】)【駐云飛】 “五大套曲”為主要腔調。而肘鼓子系統中的柳琴戲、淮海戲、泗州戲又同屬于拉魂腔系。此外,這些劇種中的許多腔調,還具有積極吸收其他聲腔,以及生發新腔調的活力。因此,籠統、簡單地歸屬“腔系”,不僅其行為值得商榷,也與各個劇種“多腔共和”的現實不符。筆者認為,根據當下許多劇種的實際情況,對于山東諸聲腔,可采取民族音樂學“懸置”的方法,暫時不作腔系分類,只保留昆、弋、梆三個腔系的說法。